异彩纷呈女儿《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docx
《异彩纷呈女儿《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异彩纷呈女儿《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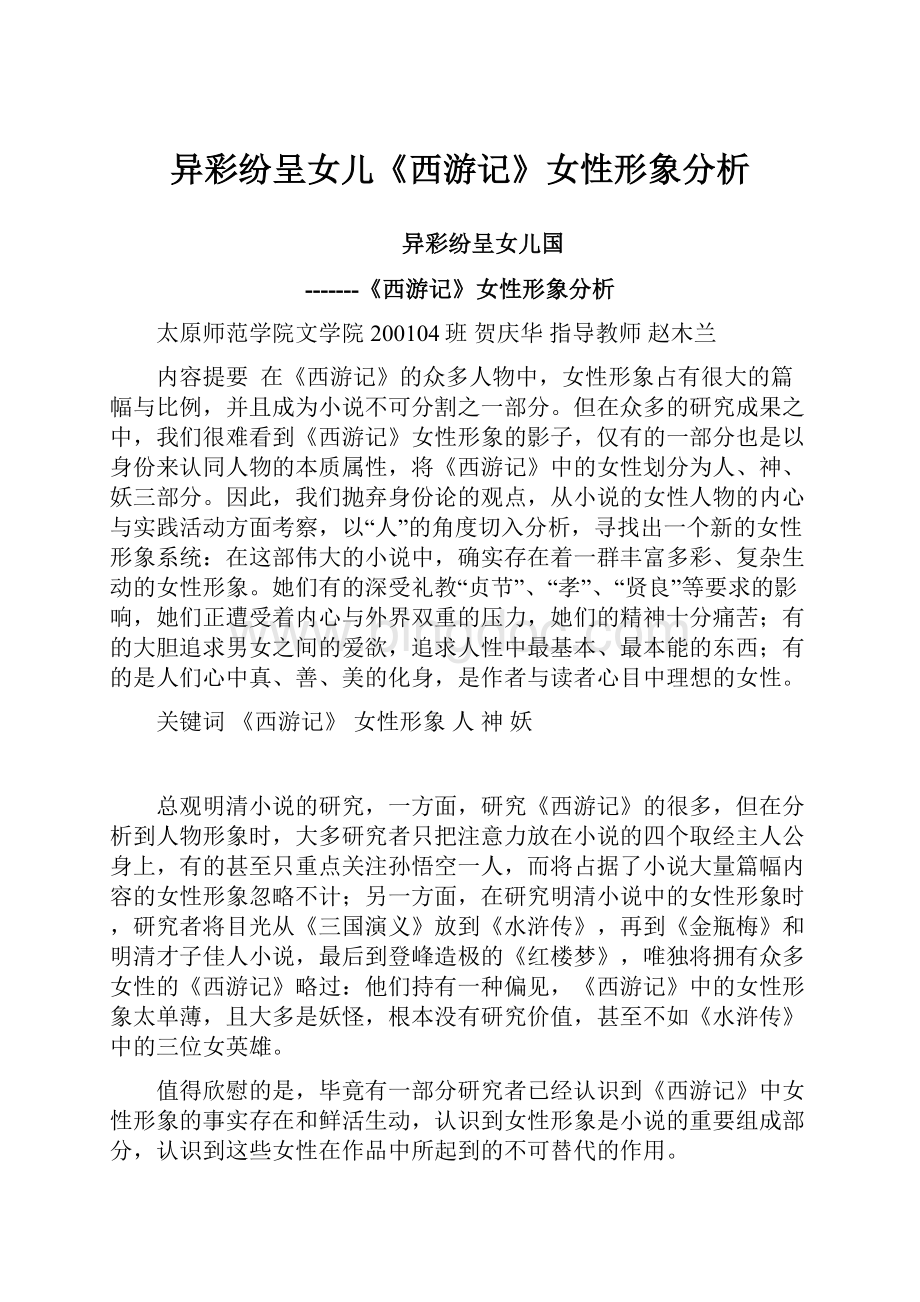
异彩纷呈女儿《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
异彩纷呈女儿国
-------《西游记》女性形象分析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4班贺庆华指导教师赵木兰
内容提要在《西游记》的众多人物中,女性形象占有很大的篇幅与比例,并且成为小说不可分割之一部分。
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中,我们很难看到《西游记》女性形象的影子,仅有的一部分也是以身份来认同人物的本质属性,将《西游记》中的女性划分为人、神、妖三部分。
因此,我们抛弃身份论的观点,从小说的女性人物的内心与实践活动方面考察,以“人”的角度切入分析,寻找出一个新的女性形象系统:
在这部伟大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一群丰富多彩、复杂生动的女性形象。
她们有的深受礼教“贞节”、“孝”、“贤良”等要求的影响,她们正遭受着内心与外界双重的压力,她们的精神十分痛苦;有的大胆追求男女之间的爱欲,追求人性中最基本、最本能的东西;有的是人们心中真、善、美的化身,是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
关键词《西游记》女性形象人神妖
总观明清小说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西游记》的很多,但在分析到人物形象时,大多研究者只把注意力放在小说的四个取经主人公身上,有的甚至只重点关注孙悟空一人,而将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内容的女性形象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在研究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研究者将目光从《三国演义》放到《水浒传》,再到《金瓶梅》和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最后到登峰造极的《红楼梦》,唯独将拥有众多女性的《西游记》略过:
他们持有一种偏见,《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太单薄,且大多是妖怪,根本没有研究价值,甚至不如《水浒传》中的三位女英雄。
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有一部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事实存在和鲜活生动,认识到女性形象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些女性在作品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就是在这些少之又少的研究成果之中,研究者只是将小说中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做了简单粗糙的分类:
他们仅仅以女性在小说中的身份作为标准,将她们分析为人、神、妖三类。
不能否认,这样的看法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却忽略了这些女性形象之间的本质异同,女妖中的铁扇公主罗刹女就不能简单地以妖来区别,观世音菩萨也不单纯是一个神的形象。
这些形象中,妖也有人性,神也有人性,人也有某种神性或妖性。
小说的作者所创作的女性形象是一个个复杂多样的形象。
事实上,神、妖这两种形象只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是以现实中的人为基础而想象出来的。
因此,在分析《西游记》中女性的形象塑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抛弃以身份认同本质的观点,将人物的身份淡化,转而从人物的活动、内心表现等方面,以一视同仁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女性。
经过这样观念角度的变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女性形象系统:
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一群以礼教要求为生活原则的女性;存在着一群追求男女之爱的女性;还有一位作者与读者心中的完美女性。
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使《西游记》成为一部完整的伟大作品。
一、内苦外困女儿国
在《西游记》的女儿国中存在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的内心已被礼教的要求所同化和控制,她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着礼教的“一双眼睛”,盯着她们,一直将她们送入痛苦与死亡的深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司马光在《训子孙》中说: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
”[2]周易的乾坤定位奠定了传统的妇女观的哲学基础。
他们将这种观点解释为:
父为“天”,夫为“天”,高高在上;母为“地”,妇为“地”,自然居下。
女性地位低下,男尊女卑乃宇宙之公理,不易之法则,天然之事实。
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礼教,为了确保男尊女卑的公理性,便产生了三从四德。
三从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3];四德者,“妇德、妇言、妇容、妇功”[4]。
三从,是女子立身之本;四德,乃女性为妇之道。
三从四德实则是戕杀女性自主人格的一把毒剑,仅一个自生至死的“从”字,便将女性的一切权利剥夺殆尽。
礼教化,就是人的身心被礼教所驯化,为礼教所制约的过程与所表现出的结果。
礼教化的人,生为礼教生,死为礼教死。
小说中突出地表现了这样的观点。
苦难的女儿
《西游记》附录“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中,满堂娇温娇,本为唐太宗的丞相殷开山的女儿。
因未婚配,搭彩楼抛绣球卜婿。
新科状元陈光蕊跨马游街经过楼下,被绣球一击而中,天赐良缘,郎才女貌,二人遂结同心。
婚后不久,温娇与丈夫赴任,行至途中,却遇强贼。
强贼刘洪因见温娇“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而顿起狼心,杀死家童,尸沉光蕊,温娇“见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将身赴水”,想从一而终,以死相殉。
但是,中国古代,节妇的三件大事:
奉养舅姑,为夫存后,育子成人,满堂娇在此时尚一件未完。
而此时温娇已怀有陈光蕊的骨肉,即后来的玄奘。
为了保住陈家的一脉香火,也为了将来明冤雪耻,为夫报仇,为了还有一个婆婆不知生死,温娇虽“痛恨刘贼,恨不食肉寝皮”,但“万不得已,权且勉强相从”,忍辱偷生,整日“思念婆婆、丈夫”。
后来胎儿出世,料刘贼不容此儿,无奈将孩子置于江中木板之上,血书身世,被金山寺长老收留并抚养长大。
一十八年之后,母子相见,为夫报仇雪恨。
一切到此本应十分圆满,但是,在温娇的内心中,“妇人贞吉,从一而终”[5]的影子一直在提醒着这位受尽凌辱的女子。
雪耻团圆并不能洗脱忍辱偷生、丧失贞操的罪恶。
因此,一个既出于意料之外又在乎情理之中的选择由温娇作出了,那就是——以死洗去一切屈辱与“罪恶”。
小说中这样写道:
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
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
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
“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
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
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
”丞相亦进衙劝解。
小姐道:
“吾闻‘妇人从一而终’。
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靦颜从贼?
只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辱偷生。
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
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
”丞相道:
“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
”(附录)
正如殷丞相所言,温娇不应该以此为耻。
但,在礼教熏陶下成长的温娇,在“妇人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教育出来的女性,纵然遇到像殷丞相这样明理达情的父亲和玄奘这样善解母亲苦衷的儿子,也不能缓解整个社会给予她的压力。
礼教观念已经牢牢地在她的心中生根,“贞操”意识已经深深地溶入她的血液,渗透进她的灵魂,成为她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不能分离的固有组成部分。
正是在社会和内心的这两种力量的逼迫之下,温娇一心寻求以死来解脱。
亲人的原宥,无法改变深深铭刻在她心灵上的礼教原则;家人的劝解,更会加重她内心上的罪恶感。
因此,她选择死。
死,对她而言,是真正彻底的解脱,无边的痛苦将会伴随她的生命的消逝而消逝,留下的,将是永远的清名与钦佩。
这,就是她死的原因和动力。
于是,在她第一次寻死未果后,杀刘洪,祭奠她的丈夫亡灵时,她“又欲将身赴水而死”,却被玄奘“拼命扯住”。
陈光蕊得龙王之助,还魂复生,一家三口终得团圆,婆婆也眼睛复明,“真正合家欢乐”。
但是,这些欢乐也难以动摇温娇的必死之念,“罪恶感”始终强烈地主导着她的心灵,“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以生命的终结赎罪,求得心灵深处的平静与安宁,洗刷那始终难忘的“忍辱偷生”。
与满堂娇相比,百花羞公主也是一个不幸的女性。
但二者不同之处就在于:
同样的遭掳,满堂娇选择了“死”,而百花羞选择了“生”,但“生”得十分痛苦,“不孝”时时刻刻在鞭挞着她的心灵。
百花羞,本为宝象国公主,被妖抢走一十三年,生有二子,并且与妖也生了几分情,但整日“思量我那父母,不得相见”。
“不孝”的意识和羞辱感如毒蛇般时时撕咬着她的内心,她的深刻的负罪感明显体现于她给她的父亲——宝象国王——的家书之中:
不孝女百花羞顿首百拜大德父王万岁龙凤殿前,暨三宫母后昭阳宫下,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宫感激劬劳万种。
不能竭力怡颜,尽心奉孝。
乃于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宫排宴,赏玩月华,共乐清霄盛会。
正欢娱之间,不觉一阵香风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将女擒住,驾祥光,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
难分难辨,被妖倚强,霸占为妻。
是以无奈捱了一十三年。
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
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
正含怨思忆父母,不期唐朝圣僧,亦被魔王擒住。
是女滴泪修书,大胆放脱,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
伏望父王垂悯,遣上将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获黄袍怪,救女回朝,深为恩念。
草草欠恭,面听不一。
逆女百花羞再顿首顿首。
(第二十九回)
读罢此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十三年的屈辱都是妖魔侍强所为,本非自愿。
“自幼在宫,曾受父母教训”,深知“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内心深处的羞辱感与负罪感使她想过死,她也想与温娇一般,以死洗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只好偷生,却时刻与羞辱为伴,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说。
两难的境地让这位本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女性时刻都记得“不孝”二字。
一封家书,“不孝”、“逆女”充斥其间,心灵的痛苦难以言表。
与温娇一样,百花羞在内心强烈自责的同时,深深地恐惧社会再对她进行谴责。
事实却正是如此。
第三十回,唐僧传书之事走漏,黄袍怪指责道:
“你这狗心贱妇,全没人伦!
……四时受用,每日情深。
你怎么只想你父母,更无一点夫妇心。
”面对这样的指责,百花羞“吓得跪倒在地”。
虽非三媒六聘之婚,却有夫妇之实。
“夫为妇纲”的礼教在此体现尽致。
百花羞一面受丈夫责骂,一面却被作者指责为“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
另一面,行者抓走她的两个儿子作为人质,百花羞母子情深,护犊意切,但行者却一通谴责:
行者笑道:
“公主啊,为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便是得罪?
”公主道:
“我晓得”。
行者道:
“你女流家,晓得甚么?
”公主道:
“我自幼在宫,曾受父母教训。
记得古书云: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行者道:
“你正是个不孝之人。
盖‘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故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
非得不孝之罪,如何?
”(第三十一回)
百花羞公主听了这些话,就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半晌家耳红面赤,惭愧无地”。
自认其罪,“诚为天地间一大罪人也!
”就连对儿子的亲情也顿时被“不孝”之罪名扫荡干净。
面对着来自丈夫、作者、悟空的指责,加上内心深深的自责,百花羞过着比温娇更痛苦的生活。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内心自责之下,礼教的“贞操”、“孝”等观念给女性所带来的深刻的负罪感,让女性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情、爱情,“罪恶”已经将这些女性剥夺成为行尸走肉,等待她们的只有死亡。
在这一点上,百花羞与满堂娇的结局其实是一样的。
贤妻良母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人物十分特殊。
第五十九回铁扇公主罗刹女,她是一个妖精,“凶比月婆容貌”,与小说中那些容比西施,貌若王嫱的美丽女妖无法相比。
但是,她“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她与人为善,被称为“铁扇仙”。
而她所住地人“只知他叫罗刹女,乃大力牛魔王之妻也”。
作者对罗刹女这样复杂的描写,正显出了她与妖、与人之异:
她是妖,却是个仙一样得道的,连身边的毛儿女也是“一身蓝缕无妆饰,满面精神有道心”;她是人,却掌握着灭火的宝贝,可以兴风作浪,占山为巢,与牛魔王为妻。
可以说,罗刹女在小说中是一个复杂的形象:
她同时具有人、神、妖的本质。
她是一个女妖,占据翠云山芭蕉洞,掌握了使火焰山地区人民生活的希望。
她没有为非作歹,只是要求这里的人“十年一拜求,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沐浴虔诚”。
可以说,这点要求对于她所赐予这个地方的,微不足道,她图什么?
只是为了修行,只是为了获得人们对她的一点尊重和膜拜!
在这里,她根本就不是妖,也不是仙,宝贝只是一个手段,她是一个寻求尊敬和尊严的普通女人。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具有传统女性几乎所有的品质:
她严守人间礼法,“家门严谨,内无一尺童”,洞内只是她与几个女童。
门也是紧闭牢关,牛魔王抛弃糟糠另觅新欢,她不敢怨言。
悟空变化牛魔王骗她,她一听丈夫回来,“忙整云鬟,急移莲步,出门迎接”,只是在叙及寒温时小心谨慎地问道:
“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是哪阵风吹你来的?
”一闻丈夫说起悟空事,便滴泪道:
“……男儿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向牛魔王诉苦;随后又笑着劝丈夫息怒,整酒接风贺喜,并小心劝求:
“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吃一杯乡中之水”,极力想挽回丈夫之心。
牛魔王与悟空赌斗,她宁舍扇子不愿丈夫再斗。
牛魔王失败时,她极力哀求保住他的性命。
这样的行为,丝毫无半点妖气,正是一个凡间“遵从夫妇之礼,严守为妇之道”的女子形象。
红孩儿是她的儿子,被悟空打败,观音菩萨收伏。
作为一个母亲,无法忍受不能相见儿子的痛苦,为此,她一听说“孙悟空”三字,“便似撮盐入火,火上浇油;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与悟空反目为仇,披挂打斗,被悟空钻入腹中,依然不肯轻借宝贝。
重视团圆的天伦之乐,不正是凡间母亲最在意的吗?
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妖,在小说中已经脱尽妖气,成为作者心目中的一位贞妇形象,难怪作者最后写她“后来也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流芳。
”
在小说中,除了铁扇公主之外,还有这么一群女性,她们着墨不多,但寥寥几笔,却诠释出礼教所提倡的温柔敦厚、贤妻良母的要求,如陈光蕊之母张氏,因思子而哭瞎眼睛;如双叉岭伯钦之母、之妻,身处荒山野岭依然重礼待客,精心操持,等等。
二、十全十美女儿国
《西游记》中的女性神,有王母、嫦娥、观音、黎山老母等几位。
其中王母只是作为蟠桃大会的召集者,作者并没有怎样着力描写她。
嫦娥,在小说中虽然多次出现,但并不曾实际写到,一次是作为猪八戒下凡的引子,另一次是玉兔下界为妖的收伏者,两次都不曾真正描写,收复玉兔时连话也未说。
剩余的就只是借她的“仙姿绰约”的美貌来形容那些美貌女子了,如“真个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第二十三回),“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第五十四回)等等。
其余如毗蓝婆,如“四圣试禅心”的闹剧,只是借以体现佛、神的法力广大和劝诫之心而已,其中的几位佳人只是徒有美貌的外表罢了。
观音菩萨是贯穿全书的一位重要女神,也是小说塑造最为成功的女性,是小说作者心目中完美的理想女性。
在佛教初传入我国的东汉时,观音菩萨本来是一位男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观音就从男相转为女相身份出现。
唐代雕塑使女相观音愈加深入人心。
宋代观音就定型为端庄秀美、慈祥可亲的女神了。
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彰显了佛教及佛教神灵进入中土后,揉合进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及审美意识。
大慈大悲观世音
如果说观音菩萨的外表形象美只是一个形式的话,那么内心中所表露出来的大慈大悲就成为人们对她顶礼膜拜的原因了。
观音菩萨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救苦救难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中的。
同样的,在小说中,作者也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
首先,我们从人们对她的称呼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中,菩萨在流沙河遇沙僧,沙僧知是菩萨,连声诺诺说“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
随后猪八戒称其为“扫三灾救八难的菩萨”。
五行山下,孙大圣连口称菩萨为“南海普陀落迦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
其前还经常加上“灵感”二字。
取经途中,菩萨不时显相,人们俱都“朝天礼拜,跪地焚香”,可见观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份量与地位,她有三十三化身就情有可原了。
菩萨的慈悲是建立在强大的法力之上的。
小说中,“盂兰盆会”上,观音菩萨勇挑重担,去东土寻取经人;她法力广大,如来也说:
“别个是也去不得,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得。
”(第八回)取经路上,凡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只要请观音菩萨,俱是逢凶化吉。
金圣叹也说:
“《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6]。
慈悲的观音总是救人于危难之时:
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向她求情,她“闻言,即与木叉撞上南天门”,向玉帝求情,救下他终成正果。
为流沙河受难的沙和尚,福陵山的猪八戒,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的孙悟空指了一条成正果的道路。
小说中观音菩萨具有洞察事实,预知未来的能力,随叫随到,有求必应,甚至第四十九回悟空还未到,她便早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去了”。
原来是削竹编篮,准备前去降妖,并让诸天在外接候大圣,出来后“不消着衣”,径至通天河降妖,留下一个“鱼篮观音”的化身。
观音的善,并非只对人不对妖。
小说中,唐僧的“慈悲”只对于人不对动物,不管人是什么样的,是平民还是强盗,抑或是妖怪变化的,一概慈悲对待,哪怕他们要杀了他;如果是妖或动物,无论是否伤害于他,无论是否逞强作恶,一概以“妖”字对待,以动物看待,行者一一打杀而毫不怜惜。
菩萨却不同,黑风山收熊罴一回,菩萨看待万物,凡有向道之心便心存善念。
第四十二回,菩萨号山收伏圣婴大王红孩儿时,唤出众多土地神鬼,吩咐道:
“……你与我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地方,不许一个生灵在地。
将那窝中小兽,窟中雏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
”这番话只让那大圣暗中赞叹:
“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
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什么禽兽蛇虫哩!
”全部小说中,没有看到过一处菩萨打杀哪个妖怪甚至花草鱼虫之类,此可见菩萨是真慈悲,真善心,读者自可细心体会。
世俗观世音
一个鲜活的形象,不可能只拥有一个品质。
一个人,一个形象具有多样性的性格与品质以及心理状态,这样的形象才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真正的人的形象。
同样的,我们的小说中塑造的观音形象也是如此。
观音的美、善是不容置疑的,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能感觉到,她更是一个真正具有人的天性的“真人”。
观音的“真”,不仅体现在她发自内心的慈悲和骨子里所透出的气质美,这里的观音具有与小说中任何修仙得道的人所不同的品质。
神仙、佛祖、菩萨等修道之人,本应是无欲无求,看透红尘,没有喜怒哀乐的,但看看小说中的观音菩萨:
小说的作者在写到观音时,经常会用到“喜”、“笑”等词,且不细述。
在第四十二回,观音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骗猪八戒时,“心中大怒道:
‘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
’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望海心里扑的一掼”。
这一下,把行者也唬得“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面”,也说“这菩萨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他的德行,就把净瓶掼了。
”李卓吾评本在这里有个眉批:
“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
”[7]一语点破作者把观音菩萨当作人写的秘密。
不仅如此,在第十五回鹰愁涧收伏龙马时,行者对她大叫,像“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
”这样的粗话竟然也出自典雅、慈悲的观音之口。
在悟空时不时指责时,她也经常地用“你这猴头”之类的话来骂悟空,甚至在悟空面前也要卖弄一番神通(号山收伏圣婴大王)。
这样一位集喜怒哀乐于一身、时常会口出脏话的观音,很难以让人相信她就是一位成道的菩萨。
看得出来,观音的形象,是作者用一种世俗化的手法精心塑造的。
与那些符号化、雕塑般的女神相比,观音菩萨更富有人间的气息,更像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真人而非一个想象中存在的女神。
可以说,是作者赋予了观音凡间人类的品质,也使观音的形象更生动和贴近世人的心态。
菩萨与悟空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或者说是一对关系:
观音与悟空的关系。
读者很容易就会看出来,二人的关系是与其他关系不同的。
小说中,观音在如来面前,是一个法力广大的徒弟,严格遵守如来法旨,在唐僧、沙僧和八戒眼中,以及众多的普通人眼中,观音菩萨是一个救苦救难、灵验、法力无边的救星,具有高不可及的威仪,是一个受人膜拜的对象:
她是一个神;但在孙悟空的眼中,菩萨究竟是怎样呢?
或者说,观音与行者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从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似乎可以看出些端倪:
第十五回,收伏龙马一节,悟空对菩萨大叫道:
“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
”菩萨道:
“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
我倒再三尽意,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嚷闹?
”行者道:
“你弄得我好哩!
……”第十七回,悟空指责观音受了人间烟火,却容妖精邻住;第三十五回,悟空收伏金银童子后,心中作念道:
“这菩萨也老大惫懒!
……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
”等,第四十二回,观音要他“留下什么东西作当”,悟空却一毛不拔,还讨价还价。
而遍观全部小说,菩萨从来没有与其他任何人有这种嬉笑怒骂的平等对话。
这样的一种平等关系似乎应该建立在悟空的反叛精神和观音对悟空的特殊感情基础之上的。
观音与悟空不仅是这种平等的关系,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近似于母子关系的长者与幼者的关系。
当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时,是观音第一个去看他;当悟空途中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时也是观音为他解困的。
观音甚至会按照悟空的安排去做,并且不失时机地在谈笑中对他进行谆谆教诲(第十七回)。
观音与悟空之间似乎有一种人间的亲情。
她特地为行者准备了三根救命的毫毛,并准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在悟空再次被唐僧驱逐后,无处可投,找到观音菩萨:
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
菩萨叫木叉与善财扶起道:
“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
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
”(第五十七回)
多么像一位母亲在安慰她受了委屈的孩子呀!
通读小说,什么时候见过行者在别人面前“放声大哭”,只有见了最信任的人!
第七十一回,菩萨降金犼,要悟空还铃一节,就像一位孩子藏了母亲的东西一样,多么熟悉的情景呀!
你感受到的不只是这样的神妖,而似乎是一种人间的至亲之情。
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的观音菩萨,将高高在上的神与人拉近了,也使她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鲜活。
一位真、善、美相结合的菩萨,在作者眼中,在世人眼里,已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女性:
她摒弃了凡间女人的一切欲望,但又有喜怒哀乐之情;她随心所欲,无牵无挂,法力无边,却从不逾矩,慈悲为怀;她是一位女神,却又是一位母亲、长者;世俗与圣洁的美都集中于这样的形象之中,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便不足为奇。
三、真性真情女儿国
清代戴震将人性概括为欲、情、知三个方面,他认为,只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必然是三性俱全,“凡是全气心知,于是乎有欲。
……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
”[8]三者对人各有作用,缺一不可。
而在欲、情、知三者之中,戴震认为“情、欲”较之“知”,与人性的关系更为密切,情欲是人性的主要内容,他说:
“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
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
”[9]而在情与欲之中,欲又是更根本的东西,它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
与吴承恩处于同一时代的李贽主张“顺其性”,以提倡“独抒性灵”著称的“公安三袁”(袁中郎)也直言不讳的宣告:
“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0]。
虽然明律严格规定:
“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
”[11]但在明中叶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李贽,三袁等一批学者文人要求从圣贤偶像中和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而重视妇孺肯定人欲的思潮。
因此,作为弄潮儿的吴承恩,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在《西游记》中创造出一系列勇于追求情爱的艺术形象。
真假女性辨
吴承恩《西游记》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之中,有一部分人物值得我们注意。
这些人物拥有女性的外表特征,但事实上,那只是一个符号,小说中所写出来的仅是一个具有妖性的人物而已。
第二十七回,白骨夫人能够变化作“月貌花容的女儿”,“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并肆意编造身世来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既能变化作妇女,也能变化作男儿,在那幅“夫人”的女性皮囊之中,包裹的是真正的妖性,这种妖性从来没有具备过女性本质特征,与其他男性妖怪并无本质区别。
第七十二回,七个蜘蛛精的“吃肉长生”的残忍行为也并非美丽的皮囊所能掩盖的。
第四十八回,斑衣鳜婆出谋划策,只是作为一个“智者”出现。
像此类形象,她们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是中性的,但却具有女性表象,或许正是世俗“红颜祸水”的偏见将丑恶嫁接于女性身上的结果。
理想的西梁女儿国
《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创造了一个非凡的,理想的女儿国:
小说中,师徒四众行至西梁女国,得遇奇景:
本应深藏绣闺的妇女,竟抛头露面,妇人摆渡;所见妇人,皆“笑嘻嘻”、“欣欣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