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需要人情味.docx
《医学需要人情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医学需要人情味.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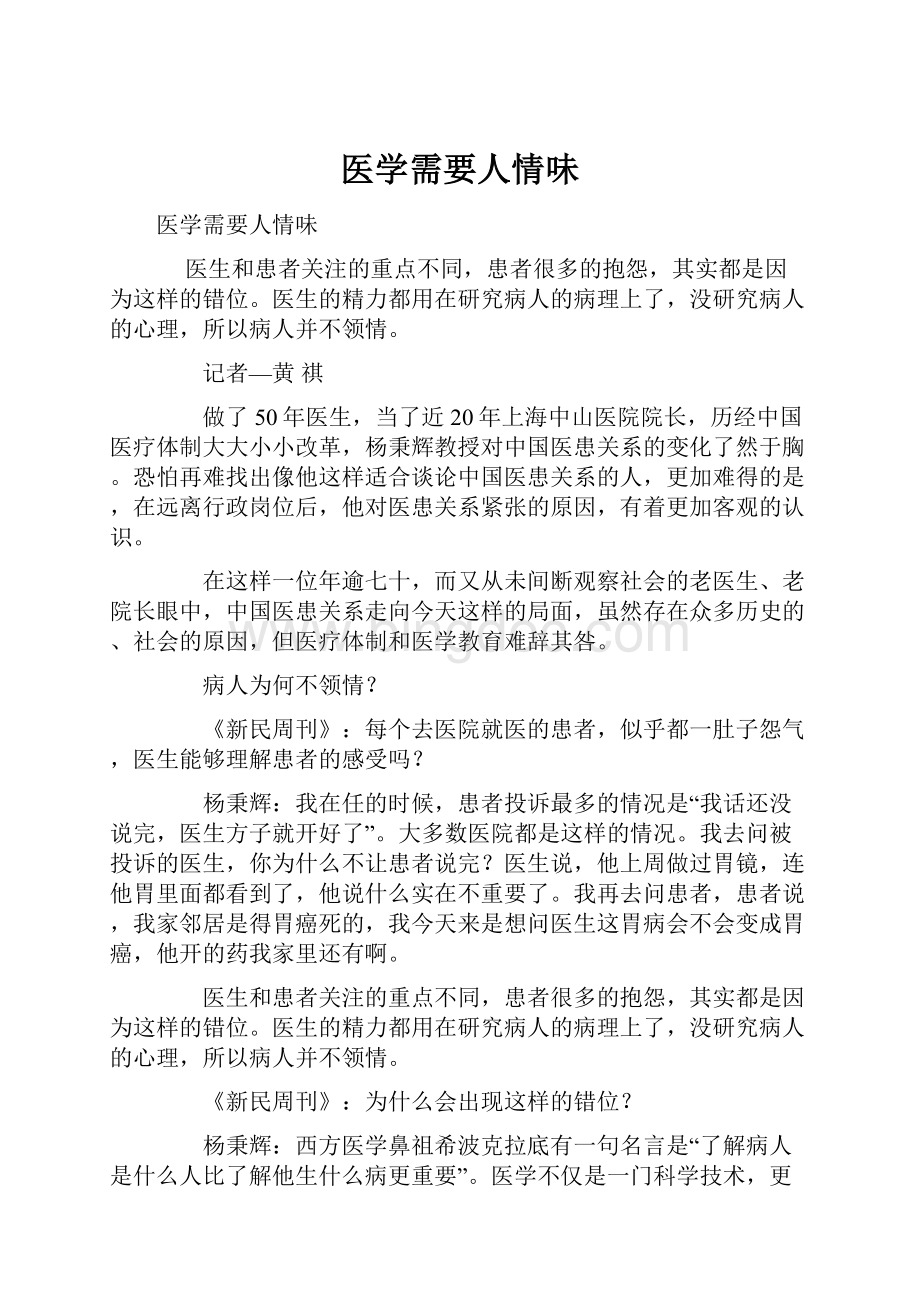
医学需要人情味
医学需要人情味
医生和患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患者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错位。
医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病人的病理上了,没研究病人的心理,所以病人并不领情。
记者—黄祺
做了50年医生,当了近20年上海中山医院院长,历经中国医疗体制大大小小改革,杨秉辉教授对中国医患关系的变化了然于胸。
恐怕再难找出像他这样适合谈论中国医患关系的人,更加难得的是,在远离行政岗位后,他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着更加客观的认识。
在这样一位年逾七十,而又从未间断观察社会的老医生、老院长眼中,中国医患关系走向今天这样的局面,虽然存在众多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医疗体制和医学教育难辞其咎。
病人为何不领情?
《新民周刊》:
每个去医院就医的患者,似乎都一肚子怨气,医生能够理解患者的感受吗?
杨秉辉:
我在任的时候,患者投诉最多的情况是“我话还没说完,医生方子就开好了”。
大多数医院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去问被投诉的医生,你为什么不让患者说完?
医生说,他上周做过胃镜,连他胃里面都看到了,他说什么实在不重要了。
我再去问患者,患者说,我家邻居是得胃癌死的,我今天来是想问医生这胃病会不会变成胃癌,他开的药我家里还有啊。
医生和患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患者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因为这样的错位。
医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病人的病理上了,没研究病人的心理,所以病人并不领情。
《新民周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
杨秉辉:
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是“了解病人是什么人比了解他生什么病更重要”。
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技术,更是一个为人服务的行当。
现在的医学教育,只教学生细菌、病毒、细胞、药理,很少教学生社会是什么样的、病人心态是怎么样的。
医生不应该是纯粹的科学家,应该提倡医学人文精神,这一点是目前中国医学教育欠缺的地方。
有一个笑话说,国外一个医学团体访问中国后,笑谈中国的医学教育与兽医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兽医也教牛生了什么病,是什么细菌引起,用什么药。
我们注重医学技术的方面,忽视了医学是为人服务的。
行政部门对医生的评价也是纯科学性的,只看医生论文有多少,论文的级别有多高。
我认为,医生是应该做一些研究,但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不能跟对生命科学院的专家一样,他们的精力都在科研上,而医生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看病上的,我认为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服务好病人。
《新民周刊》:
为什么说了解病人比了解疾病更重要?
杨秉辉: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多年前一位江西农村患者,风湿性心脏病拖了太久,变成严重的心力衰竭。
从病情上看,他需要做一个心脏瓣膜置换手术,但由于他病情严重,手术的风险很大。
这个患者到过很多医院看病,医院都不敢给他手术。
后来到上海的某三甲医院,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接收了他。
这名医生认为,患者病情非常严重,不手术就只能“等死”,尽管风险大,还是要“搏一搏”。
患者对医生愿意手术感激不尽,跪下来磕头,说是终于找到救星了。
他回老家凑够几万元手术费用,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
手术后第三天,患者因心力衰竭而死亡。
家属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到医院大闹。
他们认为既然你医生同意手术,就是一定能治好的,现在人死了,一定是医生的责任。
这位医生的技术是好的,他也是好意想要治好病人,但他没有考虑病人的背景,像这种高风险的手术,患者和家属是无法承担的。
这个手术,可能不应该做。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真实故事。
有一年我带队到江西农村巡回医疗,遇到一名患心脏病的农村妇女。
她的疾病是主动脉狭窄,她说经常感到胸口痛。
我问她,这里的医生
是怎么给你治疗的。
这名妇女告诉我,医生说,胸口痛的时候,就回家喝一碗糖水,喝了糖水就会好很多。
其实,糖水并不能治疗她的心脏病,但这名医生很聪明,胸痛一般总是在劳作时冠状动脉血供不足,患者回家喝糖水就是得到了休息,休息才是症状得到缓解的原因。
像喝糖水这样的“缓兵之计”,对于这名妇女来说可能就是最好的治疗。
医学能做的,是对病人的照顾,包括心理的、社会因素的照顾。
《新民周刊》:
越是大医院,矛盾似乎越多,这是什么原因?
杨秉辉:
你到大医院看病,医生就有责任。
你跟医生讲病情的时候,一定说得严重些,非常不舒服、难过死了。
医生能不重视吗?
重视了,就要检查,现在的科学发展到超声波能发现肝脏上0.5厘米的肿瘤,医生手摸怎么能摸出来。
如果误诊,罪不可恕,尤其大医院。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头痛,他去看神经科的专家,这个专家不敢不给他做CT,若检查不能确定病情,CT做完再做核磁共振,然后医生说“未发现明显病变”。
过两天病人自己头也不痛了,对于患者来说,检查不是白做了吗?
所以患者觉得多花了钱,医生多做了检查。
但问题是你看了专家,他擅长脑肿瘤的治疗,当然要给你查清楚。
《新民周刊》:
还有一种说法是,医生让病人做那么多检查,是为了保护自己,推卸责任。
杨秉辉:
病人、社会都不会轻易饶恕医生的失误,所以现在医生责任很大,必须步步为营。
医疗纠纷要举证倒置,医生要证明自己没有错。
经常有报道说,看感冒做了多少检查,花了多少钱。
我要问,既然你知道是感冒,为什么一定要到大医院去看,自己买点感冒药吃不就得了吗。
医学越发达患者越不满
《新民周刊》:
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很多疾病在早期就能被发现,应该是好事,为什么患者反而不满意?
杨秉辉:
对,医疗技术是先进了,但病人的自我意识也提高了,不只在中国,在其他国家,病人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但人家都是通过法律途径,医生常常要应对官司。
人对自我价值的理解,是社会进步的一面。
《新民周刊》:
很多患者的抱怨是,医生故意让我做不必要的检查,让我花更多钱,过去没有这么多仪器,不是也能看好病吗?
对此你怎么看?
杨秉辉:
过去医生看病很简单,没有这么多仪器。
我是内科医生,来一个发烧病人,医生先考虑呼吸道的感染,问问咳嗽吗?
病人说不咳。
那我就拿听诊器听,呼吸音很清晰,不像肺炎。
我再问拉肚子吗?
病人说不拉,那就基本排除肠炎。
我问头痛吗?
说不痛,检查一下头颈没有强直症状,基本排除脑膜炎。
躺下来压压胆囊的位置,如果没有压痛,基本不是胆囊炎。
如果阑尾没有压痛,不是阑尾炎。
排除了这些常见病,医生开点退热药总是没错。
如果病人第二天烧退了,病人觉得挺好,如果第二天没退烧,他又来了,我们就要查个血,白血球高,表明有炎症,打青霉素。
如不高,考虑还是感冒,继续吃药,多喝点水。
当时就是这样处理的,病人都没有意见的。
但是现在,再这样看病就不可以了。
比如还是刚才这个病人,第二天没退烧,他肯定去别的三甲医院拍片,如果查出来是支气管炎、肺炎,患者马上倒过来告你,说你不给他检查,说你误诊。
《新民周刊》:
我们总是怀念过去,很多人说二三十年前,没有医患纠纷,是这样吗?
杨秉辉:
我是1962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一直做医生,干了50年。
“文革”之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少。
那个时候医院看病的人也很多,病人要排很长的队,医生给每个人看也不过两三分钟时间,和今天的情况没什么差别,但当时病人一般没有意见。
我们医院当时与周边工厂挂钩,所以很多患者是工人,工厂里劳动很辛苦,能请半天病假出来看病,对一些人来说算是一种休息。
所以,男病人带着小说来排队,女病人带着毛线编织来排队是常见的景象。
当时工厂工人都有劳保,看病不用付钱,到月底医院会与工厂结算,患者经济上也没有压力。
所以,等他们看好病回到工厂,顶多是嘴上抱怨几句排队太长,但心里的怨气没那么大。
《新民周刊》:
看病贵是患者容易对医院不满的主要原因吗?
杨秉辉:
医改以后,患者自付部分增加,的确与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关系。
以前看病不用出钱,医院跟单位结算,患者心理压力会小。
患者到医院闹事的情况,从1980年代开始有,但不多,1990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妙了。
六七十年代,也有医疗失误发生,如果出了事,医院会跟患者单位沟通,单位会有补助啊,照顾啊。
1980年代后,人变成社会的人了,单位不管了。
医改以后病人要付更多的钱,患者经济压力变得很大。
像这样的情况,需要社会救助,但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还医疗本来的面目
《新民周刊》:
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患者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没有病,按道理患者应该高兴,但中国患者回家后还是一肚子抱怨。
这是为什么?
杨秉辉:
“你说我没病,我们隔壁邻居去年也没检查出有病,今年就得癌症了,你这个医生没给我查出病来,一定是不尽责。
”很多病人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们的公众对医疗的期望值太高,其实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把医学看成是万能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医学是一个“失败”的技术,人最终都是要死的,人死的这一次,对于这一次医疗来说必定是失败的。
这就是医学,但很多民众不理解。
中山医院一位医生去世了,医院贴了讣告,一些围观的人议论说:
“医生也死啦?
”这当然是玩笑,但也表明了大家是怎么理解医学的。
《新民周刊》:
为什么大家对医疗的期待会如此高?
杨秉辉:
医疗技术这些年进步的确很快,很多以前会导致死亡的病,现在存活的几率大得多。
比如急性心肌梗死,在我刚做医生的六七十年代,死亡率90%,也就是说收进来100个病人,最后能活着出院的只有10个。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治疗,当时的办法就是让病人卧床6周不起,吃饭、大小便、洗脸洗脚都在床上,护士很辛苦。
卧床为的是不增加心脏的负担,医疗上没有什么办法。
心绞痛很痛,就打一点麻醉剂止痛,甚至杜冷丁。
如果出现心力衰竭,就用一点强心药,说实话,活下来的算是命大的。
现在,如果患者能及时送进医院治疗,放置支架,大量病人存活下来,死亡率到下降到30%以下。
这个支架很贵,有人说装几根支架相当于身体里开进去一部汽车的钱。
但是,人活下来啦,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当然,放了支架不等同于就治愈了冠心病,可能过两年又出现问题。
技术的进步的确让很多疾病有了治疗的办法,但人的生命很奇怪,有时候很坚强,矿工被困在矿井下,如有水喝,可能维持40天,但生病的时候,可能“转眼就死”。
比如,25%的急性心肌梗死是来不及送医院的,大面积心梗几分钟就会致命,不管他在哪个国家,科学如何发达,交通如何方便,直升机也来不及。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医疗是有很大风险的。
终究科学不能让人不死,民众不能认为,患者在医院死亡,一定是医院责任。
《新民周刊》:
我想,民众对医疗的期待这么高,也是医务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杨秉辉:
对,医务界是喜欢这样宣扬。
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我说“医学还躺在过去战胜传染病的功劳簿上”。
医疗是有风险的,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不但民众要知道,医生更要知道。
我常跟年轻医生说,你不要以为你本事很大,高血压你不过是用药把血压降低一点,并没有治好。
糖尿病患者一针胰岛素20分钟内血糖就会降下来,这个不是你的本事,糖尿病不可能治愈。
一些人认为医学好像无所不能,其实我们面对的大量疾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还是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前列腺肥大、肺气肿,这些都是没办法治好的。
老年病是年龄决定的,没有返老还童药,注定这些病是看不好的,人只会越来越老,病只会越来越多。
疾病能治愈的很少,但整个医学界认识不多。
到今天卫生系统还在统计住院病人的治愈率是多少,我说,医院越大,治愈率肯定越低,三甲医院住院的都是疑难杂症,都是治不好的。
大量的病需要终身照顾,所以医院才会门庭若市,就像滚雪球一样,寿命越来越长,人越来越老,病人会越来越多。
医学能做的是避开严重的疾病,推迟生命的结束,让人更健康地多活一些时间。
中国医患矛盾为何更突出
《新民周刊》:
为什么中国的医患矛盾,显得特别突出?
杨秉辉:
现在中国的患者以相对低的收入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科技,这中间有很大的落差。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高血压的常用药络活喜,前几年一粒8元,相当于1美元。
如果一个患者自费吃药,一天1粒,一月要花240元。
如果这个患者只有1000元的退休金,吃这个药负担就很重,生活必定拮据。
如果他的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患者当然怨气就来了。
但是,中国退休工人吃的药与美国总统吃的药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某美国人每月收入3000美元,他只要花30元吃这个药,当然不觉得贵。
按照这样的比例,如果中国患者只花10块钱吃药,抱怨可能就没那么严重。
有没有便宜的药?
有。
过去我们用利血平,但这个药现在不生产了,太便宜,工厂不愿意生产。
这是医院的责任吗?
当然,这个药,有时会引起便秘,其实发生的机会并不多。
《新民周刊》:
一方面政府认为已经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医疗保障,一方面民众仍然觉得看病太难、太贵,这样的矛盾能够解决吗?
杨秉辉:
看病难是存在的,比如中山医院,六七十年代每天门诊量800人,我们有病床800张,当时需要住院的病人,医生开个单子基本都能住。
现在我们每天门诊8000人,病床1800张,门诊量增加了10倍,但病床数增加远远没有这么多,想要住院自然难。
但我们的城市居民看病真的有那么难吗?
杨振宁回国的原因之一,是他当时的夫人患有心脏病,在美国预约专家要等几个月,实在太不方便了。
中国要想看专家,大医院的专家都挂着牌子在那儿恭候挑选。
偏远、贫困地区的患者的确是看病难,他到县城看不了,到省城看不了,只能到上海,租一个小旅馆等着看病。
这种情况,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有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关系。
因此,解决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出路,是政府加大对医疗的投入,让患者经济压力减小。
国家应该定出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超出这个范围的,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付费就医。
就像吃饭,政府保证让你吃饱,天天到锦江饭店去吃当然不行。
目前没有很好地界定什么是“基本医疗”。
政府应该保证公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医疗以外的,例如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药物,可以由基金会的形式解决,比如一个大富商,他得了一种病,去世后他将自己的财产建立某某基金,帮助这些病人。
分诊为何难推行?
《新民周刊》:
我们常常提到分诊制的好处,很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小病找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大病才到大医院。
但我们的患者,很难相信基层医生的医疗水平。
杨秉辉:
中山医院做过研究,现在每天门诊量8000-10000,其中80%不需要到大医院看,应该到基层医院。
患者不相信基层医生,是因为基层医生水平的确是差一点,但近十几年有所改善。
十多年前,即使上海这样的城市,70%的社区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医学教育。
因为这样的人员结构,卫生部门规定社区里只能开一点“太平药”,一直到今天,有些药在地段医院开不到,也有这个关系。
大学本科毕业的医生不愿意到基层去,因为那里被人看不起,也没有学术上的深造的机会。
怎样让患者相信社区医生,我认为首先要培养社区医生人才。
我是中国全科医学最积极的鼓吹者。
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医学分会,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比发达国家晚了20年。
1993年到现在20年过去,全科医学有些进步,但进步不大。
上海有一些推进,上海的做法是,到全国各地招收本科医学生来培训,经过3年培训,如果考试获得全科医学执照,这个医生就可以落户上海,国家在你3年培训期间也有补贴。
这个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医学生留在上海做了全科医生。
这样的制度是与西方国家接轨的,英美国家也是让大学本科生接受3-4年的培训,然后去做全科医生。
最近,上海的全科医生培训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全国推进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外地毕业生可以到上海来参加各个科室的培训,毕业后做心脏科医生也可以,做内科医生也可以。
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没那么大,所以很多人会放弃选择全科医生培训。
《新民周刊》:
正如你所说,目前到基层当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是不大。
杨秉辉:
是的,我想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全科医生待遇。
在英美,一个全科医生或者叫家庭医生,挣钱不比大医院专家少。
专家名气大,职业声誉不同,但全科医生很“实惠”,这个行业竞争不大,不需要做很多论文,他只要一门心思把病人服务好就行了。
中国没有这样的气候。
国家政策是支持全科医学发展的,去年国务院的文件提出,要发展全科医生制度。
我们的全科医学分会,卫生部部长陈竺是名誉主任,他部长来做一个分会做名誉主任,表达的是对这个学科的支持。
培养更多全科医生,建立分诊制度,是解决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途径,当全科医的生名誉、地位都得到提高,就会有人愿意做。
当医生素质提高,一些药物就会向基层医院开放,患者就会去社区医院看病。
当病人得到分流,看病就不难、不贵,医患关系也会好转。
已有217人参与我要评论
分享到:
上一页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