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1.docx
《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1.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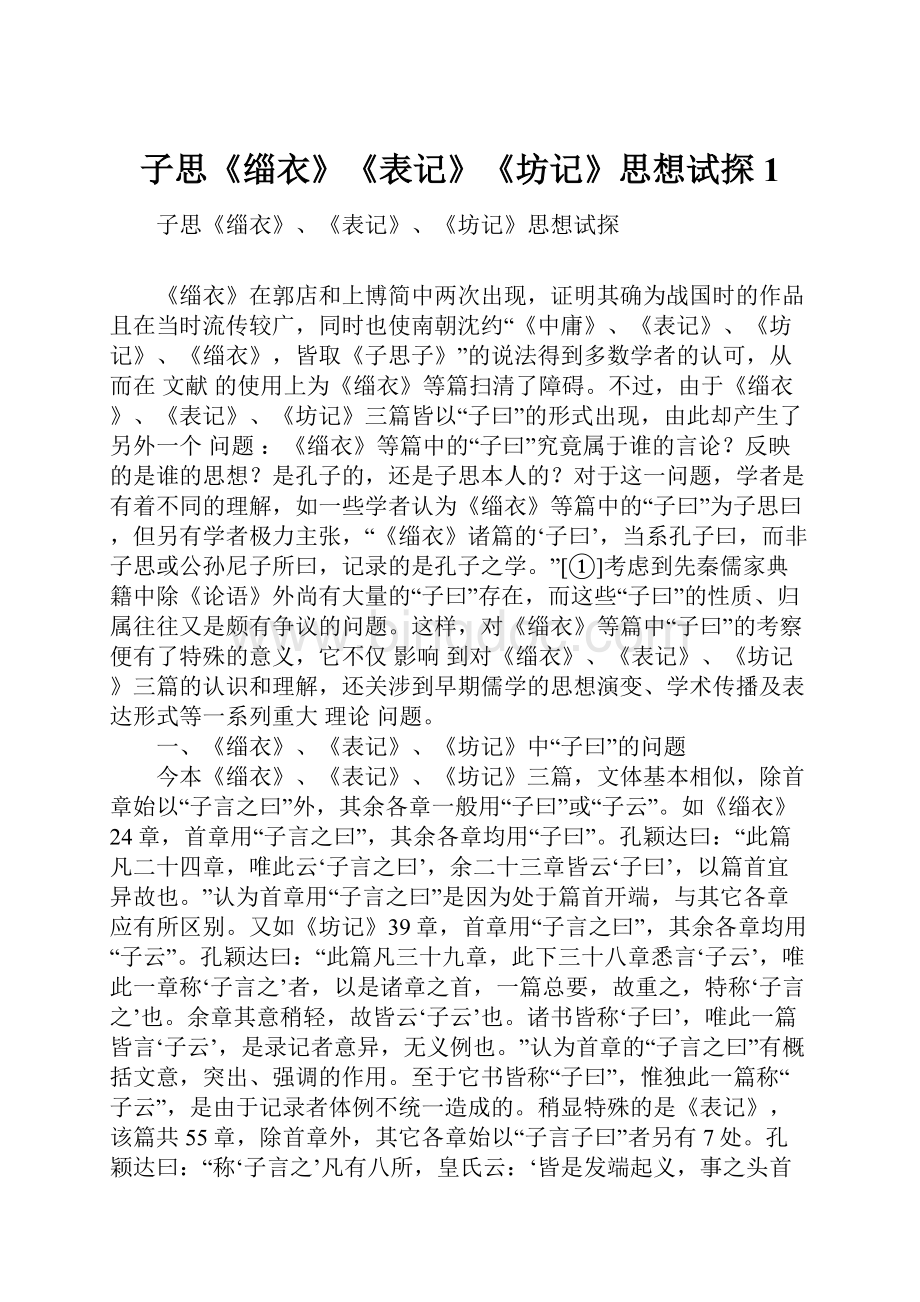
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1
子思《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
《缁衣》在郭店和上博简中两次出现,证明其确为战国时的作品且在当时流传较广,同时也使南朝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而在文献的使用上为《缁衣》等篇扫清了障碍。
不过,由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皆以“子曰”的形式出现,由此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缁衣》等篇中的“子曰”究竟属于谁的言论?
反映的是谁的思想?
是孔子的,还是子思本人的?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如一些学者认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曰,但另有学者极力主张,“《缁衣》诸篇的‘子曰’,当系孔子曰,而非子思或公孙尼子所曰,记录的是孔子之学。
”[①]考虑到先秦儒家典籍中除《论语》外尚有大量的“子曰”存在,而这些“子曰”的性质、归属往往又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这样,对《缁衣》等篇中“子曰”的考察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对《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的认识和理解,还关涉到早期儒学的思想演变、学术传播及表达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一、《缁衣》、《表记》、《坊记》中“子曰”的问题
今本《缁衣》、《表记》、《坊记》三篇,文体基本相似,除首章始以“子言之曰”外,其余各章一般用“子曰”或“子云”。
如《缁衣》24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余各章均用“子曰”。
孔颖达曰:
“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余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异故也。
”认为首章用“子言之曰”是因为处于篇首开端,与其它各章应有所区别。
又如《坊记》39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余各章均用“子云”。
孔颖达曰:
“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一章称‘子言之’者,以是诸章之首,一篇总要,故重之,特称‘子言之’也。
余章其意稍轻,故皆云‘子云’也。
诸书皆称‘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云’,是录记者意异,无义例也。
”认为首章的“子言之曰”有概括文意,突出、强调的作用。
至于它书皆称“子曰”,惟独此一篇称“子云”,是由于记录者体例不统一造成的。
稍显特殊的是《表记》,该篇共55章,除首章外,其它各章始以“子言子曰”者另有7处。
孔颖达曰:
“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
‘皆是发端起义,事之头首,记者详之,称“子言之”,若于“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
’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
”所以,今本《表记》中“子言子”凡8见,多为发端起义,提要各层大义之文。
当然,《表记》的分层未必完全合理,有学者对此曾提出疑义,这或许由于错简所致,或由于“传写之误”。
[②]
对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曰”,学者一般认为是“孔子曰”,但也并非没有疑义。
唐人欧阳修曾提出,“‘子曰’者,讲师之言也。
”认为“子曰”不独孔子之语,其他诸子、学者的言论亦可称“子曰”。
欧阳修此说,主要是针对《易传》,尚不涉及《缁衣》等篇中“子曰”的问题,以后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之言,而非孔子之言。
如胡玉缙曾“疑所称‘子云’、‘子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
故《坊记》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两句,以《论语》为别”[③]。
清代学者邵晋涵、黄以周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中的“子言之”为子思之语,而“子云”、“子曰”为孔子语也。
如黄以周《子思•内篇》卷三《表记》说:
“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表明其恉趣之所在。
……‘子言之’与‘子曰’必两人之言。
而‘子曰’为夫子语,则‘子言之’为子思子语,更何疑乎?
”当代学者中也有持这种看法者。
[④]按,《缁衣》等篇中的“子曰”应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
郭店本《缁衣》出土后,其首章始以“夫子曰”,以下各章始以“子曰”,这种称谓体例与今本基本相同,之不过将“子言之”改为了“夫子”。
郭店本的章节与今本并不完全相同,其首章实为今本第二章:
“夫子曰:
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则民咸力而型不顿。
《诗》云: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现在学者一般认为,郭店本首章由于有“缁衣”二字,符合古代篇名的命名方式,所以更为合理,至于今本首章,则可能是错简所致。
不过郭店本与今本在章节分合上虽有不同,但二者的称谓体例却基本相同,说明其首章的“夫子曰”或“子言之”确实是有意为之,它不仅是因为“篇首宜异”,同时可能还有标明身份的作用。
试以《缁衣》等篇与《中庸》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中庸》第二章至第二十章上半部分主要以“子曰”的形式出现,与《缁衣》等篇体例十分相似;而《中庸》第一章及第二十章下半部分以下主要为议论体,与《缁衣》等篇存在较大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今本《中庸》包括了子思两篇独立的作品,其中前一部分即为原始的《中庸》,后一部分则为子思的另一篇着作《诚明》,它们被编在一起乃是后来的事情。
[⑤]而原始《中庸》的首章为:
“仲尼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这里的“仲尼曰”和前面的“子言之曰”、“夫子曰”的性质无疑是一致的,它最清楚不过地说明,《缁衣》等篇中的“子曰”应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围绕《缁衣》等篇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个称谓的问题,即使我们能够证明《缁衣》等篇中的“子曰”是“孔子曰”,而不是“子思曰”,也不能由此判定其思想的实际归属。
因为,这里实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子思名义上虽然记录的是“孔子曰”,但实际表达的却是——或至少夹杂了——自己的思想。
其实,这样的质疑在子思的时代已经存在。
据《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
‘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
’子思曰:
‘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⑥],然犹不失其意焉。
其君之所疑者何?
’”鲁穆公并不否认子思记录的是“夫子之言”,但却怀疑它实际表达的是子思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怀疑并不是个别的,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在总结当时学术思想时,其批评子思、孟子的一条罪名是,“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
”可见在荀子看来,子思、孟子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提出了“五行说”,同时还在于其创立学说时,往往将自己的言论假托于孔子,[⑦]认为“此真先君子之言也”,结果混淆视听,使没有见识的俗儒信以为真,“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在思想上造成很大混乱。
战国后期的另一位着名学者韩非,甚至将这种假托先师之言的做法扩大到儒墨显学,看作是当时思想界的普遍现象。
《韩非子·显学》说: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这里“皆自谓真孔、墨”,显然包含有假托先师之言,借先师之言以自重的意思。
所以至少在韩非看来,假托先师之言已成为“八儒”、“三墨”宣传自己思想学说的特殊形式,它显然已不是一种“实录”,而是属于思想创造的范畴。
如果说,战国时期人们对“子曰”的怀疑多少与学派纷争有关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学者对“子曰”的理解则更多地与研究 方法联系在一起。
自上个世纪初“疑古”思潮兴起以来,以为只有《论语》所称引的“子曰”或“孔子曰”是可靠的,其他古书中的“子曰”或“孔子曰”都是后人的伪托,已成为长期支配学术界的一项成见。
这一成见在表面上维持了学术研究所必须的严谨的同时,却使古书中大量的“子曰”统统陷入身份可疑,不被重用的境地。
而且这一成见似乎以为,早期儒家学者在引述“子曰”时,是毫无根据,随心所欲,且有意造伪的,其不合理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有学者试图打破成见,另立新说,为先秦古籍中大量的“子曰”翻案。
如郭沂先生近些年提出,先秦两汉儒家典籍中大多数的“子曰”都是可靠的,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的记录。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了“《论语》类文献”的概念。
郭沂先生认为今本《论语》并非孔子“门人相与辑而论撰”,因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即已分化,时称“儒分为八”,并且相互攻讦,怎么会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呢?
所以今本《论语》只能是由孔门少数弟子结集、编撰,只是当时孔子言行的很少的一部分。
《论语》之外那些门人所记孔子言行,其性质与《论语》相同,故可称之为《论语》类文献。
至于《论语》类文献的内容,郭沂认为,今本和帛书本《易传》、《孝经》、大小戴《礼记》、上博简、定县竹简、《荀子》、《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涉及孔子言行的内容都应包括于其中。
[⑧]
郭沂先生创立新说的主观意图暂且不论,但他立论的根据却存在明显的疑问。
首先是《论语》的成书问题。
郭沂先生认为,《论语》只是出于孔门少数弟子之手而不是集体编纂,是不符合事实的。
《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衡·正说篇》说: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
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
”赵岐《孟子题辞》说:
“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
”从上述记载来看,《论语》的成书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起初只有弟子各自对孔子言行的回忆、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等等,这些回忆、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分散在个人之手。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整理、记录了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相与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
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个别人之手。
《论语》中常有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姓名者三十人,这些内容往往就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
从《论语》涉及众多弟子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集体的编纂,如果没有弟子的广泛参与,《论语》的成书是难以想象的。
至于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发生分化,也主要是基于思想的分歧,而不是出于派性,并非水火不容、无法调和。
《论语》中常有子游、曾子、子张互相攻讦的言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以朋友相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对导师的言行“相与辑而论纂”呢?
其实,可能正是孔门后学的分化和分歧,才使“共纪孔子之言行”变得紧迫和必要。
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丰富,包含着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加之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自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
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
“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
”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纂”,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着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
这样的着作显然只能是由集体编纂,而不可能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
由于《论语》的结集是由孔门弟子集体发起,集体参与,这种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为儒家各派所尊奉。
如孟子、荀子分别属于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但他们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
如果《论语》不是集体结集编纂,而是出于个别人之手,它又如何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
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郭沂先生为了说明《论语》类文献的存在,曾引《论衡·正说篇》“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的说法。
他认为,从汉代出现的各种《论语》看,每种只有二十篇左右,其合并本也不过三十篇,因而王充所说的《论语》应兼含《论语》类文献,所谓“数十百篇”当指若干种《论语》类文献的总篇数。
其实,王充所谓“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是指编纂《论语》时收集到的材料,而不是指《论语》编定后的篇数。
《论语》编纂时收集到的材料甚多,有“数十百篇”,而《论语》编定后的篇数则相对较少,仅二十篇左右,这一现象说明,可能在《论语》结集时,某些“子曰”的可靠性已受到了质疑,今本《论语》二十篇不过是其中被孔门弟子普遍接受、认可的部分,另有大量的“子曰”在《论语》结集时并没有被采用,而之所以不被采用,除了部分内容雷同、重复以及不能真正地反映孔子的思想外,[⑨]可能还因为存在着记录失实甚至是假托的情况。
郭沂认为今本《论语》只是当时少数弟子的一个传本,在其之外还存在其他传本。
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何当时流传的三个传本——《古论》、《鲁论》、《齐论》——与今本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他所说的其他传本则全无踪迹?
我想这决不是可以用“没有流传下来”来搪塞的。
郭沂先生提出,“先秦两汉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言行,其中只有少部分见于今本《论语》,那些占绝大部分的,不见于《论语》的资料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论语》结集时没有被收入的部分,还有就是晚出“子曰”,而不是郭沂先生所说的《论语》类文献。
郭沂先生的想法是,孔门弟子曾编纂了数量庞大且有多种传本的《论语》,今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那些不同于今本的其他传本,则成了先秦两汉书中大量“子曰”的来源。
但实际情况是,孔门弟子虽记录、收集了大量的孔子言行,但只有部分被编纂进《论语》中,此外还有大量内容因各种原因而没有被采用。
《论语》虽有《古论》、《鲁论》、《齐论》等传本,但内容基本相同,实际只有一种,约二十篇,为今本的前身。
而且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并不限于某一时期,《论语》结集完成后仍不断有“子曰”出现,如《缁衣》、《表记》、《坊记》所记录的内容。
这些不见于《论语》的“子曰”,虽不能说全无根据,但与《论语》的内容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一是没有经过孔门多数弟子的认可;二是在孔门后学中不具有《论语》那样的权威地位。
这样看来,郭沂先生关于《论语》类文献的说法多少是有问题的,[⑩]至于他论证先秦两汉古书中大量的“子曰”都是孔子的言论,则更不可取。
因此在我看来,郭沂先生虽然注意到了以往研究中“子曰”问题的结症所在,但却并没有找到根治病情的灵丹妙药。
他的《论语》类文献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造成了思想的混乱。
因此,如何看待古书中的“子曰”仍是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宏观的理论预设固然重要,但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这样,《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便显示出其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这三篇的内容均以“子曰”的形式出现,同时,由于子思的特殊身份以及曾引起的争议,也使这些“子曰”倍受关注。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缁衣》等篇的思想,考察它与孔子、子思思想的复杂联系,并进一步对先秦古籍中的“子曰”以及早期儒学的思想发展、表达形式等问题做出说明和探讨。
二、《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
孔子创立儒学,主要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仁和礼。
前者亲亲、爱人,内在自觉;后者等差、名分,道德规范。
孔子通过仁、礼范畴实际提出了道德实践中内在自觉与外在规范的问题,并由此展开对儒学思想的论述和讨论。
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构成其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如何理解仁与礼的关系,也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缁衣》等篇的内容看,它实际仍主要延续了孔子仁与礼关系的问题,其中《表记》主要讨论仁,《坊记》主要论述礼,而《缁衣》则泛论为君之道、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较之孔子的思想有所发展,提出与孔子不同的见解,下面将分别论述之。
仁、义思想
孔子谈论仁,也谈论义,却很少将仁、义联系在一起。
孔子之后,讨论仁、义,将仁、义并举却成为一种趋势。
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云:
“士执仁与义而明行之。
”《曾子制言下》:
“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
”郭店竹简更是提出“仁内义外”的说法,如《语丛一》云:
“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
由中出者,仁、忠、信。
由外入者,礼义刑。
仁生于人,义生于道。
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可以看出,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与孔子仁与礼的问题存在密切联系,是由后者进一步发展而来。
在孔子那里,义是与礼密切相关的概念,[⑪]都有外在规范和原则的意思,同时,它的含义又相对具体,且与内在主体发生联系。
如,“子曰: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义可以转化为内在的品质,而礼、谦逊和诚信则成为实践和完成义的。
又如,“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这里“义之与比”一句中的“与比”,有学者认为应当即是“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与权”。
[⑫]这样,义便是一种主体的灵活原则,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裁断和抉择。
由于义的这些特点,孔子提出的仁与礼的问题逐渐转化为仁与义的问题,讨论仁、义也成为孔门后学的一种时尚。
《表记》开宗明义提出,“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
”所谓“报”,郑玄注:
“谓礼也。
礼尚往来。
”故在《表记》看来,义乃是居于仁与礼之间的概念,其中,仁是天下的表率,义是天下的尺度,而礼尚往来则是天下的大利。
所以,仁与义在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但二者又是互为联系,相反相成。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
道有至,义,有考。
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仁是右,义是左,“此明仁义相须,若手之左右。
”其中,“仁者,人也”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
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中,当然是“亲亲为大”;而“道者,义也”是说,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秩序,总是要承担着相应的义务,这便是义。
所以,仁是内在性的主体原则,可表现为亲亲、爱民等等;义是外在性的规范原则,可表现为尊尊、尚贤等等。
仁和义不可偏废,“道有至,义,有考。
”郑玄注:
“有至,谓兼仁义矣。
有义,则无仁矣。
有考,考,成也,能取仁义之一成之,以不失于人,非性也。
”最高的道是仁义兼备,达到了二者的统一,而其它的道只能是“取仁义之一”也。
《表记》提出仁与义,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有其根据的。
一方面,作为高度进化的生命存在,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主体意识和自觉,在于他不是消极地适应外在环境,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意志做出选择、判断,并创造出其认为合理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人又是生活于社会之中,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关系,不得不承担与其身份相应的道德规范与义务。
这样,外在的规范和秩序与人的内在情感和自觉的关系如何,便成为人类道德实践中一个普遍而永恒问题。
当年孔子提出仁与礼,便是要面对周文的疲敝,试图通过以仁释礼,唤起人们的内在自觉,并重建合理的礼乐秩序。
《表记》将仁与义分别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原则,并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无疑是承续了孔子仁与礼的关系问题,是对后者的具体和深化。
不过,《表记》虽然试图将仁与义统一起来,但却感叹,“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
”并引《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认为“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
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仁之所以为难,是因为要做到仁与义的统一,正如要为“民之父母”,需要“有父之尊,有母之亲”一样。
仁与义是不同的,仁是内在的主体原则,从内在的情感出发,最显着的莫过于“亲亲”之情;义是外在的规范原则,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角色所决定,表现为“尊尊”、“敬长”等等。
所以,仁和义虽然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又可具体表现为“亲亲”和“尊尊”两项基本原则。
在《表记》看来,亲亲和尊尊乃是相反相成的。
所谓相反,是指亲亲与尊尊性质不同,往往体现在相对的事物之中,如,“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
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
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
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
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所谓相成,则是指亲亲与尊尊需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
”以及水与火、天与地、命与鬼的相成相济,才能成就宇宙万物、纷纭的人事活动等等。
不过,如《表记》所感叹的,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可谓“其难乎”!
《表记》对仁、义的这种理解,既不同于孔子对仁、义的分而论之,也不同于以后孟子将仁、义合并在一起,提出所谓的“仁义内在”说。
在形式上,它更接近郭店竹简中的“仁内义外”说。
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有几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一是分别将仁、义看作是内在和外在的道德规范。
如上引《语丛一》:
“仁生于人,义生于道。
或生于内,或生于外。
”《尊德义》:
“故为政者,或论之,或义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列其类。
”二是分别将仁、义看作是家族之内与家族之外的管理、统治原则。
如《六德》:
“仁,内也。
义,外也。
礼乐,共也。
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三是分别将仁、义理解为亲亲与尊贤,如《唐虞之道》: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
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孝之杀,爱天下之民。
禅之传,世亡隐德。
孝,仁之冕也。
禅,义之至也。
……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
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
”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在具体内容和表述上虽有所不同,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仁由于“生于内”,是发自于内心的,所以它首先体现于有血亲关系的家族之内,表现为爱亲、事亲的道德实践活动;义由于是“生于外”,产生于外在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角色,它更适合处理家族之外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尊尊、尊贤等等。
[⑬]可以看到,《表记》对仁、义的理解,与郭店竹简的“仁内义外”说尤其是其第三种说法是十分接近的,它们都将仁、义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原则,同时又试图将其统一起来,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差别而已。
在《表记》看来,亲亲与尊尊的相反相成,不仅体现在宇宙万物及人事活动中,同时也存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
在具体的历史朝代中,要做到亲亲与尊尊的统一,同样是“其难乎”!
其文云:
子曰: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
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不敝。
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
子曰:
“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
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
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
子曰:
“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
子曰:
“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
亲亲与尊尊是三代政治文化中两项基本原则,在促成宗族组织的和谐稳定上,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
《礼记·大传》说: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
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
是故,人道亲亲也。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
”所以亲亲与尊尊本是相辅相成的,但在具体的进路上,二者又有所区别。
亲亲侧重于子孙的世俗世界,它由内在的血缘亲情出发,由父母推及先祖,以实现宗族组织的整合、调整;尊尊则侧重于先祖的神灵世界,它通过对祖神的崇拜、信仰,由先祖延及父母,以维系宗族的等级秩序。
“若仁则父母重而祖轻,若义则祖重而父母轻。
”亲亲、尊尊这两项原则在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中本来是有机结合、二位一体的,这就是所谓“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
但在《表记》看来,夏商周三代在把这两项原则具体应用于政治的运作时均有所偏差,均无法真正作到亲亲、尊尊的统一。
“‘夏承重黎绝地天通之后,惩神人杂糅之敝,故事神敬鬼而远之,而专以人道为教。
’虽然也事鬼敬神,奉行祖先崇拜,但是强调的重点是子孙的世俗世界,把亲亲置于尊尊之上。
这种政治的优点是‘寡怨于民’、‘民未有厌其亲’,加强了人民之间的团结。
其缺点则是质朴有余而文饰不足,不能促进社会的分层,树立政治的权威,文明进化程度不高。
殷人承夏之弊,反其道而行之,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侧重于对祖先的崇拜,把尊尊置于亲亲之上。
这种政治虽然强化了权威意识,促进了等级观念,但却破坏了亲切和睦的气氛,人民放荡而不安静,务求免于刑罚而无道德上的愧耻之心。
周人承殷之弊,又回到夏代的那种事鬼敬神而远之,而专以人道为教的政治,把亲亲置于尊尊之上,但是尊礼尚施,致力于文教礼法的建设,与夏代的质朴无文有所不同。
这种政治,其赏罚用爵列,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亲者贵者享有特权,虽然合乎祖先崇拜对子孙关怀的亲亲之义,但是人民却变得贪利取巧,不畏刑罚,文过饰非,风俗浇漓,道德虚伪,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也是非常严重的。
”[⑭]可见,后儒所赞美的三代实际并非什么理想之世,充其量只不过是做到了“亲而不尊”或“尊而不亲”,是“厚于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