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docx
《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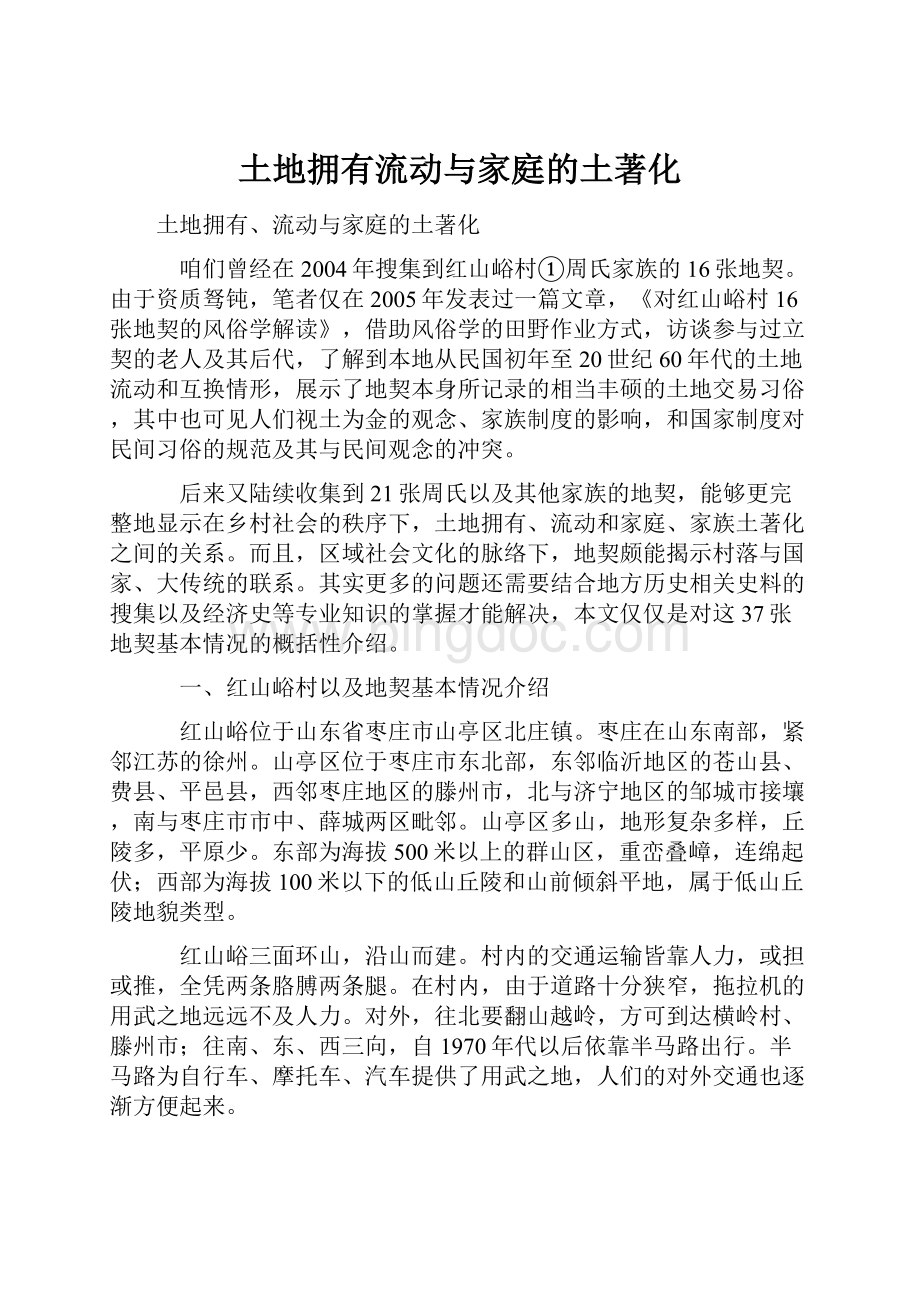
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
土地拥有、流动与家庭的土著化
咱们曾经在2004年搜集到红山峪村①周氏家族的16张地契。
由于资质驽钝,笔者仅在200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对红山峪村16张地契的风俗学解读》,借助风俗学的田野作业方式,访谈参与过立契的老人及其后代,了解到本地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土地流动和互换情形,展示了地契本身所记录的相当丰硕的土地交易习俗,其中也可见人们视土为金的观念、家族制度的影响,和国家制度对民间习俗的规范及其与民间观念的冲突。
后来又陆续收集到21张周氏以及其他家族的地契,能够更完整地显示在乡村社会的秩序下,土地拥有、流动和家庭、家族土著化之间的关系。
而且,区域社会文化的脉络下,地契颇能揭示村落与国家、大传统的联系。
其实更多的问题还需要结合地方历史相关史料的搜集以及经济史等专业知识的掌握才能解决,本文仅仅是对这37张地契基本情况的概括性介绍。
一、红山峪村以及地契基本情况介绍
红山峪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北庄镇。
枣庄在山东南部,紧邻江苏的徐州。
山亭区位于枣庄市东北部,东邻临沂地区的苍山县、费县、平邑县,西邻枣庄地区的滕州市,北与济宁地区的邹城市接壤,南与枣庄市市中、薛城两区毗邻。
山亭区多山,地形复杂多样,丘陵多,平原少。
东部为海拔500米以上的群山区,重峦叠嶂,连绵起伏;西部为海拔1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倾斜平地,属于低山丘陵地貌类型。
红山峪三面环山,沿山而建。
村内的交通运输皆靠人力,或担或推,全凭两条胳膊两条腿。
在村内,由于道路十分狭窄,拖拉机的用武之地远远不及人力。
对外,往北要翻山越岭,方可到达横岭村、滕州市;往南、东、西三向,自1970年代以后依靠半马路出行。
半马路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提供了用武之地,人们的对外交通也逐渐方便起来。
依据村中公认为居住最久的高姓人家的墓地,他们是在清雍正、乾隆年间来到红山峪的,其他九个姓氏都在高姓之后迁到红山峪。
根据对高姓家族的调查,我们得知在高姓定居之前,尚有郎姓和赵姓居住在村内。
而村中一位外柜先生②又曾亲见赵家坟墓的后土碑有“万历十三年”的字样,据此乡镇地名志的编辑人员以为红山峪始建于万历十三年。
笔者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资料,暂时只能对这一结论表示认同。
山东人往往自称是在明代从山西洪洞迁来的,“问我家乡哪里去,山西洪洞大槐树”。
在红山峪村虽然也存在大槐树的传说,可是由于人们超级明确本族的迁移线路,尤其成年人差不多都清楚了解自己是从哪个村子因为何原因搬迁过来的,所以人们谈论的常常是因何迁移、如何迁移和迁移到此地以后如何落脚、生根的故事,对于大槐树的传说反却是相对冷淡许多。
37宗交易中,既有生产性用地的交易,也有房屋或宅基地的交易,同时有一宗是土地交换,即坟地和生产性用地的交换。
详细的土地交易资料参见附录。
二、土地交易习俗的传承是土地契约与交易的内生机制
本人曾经在2005年以《对红山峪村十六张地契的民俗学解读》[1]一文对地契中所透出的土地交易习俗惯制进行解读,内容包括:
地约里的家族制度、“正用不足”;以土地为财富的观念、卖约人;缘何卖地、买地的原因;实现土著化、“有事的中人,无事的代字”;中人的意义、土地名称与丈量习惯、京钱与大洋;土地价格的制定与支付、“割税”与“大粮”;国家的在场、另类地约;国家制度与民间观念的冲突、卖地日期的选择;民间“和顺”观念。
因此在这里本人将对当时因为材料有限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补充,着重探讨土地拥有、流动与人们实现土著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从37张地契来看,无论是周氏家族的地契还是其他姓氏的地契,书体不是特别规整,有村落内流行的异体字,也有相当文言的色彩。
地契文笔畅达,而单就其格式、表述而言,又相当类同,显而易见是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典型产物。
本文所说的37张地契均为白契,载明了买主和卖主姓名、出卖原因、土地数量(亩、分)、坐落、四至八到(土地界限)、卖价、交讫日期、过割时间、税额、管业归属、防止和注意事项等、中人和代字姓名等等。
另外有一张红契,应为经政府登记入册认可的原始文书,故亦称官契。
图1 红契
图2 与红契对应的白契
从白契来看,红山峪村的土地买卖,没有皖、闽地区土地制度较多存在的“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2],不存在田面权和田底(田骨)权的分别,只要买卖,必定是彻底的地权让渡,卖主一次性将地权卖断,价格也一次性支付,同时地契上一般都要表明土之上下尽属买主所有,与卖主无干,并表明税粮从此由买主负担。
这是永久性的契约,当属死契。
这份红契文字内容如同白契,近乎重抄白契内容写在统一印制的官契纸上,收取契税之后加盖政府印钤。
红契应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的政府如何对民间的土地买卖进行监管控制。
事实上,官方规定的土地买卖程序虽然被切实履行,不过民间仍然流行保存白契,它虽然没有官方的认可,但同样有着法权效力,因此尽管人们照常纳税,但更多保留的是白契。
从人们所保留契约的情况来看,确实绝大多数人家保留着白契,因此白契所明确表明的买方对其购买土地的所有权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和合法性,显而易见。
对于白契,人们从不怀疑它的效力。
时至今日,土地改革已经50多年了,村民仍然认为,购买土地后,只要持有地约,就可以走遍天下。
地契照片4、8中民国十年和二十一年签订的地契均有“除林地三分三”等字样,意思是所卖土地,其中有三分三厘的面积是作为“林地”即墓地,仍然归卖主所有。
村民对自己祖先所购买土地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利,这就是人们对土地所有权的奇特观念。
土地划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安葬死者时,仍然选择入社之前属于自家的那块土地来作为墓地,此俗至今如此,且非红山峪村独有。
人们对白契效力的认可,和土地交易习俗的传承惯制有关,传承是土地契约与交易的内生机制。
白契之所以具有效力,是因为中人③的存在。
37份地契(除一份不清楚之外)所反映出来的中人共有47人,合计担任过78人次的中人,平均至少两人担任一地契的中人。
47人中,其中32人担任过一次中人,15人担任过两次以上的中人。
村内土地和宅基地的生意,多数由周德承、王广山、段德基、田中吉这几人担当,因为他们对土地交易中的适应都超级了解,操作起来驾轻就熟。
何况,若是多数村民都请他们当中人,而有个他人不请,这就显出了对他们的轻视,无视他们的重要作用,如此可能会造成乡邻间的矛盾。
因此进行土地生意交易时请不请中人、请哪些人担当中人,都不可能离开村里的权威格局。
可是,由于中人的主要功能在于证明作用(比如地契照片25反映出的赵孙氏卖地,就找了4个人担当中人,特别强调中人的见证功能),因此仍是造成了中人的分散。
中人分散而不集中,反映出当地土地交易并没有实现土地市场化。
他们的功能不同于牙行,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中人既不集中,也不确定,因为中人在当地土地交易中的作用在于测量土地和证明作用,仅有一份地契(照片29)特别注明“自卖之后土之上下尽属买主管业于卖主无干如有争差有中人一面承揽”,其他有16份地契一般注明“如有争差由卖主一面全管”,另有18份地契没有注明此类争执如何解决,但习惯上人们认为地约签订以后的纠纷由卖主负责。
而且,所有地契均注明了“口说无凭,立约为证”之类的话语,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地契的功能,地契本身就可作为解决争执的凭证,表明了白契同样具有相当的法律或者习惯法效用。
白契的这种效用离不开中人的性质——因其“公道”而可作为“证家”。
真正以经营土地买卖作为固定职业的现象还没有正式出现,因此土地买卖虽然频繁(周克安1909-1935年26年间有9宗土地交易,周德俊在1921-1960年39年间有12宗土地交易),但土地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商品,其主要功能仍然是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背后所附带的功能和意义,而买卖双方进行土地交易的目的大部分也不是为了进行投机获取利润,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市场还远得很。
结合各种分析表明,土地交易习俗的传承是土地契约与交易的内生机制。
从1909到1990年,土地买卖文书长期使用并不断完善,土地契约的格式也逐渐固定并规范化,且富有较强的延续性。
从各历史时期地契的样式、内容来看,存在一个显著的继承、发展过程。
这是习惯力量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契约关系、契约意识的深入人心。
三、陌生人凭借姻亲与家族进入村落
根据能够找到的家谱以及多数家族族长的回忆,笔者大致可以整理出村中10个姓氏的基本情况。
村中10个姓氏,分为11个家族④,别离附属于其他村落的大家族,在家谱上他们是很小的一支,因为各类原因来到红山峪投奔姻亲或同姓。
迄今为止,红山峪任何一个家族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家谱。
从我能找到的家谱看,无一例外都是附属于其他村落的,巩姓的家谱乃至都保留在他们的迁出村落中。
如此一个村落,没有特别大的家族,可是若是有一个家族在进展进程中壮大起来,它极可能就成为其他家族所依附的对象。
红山峪村的田氏家族曾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当地人的社会记忆中甚至取代了高姓成为村落中现存姓氏历史最久的一个。
如果一个村子里有自己的同姓或者亲戚,人们就可以投奔而来。
田姓算是较早投奔姻亲(高姓)来到红山峪村的,以后的姓氏多是依靠来此。
但田氏家族都认为高姓算起来实际上是红山峪的“老户人烟”⑤,只是后代香火不旺算了。
可是此刻即即是高姓,也在公开场合承认田姓“占业”⑥,田姓才是“老户人烟”,自己是依托田姓而来。
高姓已然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姓氏的态度了。
田姓在村民的记忆里取代了高姓成为红山峪的老户人烟,最初的原因不外乎田姓家族的实力。
根据村民的记忆,20世纪初期,田姓在红山峪和邻村天喜庄都拥有大量土地,即使是田姓迁移到红山峪村,仍然占有500亩良田,其余200亩才是村里其他家族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田姓势力逐渐衰落,但是尽管如此,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仍然在村子里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我们在1960年以前见不到田氏家族的成员卖地。
这是由于田姓早已依靠自己的实力与声望,通过与外界富家大族联姻,从而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外界,甚至在政治上也建立了新的地位并掌握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因为联姻形成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巩固了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
正如华若璧(Rubie所说的那样,富人阶层通过联姻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与姻亲的往来密切,与穷人极为不同,但是这种区别也是创造和保持那些区别的制度结构的一部分[3]。
种种关系网络奠定了田家的政治基础,使之基本能够左右本村的形势。
全村10个姓氏,其中不少属于单门独户,谁受到异姓的威胁,或者与其他家族之间关系不称心,都来与田氏家族表示亲近,或者说与田家有亲戚,或者说父辈与田家关系如何如何好,或者说自己是依靠田家才能在村里落户。
田氏家族依靠姻亲进入村落,从而为扎根本村打下了基础,这一点也是其他姓氏所采取的普遍方法。
本文要在此处以及下文特别以周氏家族为例进行分析,因为从地契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周氏家族在家族内部以及与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交易特别活跃,当然这和我们收集到的地契多是周氏家族的有关,但根据后续访谈,其他家族确实没有周氏家族如此频繁的土地交易。
根据调查,红山峪的“周”虽已成“一周”,但其实最初是不同的两支,一支以周克安为始,从徐庄镇岩底村搬迁到徐庄镇罗子湾村,后又辗转来到红山峪村,又娶田氏家族的姑娘为妻,从此正式安家落户。
另一支据说原姓欧或邹,从徐庄乡柳泉迁来此地,为了能够长期在此村立足,转而改姓为周,现在有5代,也曾与田姓联姻。
从村里姓氏的迁移史[4]可以看出,人们进入一个村子的途径⑦一般有两种。
第一是若是村子里有家族近亲和亲戚,能够“偎”本家或“偎”亲戚,先利用他们的土地,再随实在力的提高而购买土地。
第二是通过与该村村民联姻,继而取得土地,才逐渐得以安家落户的。
总之,初步在村里居住下来方式大多是依托家族或姻亲,再加上取得土地以后,家庭经济条件慢慢提高,并在村子里有了良好的关系网络,这是“外来户”成为“新发户”继而在若干年后被人们视为“坐地户⑧”的必经历程。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就曾经注意过“如何成为村子里的人”这个问题,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
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
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5]72。
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是站稳脚跟的一个主要方式,进入了村落里的亲属网络,才有了可以依赖的人际关系。
移民既要借助联姻定居村庄,进而通过占有土地实现土著化,接着还是要借助联姻稳固地位、扩展社会网络。
婚姻与家族的关系之重要,不仅在于单纯的两个联姻家族之间,而意义更大至一个地域社会,借以融洽关系,进而融入当地社会,最终实现土著化,这是根本目的。
此外,认干亲,拜仁兄弟,交朋友,春节拜年,经济上的互助拉拢,红白喜事请外姓帮忙,日常生活中的专程拜访,也是人们借以扩展社交的机会。
四、土著化的实现以家庭而非家族为单位
从地契来看,所有出卖土地的人,无不避免称“卖地”,而是自称“卖约人”;出卖土地,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均称“正用不足”。
这些都是和人们对土地的珍视有关。
但购买土地的原因,不外乎生计,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买地人在村子里的地位、实现土著化。
或者说,红山峪村的土地交换,并不是像江南那样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地权转移[6],而更多的是由于生计、土著化引起。
红山峪村处于三面环山的山区。
以大山地形为主,适合成片的耕种之地较少,土地以散碎为主。
每一块地都有名字,每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也都有名字。
有几块土地的范围和方位比较清晰,故而连小孩子都知道。
笔者到一户人家家里拜访一位老人,他的孙子告诉我,“俺老爷上北台子地了”。
北台子地在村子的北面,南面即上村和底边之间有一部分地,西山顶的地很少,东山顶山上山下的土地叫东岗地。
土地数量多,面积小,地块零碎⑨,位置明确,这在必然程度上不仅方便了土地生意,同时也决定了村民没有较多的利益连带关系,这和江南水乡的特定生态条件所形成的村落水面公产,使村民有了更多的利益连带关系不同[7]。
再加上红山峪村人口密度低,因此村民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和保护就不那么明显,村落关系结构偏于开放而非封锁,这各种因素有利于吸引外来人口。
然而进入村子容易,可是要把村子变成自己的村子,实现土著化,成为“坐地户”,却是非常之难。
移民来到此地,一般都是以寻求可耕之地为主要目的。
由于大多数是家庭迁居,人数不多,对于家族聚居造成障碍,即使有家族聚居,也难以形成较大规模。
因此,对于势单力薄的家族来说,要想形成自己的势力,壮大发展,必须要依靠外界力量。
因此,村落内部的各个家族,一般来说都是合作多,对抗少,家族之间的联姻也比较普遍。
尽管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家族聚居,但人们非常尊重家族制度。
家族内部的土地交易也经常出现,仅在周氏家族内部就出现了9例。
当一人要卖土地时,必先告知同胞以至叔伯兄弟,告之出卖的原因和价格。
当兄弟决定购买时,价格会适当降低,若他们无意购买,再在其他家族人员中寻找买主。
除非未能在本家族中寻得买主,否则不可召其他姓氏购买。
最先购买权从同胞兄弟开始,以血缘关系的远近层层外推,反映了土地和家族组织的密切关系。
对于不遵守这一“规矩”的人,家族成员自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对之进行制约。
如1950年代初,村民田某欲出卖老宅子⑩西面的一片山坡,他不曾与家族近亲商量,而是自主决定直接卖给家族远亲,计价60万元(相当于此刻的60元)。
田某的亲婶子田王氏明白他要出卖土地后表示自己也要买,不料田某抬价至80万元。
田王氏考虑到这是家族近亲的土地,以为价钱再高也得买下来,而不能任其流落到远亲手中,于是即以80万元买了下来。
不过从此以后,田某失去了家族近亲的庇护,而且也给其子孙仍留下了备受近亲冷落的后遗症。
家族内部的土地交易,一方面反映了土地的珍贵,即使同胞兄弟、叔侄之间,买卖照旧不含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族内部也需要依靠契约来确认法律关系,从法权上确立对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避免家族内部的矛盾或冲突,理顺人际关系,同样依靠地契整合交易。
因此,土地契约文书也是法权的体现,表明社会已逐渐步入法权的阶段。
虽然地契表明周氏家族活跃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但并没有出现土地集中于家族的趋势,红山峪村的土著化社会诞生也比较晚。
家族的确是人们进入村落的一个路径,但土著化的实现却是以家庭为单位,这样做的结果是减缓了家族的土著化进程。
下图表示地契中所涉周氏家族成员的关系图。
其中克字辈的四位是家族内部近亲兄弟。
据说,宣统元年和宣统二年周德田两次卖地给周克安很可能是为了筹办红白喜事而“花地”。
周克安在村民记忆中特别能“弄钱”,他一点一点积攒钱,有钱就买地,而不管所购土地来源于同姓还是他姓。
而周德俊在一年之中先后三次从亲侄子周振方手中买地。
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购买土地是出于一种家庭意识,而非家族意识。
当然,周振方没有把土地卖给族外之人首先也是出于对家族制度的尊重。
虽然人们尊重家族制度,但红山峪村的家族关系并未得到充分发育(11)。
通过姻亲关系可以进入村落,但通婚并不能真正实现土著化;家族关系也可以进入村落,但实现土著化并不是依靠家族。
购买土地有助于实现迅速的土著化进程。
对土地的渴望使得人们超越了对家族发展的关注,更加重视家庭的土著化。
因为土著化以后,家庭同样可以在红山峪村这种家族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地方落脚、繁荣。
只有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前提下,家族关系高度发育,才会产生严重的排外现象,即使是借助姻亲和同族关系也难以在较短的时期为村民所认可。
图3 地契中所涉周氏家族成员的关系图
五、未了问题
土地私有引发土地流转,由此产生了土地契约这种鲜活的历史见证。
本人尚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
本人对地契的解读,因为欠缺专业基础知识,未见得准确。
而且土地契约文书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关系密切,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研究。
土地契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土地的开垦、价格、生产以及生态的变化,同时它本身所记载的地价也足可反映社会经济的变动。
地价与本身的肥瘠、环境、位置有关,同时又与时空关系密切。
红山峪村这些地契的价格和处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社会的土地相比如何?
37份地契本身的纵向地价相比又如何?
税粮问题同样也存在这些比较。
第二:
资料的缺乏导致不能进入更深层次或更广时空的讨论。
地契中有卖主是红山峪村邻村人,也有个别土地是辗转经由第三村交换而来。
以红山峪村为中心,若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文化、历史资料,可以探讨小区域内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进而探讨村落与较大范围内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三:
从立契时间来看,1909到1990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几次改变,而中国历史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土地交易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村落内部的土著化进程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发生中断?
时代交替、制度演变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可以确认,人们对土地的珍视观念一直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农村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土地私有逐渐转变为集体所有,到1960年买卖土地已经非法,但人们仍然在地下进行土地的买卖,虽然这种契约没有实际效用,但这至少反映了长期以来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地权意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9-07-01
注释:
①本文资料全数来自山东南部乡村红山峪。
田传江著有《红山峪村风俗志》,1999年由辽宁音像文化出版社出版。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村落风俗志专著,44万字,全书共4部份10章45节,包括有关农业、林业、畜禽、野生动物、副业、气宇衡、贸易、纺织、饮食、居住、交通、婚嫁、丧葬及游戏等方面1000余个风俗书象,作者也记录了它们的产生、进展、演变……
②村中专门负责在丧葬仪式上记账的人,因识文断字,被称为“外柜先生”。
③中人,生意两边签定地契时在场的证明人。
④同一个姓氏居住于同一村落的反而并非必然彼此认同为同一家族。
而且,村民心目中从未有“族”的认同,言谈当中唯有“姓”的意识。
红山峪村的姓氏结构不是简单的姓氏与家族一一对应的结构,一方面存在着同一个家族的人群分散居住的情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形。
因此,能够肯定地说红山峪的聚落性质是多姓聚居,而不是多族聚居。
参见文献[4]。
⑤老户人烟的意思大体上是某一个家族在某村居住相对最久。
人烟与家族的男性后代联系在一路,人烟旺就是家族人口繁多,人烟不旺则是人口少,往往一代仅有一个男性后代。
⑥占业的意思是田姓最先来到红山峪村,村子里的一切最先应该是属于田姓的,田姓才是村里的主人。
⑦在近代华北农村,某人是不是是某个村社的成员,要看他是不是具有被该村社认可的村民资格,仅仅居住在那个村子还不够。
在河北顺义县沙井村,申请取得村民资格的人应没有劣迹,并须有自己的衡宇能够独立生火做饭。
那种虽在村内居住但不肯常住该村的人(如村中学校教师)被以为是“外人”,不能参加全村性活动。
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要求新来者在村中拥有土地和衡宇,那些没有土地、租房居住的寄庄户,往往须经地主担保他们遵纪遵法,若是有不轨行为,其担保者受罚。
如此的寄庄户如在村中居住10年以上,而且没有过错,才能够成为村中一员。
在有些村落还要求新入村者在该村拥有坟地。
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只有当一个人其先人三代都居住在该村,才会被以为具有完全的村民资格。
在山西省太谷县的贯家堡村,那些到本村投奔亲戚赁屋居住的人家,仍然被村里人目为借居者。
参见:
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704~705。
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居住的自然形态,而未考虑“入籍”,即被政府纳入户籍管理的肯定意义。
⑧“外来户”、“新发户”、“坐地户”是红山峪村的特有方言辞汇。
“坐地户”意指土著。
“坐地户”与“外来户”相对应,后者被认可为前者的进程,即土著化的进程。
而“新发户”是“外来户”通过一段时刻的进展,在村子里拥有土地,进入村子里的关系网络,并有良好的口碑,由此被称为“新发户”。
“新发户”到“坐地户”的进程,是“外来户”成为“新发户”若干年以后,家族确已根深叶茂,渐渐被等同于“坐地户”。
⑨红山峪村流传着“家有百块地”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前后,给闺女说婆家第一问男家有多少地,即便土地归集体后好长时期,媒人介绍男家,仍然追溯到集体化前有多少多少地,以此夸耀男家“是过日子人家”。
一家找媒人给说儿媳妇,女方先问家有多少地,男方父母说“不用问,给女家说,咱们家有一百块地”。
媒人就把话如实转告子女家,女家父母听了,心想“一块地一亩,最少也有一百亩”。
女家离山区很远,是平原地域,不明白山里地块零碎,就承诺了这门亲事。
过门后,小两口去耪地,一气完成了99块,就是找不到最后一块,最后发觉“席夹头”(一种草帽)底下还盖一块地。
故事讲述人:
李桂枝,讲述时刻:
2001年4月20日,访谈人:
刁统菊。
⑩父母居住的屋子。
当兄弟分家以后,就会把父母的宅子叫做“老宅子”。
(11)直至今天,村落仍然离不开十个姓氏之间的联姻和互相依赖。
当然其中绝对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形。
为了争夺空间和资源引起的斗争,或者因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都曾经存在甚至从未消歇过。
从表面上来看,十个姓氏之间的关系很好,其中原因是大姓已经没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小姓则在千方百计地通过联姻寻求广泛的合作和依赖的对象,结果使得村民的利益更趋于一致,矛盾也大为减少。
在附近其他村落看来,“红山峪的人很平和,姓杂,都是亲戚,好办事”。
姓氏之间彼此互有姻亲关系,在这个姻亲关系网中,异姓村民之间的互助不再纯粹是乡邻互助的性质,联姻关系的介入使得这种互助更多地具有了亲戚情感的意味。
多姓聚居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加了村落的向心力。
单姓村的村落意识往往是和家族意识重叠在一起的,而在一个多姓村内部,姓氏之间虽然有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