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docx
《三星堆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星堆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docx(36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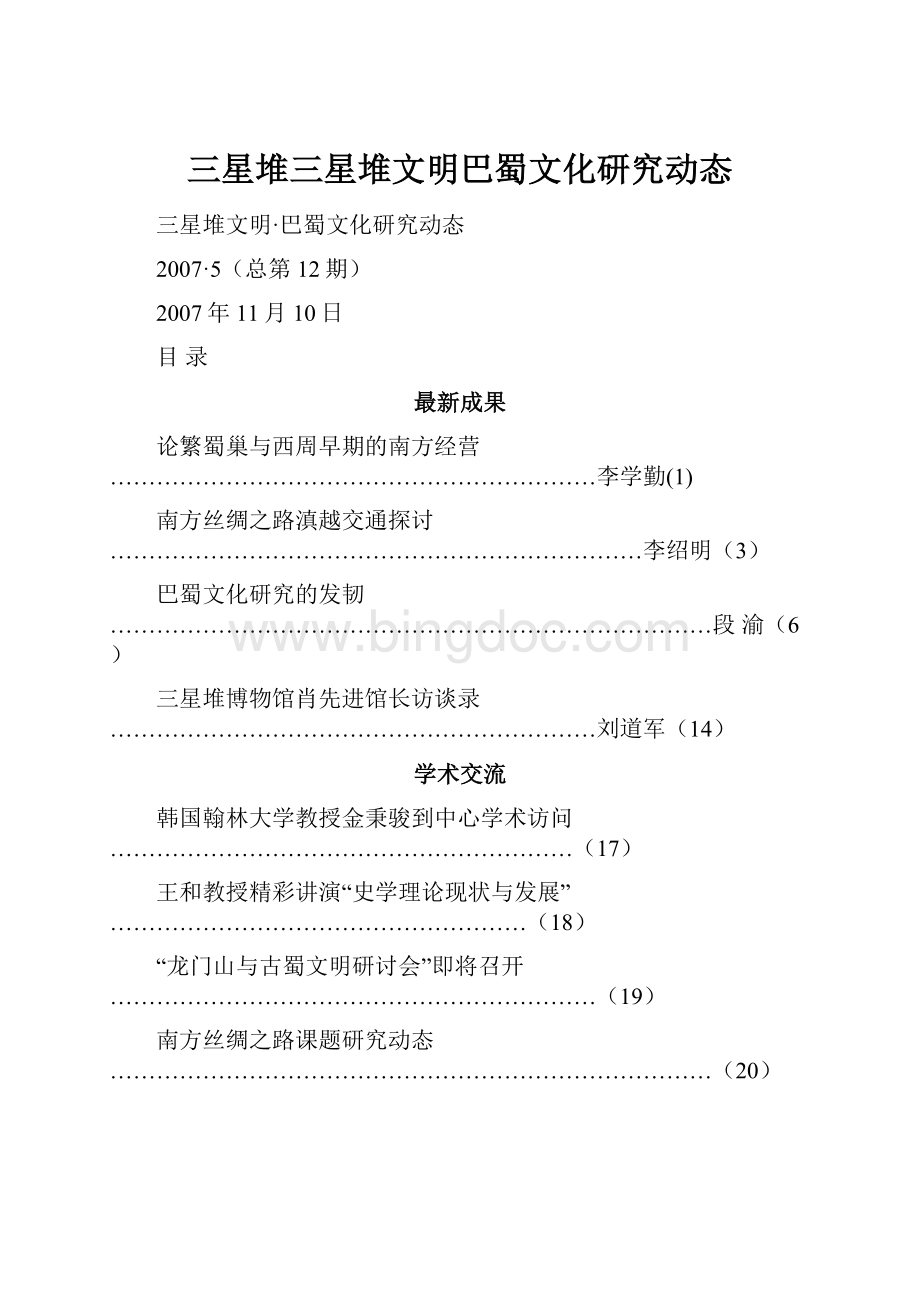
三星堆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2007·5(总第12期)
2007年11月10日
目录
最新成果
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李学勤
(1)
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李绍明(3)
巴蜀文化研究的发韧……………………………………………………………………段渝(6)
三星堆博物馆肖先进馆长访谈录………………………………………………………刘道军(14)
学术交流
韩国翰林大学教授金秉骏到中心学术访问……………………………………………………(17)
王和教授精彩讲演“史学理论现状与发展”………………………………………………(18)
“龙门山与古蜀文明研讨会”即将召开………………………………………………………(19)
南方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动态……………………………………………………………………(20)
基地建设
段渝、庾光蓉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22)
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
李学勤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著名青铜器班簋,曾著录在清乾隆时的《西清古鑑》,后自宫中流出,到1972年重新发现,已经残破,幸好内底铭文没有损坏〔1〕。
簋的时代是周穆王,其铭文开首说:
惟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
王命毛伯更(赓)虢城(成)公服,(屏)
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巢
命,锡勒。
……
这里毛伯受王命接续已故虢成公的职位,辅佐天子,为四方即周朝四土的中枢,地位高贵,所以铭文下面就改称他为毛公。
“秉繁蜀巢命”一句较难解释,多数学者同意“繁、蜀、巢”是三个地名。
我以前说明过,“秉命”犹如《论语·季氏》的“执命”,意思是掌管其政事〔2〕。
管理繁、蜀、巢的有关事务,是毛公的特殊职权。
由铭文在四方以外特举繁、蜀、巢看,三者应该都是王朝辖属地域外面的蛮夷之邦。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周早期的古文字材料中,繁、蜀、巢都有被周人征伐的记录,伐蜀还见于传世文献。
按《尚书·牧誓》,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蜀人本随周伐纣,但《逸周书·世俘》云在克商之后,“新荒命伐蜀”。
这件事,可能与追擒商朝的霍侯等人有关〔3〕。
“伐蜀”也见于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的西周早期卜甲H11:
68〔4〕;同出卜甲H11:
97还有“克蜀”〔5〕,两者的“蜀”字写法和班簋是一样的。
卜辞的“伐蜀”,“克蜀”,有可能同《世俘》所记武王伐纣后命新荒伐蜀是同一件事情。
揣想纣死之后,商臣霍侯等逃亡入蜀,武王遣军追击,将霍侯等擒获〔5〕。
蜀国对周人叛服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凤雏卜甲H11:
110有“征巢”〔7〕。
《殷周金文集成》2457陕西长安张家坡所出西周早期鼎铭云:
“侯获巢,俘厥金胄,……”有可能就是征巢之事。
巢国本来也是服属于周的,《尚书序》载: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排在《金縢》之前,也是武王克商后不久的情况。
张家坡鼎不能早到武王,可见巢国对周也是时叛时服。
对繁的征伐則见于2003年12月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发现的周初背甲C10④:
2。
该甲“〔惟〕王月(哉)死霸壬午”一辞,“繁”字上面一字不很清楚,现据董珊博士摹本及考释〔8〕,知道应隶定为“”,当依刘釗博士意见读为“翦伐”的“翦”〔9〕,“翦繁”亦即伐繁。
由上述可知,繁、蜀、巢在西周早期均曾为周人征讨,到周穆王即班簋的时候,則已归属于周。
《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称,武王克商之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在今成都盆地的蜀,位于巴国之西;今安徽巢县的巢,位于楚国之东,刚好夹居周朝南土的两侧外
〔作者简介〕李学勤,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北京100000。
翼。
现在问题是繁在什么地方。
以前讨论班簋的学者,都以为是在今河南新蔡北的繁阳,不过该地名《左传》襄公四年作“繁阳”,定公六年作“繁扬”,青铜器晋姜鼎作“繁汤”,繁阳之金剑作“繁杨”,鄂君启节作“繁昜”,从没有去掉后一字单作“繁”的。
况且繁阳在周朝南土之东,宜于与巢连称,同蜀连称并不合适。
最近,北京大学的学者发表了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一件甗〔10〕,铭文是:
惟十又(有)〔二〕月王命南
宫〔伐〕虎古之年,〔惟〕正
月既死霸庚申,王在
宗周,王〔命〕□吏(使)于
繁,錫貝五〔朋〕,□扬对
王〔休〕,用作……彝,
子子孙……永……
我已写了一篇小文详细讨论〔11〕。
小文将这件甗同过去著录的周昭王南巡时诸器联系起来,知道甗銘“十有二月”是周昭王十八年十二月,“正月”是十九年正月。
周正建子,晋国沿用夏正則建寅,因而在器主晋人看来,周正十二月和正月属于同一年。
昭王命南宫伐虎方,也見于北宋时在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虎方从有关銘文推断,乃是崇拜白虎的巴人。
我以为繁的地理位置可由汉代的繁县推断。
《汉书·地理志》蜀郡繁县,据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在今四川彭县西北,原新繁县北20里。
繁县命名,《后汉书·臧宫传》注云来自繁江,所以有古远的依据,繁江当即湔水。
这样,我们便不难明白,周朝出军讨伐巴人,为什么要遣使到繁。
这是因为繁居蜀国之北,或许是蜀的北部,故而征巴有必要安抚繁以及蜀。
班簋之所以连称繁、蜀,也容易理解了。
《华阳国志》讲巴、蜀同囿,彼此关系密切,伐巴自然有必要派使臣安蜀。
至于那时繁、蜀是否两个诸侯国,尚有待更多发现证明,我个人仍觉得繁只是蜀国的一部分。
大家了解,被称作繁的这一带多有商周遗存,过去报道的如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都已脍炙人口。
其间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有可能是繁的都邑的,无疑便是广汉三星堆城址了。
这当然属于猜想,留待读者考虑批评。
〔参考文献〕
〔1〕郭沫若:
《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2〕李学勤:
《青铜器与古代史》,第304页,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
〔3〕前人一般认为《世俘》所说是另一蜀地,有关问题另文详论。
〔4〕曹玮:
《周原甲骨文》,第5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5〕同〔4〕,第71页。
〔6〕黄怀信等:
《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430—4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7〕同〔4〕,第77页。
〔8〕周原考古队:
《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第179页,图二五;董珊:
《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同上,第245页。
〔9〕刘钊:
《古文字考释丛稿》,第140—148页,岳麓书社,2005年。
〔10〕孙庆伟:
《从新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第1期。
〔11〕李学勤:
《论甗铭文及周昭王南征》,待刊。
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
李绍明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从今成都出发,经川南进入云南,然后通往缅甸、越南诸国,再转至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一些地方的古代交通要道。
以往对由蜀往滇的东西两道探讨较多,情况较明。
但由滇至缅或越的两道则研究不够充分,尤其是对滇越一道存疑之处较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今略述拙见以求教于方家。
法国学者伯希和曾言:
“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按今河内)交通之事,今尚无跡可寻,六世纪之《水经注》似未言及此。
”〔1〕实则滇越间早在西汉时已有交通记载。
严耕望先生于《唐代交通图考》书中曾言:
“中国史料所见,滇越间早有通道。
西汉时代牂牁郡进桑县为郡南部都尉治,置关,几出入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
是即滇越有通道之明征。
故东汉初年,马援在交趾,上言欲自交趾出进桑至贲古(约今弥勒E103°、N24°30’地区),击益州(今昆明)也。
就《水经注》所记,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
此道至东汉末年仍见通行。
如刘巴由交趾经牂牁至益州,即此道;而交趾太守士燮与益州时通音信,许靖由交趾西北至益州,殆亦由此一道耳。
”又云:
“三国末年,魏灭蜀,吴国交趾人吕兴杀太守,遣使‘诣进乘县’,因南中护军霍戈上表于魏。
进乘即进桑,南中沿今曲靖县,是仍与汉道不异。
当时此道行旅盖颇盛,故晋初陶璜谓‘宁州(南中更名)兴古(今罗平地区)接据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为维衛’也。
惟此道沿途实‘崇山接险’,绝非坦途,《南中八志》有‘鸟道’之名。
”〔2〕关于汉晋之时滇越之间这一通道严先生考证颇详,为了说明问题可暂称之为“进桑道”。
关于进桑道,方国瑜先生亦有考证,认为此道确为汉晋间滇越通途,但却将进桑的方位定于今云南的河口、马关二县间,系在红河流域,而与严先生将进桑定位于今盘龙江流域之越南河江县是完全不同之处〔3〕。
于是,这便有了汉晋以及此后的唐代滇越间主要通道究竟是一条或两条的问题。
有关唐代滇越间的交通,《新唐书·地理志》附录有贾耽《安南通天竺道条》以及樊绰《蛮书》之《界内途程条》,皆有述安南西北至拓东(今昆明)、安宁(今县)的路程甚详。
但学者对此路途的走向则有不同解释。
诚如严耕望先生言:
“此道详程虽明,然究取何条路线,则有问题。
有人论者,皆以为取今红河路,所谓水行,即浮红河(富良江)也。
但实考之,仍即汉晋以来之叶榆水道,即今盘龙江道,非红河道也。
”〔4〕但是,严先生亦未完全否定当时已有一条自云南之步头通往越南北部的道路。
故他言:
“至于步头,则在今红河(富良江)沿岸,似蔓耗(E103°22’、N22°55’)地,或在其西北,建水直南之红河岸,或在其北,蒙自南之南溪河岸,未可知也。
步头一下亦水道通安南。
此已开元明清水道之渐;但在唐世,似仍不若汉晋以来沿盘龙江旧道之重要也。
”〔5〕
有关唐代滇越之间的“步头道”,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此道系沿红河南下而达于河内者。
方先生谓:
“《南诏德化碑》说:
‘赞普钟十四年(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贰诏,佐镇抚。
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诰所及,翕然俯从。
’又说:
‘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
’……步头为一地区之称,且当冲要之地,是可想而知的。
樊绰《云南志》卷四“两爨”条说:
‘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
’亦载《新唐书·南蛮
〔作者简介〕李绍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00。
传》“两爨”条。
这是《南诏德化碑》所说:
‘置府东爨,路通安南’。
……是时开步头路,正由于步头地区有优越的地理和社会条件可以凭借,并非偶然。
”〔6〕有关步头的位置,方先生谓:
“从地理情况及历史实际,当考订步头在今之元江。
”〔7〕而步头之南有一要地名贾涌步(古勇步)者,方先生以为应在今云南的河口〔8〕。
由此,方先生将步头道确定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将汉晋之进桑定于河口则所据不足。
有如上述,余以为自汉晋以降,以迄唐代,滇越之间除原已存在的进桑道外,尚有另一通途即步头道。
此二道中进桑道系沿盘龙江而下,而步头道系沿红河而下,二者走向是不相同的,不可仅视为一途以概之。
余以前在滇进行民族历史考察时曾走过上述两道,近来又赴越南北部中越沿边一带考察,经过实地踏勘与调研,进一步证实了滇越通道自古即有此二途之存在。
前已言及,汉晋之时进桑道为由滇至越之要道,盖由于当时之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
其时中央王朝经营南中,其主要趋势是由北而南和由东而西,西汉之设置越嶲、益州、牂牁三郡及犍为南都都尉,以及西晋之设置越嶲、云南、永昌、建宁、兴古、牂牁、朱提七郡莫不如此向前推进。
进桑一道偏于东部,较易于受中央王朝控制,故而成为当时通越之主要道路,即官道之所在。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完全否定偏于西部的唐代之步头道于汉晋时已有民间道路的存在,只不过此道并非官道而已。
但是,到了唐代形势有了较大变化。
南诏政权由于种种原因在云南逐渐坐大,南诏的中心最初在今滇西大理一带,中央王朝为制约南诏不得不着手于经营偏西之步头道,以便实施由安南对南诏的大包抄,由此步头道之身势大增,遂逐渐取代了进桑道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滇越之间的主要通道。
此乃唐代这两条道路重要地位互易的主要原因。
除此,若就传说而言,滇越间之通道尚可追溯至战国时代。
此即史籍中所言蜀王子泮王越之事。
此事见于《史记》卷一一三《南越传》之《索隐》以及《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诸书。
余在越南考察时,知越人至今对蜀王子即安阳王仍十分崇敬,不仅将安阳王所建的瓯雒国视为其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且还建有安阳王祠庙多处以兹纪念,且至今河内新开的一条大道仍以安阳王大道命名〔9〕,足见此说应有所据。
不过安阳王究竟经过何途入越,由于资料的不足,现仅能作出一些推论。
滇越之间古代之进桑、步头两道以今地位度之,前者系沿盘龙江而下,后者则沿红河而下者。
进桑道所经系由滇中经今日之弥勒、开远,而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之文山、麻栗坡等地,再由此进入越南的河江省境。
迄今麻栗坡县盘龙江(南温河)畔之天保口岸仍是中国通向越南之重要关口。
而步头道所经,系由滇中经今日之元江,而进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之红河、元阳、个旧、河口等地,然后再进入越南的老街省境。
迄今河口县红河畔之河口口岸仍是中越边境之重要关口。
以上两道,现皆有陆路之公路(沿红河尚有滇越铁路)以及水路相通。
但在古代,由于条件有限,两道有些段落仅有陆路,而有些地方,尤其是此两江的下游则可通舟楫。
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审视,沿红河的步头一途,元江以下即可行舟,交通条件较为优越。
我们若从古代蜀人入滇后所居地域而论。
《史记·三代世表》载汉禇少孙言:
“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于此,唐张守节《正义》引文云:
“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
”由此可知汉时蜀人后裔尚有居于南中之姚(州)、嶲(州)一带。
此中所谓嶲州,大体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范围,而姚州之中心则在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一带。
而红河(亦名礼社江、七河底江)发源于云南祥云,经弥渡流入楚雄彝族自治州之南华,楚雄、双柏等地,然后经新平而至元江,元江以下则流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以至在该州之河口流入越南北境。
由此可知,红河一途即古步头道当是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最佳路径。
我们再从古蜀人的民族属性而论。
此前笔者曾对古蜀人的族属进行过分忻,认为“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蜀族应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其体质具有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的民族,既有属于氐羌系的民族,也有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濮越系的民族,而后者的体质则具有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
”〔10〕前已言及,红河流域主要聚居之民族为古氐羌人后裔之藏缅语族的民族,而现今仍主要为彝族和哈尼族所居之地。
但盘龙江流域主要聚居之民族为古濮越人后裔之壮侗语族的民族,而现今仍主要为壮族及其支系所居。
古蜀人的统治者及其主流既为氐羌系之民族,则他们之迁徙路线以在本族系范围之内较为便利,而少受阻碍,故亦以走红河一道南下为宜。
有如上述,笔者推论古蜀人由滇迁越之路线应为沿红河流域南下,并即步头道一线。
总之,南方丝绸之路滇越间的交通为时甚早,先秦之时即有传闻,汉晋之间已有记载,其最重要者莫过进桑与步头两道。
此不过大略言之,实则滇越之间尚有一些较次要之通道存在,至今尤然。
直至近代滇越间陆路始有滇越铁路及一些公路开通,由此这些古道之地位始被逐渐代替。
不过这些铁路与公路之许多段落仍循原古道线路而行,可见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上滇越交通一直处于盛而不衰地位。
〔参考文献〕
〔1〕伯希和:
《交广印度两道考》之上卷《陆道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史地丛书”本。
〔2〕皆见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三五《汉晋时代滇越道》,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台北版。
〔3〕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四篇《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地理考释》之《交通沿线地名·南诏通安南道》,中华书局,1987年版。
〔4〕〔5〕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三六《唐代滇越道》。
〔6〕〔7〕方国瑜:
《步头之方位》,载方氏著:
《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方国瑜:
《古涌步之位置》,载方氏著《滇史论丛》第一辑。
〔9〕李绍明:
《越南访古札记》,《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2期,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10〕李绍明:
《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巴蜀文化研究的发韧
段渝
〔摘要〕“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正式提出来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内迁,国内许多知名教授和专家学者进入四川,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
其中一些大学者,鉴于四川上古史的复杂性,开始潜心研究有关史料和当时极为有限的考古资料,于是提出“巴蜀文化”的命题,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辩,巴蜀文化研究竟一时蔚然成风,终至成为一个科学命题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
〔关键词〕抗战时期;巴蜀文化;学术史
〔作者简介〕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一、巴蜀文化命题的提出
巴蜀文化命题的提出,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一是广汉真武宫玉石器坑的发现与发掘,二是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由这两条主要线索,揭开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序幕。
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城西18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批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H.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D.S.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
戴氏据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AncientCircles,Squares,AnglesandCurvesinEarthandinStoneinSzechwan),备记其事,并对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讨,发表于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oftheWestChinaBorderResearchSociety)第4卷(1934)。
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氏购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发表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文中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
1933年(一说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教授及该馆助理馆员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在燕宅旁开展正式田野考古发掘,颇有收获,由此揭开了日后三星堆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1934年7月9日,时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的发现相似,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
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认为广汉遗址的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
1936年,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PreliminaryReportoftheHanchou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
林名均亦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
两文均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
至于年代,葛维汉认为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则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认为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作为该馆专刊之一。
在这部著作里,郑德坤把“广汉文化”作为一个专章加以讨论研究,从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等五个方面详加分析,不同意葛维汉、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之间。
广汉发掘尤其“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者对广汉遗物与中原文化有异有同的现象开始寄予了关注。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广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特别重视。
1941年,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在上海出版,本期题名为“巴蜀文化专号”。
在本期中发表了卫聚贤题为《巴蜀文化》的文章,该文洋洋洒洒数万字,并附有大量在四川出土的各类器物的摹绘图。
该期还同时发表了郭沫若、常任霞、张希鲁等文史名家的论文。
金祖同在该期的《冠词》中写道:
溯自抗战军兴,国都西徙,衣冠人物,群集渝蓉,巴蜀一隅,遂成为复兴我国之策源圣地,政治、经济、人文学囿,蔚为中心,粲然大盛,日下风流,俨然见汉家旧典,中华崭然新文化,当亦将于此处孕育胚胎,植其始基,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
……奋起有人,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其光华灿烂与国运日新不已。
1941年12月,《说文月刊》出至第3卷第6期时,因上海沦陷而停刊,该刊编辑部随之南迁四川重庆,于1942年7月在重庆复刊,此为第3卷第7期。
《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为该刊“渝版第1号”,与第3卷第4期一样,题为“巴蜀文化专号”。
在本期中,卫聚贤的论文经过大量补充,仍以《巴蜀文化》为题发表。
该期还发表了自抗战以来云集四川的一些著名学者研究巴蜀文化的论文,如于右任、张继、吴敬恒、王献唐、商承祚、郑德坤、林名均、董作宾、朱希祖、缪凤林、徐中舒、傅振伦、郭沫若等。
作为该期篇首,于右任在《巴蜀文化之研究》一文中写道:
四川古为巴蜀之国,战国末年被秦所侵,期人民退居四面深山中,因其历史为曾传世,考古者亦多不注意于此。
而其古代文化,遂不闻于世。
其实古巴蜀自有巴蜀文化也。
历代出土铜器,有一种花纹文字与周异,而与殷亦不同,金石家将其年代向前推求,目为夏代物。
今其出土地在四川,则知其物非夏代,而为巴蜀人固有之文化也。
如能作一次科学之发掘,得事实之证明,则对于学术上之贡献,可胜言哉!
“巴蜀文化”的命题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十分热烈的争论,直接导致了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的最终确立。
二、抗战时期的巴蜀文化研究
在热烈的争辩中,学者们主要从巴、蜀的地域、族属、时代、青铜器、经济、城市、文字以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讨论,从而丰富了巴蜀文化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和外延。
(一)关于“巴蜀文化”
卫聚贤在1941年出版的《说文月刊》3卷4期上发表的《巴蜀文化》论文中,开篇即说:
四川在秦以前有两个大国――巴、蜀。
巴国的都城在重庆,蜀国的都城则在成都。
巴国的古史则有《山海经》、《华阳国志》的巴志所载,惟其国靠近楚秦,故《左传》上尚有段片的记载。
蜀国的古史,则有《尚书》、《蜀王本纪》(杨雄作,已亡,他著有引),《本蜀论》(来敏作,《水经注》引),及《华阳国志》的《蜀志》。
不过这些古史既不详细且多神话,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
去年四月余在重庆江北培善桥附近发现汉墓多座,曾加发掘,得有明器若干,由其墓的建造,砖上的花纹及文字,其他的俑钱剑等物看来,文化已是很高。
不过,这是汉代的汉人文化,与先秦的巴人无干。
再就重庆各地的蛮洞子——崖墓而论,固是蛮人的遗物,但是在汉代的汉人在四川也曾以崖墓为葬地。
是以巴人的文化,除书本子外,无。
去年八月余到汶川访石纽,闻有石器发现,路过成都参观华西大学博物馆,见有石器甚多,皆川、康境内出土,其形状除一种扇面形外,多与黄河流域同。
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之异。
陶器在川北,找到彩陶一二片,但块甚小,花纹也看不清。
在广汉太平场则有黑陶,但亦多系碎片,惟有一玉刀,形状特别,并有二尺以上的大石璧,其时代则在石铜之交,已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无他物为证而罢。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