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doc.docx
《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doc.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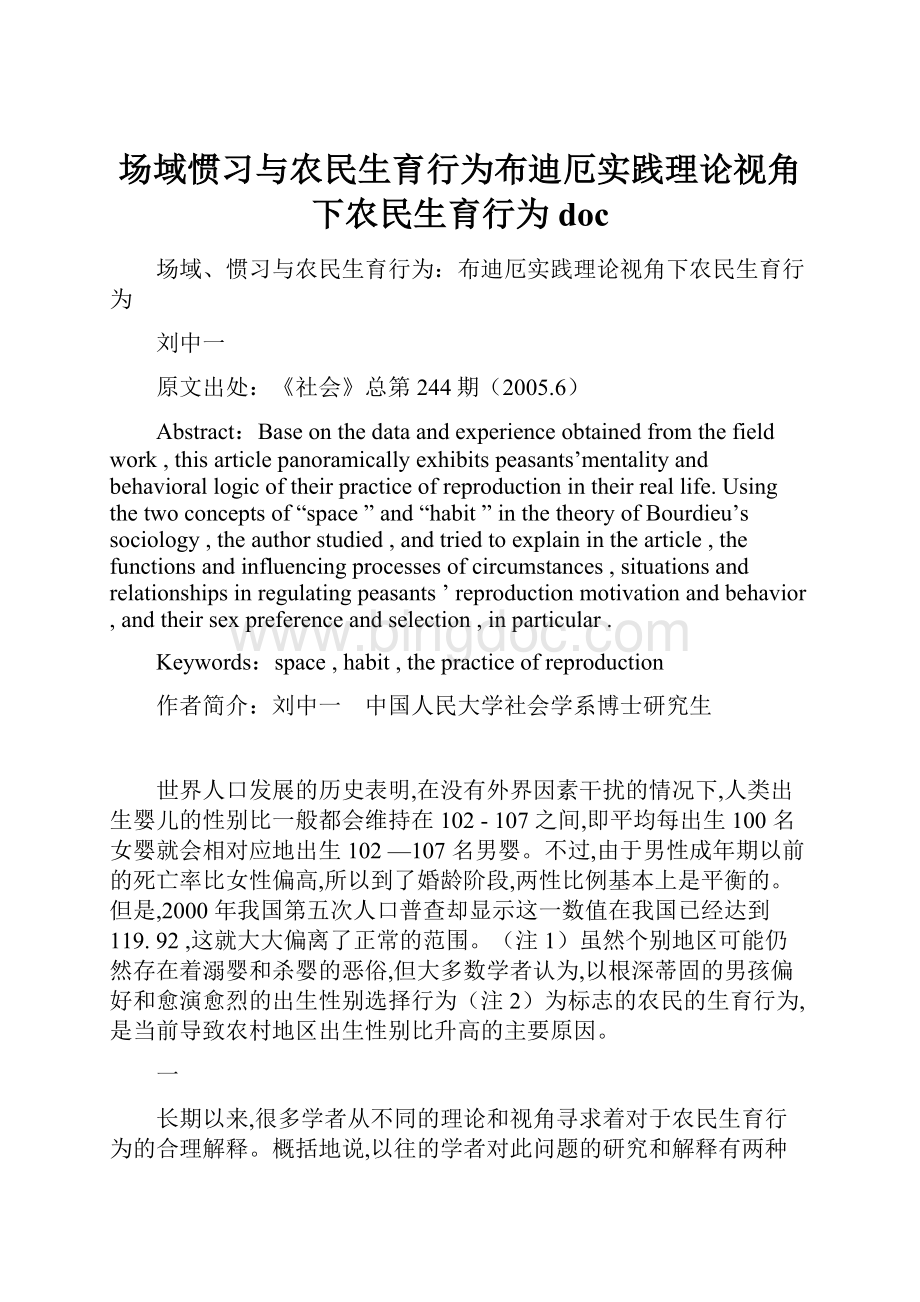
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doc
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农民生育行为
刘中一
原文出处:
《社会》总第244期(2005.6)
Abstract:
Baseonthedataandexperienceobtainedfromthefieldwork,thisarticlepanoramicallyexhibitspeasants’mentalityandbehaviorallogicoftheirpracticeofreproductionintheirreallife.Usingthetwoconceptsof“space”and“habit”inthetheoryofBourdieu’ssociology,theauthorstudied,andtriedtoexplaininthearticle,thefunctionsandinfluencingprocessesofcircumstances,situationsandrelationshipsinregulatingpeasants’reproductionmotivationandbehavior,andtheirsexpreferenceandselection,inparticular.
Keywords:
space,habit,thepracticeofreproduction
作者简介:
刘中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没有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人类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一般都会维持在102-107之间,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就会相对应地出生102—107名男婴。
不过,由于男性成年期以前的死亡率比女性偏高,所以到了婚龄阶段,两性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
但是,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却显示这一数值在我国已经达到119.92,这就大大偏离了正常的范围。
(注1)虽然个别地区可能仍然存在着溺婴和杀婴的恶俗,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以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和愈演愈烈的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注2)为标志的农民的生育行为,是当前导致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
一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寻求着对于农民生育行为的合理解释。
概括地说,以往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进路。
一种主要强调从行为者主体出发,认为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是行为者的“主动选择”。
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唐贵忠,1991;董辉,1992等)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基本假设,认为无论农民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出于对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虑或盘算的。
由此,他们认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更加偏爱男孩,那一定是因为养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进行了相同的投入,养育男孩比养育女孩能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
另外,也有少部分研究把这个问题化约到心理学层次,用从众行为来解释农民在男孩偏好或者出生性别选择行为上的趋同现象,认为农村社区相对于城市社区的要求人们一致的压力要大得多。
在出生婴儿的性别问题上,农村人口经受着比城市人口大得多的从众压力。
由此,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强烈的出生婴儿的性别偏好并且在出生性别选择的问题上具有更明显的倾向性。
另外一种进路则主张从社会结构(文化)出发,认为性别偏好是社会结构(文化)的“被动选择”。
其中一些研究者(参见李冬莉,2000;吕红平、孙平,2002等)认为,决定农民性别偏好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文化中生育伦理和生育价值观念。
因此,动辄就搬出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念文化来解释性别偏好现象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
此外,也有学者(李银河,1994;陆益龙,2002等)认为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问题。
他们指出只有将农民置于都市文化环境之中,也就是将他们置于一个新的可能性空间之中,使农民意识到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进而使农民不必再固守于传统的生育方式,才可能使农民真正地认同计划生育——其具体体现可以概括为“独生子女”——的国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别。
无可否认,这两种不同研究进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视角,并且对于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分析理解,以及对策研究都有着直接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种研究进路的不足之处,即这两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断裂的危险,它们要么偏重社会,要么偏重个人,而忽视了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的可能。
比如,单纯从行为者的角度出发的进路来解释这个问题,虽然可以部分地解释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的关系,但也不禁让人心存疑虑:
为什么我国农民对男孩的偏好由来已久,而出生婴儿性别比唯独近年来才开始出现明显升高的迹象呢?
单纯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进行的解释,认为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表现为出生性别选择行为的高发,由此造成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尽管有一些道理,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有效地回答社会结构(文化)在什么样的条件、情境、关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难以对诸如其强度、向度、中介物等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作出详尽的阐释。
由此,为了尽可能避免以上研究中存在的缺憾,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农民的生育行为,必须把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从具体的实际出发,详尽地考察具体情境当中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的作用原理和发生机制。
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只有直接进入到某个情境中去观察情境中发生的行动,才能真正了解人们作出行动的意义(邓金,2004)。
因此,要在情境现场的关系架构中探究事件发生的连续关系和意义,试图回答与文化情景脉络有关的问题,参与观察法的使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直接参与研究对象的活动,以参与观察者身份进入情境,并与研究对象发生互动关系,从而理解研究对象,对其行为意义进行解释。
另外,由于人类社会的许多面相都是镶嵌在人们的言语互动的过程和情景脉络之中的,因此,深度访谈作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调查研究手段,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深度访谈过程中,为了化解访谈的“隐私屏障”这一问题,在对象选择上,我们尽可能利用亲属网络法,通过亲戚朋友相互帮忙的方式寻找深度访谈对象。
(注3)之所以这么做,除了研究的可行性和便利性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在农民社区中作一些具有“隐私性质”的研究,访谈或调查对象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及所提供的一些其他的相关信息,能够最大程度上检验和补充调查或访谈得到的材料的真伪。
虽然,在这类调查或访谈中,调查或访谈的主要对象可能只是少数,但是从侧面验证和补充关于某访谈对象的相关信息和资料的渠道却有许多。
二
2005年2月至7月期间,我们在L村(注4)进行了三次间断性的田野工作,收集到了包括观察记录和访谈记录在内的大量的调查资料。
(注5)按照社会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惯例,在系统地分析和介绍调查资料之前,研究者应首先交代清楚调查地域的生态学特征。
我们田野工作的地点选择的是华北农村一个普通的自然村落——L村。
L村属于黄宗智等经典社会人类家笔下的那种典型的华北小农村庄,全村百余户,400余人。
拥有可耕土地1600余亩,但是大部分是大跃进时期开垦出的荒坡碱地。
虽然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中,L村村民人均收入已经突破了千元,但村民私下里却认为这个数字明显偏高,存在着为了“达标”而造假的成分。
(注6)L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状况十分不理想,到目前为止,村里还没有通公路,据说是其所在地区中唯一的一个。
一旦遇到接连下雨的日子,泥泞的道路就会使出入村庄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L村这几年进行出生性别选择的人家很多,基本上生育第二胎的时候都要去做B超,以确定是否进行出生性别选择。
用一个受访者的话说:
在L村,你只能认得(数得清)谁家的二胎没有做过(B超),却永远认不得(数不清)谁家的二胎做过(B超)。
在这样的氛围中,使得L村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着大量以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为线索的口述资料和符号系统。
我们通过对所有收集到的资料的细致划分,依据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这个叙事线索,按照事件或故事原本的发生时序,把众多个别的资料“组编”成一个个典型的故事或案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以下的叙述中,许多故事很大程度上都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合作发展的一种话语文本,都是由研究者和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而形成的片段的话语构成的。
我们之所以把大量相关访谈资料整理成一个个独立出现的故事,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再现一种可能的现实世界。
故事一:
罚款等于赡养费
近年来,L村等一些华北农村地区,二胎生育指标的限制远没有以前严格了。
只要第一个孩子的年龄达到一定的要求,或者有正规医院出具的、证明第一个孩子有生理缺陷的诊断书,是相对容易能够拿到二胎生育许可证的。
当然,交纳罚款是免不了的程序。
村内有一户寡居的老太太,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
老人每年要向三个儿子分别收取2000元的赡养费。
以前数年内,三个儿子也一直遵照这个惯例,倒也相安无事。
直到去年,最小的儿子忽然宣布他当年不缴纳赡养费了,理由是他要攒钱准备再生个儿子,“攒钱交纳超生罚款就等于每年按规定交纳了赡养费”。
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每年照常交纳赡养费,那么将大大地影响,甚至耽误他的生儿计划。
于是,从这一年开始,小儿子开始理所当然地不再向老人交纳赡养费。
其间,并没有任何人当面指责他这一荒谬的逻辑。
在这个故事中,引人深思的不仅仅是让当事人理直气壮地提出免交赡养费的理由,他声称生育儿子不仅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个人人生目的(通常所说的养老等),而是为了大家的整体利益(延续家族的香火)。
更引人深思的是整个家族包括老人以及小儿子的兄嫂们对此事的反应。
虽然有的嫂子私下里对此做法表示不满,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
至于那位老人,不仅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还高兴地到处声张说她将有第四个孙子了(她的两个大儿子已经给她生育了三个孙子)。
在她看来,这样一来,她在死后和其他的同辈群体相比就可能多了一个“戴孝帽者”;在她看来,这份荣耀足以让当事人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免交赡养费。
故事二:
是“谁”留下了小拉拉
小拉拉是L村一户人家的养子,小拉拉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
小拉拉今年8岁了,但生就一幅典型南方人的身材和面孔,身高也就五六岁孩子的样子,于是,在L村中,人们都习惯叫他小拉拉,至于他的真正名字却很少有人记起了。
谁也不好断定小拉拉一定是被犯罪分子拐骗来的,因为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据把小拉拉带来的那个女人讲,她是受人之托给孩子找条生路,小拉拉的父母在一场山洪灾难中都死了)。
我们在这里无须去探究那个女人是不是人贩子,反正全村人都知道那个女人临走的时候要了大概6000元钱,说是路费。
小拉拉来到L村的时候,L村的一户刘姓的人家收留了他,据说带小拉拉来的妇女是直接找到这户人家的。
当时这户人家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在当地属于比较典型的无儿户。
小拉拉被带来时,也正是这户刘姓人家最贫困的时候,当时支付给那个带小拉拉来的妇女的所谓的路费的钱,是刘家东拼西凑借来的或是同门近亲自愿捐献的。
当时,L村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刘家竟然连6000元钱都拿不出来,因为,很多差不多年纪的人家早已经给儿子盖起了房子。
那时候,关于刘家天生是“绝户命”、“命中没儿子的人”的议论开始在村里多起来。
也许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挣回自己的面子;也许确实从心底里真的想要有一个儿子,刘家最终还是“留”下了小拉拉。
故事三:
赵生的生育逻辑
赵生(注7)在我们访谈的前不久刚刚通过性别选择的方式“成功”生育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对他的访谈内容也主要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
当我们询问赵生进行性别选择的缘由时,他这样解释道:
自己所属的赵姓家族在L村属于一个较小的家族,本家族世代以种植业为生,至今尚未出过一位非农从业者。
所以,赵姓家族中的有些人,包括赵生本人在内都一直感到自己在村里地位地下,说话没有分量。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赵生认为改变这种处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的赵姓家族要多生男孩,直到赵姓的子孙在村里依靠绝对的数量占得优势,并认为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
在妻子经历了4次怀孕、4次B超以及3度选择人工流产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儿子。
在赵生看来,一个人要想在村里不受欺负,至多也就只有三个途径:
一是家族里多出能人,也就是说家族内要有尽可能多的人在外做官经商,做大官,发大财,有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姓氏家族在村里自然就有了影响力,别人也就自然不敢欺负你;二是在村里要有当村干部的,最起码要有民间的精英人物;三是本家族人口数量(尤其是男性的数量)的多少,人多势众,当然也就少受人欺负,甚至还可以对其他姓氏的家族形成威慑。
在三个途径中,第一个“当官发财”是可遇不可求的,要看“祖坟葬得正不正”;第二个其实和第三个是相关联的,即都与是否生儿子密切相关。
赵生说:
在村里当官,主要看“人脉”和“人气”,现在的村干部都是选举出来的,人多了自然就会票多。
如果不是大家户,兄弟哥们不多,就不要想当官(村干部)。
赵生还说:
像他以前那样子的人(意即没有儿子)就更不用想了,没有人会把你当回事,(因为)你没有年轻人(儿子)呀,一个人没有生儿子,那就是做人的失败。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儿子了),选上选不上(当村干部)是一回事,最起码你有资格做人(别人看得起),要不,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由此看来,按照赵生的逻辑,生男孩不仅是免受人欺,或者使人屈服自己的前提;而且生男孩还起到了一种“做人的资格”的“无形的证明书”的作用。
故事四:
模范丈夫逸事
这个故事其实发生在多年之前,但是至今在L村仍被当作夫妻恩爱的典范。
多年前,李生夫妇还是一对年轻夫妻的时候,他们之间表现恩爱的方式在当时村里是很少见的,“开放”程度令很多人羡慕不已,留下很多浪漫逸话。
但是一直令李生夫妇自身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膝下无子。
他们曾一口气连生了5个“赔钱货”(即指女孩)。
与村里的绝大多数丈夫们的表现不同,每次当他得知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孩时,总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亲自为妻子洗衣做饭。
这些举动对于一个平时连灶台都不会轻易去碰的农村男子来说,着实意义非凡。
转眼李妻第六次怀孕,与前几次一样,李生热切地盼望着第一个儿子的诞生。
妻子分娩的那天李生碰巧去平整田地了。
其实我们更愿意相信李生是有意识地躲开的,因为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使他几乎不再有勇气在第一时间内直接面对现实了。
不过,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李妻生了一个“带把儿的”。
于是,有人赶紧跑向田间……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李生并没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急急忙忙地赶回去照顾自己的妻子。
李生怎么啦,难道是犯了像范进中举一样的毛病不成?
于是有人忍不住再次提醒李生,李生憨憨一笑,这样解释:
当他没有儿子时,别人会对妻子另眼看待,为了不给妻子压力,他一定要摆出一幅生男生女无所谓的样子来。
而现在,他终于有了儿子,周围的人已经把妻子地位“抬”上去了,已经用不着他刻意地去做什么来“抬高”妻子的地位了。
以上所述的故事只是发生在L村的若干同类故事中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四个。
(注8)故事一从社会规则的张力的角度反映了农民生育行为中性别偏好的“强度”;故事二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生育行为中性别偏好的社会支持;故事三中主人公的生育心态和生育逻辑代表了长久以来一些农村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心理认同机制;故事四通过当事人在生育男孩前后的不同表现真实再现了传统生育观念对个人行为选择的影响力。
概括地说,这几个故事不仅再现了农民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选择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社会情境、社会关系中,对何种人的动机和行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将农民生育行为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问题展现了出来。
三
正如在上述的评述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对农民生育行为的理论解释中,以往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割裂开来的缺陷。
他们要么偏重社会,要么偏重个人,忽视了将行为者与社会结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因而大大降低了对农民生育行为的解释力。
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对实践的解释问题上,明确反对机械论的结构主义和目的论的个人主义,反对在结构与能动、系统与行动者、集合体与个人之间进行二者择一。
我们认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研究农民生育行为的理想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启示作用。
布迪厄认为实践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社会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和“逻辑”。
为此,他提出了“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两个概念,才能更好地揭示出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和“逻辑”。
尽管布迪厄没有专门地讨论农民的生育问题,他也没有提出“生育场域”和“生育惯习”之类概念,但是按照他的实践理论,我们认为提出这些概念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的。
在实践理论中,布迪厄将“场域”看作是一个网络,一个不断建构的结构。
进一步说,他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独特的圈层,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各自不同规则的游戏。
在他看来:
场域不是一个死的结构,不是空的场所,而是一个游戏空间,那些相信并追求其所能提供奖励的个体参加了这种游戏(布迪厄、华康德,1998)。
按照布迪厄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我们尝试提出了“生育场域”的概念。
在这里,“生育场域”同样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即它指代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而是一种分析和研究过程中的功能概念。
具体来说,“生育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当中的一系列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
不过,需要记住的是这些位置是相对于这个生育场域才存在的位置,是只有相对于参与到这个场域中的人才具有意义的位置。
具体而言,在“生育场域”当中,是否拥有儿子或者拥有儿子的数量是将不同的人置于各种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的地位上的关键。
在生育场域中,具有区分作用的位置既是客观存在着的,同时又是一种建构。
在一个性别偏好十分明显的生育场域中,有儿子的人占据一定的位置,而没有儿子的人则被排斥到另外一些位置。
在这里,有没有男孩或其数量的多少,不仅仅成了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往往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的体现。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回顾上面的故事。
在第三个故事中,在赵生看来,现在村干部都由选举产生,若像他以前那样,没有儿子的人连想都不用想了,因为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一个人没有生儿子,那就是做人的失败。
相反在有儿子后,选上选不上(当村干部)是一回事,最起码使他感到有资格做人(别人看得起),要不,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由此可见,按照赵生的逻辑,有没有男孩就成为了能够参与到村干部的选举中,成为候选人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在这里,“男孩”就成为组场的重要工具。
同理,在小拉拉的故事中,那个抱小拉拉来的女人何以能直接就找到那户人家,何以又断定那户人家肯定会留下这个孩子呢。
我们说,在农村人的心目中,每家至少要有一个男孩,如果没有,就可能被当作另类。
在这里,有没有男孩不仅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且成为一种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的标准。
如果你问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农村中的人他为什么要生育男孩,你得到的回答不是为什么要生育的理由,而是为什么不要生育的理由——比如没有男孩不行。
一般是不会直接得到生育男孩有什么好处的回答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男孩是一件生活必需品。
如果你有,那你就是正常的,如果你没有,那好一点就是“令人可怜”,坏一点则是“罪有应得”。
布迪厄还分析了场域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其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力的犬牙交错和游戏者的谋划策略,随时随地改变着场域的某些形态。
同时,场域也是权力关系的场所,是不断变化的、具有连贯性的、在冲突和竞争中产生的新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场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性格和自己的形态,具有自己全新的逻辑规则(同上,1998)。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我们形成了如下思路:
在农村社区中,乡村资本和权力(土地、房子、关系、政治权利、声望等)传统上往往是依据着儿子的多少进行某种分配。
这样,农民的出生性别选择行为,不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各种资本和权力进行争夺的方式或者说游戏的规则。
在自然出生状况的前提下,村落内人们都遵循着“一切由命运决定”的游戏规则。
原则上讲,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每个家庭因为生育(儿子)机会基本相等,那么占有这些资本和权力的机会也是基本上均等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当有一些人不遵守游戏规则,通过人为的出生性别选择以增加自己拥有儿子的机会,希望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游戏筹码的数量,以求资本和权力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的时候,乡村生育场域的原有形态就被破坏了。
于是,生育场域必然要重新经历一个对各种资本和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再次经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
通俗地说,在乡村生育场域的原有形态被破坏后,为了尽量多占有乡村资本和权力,“出生性别选择”这个游戏规则就会不断地得到强化、认同乃至内化,这样使进入这个“生育场域”中的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如何依据“出生性别选择”游戏规则去思考和行事,在各种力量的冲突和竞争中来为自己谋求最大可能的利益。
在赵生的故事中,赵生的那种希望通过出生性别选择,人为地扩张自己家族在村庄内的影响力——男性人口数量绝对增长,以最终实现村落内部的资本和权力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的想法,反映出的正是农民的那种生育逻辑:
大量地生育男孩,不仅可以大量地占有乡村资本和权力——改变原有生育场域的某些形态,甚至可以实现在村里不受人欺负,还可欺负别人的愿望——在一个敞开的游戏空间占据有利位置。
在罚款的故事中,那个寡居的老人之所以非常自豪,也正是因为她认为如果她小儿子能够给她生育一个孙子,那么她将比其他人又多出一个“戴孝帽者”,这在一个把“身后事”看得比较重的农村老人眼里,就是一个通过增加自己的游戏筹码的数量,以求资本和权力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的难得的机会,就是一个可以改变原有的不利于自己或者将来的更利于自己的生育场域的机会。
另外,我们知道不交赡养费用,在乡村本来是一件影响很坏的不孝事件。
那么为什么不仅当事人自己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反而可以明正言顺地提出来?
为什么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都对这件事相当一致地保持默许或者说不反对呢?
仔细分析的话,对此可以作出这样一种解释,那就是生育场域在各种资本和权力的冲突和竞争中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和形态”,产生了一个“新领域”,从而具有一些全新的逻辑——生育行为不是为了当事人自己,而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
如果说“场域”的概念着重描述的是农民生育行为的客观性结构的话,那么“惯习”的概念则是偏重于强调行动者自身方面。
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看作一种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即身处场域之中并被游戏规则内化的人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或曰是游戏规则内化的行动,是身处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知道自己如何遵循规则和艺术地变通游戏规则,以达到角色扮演。
布迪厄认为,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
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同上,1998)。
对于恩爱夫妻的典范的故事,笔者开始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李生夫妇在很多问题上都能“特立独行”,都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他们敢于向乡村世俗挑战的“开放”思想和行为。
但是,为什么唯独在男孩偏好这件事情上表现出那种强烈的保守倾向呢?
后来,我们终于明白在农村那种以“有没有儿子”作为判断一个家庭正常不正常、完整不完整的标准的生育场域中。
“尽一切的可能生养一个儿子”就成为了一整套不断地被灌输的性情倾向。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