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埔族音乐纪实系列之6巴宰族Ayan之歌.docx
《平埔族音乐纪实系列之6巴宰族Ayan之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平埔族音乐纪实系列之6巴宰族Ayan之歌.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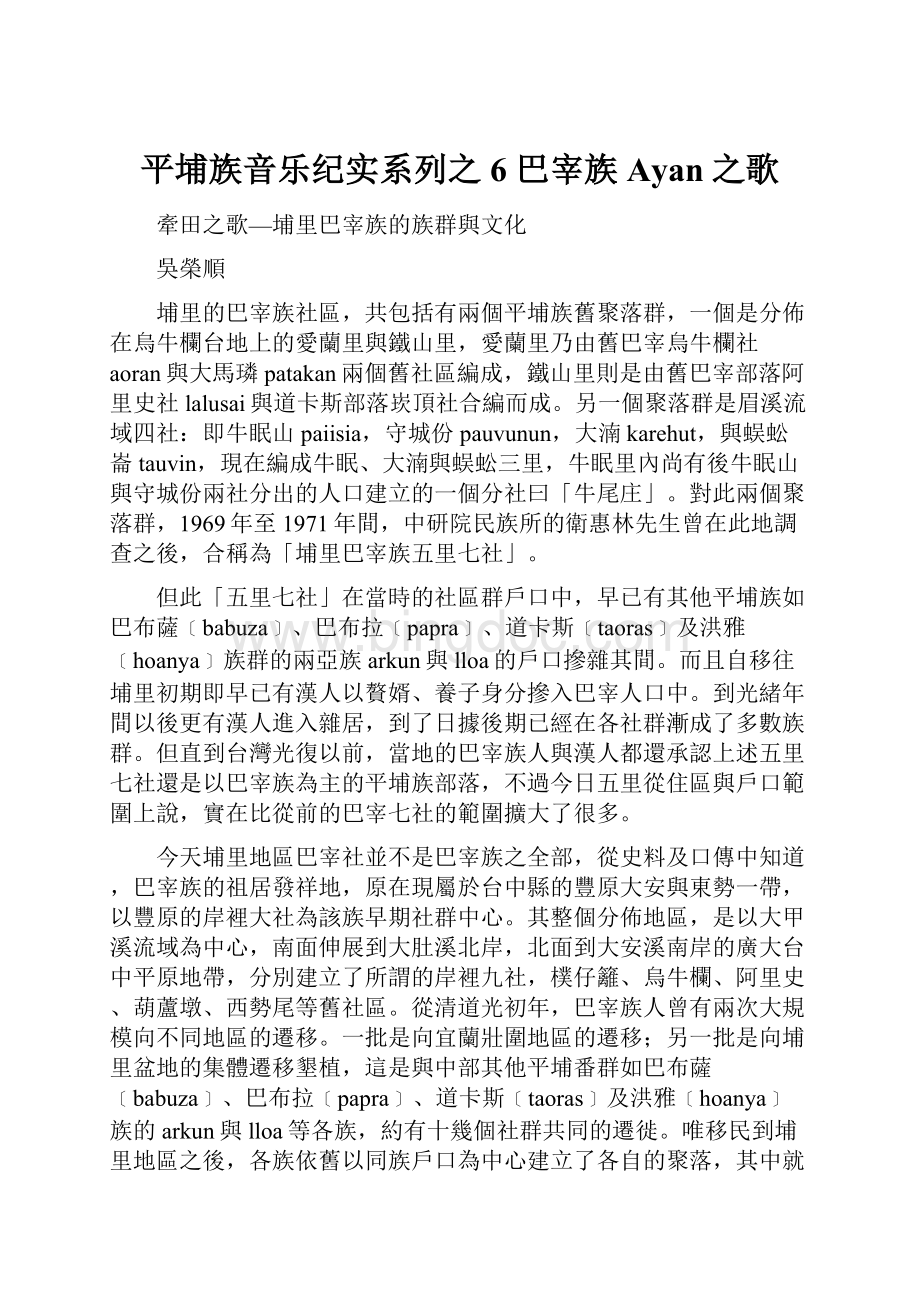
平埔族音乐纪实系列之6巴宰族Ayan之歌
牽田之歌—埔里巴宰族的族群與文化
吳榮順
埔里的巴宰族社區,共包括有兩個平埔族舊聚落群,一個是分佈在烏牛欄台地上的愛蘭里與鐵山里,愛蘭里乃由舊巴宰烏牛欄社aoran與大馬璘patakan兩個舊社區編成,鐵山里則是由舊巴宰部落阿里史社lalusai與道卡斯部落崁頂社合編而成。
另一個聚落群是眉溪流域四社:
即牛眠山paiisia,守城份pauvunun,大湳karehut,與蜈蚣崙tauvin,現在編成牛眠、大湳與蜈蚣三里,牛眠里內尚有後牛眠山與守城份兩社分出的人口建立的一個分社曰「牛尾庄」。
對此兩個聚落群,1969年至1971年間,中研院民族所的衛惠林先生曾在此地調查之後,合稱為「埔里巴宰族五里七社」。
但此「五里七社」在當時的社區群戶口中,早已有其他平埔族如巴布薩﹝babuza﹞、巴布拉﹝papra﹞、道卡斯﹝taoras﹞及洪雅﹝hoanya﹞族群的兩亞族arkun與lloa的戶口摻雜其間。
而且自移往埔里初期即早已有漢人以贅婿、養子身分摻入巴宰人口中。
到光緒年間以後更有漢人進入雜居,到了日據後期已經在各社群漸成了多數族群。
但直到台灣光復以前,當地的巴宰族人與漢人都還承認上述五里七社還是以巴宰族為主的平埔族部落,不過今日五里從住區與戶口範圍上說,實在比從前的巴宰七社的範圍擴大了很多。
今天埔里地區巴宰社並不是巴宰族之全部,從史料及口傳中知道,巴宰族的祖居發祥地,原在現屬於台中縣的豐原大安與東勢一帶,以豐原的岸裡大社為該族早期社群中心。
其整個分佈地區,是以大甲溪流域為中心,南面伸展到大肚溪北岸,北面到大安溪南岸的廣大台中平原地帶,分別建立了所謂的岸裡九社,樸仔籬、烏牛欄、阿里史、葫蘆墩、西勢尾等舊社區。
從清道光初年,巴宰族人曾有兩次大規模向不同地區的遷移。
一批是向宜蘭壯圍地區的遷移;另一批是向埔里盆地的集體遷移墾植,這是與中部其他平埔番群如巴布薩﹝babuza﹞、巴布拉﹝papra﹞、道卡斯﹝taoras﹞及洪雅﹝hoanya﹞族的arkun與lloa等各族,約有十幾個社群共同的遷徙。
唯移民到埔里地區之後,各族依舊以同族戶口為中心建立了各自的聚落,其中就以巴宰七社的部落人口保持同源性質最強,因此到目前為止,還有部份的巴宰族人還能保持其語言、音樂等部份傳統,所以今日埔里的巴宰七社可以被認為是巴宰社會最具代表性的聚落群。
烏牛欄聚落群與眉溪四庄社聚落群的族人自己也分成pazeh與kaxabu兩大語言系統。
Pazeh語群的三個聚落就分布在烏牛欄台地上,kaxabu則與烏牛欄台地三個巴宰部落由埔里市街南北隔開,而分布在埔里盆地東北的眉溪南北西岸。
(1)烏牛欄聚落,舊稱rudelaorang。
原為豐原地區的舊社名,在清光緒三年就在台地中央建社,而成為rudelaorang。
(2)大馬璘聚落,舊稱rudelpatakan。
約道光五年(1825年)左右,由東是舊部落遷移到現在愛蘭國小向南延伸,其西邊到梅村路一帶。
(3)阿里史部聚落,舊稱rudellalusai。
該聚落是約在道光初年由好幾個同時由中部遷移來的平埔族群,而以巴宰族人為最多而建的聚落。
其聚落在烏牛欄上的東北,而與鄰近的道卡斯族崁頂聚落,在日據時代併為一社。
(4)牛眠山聚落,舊稱rudelpaiisia。
牛眠山聚落的分布位置在眉溪四庄中的最西端,但過去卻是四庄當中最強的一個聚落。
(5)守城份聚落,舊稱rudelpauvungung。
聚落在守城大圳堤道以北,牛眠山的東北。
(6)大湳庄聚落,舊稱rudelkarehut。
大湳庄位於眉溪南岸靠近埔里街道上,是巴宰聚落當中最早與漢人接觸的聚落。
(7)蜈蚣崙聚落,舊稱tudeltauving。
其位置是在四庄中的最東端,最為孤立,過去直接與眉溪對岸的眉原社泰雅族人相對,現今的埔里榮民醫院之地即為舊址。
南投縣埔里盆地位於台灣的地理中心,是一個被崎嶇山脈所包圍的陷落盆地,盆地總面積為120平方公里,四周被關山刀、守城大山、觀音山、西塔山、白葉山等山脈所包圍。
盆地中,北有眉溪從霧社方向流經切割,向西流至水尾、觀音山附近,與從日月潭東北方丘陵流經盆地南邊的南港溪匯流,至國姓鄉後,再匯入北港溪成為烏溪,而向西奔流出海。
因此埔里盆地自古即為台灣東、西方民族間交通的孔道。
埔里盆地昔日原本是個大湖,之後因淤積與眉溪、南港溪的切割於決涸,證諸至今發現的大馬璘、石墩坑、水蛙窟等處遺址,以及虎仔山被挖出的石棺群,可以證明往昔埔里盆地的確是一個大湖,而這些遺址的先住民們乃傍水而居,因此這些現今發現的遺址大都在盆地邊緣海拔稍高處。
另外在各處遺址內亦發現東部玉石磨製的玉器,可見在數千年前的先史時代,埔里這條東西交通孔道上,台灣東、西方民族間的交易已是非常興盛了。
平埔族群入墾埔里的契機,乃是由於埔社族人因「郭百年事件」導致人丁稀薄,無力抵禦外族入侵,恰巧洪雅族北投社族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邵族人於山中打獵相遇,得知埔社族人的困境,在一邊是急需人力抵禦敵對外族;一邊是飽受漢人欺凌,另覓新天地安居,於是透過與埔社族人關係親密的邵族人居中撮合,始得進入埔里盆地開闢新家園,而位於今草屯鎮的洪雅族北投社因地利之便,不僅是入埔的開路先鋒,更是後來大舉入墾的主要勢力!
清政府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成立的番屯制度,使台灣中部的平埔各族群之間有了密切的交流和聯繫。
當在西部的平埔族群備受漢人欺壓,日感生活困頓之時,聞知埔里地廣人稀,漢人悉遭政府驅逐出山,並且原住埔社族人亦歡迎入墾時,北至苗栗通宵、南至雲林斗六廣大區域內的平埔五大族群,包括道卡斯、巴宰、巴布拉、貓霧拺、洪雅諸族,即透過屯墾制的聯繫,組織成大規模的集體移墾行動!
從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及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清朝文獻的統計,平埔族於道光三年最初入墾埔里之後,二十餘年間,平埔族移入的人口大約有二、三千人;並且移入的腳步一直持續到同治年間,受「載萬生亂」的影響,仍有萬斗六(貓羅)、岸裡、北投等諸社族人遷入。
而埔社族人的人口數,據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親屢埔里盆地的閩浙總督劉韻珂調查,只有二十七人,而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鳥居龍藏至埔里調查時,埔社人口數,更是僅存五人!
至此平埔族已取代埔社族人,成為埔里盆地的主人,埔社族人引平埔族群入埔以求得永居埔里的努力徹底失敗。
平埔族群入墾埔里的埔社族人失去了埔里盆地南半部主人的地位,而盆地北半邊的原住主人眉社族人,雖在平埔族入墾之初,即藉口「社仔社」因招墾而亡,拒絕了平埔族群進入其領地開墾,但平埔族群仍不斷侵墾眉社族人的領地。
發生於道光二十七年春天,平埔族人徐憨棋率眾私墾眉社土地事件,猶如「郭百年事件」的翻版,在無力抵禦大量入墾的平埔族移民之下,只得在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與平埔族人簽下「眉社之收番租清款甘願手摹完結字據」等招墾契約後,無奈地交出北埔里盆地世代居住之領地!
至此平埔族可說完全成為埔里盆地的新主人了!
牽田與阿湮
劉還月
牽田是平埔人傳統祭體中,最特別而隆重的大典,巴則海族(編按:
即巴宰族)人、道卡斯族人、巴布拉族人、和安雅族人、貓霧拺族人都有相類的習俗。
埔里盆地中,以巴則海族人的牽田儀式最盛大而完整,著名的祭歌「阿湮」,最為哀怨悲涼,動人心弦。
如今,也已走入歷史長廊中的巴則海族牽田,每年都從十一月開始進行九天,前面三天是準備期,部落土官、頭目召集耆老、宗長們開會,分配每天的任務,並指派祭司。
婦女們得忙著釀酒,製作各種糕點,壯丁們得整理好獵槍和魚具……。
十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是「捕大魚」之期,青年及壯年男子都必須參加,一齊到眉溪或南烘溪中捕魚,看誰抓得最多,他的魚簍將可高掛在集會所前,驕傲地炫耀著主人的名字,直到祭典全部結束。
「抓大魚」所抓的魚,其實都只是些一、二兩指大的小魚,這般大小的魚放在石頭上曬一、兩天便成乾,才趕得及在牽田時祭祖之用。
農曆十一月十四日夜,正式展開夜祭和牽田。
黃昏時分,家家戶戶都用竹籩裝著魚乾、鹿肉乾、糯米糕、酒…等祭品,送到集會所前,和部落準備公祭的牛或豬擺在一起;晚飯之後,月亮緩緩升起,族長才率領長老和族人們,慎重其事地祭拜每個時代不同的開拓先組,包括:
神話中渡海來台的先人、舊社的開基立業之祖及遷移來埔的祖先。
完後由各親族族長負責分祭各家族的宗祖,這時子弟們分成幾堆,圍在祭品四周,交互地牽著手,跟隨著祭司的舞步,唱起「阿湮」祭歌。
十五日早上,要舉行「走鏢」,這是年輕一代最熱衷的節目,一大清早便聚集在集會所前,由頭目下令,依照規定的路線賽跑,取優勝的前五名,由各社土官頒給錦旗或賞以色布,從此變成了部落中的「好漢」,不僅容易獲得少女的青睞,也可以贏得各階層人士的尊敬,更是往後取得長老地位的重要踏腳石。
十一月十八日,巴則海族人以集體授獵的方式,為新年的活動劃下休止符。
男人們所組成的狩獵隊伍,一大清早便出動了,經驗豐富的老獵人在前開路引道,各年齡階層的好漢和壯丁們亦步亦趨地跟隨在後,學習著前人的智慧與勇氣。
四社庄的歌謠與語言
李壬癸
巴宰族(pazeh)是台灣南島民族之一。
他們的原始社群中心在現在的豐原附近,以大甲溪左右為中心,地理分佈頗廣,在日治時代尚有九社。
可惜在原居地已經沒有族人能說自己的母語,也不會唱傳統的歌謠了。
清朝道光五年(1825),部分巴宰族人遷移到埔里盆地,幸而他們至今還保存一些母語文化,包括傳統歌謠。
現存的兩種方言都可以在埔里採集得到:
一稱pazeh,主要在愛蘭,另一稱kaxabu,在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崙等四庄。
本專輯所收錄的傳統歌謠,主要是在四庄採錄的。
巴宰族歌謠的採集
1988年元月,埔里的鄧相揚先生親自帶我到牛眠山去請潘林阿雙女士(時年88歲)唱傳統歌謠,包括一首ayan,歌詞是母語,兩首閩南語歌謠,七字一句,卻都是平埔調,也都是傳統的巴宰曲調。
幾天後,林清財先生從台北趕到埔里,我們就一起到守城份採集他們的傳統歌謠,包括兩首ayan都是潘郡乃先生(時年82歲)作的詞,一首搖籃歌,一首飲酒歌,以上都是kaxabu母語,另外三首閩南語歌謠:
情歌(阿娘阿君)、工廠歌、長工歌,前兩首用平埔曲調,而最後一首就是漢人曲調了。
以上都是由潘秀梅女士主唱(幾年前才過世),潘英嬌女士和潘永歷先生一起合唱,而當時潘郡乃先生仍然健在。
我和林清財先生一起採集的守城份歌謠就是兩年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發表的「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李壬癸、林清財1990)。
今年(1998)七月,吳榮順博士再到四庄採集傳統歌謠。
守城份的由潘英嬌女士(潘郡乃之長女)及潘永歷先生(潘郡乃之長男)合唱,曲調和歌詞內容都和十年前我們所採錄的大同小異,不過卻多了兩首聖詩。
聖詩當中,一首是採用過去大社部落巴宰族人的傳統歌謠曲調,配上台語歌詞,然後再由駱維道博士配上四部和聲;另一首聖歌來源更曲折,歌詞原來是以一首海頓所作的歌曲配上台語聖詩,守城份的族人便採用這首聖歌詞,配上ayan曲調來演唱。
牛眠山的也是由潘林阿雙女士(現年98歲)唱ayan和兩首歌謠(閩南語歌詞)。
我核對十年前所錄的ayan歌詞,內容大致相同,但歌詞稍微有點改變。
其實,今年九月我再去請她唱一、二遍,每次她唱的歌詞都會有一點點改變。
為了對照的方便,我們就依吳博士所錄的版本記下歌詞。
從歌詞和曲調看來,巴宰族四庄的傳統歌謠可以分為以下這三大類:
第一、根源歌曲ayan、搖籃歌、飲酒歌,詞、曲都是巴宰族的,歌詞卻都是當代的人所作的,因詞沒有什麼艱深難懂的地方。
隨著唱者的母語能力,歌詞也可能稍作改變。
其中當以ayan的曲調最為典雅古老,歌詞的內容涉及族群來源的傳說。
搖籃歌和飲酒歌都反應傳統巴宰族的狩獵和農耕生活。
第二、情歌、工廠歌等都是巴宰族曲調,都是七個音節一句,有時加插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虛詞。
第三、長工歌的曲調和歌詞都是漢人的。
巴宰族歌謠的形式和特徵
巴宰族歌謠文獻記載最早可見的是清代黃叔王敬著《台海使槎錄》中的番歌。
有樂譜記載的是台語聖詩中收錄的二首歌謠和呂炳川(1982)發表的「巴宰族開國之歌」。
根據呂炳川先生的說法,巴宰族的歌謠完全以這種曲調來唱不同的歌詞,可形成不同的歌,如「讚揚祖先之歌」、「開國之歌」、「迎新年之歌」……,基本上是五聲音階(呂1982:
111)。
呂先生是否也蒐集了不同歌謠,因其人已去世,又未見發表,也就不得而知了。
從作者採錄的歌謠來看,巴宰人使用五聲音階的看法是很可靠的,但若說其歌謠都是由同一旋律配上不同歌詞而成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請看ayan的曲譜變化,乍聽之下都是以「ayan」當開頭,旋律動機也很相近,但是發展下去卻是截然不同的兩首歌謠。
從文獻上我們雖然不曉得巴宰人的音樂特徵,但若就我們採錄的歌謠中,有以下幾點特徵是值得注意的:
1.使用無半音五聲音階為主。
但也有使用三聲音階的,如搖籃曲只用了re、mi、la三個音。
2.歌謠包含有搖籃歌、長工歌、苦命歌、思親曲、相褒歌、四季春,也有慶典儀式的歌曲(ayan)。
尤其以舉行儀式(牽田)所唱的歌,又包含了祖先起源的口述歷史,值得民俗學者的注意。
3.轉調的運用。
如ayan
(1)由第一段re起音的商調式轉到sol起音宮調式,尾聲再回到re起音的商調式,非常巧妙。
4.以一個旋律填入多遍歌詞的用法,類似中國音樂上的「鼓子詞」用法,也就是西方音樂所謂的有節形式歌曲(strophicform)。
5.音樂形式的運用包括有一段體(搖籃歌)和二段體(ayan)。
6.融入漢人音樂的思想。
如長工歌,雖是用巴宰族傳統旋律,卻用閩南語填詞,且用台灣民謠七字仔方式填入。
所有閩南語來演唱的歌謠是以七個字為一句,四句為一段,也就是如台灣民間藝人所稱的「一葩」。
7.接受漢人音樂。
如長工歌已經是完整的漢人歌謠。
8.受到西方音樂的影響,尤以教會的影響力最大。
巴宰傳統旋律配以四聲部合唱;ayan
(2)是慶祝福音來台130週年而做的。
9.其歌詞反應了不同時代的生活情況。
如搖籃歌至少是描述十九世紀以前巴宰人的狩獵生活。
ayan
(1)傳說歷史的年代可能更早。
長工歌、苦命歌、思親曲、相褒歌、四季春,可能反應最近十年的生活情況。
ayan
(2)則已將傳統信仰方式「牽田」祭儀融入基督教的信仰世界裡,這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而已。
巴宰族歌謠的書寫
本節列舉作者採錄的各種巴宰族歌謠。
值得注意的是,歌詞唱出來和唸出來有時會有出入:
有時唱的時候會拉長會重覆某些音(特別是元音,半元音y,w一拉長就分別變成元音i,u);有時唱時會插入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虛詞(在本文中都加上小括弧()以示區別);偶而也會唱錯歌詞(尤其是唱者的巴宰語能力欠佳)。
因此,在本文唱和唸的歌詞就以略為不同的形式出現,我們儘可能存真以資比較研究。
《參考書目》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公報社編1966《聖詩》
伊能嘉矩1908《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72:
39-48。
李壬癸、林清財1900(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3:
1-16。
佐藤文一1931(台灣府志見熟蕃歌謠),《民族學研究》2
(2):
82-136。
1934(大社庄的歌謠),《南方土俗》3
(1):
114-126。
呂炳川1982《台灣土著族音樂》。
台北:
百科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音樂采風傳真
吳榮順
巴宰音樂史的回顧
關於巴宰族的音樂最早的文獻記錄是清代黃叔璥《台海使槎錄》中的番歌歌詞。
日據時代則有伊能嘉矩(1908)、小川尚義先後記錄過巴宰族的ayan祭歌歌詞。
小川尚義研究室也曾收藏了「開基之歌」、「大水氾濫之歌」、「氾濫後人民分居之歌」等三首歌,後來由佐藤文一(1934)整理了原文、注解、大意,在《南方土俗》中發表。
從清代到台灣光復初期,所有關於巴宰族音樂的文獻,都只是記錄了歌詞及歌名,歌譜均付之闕如,從民族音樂研究的角度來說,是相當遺憾的。
因為沒有譜的記錄,我們無法真正瞭解過去巴宰族人在音樂本身進行的模式與風格。
目前在南投埔里的愛蘭巴宰族人,也正以當年佐藤記錄下的三首歌,努力的恢復巴宰音樂的原貌。
台灣光復後民族音樂學家呂炳川先生也曾在埔里愛蘭地區採錄巴宰族的民歌,並且參加了愛蘭教會一年一度的「慕親大會」,親眼看到了巴宰族人升起火堆、敲鑼助興、演唱ayan的情景。
他在1982年《台灣土著族音樂》中就收錄了1首「巴則海族開國之歌」的ayan。
雖然他只記下一段譜例及開頭的第一句歌詞,但卻是在文獻資料上首次聽見了巴宰族的歌謠。
之後,在1990年李壬癸教授及林清財老師在埔里的守城份錄下了7首屬於巴宰族kaxabu群的歌謠,並且發表了一篇「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論文在《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上(1990:
(3):
1-16)。
這7首歌都是潘秀梅女士所唱,曲目是:
祭祖歌(ayan)兩首、搖籃歌、飲酒歌、情歌、工廠歌及長工歌。
這也是首次由語言學者及民族音學者的合作研究,對於巴宰族音樂語言的瞭解,也提供了一個較完整的資料。
1991年水晶唱片公司也為潘秀梅女士錄下了4首歌謠(ayan、長工歌、工廠歌、飲酒歌),收錄在《來自台灣底層的聲音》唱片中。
四庄的音樂記錄
今年(1998)七月,在「平埔族音樂紀實系列」的保存研究計劃之下,我們來到埔里地區進行巴宰音樂的採錄工作,雖然來此的時間已嫌太晚,而且文獻上記錄下的歌謠有限,我們仍然抱持著樂觀的想法。
來到埔里之後,在最熱心當地文史研究的黃炫星老師協助下,我們從巴宰四庄kaxabu群開始,展開地毯式的查訪。
首先拜訪了住在埔里的潘秀梅女士的女兒及女婿,但潘秀梅女士已在去年9月間去世,第一個希望落空了。
接著來到守城份,拜訪潘英嬌及潘永歷姊弟,他倆的父親潘郡乃先生已於1990年去世。
但潘郡乃在世時,曾寫下兩首ayan祭祖歌的歌詞,潘秀梅所唱的ayan也就是潘郡乃先生所寫的歌詞,然後再由潘郡乃先生教唱的。
很慶幸的是姊弟倆使命感很強,雖然也都60多歲了,仍忠實的保存及承襲了父親傳下來的歌,因此我們錄下了8首現階段四庄地區的巴宰族民歌,分別是:
(1)ayan根源(過年時所唱紀念祖先Abuk之歌)
(2)ayan根源(慶祝福音來台一百三十周年)
(3)搖籃歌
(4)長工歌(十二月令歌)
(5)苦命歌(同十二月令歌曲調)
(6)思親曲(同十二月令歌曲調)
(7)聖詩—真主上帝造天地
(8)聖詩—在我救主榮光面前
前面兩首ayan都是父親潘郡乃所創作,只是第二首原來潘郡乃是以慶祝福音來台一百周年為題,其長子潘永歷在一百三十周年紀念時,將一百改成一百三十,其餘歌詞並未修改。
接著我們又走訪了牛眠山98歲的潘林阿雙女士,在黃老師的帶領下,我們才知道埔里地區還有一位對巴宰音樂身藏不露的巴宰耆老。
她為我們演唱了兩首歌謠,一首是ayan,另一首是以閩南語來演唱的「相褒歌」。
不可思議的是,她依然聲如宏鐘、記憶力驚人,兩首近20分鐘的歌謠,除了因年事已高,高音的支持度不夠,而造成曲調的音高常有習慣性的偏低現象外,演唱的歌詞卻句句清晰毫不含糊。
她所演唱的巴宰民歌,ayan是學自她的母親,「相褒歌」卻學自年輕時在一起工作的姊妹淘們應答對唱的歌謠。
然後,我們到了蜈蚣崙,在不斷的探詢下,我們找到了潘秋香(70歲)及潘阿水(82歲)兩位女士。
她倆都是巴宰後裔,曾跟已過世多年的蜈蚣崙長老潘阿敦學過ayan,但尚未完全學會他就過世了,因此我們採錄到她倆所唱的ayan,並不是很完整的一首歌,但我們仍將蜈蚣崙聚落的ayan唱法保留下來。
此外,潘秋香還演唱了一首以閩南語來唱的「四季春」,當地族人也稱之為「五空小仔」,或「姓潘的歌」。
基本上,它是一首漢民族的七字一句,四句一段的即興歌謠,傳到埔里地區之後,巴宰族人已將之「巴宰化」。
至於大湳,因無法找到還能演唱完整巴宰民歌的歌者,因此我們並沒有採錄到該聚落的歌謠。
此次埔里地區巴宰族歌謠的採集,我們分別在四庄及愛蘭兩地進行。
四庄kaxabu群共收錄了13首歌謠,全部都納入本專輯當中。
我們也邀請語言學家李壬癸教授一同參與我們的保存計劃,請他協助我們處理巴宰歌詞及音樂語言上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請到對民間文學頗有研究的顏美娟博士,為我們處理閩南語歌詞的採擷。
至於愛蘭地區的採錄工作,仍在進行當中,等完成記錄之後,將再進行「平埔族音樂紀實系列出版」的補遺工作。
四庄巴宰族的音樂現象
本專輯所收錄的13首埔里四庄巴宰族民歌,可以區分成四種類型的歌謠:
(1)屬於傳統祭典上的歌謠:
ayan
這種歌謠共有五首,守城份潘英嬌及潘永歷所唱的ayan,以及牛眠山潘林阿雙所唱的ayan,已經相當完整的保存了傳統的ayan演唱風格,即使與1982年呂炳川在愛蘭地區所採錄的ayan來比較,也相差無幾。
換言之,ayan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呈現相當穩定的歌謠曲調輪廓,變的地方只在於每個演唱者的詮釋風格的不同,以及因演唱時主題不同,而改變歌詞而已。
可見在埔里地區,ayan在巴宰族人心中,不但是一首傳統聚會當中都要被演唱的歌曲,也應該是巴宰族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首歌謠。
至於蜈蚣崙所演唱的ayan,只保留了ayan開頭的片段音樂動機。
過去ayan是在過年祭祖時才演唱,也就是每年的農曆11月15日。
當時演唱ayan的情景,根據目前在四庄年長的巴宰族人描述,與呂炳川所記述的一模一樣:
「舞蹈時,則作成圓形,一面緩慢向右回轉一面唱歌,在正中央燒火並敲打銅鑼….。
」(1982:
111)
ayan的歌曲形式,已經發展出小三段(A+B+A)的形式。
開頭有一段引子段落來當前導(A段),然後進入到曲調不斷反覆,歌詞卻不斷更新主題的有節形式(strophicform)段落(B段),最後又重覆開頭的第一句歌詞及樂段,當做這首歌謠的尾聲(A段)。
曲調很明顯的以五聲音階為旋律素材。
從ayan使用的歌詞來看,對於族人而言,它等同一首「鼓子詞」一樣,曲調不段的反覆,歌詞卻隨時可以依主題的不同加以即興變更。
所以才有「開基之歌」、「大水氾濫之歌」、「氾濫後人民分居之歌」、「巴則海族開國之歌」等等不同主題的ayan。
(2)教會聖詩上的巴宰歌謠:
真主上帝造天地、在我救主榮光面前
目前在埔里地區的巴宰族人,幾乎都以基督長老教會為信仰中心,教會演唱的聖詩都以閩南語發音的「台語聖詩」為主。
本專輯當中就收錄了兩首聖詩,曲調都是巴宰族人傳統的民歌調。
「真主上帝造天地」是當時流傳在大社部落的巴宰曲調。
在1964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音樂委員會編輯、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的「聖詩」第63首當中,就收錄下這首歌謠曲調。
原曲調是la起音的羽調式五聲音階歌謠(la、do、re、mi、sol),曲式是西方音樂標準的小二段體形式(ab+cb)。
雖然聖詩上載明是大社庄巴宰平埔族曲調,但從曲調的結構法則(標準平整的小二段形式)與旋律進行語法(工整對稱的旋律法)來看,似乎又說明了是否荷蘭人或西方傳教士來到台灣後,早已將原巴宰歌謠徹底西化了,再收錄到聖詩中。
「在我救主榮光面前」,歌詞原來是「聖詩」第444A首的「在我救主榮光面前」歌詞,然後再配上ayan的旋律型曲調。
(3)傳統童謠:
搖籃歌
用巴宰語言及巴宰曲調來演唱的歌謠,在現階段仍保存巴宰民歌的埔里四庄來說,除了ayan之外,就只有這首搖籃歌。
搖籃歌歌詞完全是巴宰語言,語意並不是漢人系統的思維法則,相當程度反應了原巴宰文化的獨特性。
曲調是re、mi、la形成的三音音階,旋律法若不配上巴宰語演唱,日本東洋童謠的旋律型模式馬上出現。
筆者不敢妄下斷語,尚待釐清疑惑。
(4)以閩南語演唱的歌謠:
長工歌、苦命歌、思親曲、相褒歌、四季春
巴宰族人在強勢的漢文化撞擊下,從台中北豐原一帶的原居地遷徙復遷徙,仍然無法逃過被當時閩南文化涵化的命運,我們從族人仍保存的歌謠數量來看,就知道以閩南語來演唱的歌謠數量多過比自己母語(kaxabu)來演唱的民歌。
這些以閩南語言來演唱的歌謠,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是:
[1]歌詞一定「七字一句、四句成段、句尾押同韻」的排列組合模式,也就是台灣民間音樂稱之為「一葩」的習慣,這是典型的其中一種漢文化歌謠模式。
[2]四句成段構成一個音樂旋律型,此後此旋律不斷的反覆,歌詞則不斷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