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docx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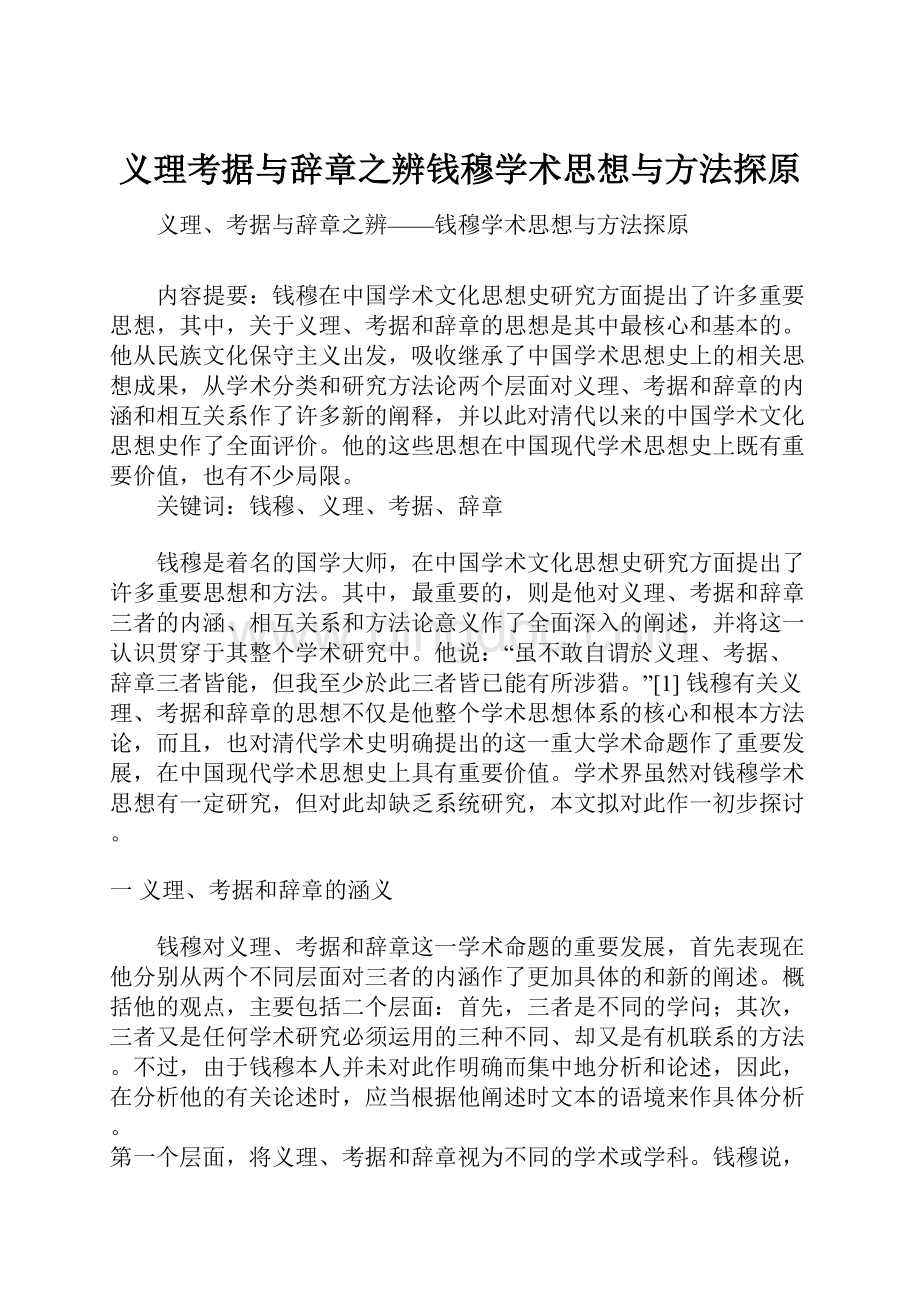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钱穆学术思想与方法探原
内容提要: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关键词:
钱穆、义理、考据、辞章
钱穆是着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
“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1]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
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
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
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
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
。
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
“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
”也就是文学。
钱穆认为,文学本质上反映人生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他说:
“文学则是情感的。
人生要求有趣味,更求要有情感。
”又说:
“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
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
”
第二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他说:
“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
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
”这里,钱穆显然是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运用的方法。
他又说,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其实此种分法,仍不是就学之内容分。
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
下面,再来看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内涵的阐释。
关于义理。
钱穆说,义理“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
义理当然要有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是义理。
义理也不是今天所说的哲学,双方有些不同。
”“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
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
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
”[10]在他看来,义理是思想,但必须是有人生理想和道德的,同时又能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
而思想的涵义则比义理宽泛。
也就是说,义理是思想的一种。
钱穆在论及学术研究中“道”与“术”的不同时,对义理又作了解释,说:
“道指义理,……凡有关从事学问之方向、及其所应达到之目标等,应属‘道’,即凡论该做何等样学问,或论学问之‘意义’与‘价值’等皆属之。
”[11]
关于考据。
钱穆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和是非的方法。
他说,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重视明据确证,不然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12]又说:
“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
”[13]值得注意得是,在这里,钱穆并不是对考据作狭义的理解,仅将其视为对文字、史料进行音韵、训诂、校勘和考证,而是包括更广的含义,即对历史事实和思想的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评判。
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考据思想,说曾氏将考据渊源分杜马和许郑两派,以顾炎武和秦蕙田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
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
……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至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
”[14]钱穆还特别提出考据要考其义理,说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
那亦即是考据。
”[15]又说:
“考据应是考其义理。
”[16]明确提出考据还应当以包括义理的阐发,这已经与现代西方阐释学有相吻合之处了。
[17]这是钱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关于辞章。
钱穆说,义理是离不开开口讲话的,“中国古人说:
‘有德必有言’,言就是辞章。
”又说:
“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
”[18]这基本是从方法论意义来说辞章的功用的。
二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合与分的关系
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钱穆实际也是从学问性质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来论述的。
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者既是合一和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别看待的。
第一,从义理、考据和辞章分属不同的学术层面上说,三者既各有其用,又相互贯通,它们在本质上是合为一体的。
钱穆认为,不同的学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人生的解决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各有其用;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又必须将它们共同运用于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才是周全和完善的,他说:
“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的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
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
”[19]又说:
“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
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
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
”[20]钱穆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心性道德修养的基本精神出发,论证了各门学问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
他说,依照中国传统,学问有三大系统。
第一系统是以人为学问系统中心的“人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一人,如何做一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以事业为中心“事统”,即“学以致用”。
而人生与事业是不能分的,“故亦惟就其事业,始能见其学问之大体。
”第三系统是以学问本身为系统的“学统”,如治史学、哲学等,好像每一套学问于人生实际和社会应用之外,各有其外在客观的存在,各成一系统。
它与前两系统的分别:
一在由学人来做学问;一来由学问产生学人。
他说,似乎中国人开始只看重第一、二系统;中国传统观念中之理想人格是圣,主要在求完成自己所具之德,“学问则只是一工具,其本身不成一目标。
”[21]然而,西方却不同,“似乎西方人一向认为学问乃有一外面客观的存在,有其本身自有之疆境与范围。
所谓学问,则止是探究此客观之外在,而又宜分疆界范围以为探究。
”因此,重视学问的分类。
钱穆说,这种做法“固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许多的境界,提供了许多新意见。
但也有两项易见之弊:
一则各自分道扬镳,把实际人生勉强地划开了。
如研究经济的可不问政治,研究文学的可不问历史等。
第二、各别的研寻,尽量推衍引申,在各自的系统上好像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到底则每一项学问,其本身之系统愈完密,其脱离人生现实亦将愈显着。
”[22]另一方面,三者还是有主从之别的,其中,经学是阐述做人的根本道理的,是中国学问的第一系统“人统”,所以能贯通和指导其它学问的,具有核心的地位。
他说:
“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
”[23]又说:
“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子、史、集三部分的。
”[24]
以上是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的关系的总体认识。
那么,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即经学、史学和文学具体关系的论述又是如何得呢?
关于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钱穆认为,史学和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两大门类,“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
”[26]两者所以成为中国学术的两大主干,是由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重视历史的精神所决定的。
经学或心学主要是从义理和思想上阐发人文大道与如何做人的方法与真理,“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27]中国文化又注重历史精神,史学是人事之学,它主要从历史事实来探求人文大道与真理,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因此,“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道,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
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
”[28]由于钱穆视经学和史学为中国学术两大门类或主干,因此,他对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阐述得很多。
那么,经学和史学是什么关系呢?
概括起来,钱穆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或层面来阐发的。
一是,从史学与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演进中的关系阐明了史学即经学,经学即史学,“经史同源”。
钱穆说,后人所说的“五经”,有“四经”是历史。
《尚书》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历史材料,《诗经》比《尚书》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史诗,《礼》记载了当时社会的一切礼俗,也可视为一部历史书。
孔子的《春秋》则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亦可谓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29]。
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是史学,其所讲不出周公和孔子的治平实绩与理想,皆属已往历史。
后来汉代古文学家提出《毛诗》、《周官》及《左传》为经,“实是经学中之历史性愈趋浓重之证。
其趋势至东汉而益显,即是在经学中根据古代史实的趋势,益胜过了凭空阐发义理的趋势之上。
郑玄括囊大典,偏重早已在此方面;而王肃继起,显然更近于是一史学家。
杜预作春秋左氏集解,显然亦偏重在史学。
故可说经学即史学,史学即亦经学。
”[30]魏晋南北朝时,虽尚清谈玄言,史学亦鼎盛,儒学已从经学扩及到史学,由此开始出现经史并称,并有了经史学的新名目。
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未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和杜佑等史家。
宋代史学尤盛,着名史家有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
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和马端临等人皆在史学上有表现。
明初宋濂、刘基等虽不着史,却留心史学。
明末清初大史学家辈出,顾亭林、黄梨洲和王船山等也都属儒家。
清代虽考据学大盛,其实仍属史学,只是较狭义的史学和儒学而已。
“故在中国学术史中,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31]反过来说,史学又是从经学演化而来。
他说,中国最早的学术是王官学,即政府有关社会政治管理的档案文书,它形成了后来被尊称为经的《诗经》、《尚书》、《礼》和《易经》等。
因此,又可以说,“史学从经学中衍出”[32]。
二是,从“体用合一”角度说,经学为体,史学为用,两者合而为一。
钱穆认为,经史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经学是阐发人生根本道理的,故在学问中处于“体”的地位。
但是,这一“体”要变成对社会和人生有用的学问,则必须通过史学这一实践和治平之学来完成。
也就是说,讲经学,必须落到史学上才能实现。
他说: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之实际贡献。
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
”“要做一理想人,要做一圣人,便该在实际人生社会中去做,此便是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人文精神。
”[33]所以,他说:
“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
”“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工夫。
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
”[34]质言之,“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
”[35]可见,钱穆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高度看待史学和经学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其次,关于辞章与经学、史学的关系。
关于经学与辞章的关系,钱穆论述得不多,但从他强调经学的中心地位,可知他是认为经学对辞章具有理论指导性的。
关于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源于史学。
他说,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而《诗经》实为一部史诗;我们现在推尊周公,而周公所作的诗经之雅颂和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
我也根据孟子说:
‘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
”[36]其次,他还从集部源出于史学,论证文学与史学的相通性。
他说,集部有骈散之分,最先的骈体为屈原的《离骚》,诗骚并言,则《离骚》也可说来自经,故《离骚》亦可通于子和史。
三国时代的建安文学,乃由西汉的骈体辞赋转入散文中,其中曹操和诸葛亮等人的文字皆亦子亦史。
晋宋时陶潜的诗辞传记,如《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皆一人之史,亦即一家之言,实为史、子、集三部通而为一。
唐代韩愈倡古文,乃正式由骈体变为散文,“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正表明了其言亦子亦史。
所以,他说:
“一人之集,至少乃为其一人之自传,亦即当归入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道统中。
故集部兴起,乃为四部之最后。
……。
而其当可列入史部,则更不待论。
”[37]
第二,在方法论层面,钱穆对三者关系的总体认识是,义理是考据、辞章和经济的根本,“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
”[38]
不过,钱穆主要是一位史学家,他讲义理主要是从史学、而不是哲学的角度讲的,这是他与当代新儒学家的不同,他本人也不认同当代新儒家。
[39]他有时将人文学科的研究等同于史学研究,认为史学是人文学的最基本学科,说:
“自然科学基本在数学,人文学基本则在史学。
”[40]又说,中国史学“实乃一种超出寻常的人生哲学,亦是一种超出寻常的人生科学。
一切学问尽包在史学之内,而史学乃超乎一切学问之上。
”[41]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他多是从史学立场来谈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的。
基基本主张是:
首先,治史贵义理和思想,不能只重考据。
第一,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不能离开思想来考据。
史学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然而,“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
”[42]如,校勘固然贵有客观材料,可是尤贵有治史者的鉴别,“亦已包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
”[43]第二,获取思想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而考据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我们该在材料上更深进研究其意义,工夫不专用在考据上,而更要在见解上。
”[44]他又说,做学问要先求其大,否则,“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
”[45]所谓求其大,就是说须先立一深远的义理和思想。
第三,着史贵以史识对史料进行取舍,“夫着史必贵于实事而求是,固有待于考订,而着史尤贵于提要而钩玄,此则有待于取舍。
”[46]史识,即是指对历史所抱的深刻思想见解。
第四,对个人而言,是先有学问和思想才有考据。
他说,治学必先通晓前人关于这门学问的大体,然后才可从事窄而深的研究,“乃始有事于考据。
”[47]第五,考据在历史研究上有局限性。
他说,人文学研究较科学研究更难求“实事求是”,“若只在考据上求‘是’,所考据的远在身外,此与科学精神尚易近似,稍属省力。
但若要在当前群体生活之内求是,此却甚难。
因人事日变,今日之所谓是,明日亦可成为不是;此地之所谓是,他处亦可成为不是。
各人立场又不同。
”[48]
其次,治史要以考据为基础和依据,“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
”[49]钱穆是以考据名着《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扬名史坛,初步确立自己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的。
他此后的史学着述也不乏考据之作。
治史所以要重考据,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弄清事实、评判是非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严密和正确的分析,此即考据,他说:
“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
……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
”[50]第二,通过考据能够发现新的史实,使人对历史有新的认识。
他说:
“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诡。
”[51]第三,思想和理论来自考据所获得的真知识。
他说,必先有学问才有知识,必先有知识才有思想和理论,不源于知识的思想和理论是不可靠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
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
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
”[52]所谓“真工夫”和重“实”,即是要讲考据。
当然,这是比较宽泛意义的考据。
第三,治史又离不开辞章。
首先,良史必工于文。
钱穆十分赞赏章学诚的“史所载事者,事必藉于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的观点,说:
“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
文字通了,才能写书。
……讲史学,不仅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而更又讲到要文章,这又是章实斋之深见。
所以章实斋着书,取名《文史通义》。
”[53]其次,由于历史是很复杂的,一笔不能写两件事,因此,“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条线写下,此处便要辞章之学。
”[54]这是从语言文字的概括功能谈它对历史研究结果的分析和叙述作用了。
第三,历史考据也离不开辞章。
他十分推崇朱熹的校勘学及其《韩文考异》,说朱子重视从文理来考异,“言文理者,则必深入于文章的意义中去。
”“故朱子之校韩集,不仅训诂考据一以贯之,抑考据义理文章,亦一以贯之矣。
”[55]
三对乾嘉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批判
钱穆根据自己的上述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作了全面的评判。
总的看,他对宋代以后到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评价比较高,说:
“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在讲心性学方面已超过老释。
因老释离治平而讲心性,终不如理学家即治平之道而谈心性之更为圆满,更为重要。
故自宋以下之史学,亦特见隆兴。
至于清儒,在晚明诸老如顾亭林考史,船山论史,黄梨洲写史,皆极卓越。
”[56]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思想,他极力推崇和彰扬章学诚,对晚清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而对乾嘉考据学和现代学术界、尤其是对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攻击。
关于清代考据学。
钱穆说:
“夫考据之价值,亦当就其对象而判。
清学初兴,最先理论,则曰经学即理学也,又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其所悬以为考据之对象者,仍在义理。
厥后颓波日下,始散而为音韵训诂,降而为校勘辑逸,为饾饤琐碎,为烦称博引。
而昧失本原,忽忘大体,……论其考据方法,纵或操而愈熟,运而益精。
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
”[57]又说,乾嘉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
此情真可浩叹。
……若待识尽字再读书,岂不具是河清难俟?
若论考据,则范围更广大,更是考不胜考。
若果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
……清代乾嘉经学,极盛之后,正犯了这个毛病。
”[58]因此,他认为,乾嘉“汉学”实际是悖离了汉代儒学经世致用的根本精神,使儒学真正走向衰微,“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作。
所以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以下为最衰。
因其既不认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工夫。
又抱很深的门户见解,贡献少过了损伤。
其时的史学,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
”[59]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
钱穆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及其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理论和精神来源,“今文学家主张经世致用,就从章实斋六经皆史论衍出,故从章实斋接下列龚定庵。
”[60]但是,晚清的今文经学空言义理,不讲考据,“但仍走错了路,来专讲公羊春秋,仍在故纸堆中立门户。
”[61]结果,“愈讲愈坏,讲出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62]康有为则走向极端,其《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已经是一派胡言,既非经学,亦非史学。
既非心性义理,又无当于治平实迹。
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
”[63]另一方面,钱穆又对康倡言宋学和经世致用,扭转只重考据学术风气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开学术新风气方面,“则此一百年内,不得不首先要轮到康有为。
”康有为倡导的“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思想,“这竟依稀是回复到晚明诸遗老之矩矱。
乾嘉以来学者,可说无一人知有此境界。
”“平心而论,他们推孔子为教主,守公羊为教法,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以毒攻毒,推翻训诂考据的话柄,此等处未免多有可议。
然而他们以作新人才、改革政治为读书治学的大目标,以经史为根柢,以时务为对象。
就大体言,他们提倡的一套,实应与北宋晚明无大悬殊。
在中国学术史上,他们实应占很高的地位。
”[64]
关于现代学术界,钱穆认为是被只重义理和只重考据的两种风气所主宰,说:
“今日中国之史学,其病乃在于疏密之不相遇。
论史则疏,务求于以一言概全史。
……而考史之密则又出人意外。
……考史之密与夫论史之疏,两趋极端。
”[65]所谓论史之疏,是指只重义理,所谓考史之密,是指只重考据。
他对将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学术风气进行了严厉抨击。
钱穆说,那种只重考据、视史学为考据学的学术风气昧失了学问的根本,使学问成为于已于世无益的死学问。
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本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审视,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所悬对象,较晚明清初更博大高深;然而学无本源,识不周至。
结果是:
“宏纲巨目,弃而不顾。
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问之大体?
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
各据一隅,道术已裂。
细碎相逐,乃至亘不相通。
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
”[66]他认为,这种不讲学与问,只埋头找材料,只重自己成名成家,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治学风气和方法,不仅是治学方法和路向的错误,而且是“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
”“只此‘考据’二字,怕要害尽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
”[67]而治学心术不正便是不实事求是,“此其从事学问本无甚深旨义,其所潜心考据之必无甚大关系。
是安得谓实事求是?
又安可得谓客观之精神?
”[68]更严重的是,这种治学方法和风气还会造成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历史虚无主义。
他说:
“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
以活的人事,换取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
彼惟尚考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69]另一方面,钱穆又批判了那种只重义理、轻薄考据的极端趋向。
他说,近人治史实犯了高心空腹、游谈无根的弊病,“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其实多是空洞,不凭考据,自发议论,其病远超宋儒之上。
”[70]如果就学术方法而论,近世学术界是“重于明道,疏于辨术”,“所争皆在宗旨与目标上,所提出的尽是些理论,亦可说所争者用‘道’。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