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演讲文稿.docx
《王人博演讲文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人博演讲文稿.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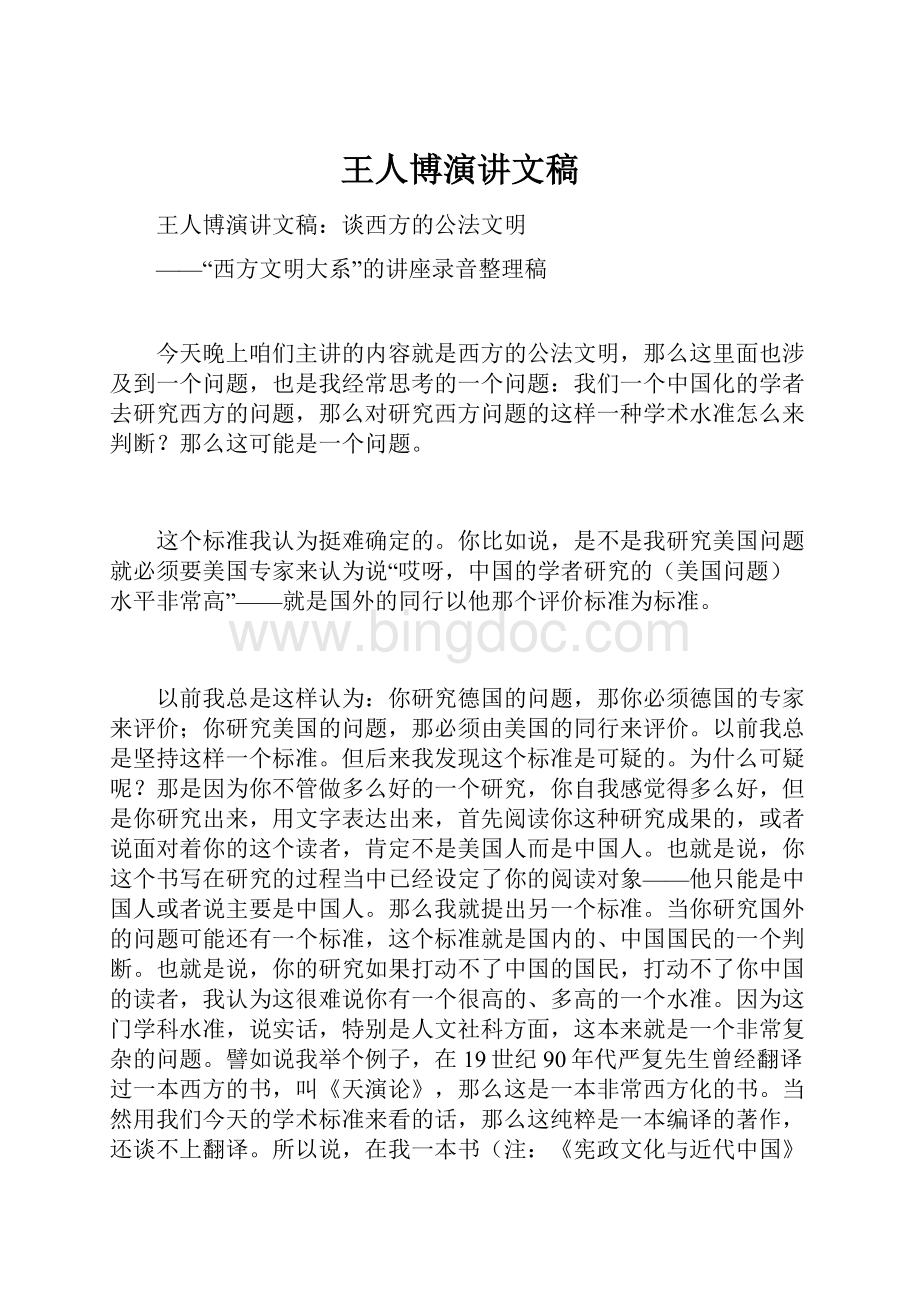
王人博演讲文稿
王人博演讲文稿:
谈西方的公法文明
——“西方文明大系”的讲座录音整理稿
今天晚上咱们主讲的内容就是西方的公法文明,那么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中国化的学者去研究西方的问题,那么对研究西方问题的这样一种学术水准怎么来判断?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这个标准我认为挺难确定的。
你比如说,是不是我研究美国问题就必须要美国专家来认为说“哎呀,中国的学者研究的(美国问题)水平非常高”——就是国外的同行以他那个评价标准为标准。
以前我总是这样认为:
你研究德国的问题,那你必须德国的专家来评价;你研究美国的问题,那必须由美国的同行来评价。
以前我总是坚持这样一个标准。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标准是可疑的。
为什么可疑呢?
那是因为你不管做多么好的一个研究,你自我感觉得多么好,但是你研究出来,用文字表达出来,首先阅读你这种研究成果的,或者说面对着你的这个读者,肯定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
也就是说,你这个书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了你的阅读对象——他只能是中国人或者说主要是中国人。
那么我就提出另一个标准。
当你研究国外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国内的、中国国民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你的研究如果打动不了中国的国民,打动不了你中国的读者,我认为这很难说你有一个很高的、多高的一个水准。
因为这门学科水准,说实话,特别是人文社科方面,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19世纪90年代严复先生曾经翻译过一本西方的书,叫《天演论》,那么这是一本非常西方化的书。
当然用我们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的话,那么这纯粹是一本编译的著作,还谈不上翻译。
所以说,在我一本书(注: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里面这样写了一句话,我说:
“一部英国的思想史可以不提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但是一部中国的思想史你不可能不提到《天演论》。
”这就是个标准!
也就是说,,《天演论》这样一本书,可能在西方同行看来它是非常通俗的。
或者说严复先生这样翻译、这样一种观察,也许它不太符合西方同行的标准。
但是这本书、它的价值,在中国国人看来的价值,我可以不夸张地说:
“它超过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学术著作。
”我记得当年,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面,他曾经写过他读这本书的、少年时期读这本书的感觉。
他用这些话来表达的(胡适当年他读这本书的年龄,大约在十五、六岁的一个少年),他说当时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像一团火在燃烧着一颗少年的心。
”所以说胡适之先生他就从这本书取了他的名字的一个字,叫胡适、胡适的“适”,跟《天演论》有个直接的关联。
你可想而知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学术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对西洋的东西,对外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研究肯定有我们中国人的情结,有我们中国人观察问题的不同的视角。
那么这就没办法完全以国外同行的这样一个评价标准来进行评价。
换句话说,我总认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外国的东西感兴趣,那肯定是怀着一颗中国心。
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是在用一个比较的方法来看看别人、再反观自己。
我们为什么对美国感兴趣?
我们为什么对马达加斯加不太感兴趣?
我们对法国感兴趣、对德国、日本感兴趣是吧,对刚果埃塞俄比亚我们不太感兴趣。
那么从这样一个道理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中国人面对外国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视角,有我们的观察思考问题的径路和方法。
那么这就决定了——判断西学一个标准——中国人做西学的标准它确实(是)挺复杂的一个评价体系。
说实话,我总认为西学在中国是一门最难的学问。
我认为这主要倒不是说因为语言的隔阂,关键是一种文化和我们的思维方式一个不同的差异决定的。
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我说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理论。
咱们不说现在的海归。
我们现在的海归不需要花多少口舌就可以把它说清楚的。
咱们说说以前。
刚才我提到的胡适。
那胡适这个人长得,你看是个中国人,是一个英俊的中国人,或者说我把胡适之先生定义为是一个具有美国气质的中国人。
他那种乐观主义、那种信念的确定性,那是完全美国式的。
那么他对美国的文化也非常的精通,他在美国又待了那么多年,二十几岁当了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但是大家想想,胡适的博士论文写的却是中国哲学史。
他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论文就写的中国哲学史。
虽然他一生在鼓吹宪政民主,但是他晚年研究的学问、他感兴趣的学问就是中国学问。
比如说他晚年研究《水经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
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我们一个中国的一种情怀、学术情怀。
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人做西方的学问总有些隔阂,它不像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东西那么得心应手。
但是,为了我们中国本身,为了我们民族本身,研究西学肯定有意义。
而且我特别敬重那些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在研究西学的人。
我想今天这么讲这个西方公法文明的时候必须谈到这一点。
我本人不研究这个东西,但并不是说我对这个问题不思考、不阅读。
我先给大家交这么一个底,请大家了解或者谅解。
那么下面我想给大家,咱们进入正题,讲西方的公法文明。
那么谈到西方公法文明,可能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用三个小时之内要把西方公法文明的所有的要素全部讲完,我认为不可能。
是吧,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可能我们要选取我们认为西方公法文明最重要的那一点来给大家讲。
那就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
”,如果西方的公法文明、西方的公法文化它有个轴心,有个圆心的话,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根据我自己本人的阅读——当然我的阅读是非常的狭窄的——我发现西方的学者从来不思考这样的问题。
西方的同行他从来不回答说西方的公法文明的轴心是什么?
它的核心是什么?
换句话说,今天我提出来“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问题。
这是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时候由我们中国人提出的问题。
这跟西方的同行没关系。
西方人从来不从这样一个出发点而提问问题。
如果你给一个西方同行冒然地提出这个问题:
请问你们西方公法的文明核心是什么?
可能这西方的同行他可能感觉很吃惊。
因为他从来不这样思考问题的。
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它对问题的取舍、对问题思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再比方说,假如西方的同行他确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一定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回答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你能回答得出来吗?
假如非要你回答出来,那这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判断。
我也阅读过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书籍,我还没发现哪一个中国学者他肯明确地回答说中国古典文化——当下文化咱不说了,当下有没有文化那还是个问题呢——的核心是什么。
我还没阅读过哪个作者,哪个中国的作者、中国的专家和学者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
我们最多说《论语》这本书它是围绕着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仁”来展开的。
我们从这个可以推导出说“仁”可能构成了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一个轴心,但这是就《论语》来讲的。
你不能说把《论语》放大为一个整个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意象。
《论语》不等于中国文化,所以就可能产生了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当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面他讲了,讲了中国的文化的一些精华和元素,但是他没讲核心,他说“仁”、“义”,包括这个“恕”、“勇”,那么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
那么这些独有的概念、这独有的要素可能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精华的、比较整体性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讲中国。
你讲西方,那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更迷惑了。
你说西方文化,特别是公法文化,你怎么来进行判断呢?
你怎么判断?
西方如此的跟我们不一样,是吧?
好像我们中国对西方的观测、思考、阅读,我老是感觉到你抓不到一个重心。
好像西方跟咱们真是什么都不一样。
那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话,你说西方公法的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思考的经验,或者说跟你的职业有关,我认为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有俩字就可以概括的。
我认为就是这俩字,就是“宪政”。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判断,而且我也不否认这样一个判断是跟我的阅读经验,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的。
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根据你的阅读经验,也可以作出一个不同的判断。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这样一种判断,这样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中国化的。
为什么说是中国化的呢?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中国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他要强调中心观。
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中心观、中心意识;而西方不是。
相对中国,西方这个中心观要弱得多。
你说,你像美国、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是个什么破城市,你告诉我华盛顿是个什么城市?
我告诉你,你别用大词形容,什么政治中心、外交中心;美国人没这个观念。
你去问美国人,美国人可能会说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从来不去居住的那个城市。
我告诉大家,美国的社会治安最差的就是华盛顿。
一般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一般不到华盛顿居住的。
而且华盛顿是一个小城市,大家都知道,你到美国去华盛顿,你点根烟从那头还没燃完呢,(城市就走)完了。
它既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
艺术中心在洛杉矶,它的金融中心在纽约,是吧。
美国的文化中心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在个一小镇上,它哪有中心呢?
我们最多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说,华盛顿你只能找到一个中心,它是政治中心。
为什么它是政治中心呢?
那是因为奥巴马住在那儿。
就这么简单。
相反,“北京”这个概念它包含的含义和意义要比华盛顿这个地方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
我们中国人的一首童谣——我们唱响了全中国的童谣——《我爱北京天安门》,可你听说美国有什么童谣说“我爱美国华盛顿”吗?
没有吧!
那肯定没有啊!
北京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呈现的印象跟华盛顿给美国人呈现的印象,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北京首先说它是政治中心,它既然(是)政治中心,它就可能成为很多很多的中心,比如说,科教中心、文化中心。
最好的大学肯定在北京,我们知道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当然还有中国政法大学。
后来我说了,如果说我们中国的首都迁都了,把首都不在北京了,迁到哪儿去呀,比如说迁到四川的绵阳。
这是我一直认为绵阳最适合做现代化的、当代新的首都。
绵阳最合适了,这是我一直认为的。
那毫无疑问,如果说绵阳成了首都,你给它三年时间,绵阳大学肯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心观。
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心观都中心到什么程度?
我们中国人没了圆心没了轴心就找不着北了。
我们必须有中心、有核心的,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不是哪朝哪代的问题,咱们中国人都这样。
所以说你看,你要提出说“什么是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什么是它的轴心”这样一个问题,它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问题。
而我认为,如果从中国从我们自己的思考出发的话,“宪政”应该是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
起码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非要给它找出一个核心的话、一个轴心的话。
为什么把宪政能看成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呢?
我认为宪政是最能区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公法问题思考的一个最大差异性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宪政可以证成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一个最大的不同。
我经常说宪政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是无缘的。
这倒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慧根浅。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跟西方太不一样了。
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经在我一本小书(中),那本小书叫《桃李江湖》,是一个杂集,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
我后面那个封底写了几句话,话是这样写的:
“一个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不值得中国人称颂,那是因为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无法理解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
”前面那句话大家可能不理解,但是后面这句话大家就理解了。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意大利的球迷为什么痛苦?
因为他们为他们的意大利足球输给巴西而痛苦,为输给阿根廷而痛苦,为输给英格兰,或者说德国、西班牙这样的球队而痛苦。
但是我们中国的球迷呢?
我们的球迷的痛苦在于我们的球队从来没赢过。
我们的痛苦是什么?
是我们的球队它谁都敢输。
所以,你说一个意大利球迷能理解我们这种痛苦吗?
那么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到我说这个痛苦在哪儿。
下面那句话为总结前面那句话来说的。
我说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美国成功的产物;正是因为美国的成功,所以产生了美国的宪政主义者。
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那是从近代以来中国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的产物。
这是中国宪政主义者的一个痛苦之源。
中国不是因为成功才产生了宪政主义者,而是(由于)中国全是挫折,一挫再挫、一折再折,到今天我们离宪政这样一个东西还是很远,还是遥不可及。
就像温总理说了我们像遥望天空的星星一样——“悬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就是够不着”。
这种痛苦,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中国越遭受挫折,中国人越想念宪政,越挫折我们就越想念,所以说我现在总结这句话“为什么我认为西方的宪政会成为我们中国人观察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
”的时候,我认为宪政这个概念最集中地表达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什么?
文化的乡愁!
什么叫乡愁?
大家可能读过余光中先生写的那个《乡愁》,“一湾浅浅的海峡,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乡愁是一枚邮票,然后乡愁是一个坟。
我住在这头,我母亲住在那头。
”这种乡愁说实话,说得难听点,这是非常矫情的一种乡愁。
当然,我对余先生这样说大家不要认为我对余先生不敬重。
余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一位诗人。
这种敬重感表达在我那本小说的序里面了。
《桃李江湖》我的序里面就引用了余先生的话。
为什么叫“江湖”,我用江湖这俩字就是引用余先生的话。
但是,我认为表达乡愁最好的是一个法国的分析学家,他叫彭塔利斯。
彭塔利斯的《窗》,就是我们开窗的那个窗,《窗》这个小册子里面,他专门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乡愁”,说的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孩子,越是感到别人的阔,越思念自己贫穷的家乡。
当我们越去阅读西方的政治、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激起了我们一个中国式的乡愁之感——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它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和公法文明呢?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宪政呢?
所以我说:
宪政是最能唤起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乡愁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前面都给解释了。
你看宪政在西方那是成功的一个产物,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但是宪政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挫再挫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渴望这样一种东西。
但是越渴望离得我们越远。
这种乡愁的感觉,我认为可能是宪政这个概念表达得很充分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宪政真能表达我们中国和西方的一个最大不同的一个概念。
从宪政这个概念身上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制度设计、规范的确定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
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
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说我们长得不好,我是说这个差别和差异性太大了。
你比如说咱们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西方有丑女人,白人有丑女人,很丑的女人,不是说西方都长得像玛丽莲·梦露那样,同样西方有丑的女人。
我们中国、东亚国家也有丑的女人,但是这个丑的差异太大了。
钱钟书先生就说了,说西方的那个丑啊,那是最经典的丑。
他的原话这样说的,“中国女人的丑好像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的一种偷工减料,而西方人女人的丑是西方在造人的时候一个恶作剧。
”哎呀,我说这我为什么想不到呢?
我说我看了,我说你看那个白人那个女人看起来挺丑的,但它确实不像我们中国女人的那个丑。
她不一样。
可这个不一样怎么表达呢?
你表达不出来。
钱先生是个高人,他给你表达出来了。
你只有拍岸叫绝的份儿。
我也讲到中西方它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它为什么那么多的不一样,最大的差异在于宪政。
我告诉大家,宪政这个概念,并不像你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给你讲的。
不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是没有意义的!
要从学术上去定义这个概念,那太简单不过了。
因为美国的、德国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同行,包括古典宪政主义者和现代宪政主义者,他早就对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不需要你来解释。
我们中国人感兴趣的不是那种解释。
我们所感兴趣的西方这个宪政这个概念到底承载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由这个概念反映出中西方那么大的差异?
这是可能我们感兴趣,或者说是我本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纯粹中国化的一个问题。
我从来不否认西方的同行和专家学者那种解释是对的,肯定是对的。
但这种解释对我一个中国人来讲没意义。
它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惑,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说得大一点,它消除不了我内心的那种痛苦、不能释怀。
所以说,学术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
学术的价值有限,学术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说它也不解决主要问题。
而中国的问题在宪政这个概念上,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这就是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把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定在宪政的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宪政这样一个价值或者说宪政这样一个概念会成为西方公法文明的一个核心?
那么下面我接着论证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我说了,西方的公法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
起码说,从我这个角度我认为它应该是宪政。
是的原因可能有以下这么几点吧。
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讲堂、这样一个场合,我想摒弃这样一个纯学术的对这个概念的解释。
刚才我说了,这样一种解释可能会解决宪政学、宪法学的某些问题,但是你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中国跟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不同。
就刚才我的命题,我认为学术解决不了一切问题,或者说学术解决不了主要问题,或者说,学术是没有回答你心中的那个疑问的这样一种能力的。
宪政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并不纯粹是学术性的。
我们暂且把宪政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先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有机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我们的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修养和教养、不同的见识来对这个概念做一些解释。
宪政这个东西它确实挺复杂但实际上挺简单。
有时候我们靠心灵、有时候我们靠双手都可以感知到它、去触摸到它。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观察点,有不同的触摸方式。
那么按照我的理解,按照我的经验、人生经历,或者说按照我对西方的阅读和理解,我认为这个东西并不神秘。
宪政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高深理论那是学者给你演绎出来的。
其实,宪政这个东西可能就生活在西方人的身边,它跟西方的每一个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生活上有关联的一个东西。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宪政是一个很值得去玩味的一个东西,如是等等。
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描述的这个宪政概念,我想我们适不适合去从我们中国出发,从我们一个中国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
或者说,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看行不行。
比如说,我认为宪政它首先表达了一种对人的不同看法。
当然表达了对人的一种不同看法这样一个表述本来就非常模糊。
我这里讲的对人的不同看法,主要表达的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中国和西方对人的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养育了我们的中国人,那么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看人的方法,而西方的文化可能孕育了西方、西方人看人的一种方法。
我认为宪政在这个方面可能体现得比较充分。
它确实表达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种对人的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我认为一般来说西方人不厚道。
西方人的不厚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认为西方人主要表现在他把人想得挺坏的。
当然用学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说西方一般都持有人性恶的这样一个看法。
那么为什么对人看得那么悲观?
我说这跟西方人的不地道、不厚道有关。
当我们把人都看得很坏的时候,说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这本来是可以研究的。
但西方人就是、他确实把人看得挺坏。
而这个坏是成这个等级序列的。
一般的人叫小坏,有本事的人叫中坏。
简单地说,老百姓那个坏是一般性的;大家都差不多、都坏得差不多。
当官的更坏,而官越大他越坏。
西方这个看法,我们大家感觉出来没有,对西方的理解,你比如说,像奥巴马是美国的总统,他是最大的官、美国最大的官。
但是呢,美国人他所有的防范的措施和制度主要给那个最大的官设计的。
他不放心。
官越大,他越不放心。
因为官越大就意味着你的权力越大;你的权力越大,你的黑手就越长;你的黑手是伸得越长,对老百姓的损害就越大。
就这个基本的道理。
所以说,美国人他那套制度跟他对人的这种看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反过来讲也一样。
奥巴马他不是什么好人。
为什么他不是好人呢?
因为他当了美国总统。
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上,坐在那个位置上,以前你没坐那个位置可能是个好人,但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我们必须把你假设为你是最大的坏人。
当我们用坏人这样的词去表达一个最大的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词去表达他啊?
这个是美国人发明的。
叫政客。
政客最大的坏就是他从来不说真话。
他只说老百姓喜欢听的话,而且他从来不干对老百姓有利的事。
当然这样说话可能比较偏激、比较极端。
但是你必须这样去想他、这样去看他。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要防他。
如果你不防他的话,他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大的官,刚才我说了,他把黑手一伸多少人要遭殃啊,是不是?
所以说西方人的宪政概念,它本身就是个防御制度。
它是防御性的、防人的。
大家记住这个本质。
宪政跟民主不一样。
宪政就是防的,是预防的,是一个预防性的东西。
万一你奥巴马干坏事怎么办?
美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不能说他干了坏事了我们还没想出对策来呢。
美国人说我们得先想好对策防止他干坏事。
这就是宪政。
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设计和假设呢?
刚才说了,主要是对人的看法不一样——西方人普遍对人性持的一个悲观看法。
它的来源很简单。
西方的文化的根子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基督教。
我们读过基督教《圣经》。
《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不就预设了一个人性的堕落吗?
为什么人被赶出伊甸园去?
那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按照《圣经》的说法——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的人,不听从上帝的告诫,受不了那种诱惑说偷吃了果子。
这个果子大家都知道,那是智慧之果。
这是一个引喻,他要表达什么问题呢?
《圣经》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说明人是经不起诱惑的。
亚当夏娃还只是经不住那个智慧之果的诱惑。
大家想想,我们现实当中的人要面对着多少的诱惑?
特别那些手握、手里面掌握权力的人,他要面对多少诱惑?
有多少人能经得起这种诱惑?
亚当和夏娃都没经得起那种诱惑,可想而知他的后人凭什么就比他的祖先更能经得起诱惑。
为什么那么多当官的纷纷落马?
我们把这当官的称之为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哪儿?
就是灵魂的堕落、人性的堕落。
从最基本的说,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贪腐的人肯定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如果你说,王老师不对,我认为主要是制度问题。
同学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你才这样看。
制度是人定的。
同样一个制度,面对着不同人的时候,它发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我们把西方那套制度移到中国来,中国就会变得更好。
那可能恰恰相反,可能变得更糟。
真正起决定性的是人性和人心。
当你人心都坏了,那个制度管用吗?
小人你是防不住的。
说制度是管小人的,但真是小人你管得住吗?
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网是恢恢,但是漏网大鱼那太多了。
历史上被捉住的就几个而已。
为什么西方人这样看法?
他跟咱们看法就不一样。
比如说,刚才说了美国的总统,他就是个政客。
他只是一个偶然的获胜者而已,在选举过程当中他偶然获胜了而已。
你不要把他预设为很高的一个人,品行很高、教养很高、智慧很高,肯定不是。
大家听说过全美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要学习奥巴马同志的讲话的运动和高潮吗?
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美国人听说老百姓要学奥巴马讲话,他肯定会说:
“你奥巴马什么人啊?
我为什么学你?
你不就是总统吗?
”这是美国人的不厚道。
美国人不厚道,他把人都看成坏人。
但实际上奥巴马他本人真实如何并不重要。
也许奥巴马是个好人,也许奥巴马是个品行很高的人、心灵很纯洁的人,但是当他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他掌握了权力,你必须再去预设他是个坏人。
我把这个称之为“西方人的不厚道”。
没办法,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没有这样一种文化怎么能发明出那么多的制度?
制度都对付坏人的。
没有小偷哪来的门呢?
哪儿来的锁啊?
锁就是一个制度。
它是规范小偷的。
你看随着小偷偷的技术越来越高,我们制锁的那个质量就越来越细化。
现在那个锁我们自己有时都打不开。
所以制度肯定是来对付坏人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制度有它的局限性。
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