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二册张汉熙168课课文翻译.docx
《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二册张汉熙168课课文翻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二册张汉熙168课课文翻译.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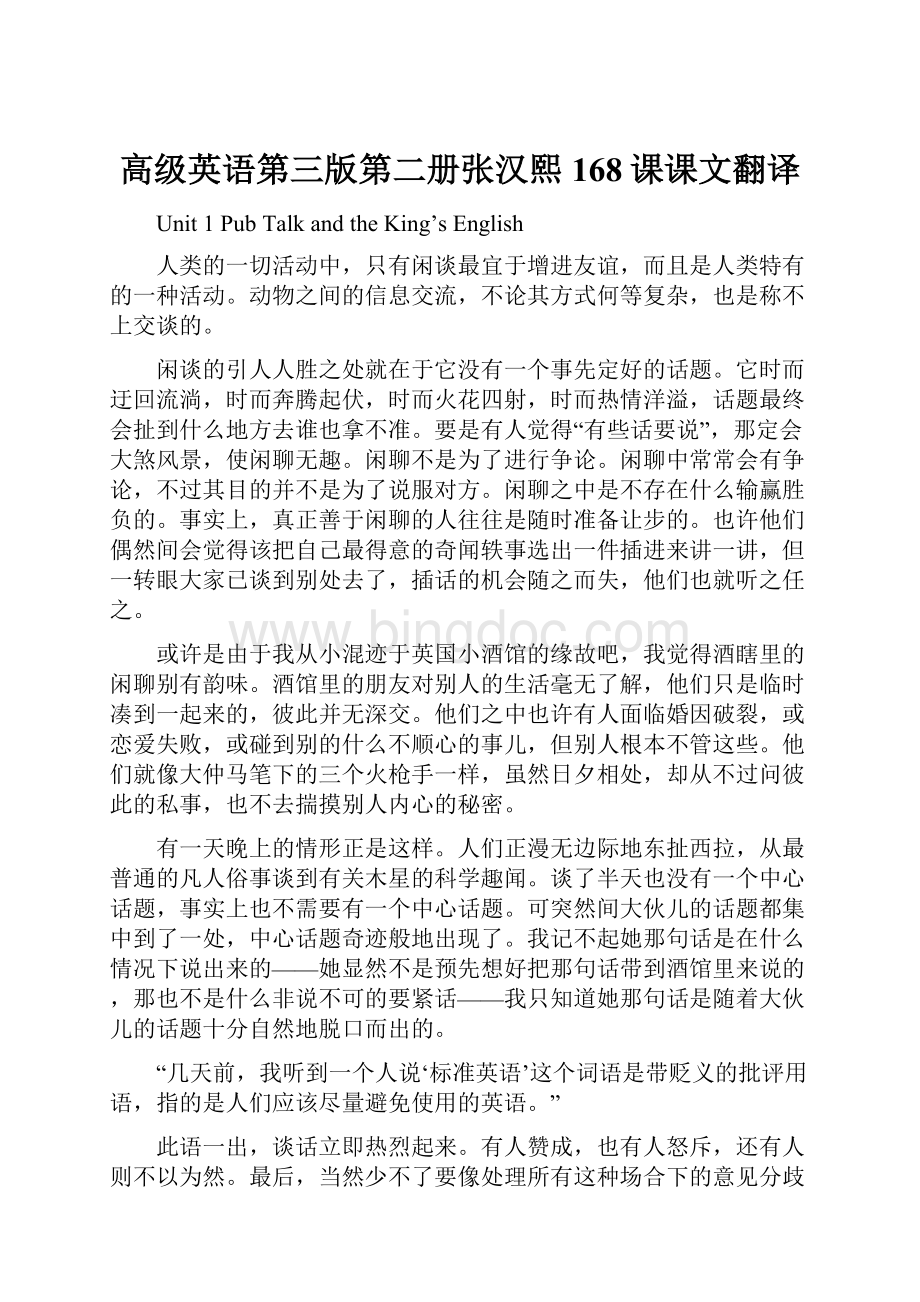
高级英语第三版第二册张汉熙168课课文翻译
Unit1PubTalkandtheKing’sEnglish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
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
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
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
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
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
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
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
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
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
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
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
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
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
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
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
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
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
于是,问题便解决了。
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
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
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
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
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
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
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
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
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
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
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
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
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
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
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
“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
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
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
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English)的提法。
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
“你把‘标准英语’(King’sEngligh)简化了”。
莎士比亚作品中是否也出现过这一提法呢?
如出现过,那就证明这个词在当时即已通用。
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桂嫂在讲到她家老爷回来后将会有的盛怒情形时说,“……少不了一顿臭骂,骂得鬼哭神愁,伦敦的官话(即“标准英语”)不知要给他糟蹋成个什么样子啦。
”(朱生豪译)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她说中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词语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
经过前后五百年的发展和与诺曼底人、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的竞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
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英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这样便有了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标准英语”。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没费吹灰之力,使其影响日盛,遍及全球。
“标准英语”再也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的性质了。
不过,那个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
下层阶级在用这一名词时总带着一点轻蔑或讥讽的味道。
我们会发现,就连快嘴桂嫂这样一个婢女也会说她的主子凯厄斯大夫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讲起平民百姓们所讲的那种粗话。
如果说标准英语就是所谓“规范英语”,这种看法常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笑讥讽,他们有时故意开玩笑地把它说成是“规反英语”。
下层人民对文化上的专制仍是极为反感的。
正如卡莱尔所说,始终存在着的一种危险是,“对我们来说。
词语会变成具体的事物”。
词语本身并不是现实,它不过是用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而已。
标准英语就像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用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
让人们学着去讲也许不错,但既不应当把它作为法令,也不应当使它完全不接受来自下层的改变。
我一向对词典有着始终不渝的酷爱一奥登说过,一个作家的全部所需就是一支笔、够用的纸张和“他所能弄得到的最好的词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把词典看成是一种常识的工具。
标准英语是一种典范——一种丰富而有指导作用的典范——但并不是一种最高的典范。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先前的话题上了。
即便是那些学问再高、文学修养再好的人,他们所讲的标准英语在交谈中也常常会离谱走调。
要是有谁闲聊时也像做文章一样句逗分明,或者像写一篇要发表的散文一样咬文嚼字的话,那他讲起话来就一定会极为倒人胃口。
看到E?
M?
福斯特笔下写出“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其用语之生动及由其所产生的生动有力、甚至可怖的形象令我们拍案叫绝。
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会客室里说“我们大家正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请他走开。
常常有一些愚人要求大文豪们谈话时也像写文章一样字字珠玑。
也有些人对18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表称羡。
可是,说不定那些文人雅士们在那里也不过是闲聊,谈论酒食的好坏哩。
当时的巴黎大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苏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作客时就曾大叫着说“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布兰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用心不一而已。
会客室里和餐桌上是无需摆上词典的。
闲聊过程中若遇上弄不明白需待查实的问题可留待第二天再说,不要话说到一半却去一边查起字典来。
否则,谈话便会受到妨碍,不能如流水般无拘无束地进行。
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当场弄清了“标准英语”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再有那一场交谈论辩,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去,一会儿扯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了。
而且,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去思考了。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人们就不会对于那位引出话题的“火枪手”那样发生兴趣,想多了解她的情况了。
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可能尽想着要讲出些正经八百的话来,因而使得谈话失去意趣。
Unit2Marrakech
一具尸体抬过,成群的苍蝇从饭馆的餐桌上嗡嗡而起追逐过去,但几分钟过后又飞了回来。
一支人数不多的送葬队伍——其中老少尽皆男性,没有一个女的——沿着集贸市场,从一堆堆石榴摊子以及出租汽车和骆驼中间挤道而行,边走边悲痛地重复着一支短促的哀歌。
苍蝇之所以群起追逐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死人的尸首从不装进棺木,只是用一块破布裹着放在一个草草做成的木头架子上,有四个朋友抬着送葬。
朋友们到了安葬场后,便在地上挖出一个一二英尺深的长方形坑,将尸首往坑里一倒。
再扔一些像碎砖头一样的干土块。
不立墓碑,不留姓名,什么识别标志都没有。
坟场只不过是一片土丘林立的荒野,恰似一片已废弃不用的建筑场地。
一两个月过后,就谁也说不准自己的亲人葬于何处了。
当你穿行也这样的城镇——其居民20万中至少有2万是除开一身聊以蔽体的破衣烂衫之外完全一无所有——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
实际上,这是所有的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
这里的人都有一张褐色的脸,而且,人数书如此之多!
他们真的和你意义同属人类吗?
难道他们也会有名有姓吗?
也许他们只是像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的蜜蜂或珊瑚虫一样的东西。
他们从泥土里长出来,受哭受累,忍饥挨饿过上几年,然后有被埋在那一个个无名的小坟丘里。
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离去。
就是那些小坟丘本身也过不了很久便会变成平地。
有时当你外出散步,穿过仙人掌丛时,你会感觉到地上有些绊脚的东西,只是在经过多次以后,摸清了其一般规律时,你才会知道你脚下踩的是死人的骷髅。
我正在公园里给一只瞪羚喂食。
动物中也恐怕只有瞪羚还活着时就让人觉得是美味佳肴。
事实上,人们只要看到它们那两条后腿就会联想到薄荷酱。
我现在喂着的这只瞪羚好象已经看透了我的心思。
它虽然叼走了拿在手上的一块面包,但显然不喜欢我这个人。
它一面啃食着面包,一面头一低向我顶过来,再啃一下面包又顶过来一次。
它大概还因为把我赶开之后那块面包仍会悬在空中。
一个正在附近小道上干活的阿拉伯挖土工放下笨重的锄头,羞怯地侧着身子慢慢朝我们走过来。
他把目光从瞪羚身上移向面包,又从面包转回到瞪羚身上,带着一点惊讶的神色,似乎以前从未建国这种情景。
终于,他怯生生的用法语说道:
“那面包让我吃一点吧。
”
我撕下一块面包,他感激地把面包放进破衣裳贴身的地方。
这人是市政当局的雇工。
当你走过这儿的犹太人聚居区时,你就会知道中世纪犹太人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在摩尔人的统治下,犹太人只能在划定的一些地区内保有土地。
受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后,他们已经不再为拥挤不堪而烦扰了。
这儿很多街道的宽度远远不足六英尺,房屋根本没有窗户,眼睛红肿的孩子随处可见,多的像一群群苍蝇,数也数不清。
街上往往是尿流成河。
在集市上,一大家一大家的犹太人,全都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色便帽,在看起来像洞窟一般阴暗无光,苍蝇麋集的摊篷里干活。
一个木匠两脚交叉坐在一架老掉牙的车床旁,正以飞快的速度旋制椅子腿。
他右手握弓开动车床,左脚引动旋刀。
由于长期保持着种姿势,左脚已经弯翘变形了。
他的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孙子竟也在一旁开始帮着干一些简单的活计了。
我正要走过一个铜匠铺子时,突然有人发现我点着一支香烟。
这一下子那些犹太人从四面八方的一个个黑洞窟里发疯地围上来,其中有很多白胡子老汉,都吵着要讨支烟抽。
甚至连一个盲人听到这讨烟的吵嚷声也从一个摊篷后面爬出来。
伸手在空中乱摸。
一分钟光景,我那一包香烟全分完了。
我想这些人一天的工时谁都不回少于十二小时,可是他们个个都把一支香烟看成是一见十分难得的奢侈品。
犹太人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他们从事阿拉伯人所从事的行业,只是没有农业。
他们中有买水果的,有陶工、银匠、铁匠、屠夫、皮匠、裁缝、运水工,还有乞丐、脚夫——放眼四顾,到处是犹太人。
事实上,在这不过几英亩的空间内居住着的犹太人就足足有一万三千之多。
也算这些犹太人好运气,希特勒未曾光顾这里。
不过,他也许曾经准备来的。
你常听到的有关犹太人的风言风语,不仅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听到,而且还可以从较穷的欧洲人那里听到。
“我的老兄啊,他们把我的饭碗夺走给了犹太人。
想必你也知道这些犹太人吧,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
我们的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银行、财政——一切都被他们控制住了。
”
“可是,”我说道,“到多数普通犹太人不也是为了一点微薄的工钱而辛勤劳作的苦力吗?
”
“噢!
那不过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
事实上他们都是些放债获利的富豪。
这些犹太人就是鬼得很
与此恰恰相似的是,几百年前,常常也有些苦命的老太婆被当成巫婆给活活烧死,然而事实上她们就连为自己变出一顿象样饭菜的巫术都没有。
所有靠自己的双手干活的人一般都有点不太引人注目,他们所干的活儿越是重要,就越不为人所注目。
不过,白皮肤总是比较显眼的。
在北欧,若是发现田里有一个工人在耕地,你多半会再看他一眼。
而在一个热带国家,直布罗陀以南或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可能看不到田里耕作的人。
这种情形我已经注意到多次了。
在热带的景色总,万物皆可一目了然,惟独看不见人。
那干巴巴的土壤、仙人掌、棕榈树和远方的山岭都可以尽收眼底,但那在地理耕作的农夫却往往每人看见。
他们的肤色就和地里的土壤颜色一样,而且远不及土壤中看。
正因如此,贫穷至极的亚非国家反倒成了旅游观光的胜地。
没有谁会有兴趣到本地的贫困地区去作依次毫无价值的旅行。
但在那些居住着褐色皮肤的人的地方,他们的贫困却根本没有人能注意大批。
摩洛哥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无非是一个能买到橘子圆或者谋取一份政府差使的地方。
对于一个英国人呢?
不过是骆驼、城堡、棕榈树、外籍兵团、黄铜盘子和匪徒等富于浪漫色彩的字眼而已。
就算是在那儿呆过多年的人也未必会注意得到,对于当地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来说,现实生活只意味着永无休止、劳累至极的斗争,其目的是从贫瘠的土壤中费力地弄出点吃的来。
摩洛哥的土地大半是一片荒凉,赖以生存的走兽至大者莫如野兔。
原先曾有的森林覆盖着的土地如今已成为光秃秃的荒漠,土壤跟碎砖头一般。
尽管如此,仍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被人们开垦,劳动强度十分惊人。
一切活儿全靠手工完成。
排着长队的妇女们弯着腰像一个个倒过来的大写字母L一样,以便慢慢地在地里移动着身子往前走,一边用手去拔除带刺的野草。
农民采集苜蓿喂牲口时,不是用刀去割而是用手将一棵棵苜蓿连根拔起,免得割剩下来的一两寸的根茬白白浪费掉。
犁是用木头做的劣货,一点也不结实,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的扛在肩上。
犁的底部安着一个粗劣的铁尖子,只能犁进地里4英寸来深。
拉犁的牲口的力气也只有这么大。
通常是用一头牛和一头驴子套在一起拉犁。
这是因为两头驴子拉不动,而如用两头牛,耗费的饲料有太多。
农民们都没有耙地的耙,他们指示顺着不同的方向犁上几遍,弄出一道道垄沟来,然后再用锄头把整块田地做成一块块长条形的小畦,以利蓄水。
除了较为罕见的暴雨之后紧接着的那一两天外,这地方总是缺水。
农民们在地边上挖出一道道深达三十至四十英尺的沟渠以便把土层深处的涓涓细流汇集起来。
每天下午都有一对年迈的妇女背着柴草从我屋外的路上走过。
由于上了年纪而又饱经日晒,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想木乃伊似的干瘪,而且身躯都是那么瘦小。
在原始社会里,妇女超过了一定的年纪便萎缩得如孩子般大小,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一天,一个身高不过四英尺的可怜人扛着老大的一捆柴草从我身边蹒跚而过。
我叫住她,往她手上塞了一枚面值五个苏的钱币(略多于1/4个旧便士)。
她的反应竟是一声近乎尖叫的哭喊,这喊叫含有感激的成分,主要还是出于惊讶。
我想,在她看来,我虽然会注意她,似乎是违反了自然法则。
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老妇人,即作为一匹驮兽的地位,她是早已接受了的。
每当一家人出门远行时,往往可以看到父亲和已经成年的儿子骑着驴子在前边走,而一个老太婆则背着包袱步行跟在后面。
然而这些人的真正奇特之处还在于他们的隐身的特性。
一连几个星期,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候总有一队老妪扛着柴草从我房前蹒跚走过。
虽然他们的身影以映入我的眼帘,但老实说,我并不曾看见她们。
我所看见的是一捆捆的柴草从屋外掠过。
直到有一天我碰巧走在她们身后时,堆柴草奇异的起伏动作才使我注意到原来下面有人。
这才第一次看见那些与泥土同色的可怜老妪的躯体——枯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被沉重的负荷压得弯腰驼背的躯体。
然而,我踏上摩洛哥国土还不到五分钟就已注意到驴子的负荷过重,并为此感到愤怒。
驴子遭到荷虐,这是无疑的事实。
摩洛哥的驴子不过如一只瑞士雪山救人犬一般大小,可它驮负的货物重量在英国军队里让一头五英尺高的大骡子来驮都嫌过重。
而且,它还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卸驮鞍。
尤其让人觉得可悲的是,它是世上最驯服听话的牲畜。
不需要鞍辔会僵绳。
它便会像狗一样更随着自己的主人。
为主人拼命干上十几年活后,它便猝然倒地死去,这时,主人就把它仍进沟里,尸体未寒,其五脏六腑便被村狗扒出来吃掉。
这种事情当然令人发指,可是,一般说来,人的苦难却没人理会。
我并非在乱发议论,只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
褐种人近于无形。
谁都会同情一只摩伤脊梁的驴子。
但往往要有某种偶然因素,一个人甚至才会注意到压在柴禾下边的老妪。
白鹳展翅北去时,黑人正行军南下——一列长长的满身征尘的队伍:
步兵,炮队,接着又是更多的步兵,总共大约四五千人,正靴声橐橐,车声辚辚地蜿蜒前行。
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是非洲肤色最黑的人——黑得简直难以看清他们颈项上的头发从何处生起。
他们健硕的身躯罩在旧的卡其布制服里面,脚上套着一双看上去像块木板似的靴子,每个人头上戴着的钢盔似乎都小了一两号。
天气正热,队伍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士兵们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得疲惫不堪,敏感得出奇的黑脸颊上汗水闪闪发光。
当他们走过时,一个身体欣长,年纪很轻的黑人回头后顾,和我的目光相遇。
他的那种目光完全超出人们意料之外。
既不带敌意,又不含轻蔑,也没有愠怒,甚至连好奇的成分都没有。
那是一种羞怯的,瞪圆双眼的黑人的目光,实际上就是一种表示深厚敬意的目光。
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
这可怜的小伙子,因为成了法国公民,所以被从森林里拉出来送到军队驻扎的城镇去擦洗地板,并染上了梅毒。
他对于白种人的确是满怀敬意的。
过去别人教导他说白种人是他的主人,对此他至今深信不疑。
然而,无论哪一个白人(哪怕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不例外),当他望着一支黑人军队从身边开过时,都会想到同一桩事:
“我们还能愚弄他们多久?
他们倒戈相向的日子离现在还有多远?
”
真是怪有意思的。
在场的每一个白人心里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思。
我有,其他旁观者也有,骑在汗涔涔的战马上的军官们有,走在队伍中的白人军士也有。
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而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有那些黑人对此尚茫然不知。
看着这列一两英里长的队伍静静地向前开进,真好像看着一群牛羊一样,而那掠过它们头顶、朝着相反方向高翔的大白鹳恰似片片碎纸在空中泛着点点银光。
Unit3InauguralAddress
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个政党的祝捷大会,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
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件。
因为刚才我已依照我们的先辈在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拟好的誓言在诸位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当今的世界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
人类手中已掌握的力量,既足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足以结束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
然而,我们的先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至今仍未能为举世所公认。
这信念就是认定人权出自上帝所赐而非得自政府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未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接班人。
此时此地我谨向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宣告:
火炬已传到我们新一代美国人手中。
这一代人在本世纪成长起来,经受过战火的锻炼,经历过冷峻的和平的考验,以珍视古老的传统而自豪,又决不愿坐视或容许人权逐渐遭到践踏。
美国对这些人权一向负有责任,今天我们也正在本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为之奋斗。
必须让每一个友邦和敌国都知道:
为维护自由,使其长存不灭,我们将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战一切困难,援助一切朋友,反击一切敌人。
以上这些是我们保证要做到的——但我们保证要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精神渊源的传统盟邦,我们保证将报之以真诚不渝的友谊。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许多合作性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胜;而一旦彼此分裂,我们就会无所作为。
因为我们之间若起争端,彼此离异,便难以与我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抗衡。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国家行列的各新兴国家,浅们发誓,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应仅是为了被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所取代。
我们并不期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他们始终能够坚决地卫护自己的自由,并时刻牢记,过去那些企图骑上虎背为自己壮声势的愚人结果都没能逃脱葬身虎腹的命运。
对于那些居住在遍布半个地球的茅舍荒村中,正奋力冲破集体贫困的桎梏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自救,不管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共产党会抢先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获得那些国家的赞成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一个自由社会如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国家,我们要作一项特别的保证:
把我们美妙的言辞付诸行动,为谋求进步而进行新的合作。
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政府挣脱贫困的锁链。
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
要让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反对外国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或颠覆。
也要让所有别的国家知道,我们这个半球仍得由自己当家做主。
在一个战争因素远远超过和平因素的时代,对于我们唯一的最好的希望赖以寄托的世界主权国家的联盟组织一一联合国,我们重申对它给予支持的保证:
阻止其成为一个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新兴国家及弱小国家的保护作用,并扩大其职能范围。
最后,对于那些不惜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要提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呼吁:
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努力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将整个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发生的自我毁灭之时。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
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无可置疑的足够的武力时,我们才能有无可置疑的把握避免使用武力。
然而,目前的局势使两大国家集团都感到不安——双方都因现代军备的庞大开支而感到不堪重负,双方都为极端危险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慌不安,但双方又都在竞相谋求改变那种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最后决战的小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记住:
礼让并不表示软弱,而诚意则永远需要验证。
我们决不能因为惧怕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惧怕谈判。
让双方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要在引起分歧的问题上徒费精力。
让双方进行首次谈判,对监督和控制军备制订出严格可行的计划?
并且把足以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致力于揭开科学的奥秘,而不是科学的恐怖。
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探测星空,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洋底,并促进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一起在世界各个角落听取以赛亚的指示,去“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
如果初次的合作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的话,那就让我们双方进而开始新的合作吧,不是寻求新的力量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有法制的新世界,使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得以维持。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第一个一百天内完成,也不会在第一个一千天内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
但我们要让它从我们手上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不仅仅是握在我的手中,更大一部分是握在你们手中。
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应召验证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应召服役的美国青年的坟墓已遍布全球。
如今那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
它不是在号召我们扛起武器一一尽管我们也需要武器,不是在号召我们去参战——尽管我们也准备应战,而是在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忍受困苦,向往未来”,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而斗争。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的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