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docx
《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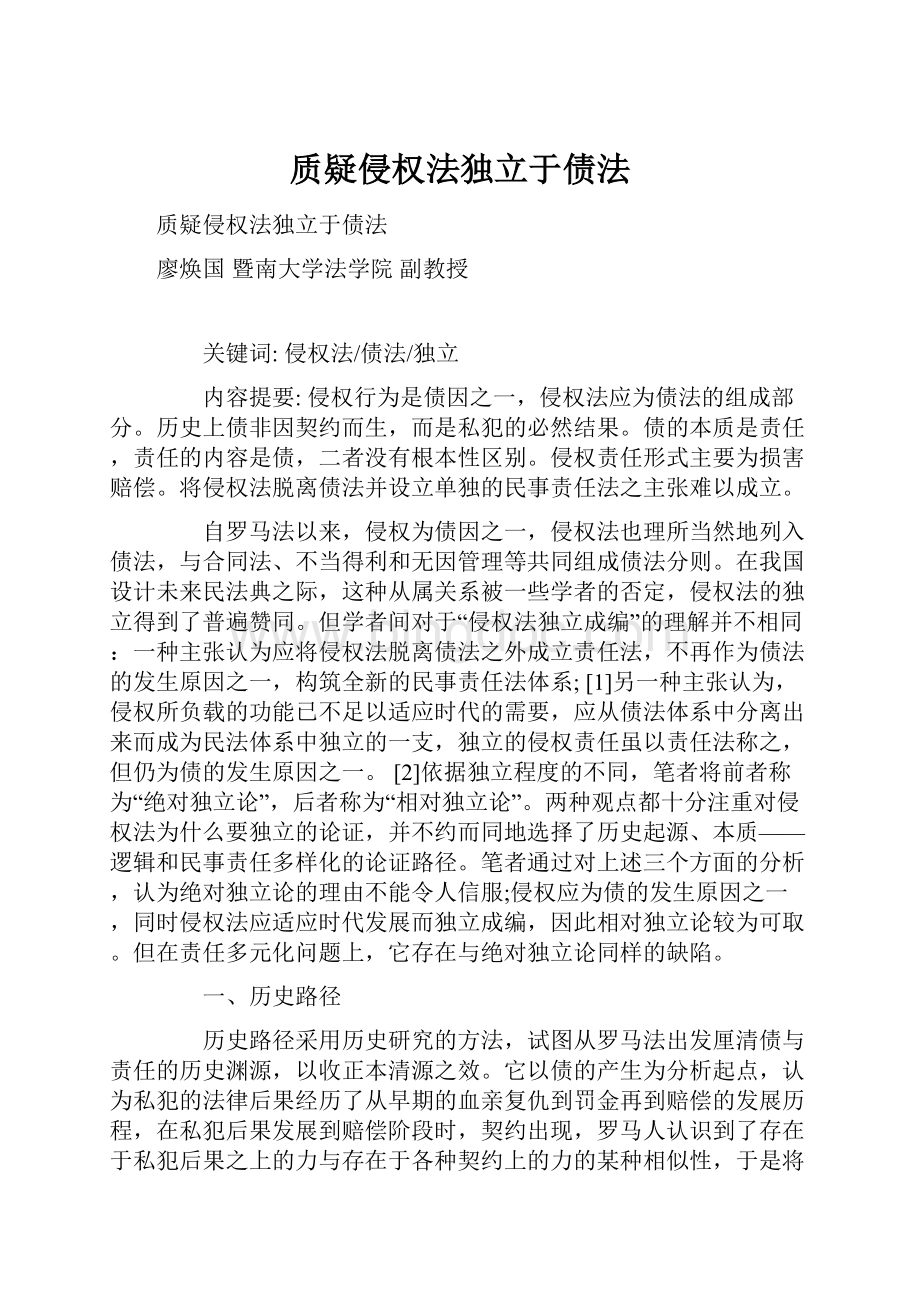
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
质疑侵权法独立于债法
廖焕国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
侵权法/债法/独立
内容提要:
侵权行为是债因之一,侵权法应为债法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债非因契约而生,而是私犯的必然结果。
债的本质是责任,责任的内容是债,二者没有根本性区别。
侵权责任形式主要为损害赔偿。
将侵权法脱离债法并设立单独的民事责任法之主张难以成立。
自罗马法以来,侵权为债因之一,侵权法也理所当然地列入债法,与合同法、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等共同组成债法分则。
在我国设计未来民法典之际,这种从属关系被一些学者的否定,侵权法的独立得到了普遍赞同。
但学者间对于“侵权法独立成编”的理解并不相同:
一种主张认为应将侵权法脱离债法之外成立责任法,不再作为债法的发生原因之一,构筑全新的民事责任法体系;[1]另一种主张认为,侵权所负载的功能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应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独立的侵权责任虽以责任法称之,但仍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
[2]依据独立程度的不同,笔者将前者称为“绝对独立论”,后者称为“相对独立论”。
两种观点都十分注重对侵权法为什么要独立的论证,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起源、本质——逻辑和民事责任多样化的论证路径。
笔者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认为绝对独立论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侵权应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同时侵权法应适应时代发展而独立成编,因此相对独立论较为可取。
但在责任多元化问题上,它存在与绝对独立论同样的缺陷。
一、历史路径
历史路径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试图从罗马法出发厘清债与责任的历史渊源,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它以债的产生为分析起点,认为私犯的法律后果经历了从早期的血亲复仇到罚金再到赔偿的发展历程,在私犯后果发展到赔偿阶段时,契约出现,罗马人认识到了存在于私犯后果之上的力与存在于各种契约上的力的某种相似性,于是将从另一个角度发展起来的私犯也归入债的渊源,侵权于是成为债的一个发生原因,因此“侵权行为作为债因不是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罗马人认识上的一个历史性误解”。
[3]
但精于法律思辨的罗马人是否轻易犯下如此严重的“历史”错误?
笔者对此心存疑惑。
事实上,罗马法起初并不区分公犯与私犯,统称为犯罪,并将其认为“是债的真正的和唯一的渊源”[4]。
在罗马王政时期将犯罪区分为私犯与公犯之前,所有的损害均为私犯,采取自力救济,并以此私人救济发挥刑事制裁的功能。
随着王权的加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刑事制裁不断扩张,导致同一行为(如盗窃)可获得两种惩罚性制裁,二者在一段时间内并行不悖,但刑事责任的扩展,使得自由报复逐渐绝迹,对人身的报复渐渐地向财物移转,人身仅是第二意义上的担保。
“法律规定首先应当要求支付罚金或债款,只是当根据债务人的财产不能给付或清偿时,权利人才能通过执行方式对其人身采取行动;直到此时,债才第一次获得新的意义,即财产性意义。
”[5]可见,私犯的救济经历了由自由报复向赎罪金发展的过程。
此时私犯的自力救济虽已纳入国家法律调整的范围,但因赎罪金是为了替代同态报复而出现的,因此它仍然保留明显的惩罚性特点。
“对于所有的私犯所产生的后果,均被认为是‘债’或者‘法锁’,都可以用金钱支付为补偿。
”[6]由此可知,债的分类虽然在安东尼时代(公元2世纪)才告完成(许多学者认为债在此阶段才产生),但债的概念自私犯的产生之初即已出现,它经历了人身刑和赎罪金等形式,直到今天仅具有财产意义上的债。
契约的产生晚于侵权行为。
一般认为罗马法上的契约源于债务口约(nexum,耐克逊),基于债务口约而产生的债务若没有清偿,已经取得人身支配权的债权人就可以将债务人作为奴隶。
可见债务口约将人身作为契约履行的担保,后来对人身的执行由于受到罚金刑的影响而逐渐消失,人们用金钱赔偿来代替人身刑,人身刑沦为罚金下的第二位的责任。
故学者认为,“契约责任在初期从属于这一概念(罚金刑)”。
[7]还有学者认为,“早期法可能只不过一种不加区分的债的概念,……契约的起源或许存在于两种债中,一是要式行为,另一个是非要式行为的给付或者转让。
”[8]可见,在契约出现之前债之概念已存在,若依据现代债法以契约法为中心的事实推断债法是因契约而生的,则难免会出现主观臆断的错误。
由于私犯与契约的救济均为罚金刑,罗马人于是依据法律效果的相同性(GeleichheitderRechtsfolgen)扩大了债的范畴:
每个债或者产生于契约,或者产生于私犯。
通过进一步的发展,罗马法上“债”(obligatio)获得较为稳定的涵义:
“债权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获得役权,而在于其他人必须给我们某物或者做或者履行某事”。
[9]
责任在罗马法上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
区分债务与责任的,首推日耳曼法。
在日耳曼法中,债务为Schuld,属于法的当为(RechtlichesSollen),不含法的强制(RechtlichesMuessen);而责任债务人当为给付而未为给付或者未为完全给付者,应服从债权人之强制取得的关系,该种责任附着于债并担保债权的实现。
可见,债务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的财产担保。
依据日耳曼法上的责任概念,罗马法上的债即含有责任的因素。
故基尔克认为,罗马法上的债的观念,并没有区别债务(Schuld)与责任(Haftung),而是融合二者而成为一个单一的“Obligatio”。
[10]从责任形态来看,最初有“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
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责任逐渐淡出,物的责任或财产责任成为责任的唯一形态。
财产责任进一步分化:
特定财产责任发展为担保物权,一般财产责任附随于其总债务,于是债务与一般财产责任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一般财产责任在观念上乃成为债权之效力或其作用之一部,两者并无区别之必要的思想遂普遍发生。
可见,即使债与责任在概念上的区分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实难区分。
后续的发展状况与罗马法相比虽然有了改观,但在债与责任的混同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上可知,债与私犯同时发生,而契约仅在罚金刑阶段丰富了债的内容。
不是由契约催生了债,而是相反。
债与责任的区分虽然有助于廓清概念,但体系上的功能却付之阙如。
德国民法即根据萨维尼的理论,将责任包含在债的效力之中,民法典不采纳民事责任。
就此而言,试图从历史起源的角度论证侵权行为独立于债法是行不通的。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除了获得历史真实面貌之外,还有两点收获:
一是侵权责任应仅限于财产(物),因为只有在此范围内的责任才是可强制执行的,这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经验法则,应成为我们设立责任形式的根本出发点;其二,由此可推断,所有民事责任都应是债,并以财产作为履行的最后担保。
二、本质和逻辑路径
与历史路径不同,本质和逻辑路径认为债与责任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现代民法虽然在概念上区分了二者,但在体系上却没有一以贯之,侵权行为产生的是责任而不是债,责任不能再转为债。
[11]因此应建立总分结构的民事责任体系。
具体而言,在民法总则部分设立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在债编总则部分规定违反债的责任的一般规定,而侵害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绝对权的责任规定在侵权行为编,侵权的损害赔偿可准用关于债编通则的规定。
与历史角度考察相同的是,侵权行为独立成编以后,“从性质和逻辑关系上看,侵权行为不再是债权的发生依据之一。
”[12]
当代民法理论界对债与责任的关系意见不一,主要有“合一”论与“分立”论两大对立派别。
“合一论”认为,债与责任二者可以分离,但二者以合一存在为原则,责任为债务的影子。
[13]“分立”论则认为,责任是不履行债务的后果,如果债务人履行了债务,就无责任可言,实践中通常是债务人自动履行债务,而没有责任,少数情况下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产生责任;应当说“责任与债务相分离为常态,合一存在是例外”。
[7]两说各有合理性和支持者,若在民法范畴内循环反复,很难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故我们借助法理学上有关责任研究成果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法理学上看,责任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责任等同于“地位”。
这一意义上的责任一语通常是指一种地位、一种职务所要求的应做的事(或行为),或者在一种特殊情势下、一种特定情况下的使命或应做的事(行为)。
其二,责任是指包括惩罚和赔偿的不利后果,即在多数场合,法律责任的含义指的是行为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所应承担的后果。
其三,责任等同于“义务”。
“法律责任就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
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做相反行为时应受到制裁。
”[14]我们认为,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约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
将责任的本质定义为第二次义务,既说明了法律责任的必为性,又说明了法律责任的当为性;同时,它还表明了二者之间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和时间上的相继性,也给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责任是无人格差别的,而义务总是依附于具体的法律角色。
此外,采纳该概念可以较为便利地解决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与衡平(公平)责任的难题,并对违反契约责任引发的损害赔偿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民法领域,责任主要用于两种较为典型的场合:
一是债务人应以其全部财产为其债务负责;二是一个人应依法行为,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为他人之行为引起之损害负责。
[15]第一种责任为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是对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制裁,为债务(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在实务上最后以诉权和强制执行作为债权之实现的后盾;第二种责任系债务履行的担保,即为一种民事义务,为债务成立后的结果,实质上为一定之义务违反后的效力或延伸的义务,亦称为第二次义务。
民法范畴内的责任应指一个人应依法为其行为,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为他人之行为引起之损害负责。
这种责任系债务履行的担保,本质上为一种民事义务,即第二次民事义务。
除了阶段上的相继性与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外,第一次义务与第二次义务并无本质差异。
若不主动承担此种义务,将导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如发动诉讼或申请强制执行,具有联结私人义务与国家强制(诉权)的桥梁或中介作用。
由上可知,责任以债之不履行为发生的停止条件,而责任的内容本质上不过是带有当为性与必为性的债。
虽然在时间上和逻辑上存在若于差别,但在本质上却相互构成彼此的内容,故二者是应以“合一”为原则,以“分立”为例外。
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将二者结合乃各法域之惯例。
各立法例莫不是将责任转化为债,通过债的一般规定,使责任得到实现。
《民法通则》将责任予以独立,是为了“既不否认侵权行为是债的一种发生根据,又突出债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性质”,[16]即侵权行为的后果是责任,但应通过债实现。
在司法上,一方面,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同样可由当事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时完全适用债的一般规定,而没有必要另设责任的一般规定,以免徒增繁复;即使法院判决损害赔偿责任,也是适用债法中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
另一方面,将债与责任分离,容易造成本权与救济措施的分离,增加法律适用的难度。
由此可知,“责任不能转化为债”的观点实难立足。
从本质角度将债与责任区分,并通过逻辑推演技术得出侵权行为应独立于债法,也是行不通的。
三、责任形式路径
在我国学界讨论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主张将侵权责任法独立于债法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
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情形下,侵害民事权利如人身权、知识产权等的方式越来越多,因此除了传统的损害赔偿外,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实际履行等就成为了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对民法体系提出了挑战,除了损害赔偿之外其余责任形式均非债法所能涵盖,故侵权责任法独立于债法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该理由不但为绝对独立主义者所持,也为相对独立主义者所采,[17]堪称当今通说。
侵权的后果与违约等其他债权的“形式共同性”,是侵权法归入债法的结构要素。
产生债权的原因也许千差万别,但最后的结果都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由此构筑起来的民法债权体系才具有形式理性。
若这一共同的基础已经动摇,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则将侵权法置于债法或者维持债法总则便不合时宜了。
因此,有必要对所谓的多样化的民事责任形式加以探讨。
如前所述,侵权责任经历了从人身刑到罚金再到损害赔偿的发展过程。
“古代法之强使债务人服役,或以之为奴隶出卖,而以其所得清偿债务,或拘押债务人,而迫其亲友代为清偿之手段,在今日已经摒弃不用。
”[18]现代民事责任仅能以财产为对象而设立,不论侵权责任抑或契约责任概不能例外。
换言之,债之给付应当具有经济价值,债务人应当以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全部财产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19]这一历史的巨大进步是人类的宝贵财富,理应成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基础。
从财产价值角度观察,所谓的“民事责任”不外乎通过两种法律后果体现,即“现有价值维持”与“损失价值弥补”。
这两种法律后果具有以下差异:
首先,价值维持的实现手段有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等;价值补偿则主要为损害赔偿。
其次,从适用对象来看,价值维持为绝对权的特有保护方式,主要适用于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含占有)、知识产权和其他支配权。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系物上请求权,它们除了能有效保护物权外,还可广泛用于与物权类似的民事绝对权益。
姓名权、占有权、商号权、商标权、特许权、著作权、渔业权、矿业所有权、专卖权、居住权等均承认妨害除去与妨害防止的效力。
损害赔偿既用于绝对权益受到损害的价值转化性补偿,同样适用于相对权益的损害补偿。
再次,就实现方式来看,价值维持所指的并不是一种不作为的请求权,而是指权利人可提起不作为之诉,即赋予受害人一方请求法院实施某种“禁令”。
[20]而损害赔偿的实现,一般需要加害方具备相当的条件才能得到认可。
复次,从基本功能角度视之,价值维持所衍生的请求权与原权利相伴而生,不能与原权利分离而单独转让,因此被称之为“非独立的请求权”,具有服务和防御功能;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不为其他权利而存在,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可与原权利相分离而单独作为让与的标的,故为“独立的请求权”。
最后,从性质特点角度来看,为实现价值补偿目标而设立的损害赔偿是因违反第一次法定或约定义务导致的第二次赔偿义务,即在原来债务上增加的实体意义的责任。
而价值维持是针对尚未发生的损害而设立,它通常不能以财产价值来评价,故与当事人的一般财产或责任财产并无必然联系。
由上可知,价值维持义务手段除了返还财产外,其余均与给付无关,不宜将价值维持衍生的请求权置于侵权法中作为侵权责任形式加以规定。
而返还财产是在标的物依然存在和完好的前提下的给付,其虽有一般给付之名,实为债权人之财产而与当事人的责任财产并无联系,故不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
价值维持手段应通过分散性的绝对权请求权方式予以确立,如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等。
除上述价值维持衍生的请求权外,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均为价值补偿性的请求权,但是否均属于责任形式,则值得斟酌。
恢复原状是指加害人或债务人负有义务,必须制造一种宛如造成损害之原因事实从来没有发生过,被害人或债权人现时或将来所应处的状态。
它是依据价值补偿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基本赔偿原则与方法。
我国有学者将恢复原状作为物权请求权的内容,作为一种与损害赔偿对立的独立请求权。
[21]实际上,物权请求权虽然以回复物之圆满状态为目的,但其与恢复原状是不同的。
恢复原状的基准是建立在现时的(或将来的)与假设的观点上,而物权请求权则建立在过去的与现实的观点上。
具体而言,负有排除侵害义务之人,只要将造成侵害状态加以排除,将权利客体恢复到过去未受到侵害所存在的权利状态即可;相对地,恢复原状责任之人除了必须将遭受侵害之权利客体修补完好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填补被害人或债权人自受到侵害时起至进行恢复原状时止或将来因侵害之原因事实在财产上所产生的变动。
[22]但这种财产上所产生的变动并非现实的,而是假设的。
如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而休假一个月,这个月所预期的工作收入,被害人始终并没有现实取得,但仍在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之内。
故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财产上的结果责任”(Vermoegensfolgeschaden)[23],而物权请求权只能称为财产上的排除责任。
由此可知,恢复原状属于损害赔偿的范畴,应无疑问。
但由于恢复原状是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同时还决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故从属于损害赔偿,而不能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与损害赔偿并列。
有学者将之称为“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请求权”[24],不失为准确。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一般为保护人格权而产生的请求权,它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的责任效果。
虽没有体现财产给付的内容,但它本质上仍然属于债的范畴,并以当事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债之履行的最终担保,故仍然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
惟其是指采取某种措施后所获得的社会效果,而不是某种直接的责任形式,在实践中可看作损害赔偿的一种变态,不宜作为独立的责任形式。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叙述了采取特定损害赔偿措施后的效果,这些特定的措施包括判决当事人承当费用登报公开判决书或反向报道澄清事实等。
赔礼道歉是《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民事责任形式,它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有一定的类似性,都可以转化为财产责任,故本质上是一种“债务”。
不同的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是要求加害人承担与加害行为反向的作为,如反报导、刊登判决书等;而赔礼道歉则除了有上述要求外,通常需要加害人书面或口头对自己的加害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若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看成是采取某种具体措施所获得特定社会效果的话,则赔礼道歉就是一种带有浓厚人身性与道德伦理色彩的强制措施。
且不说赔礼道歉具有人身性和不可强制性特点,不符合民法责任可诉性的本质;就其存在本身而言,就是对民事责任只涉及财产责任原理的一种历史倒退。
若强制一方赔礼道歉,则无异于保护一方的同时而伤害不愿赔礼道歉的另一方的人格权。
事实上,赔礼道歉所需承载的伦理意义和社会意义,已经由法庭审判和判决书得到张扬,可将其公开发表以正视听;至于当事人的精神创伤,只能通过一定数额的赔偿加以抚慰,故赔礼道歉无须也不能作为侵权责任形式。
人类社会跨越农业和工业社会而迈入信息社会,侵权形式将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但侵权责任形式是否也随着多样化,则值得怀疑。
因此,从责任多样化的角度论证侵权责任法应独立于债法也难以令人信服。
四、结语
侵权法独立于债法的三条道路均不能给予绝对独立论以有力的支持。
所谓侵权法的独立成编,只能是在债法的范围内的独立,即相对独立。
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债权法的膨胀,出于对民法典各编形式上的考虑,将侵权法相对独立,在维持债权法内部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同时,能培养侵权法的开放性性格,值得一试。
注释:
[1]魏振瀛.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J].中外法学,2001,(3).
[2]王利明.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J].侵权法评论,2003,
(1).
[3]麻昌华,罗马法上的侵权行为法[A].私法研究(3)[C].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27.
[4][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01
[5][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84,
[6][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208.
[7][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84
[8][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
170-171.
[9][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83.
[10]转引自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06,222.
[11]魏振瀛.论债与责任的融合与分离[J].中国法学,1998,
(1).
[12]魏振瀛.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J].中外法学,2001,(3).
[13]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
[1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73.
[15]黄茂荣.债法总论(第一册)[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4.
[16]佟柔.中国民法学[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0:
562.
[17]王利明.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J].侵权法评论,2003,
(1).
[18]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28-329.
[19][意]米拉拜利.论自然之债[A].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C].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77.
[20]杨良宜.禁令[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9.
[21]王利明.合久必分:
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A].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C].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48-349.
[22][德]Esser/Schmidt.SchuldRechtI/2[M].Muechen:
C.H.Beck,1984:
229.
[23]王千维.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法上因果关系之结构分析以及损害赔偿之基本原则[J].政大法学评论,1998(60).
[2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50.
出处: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