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docx
《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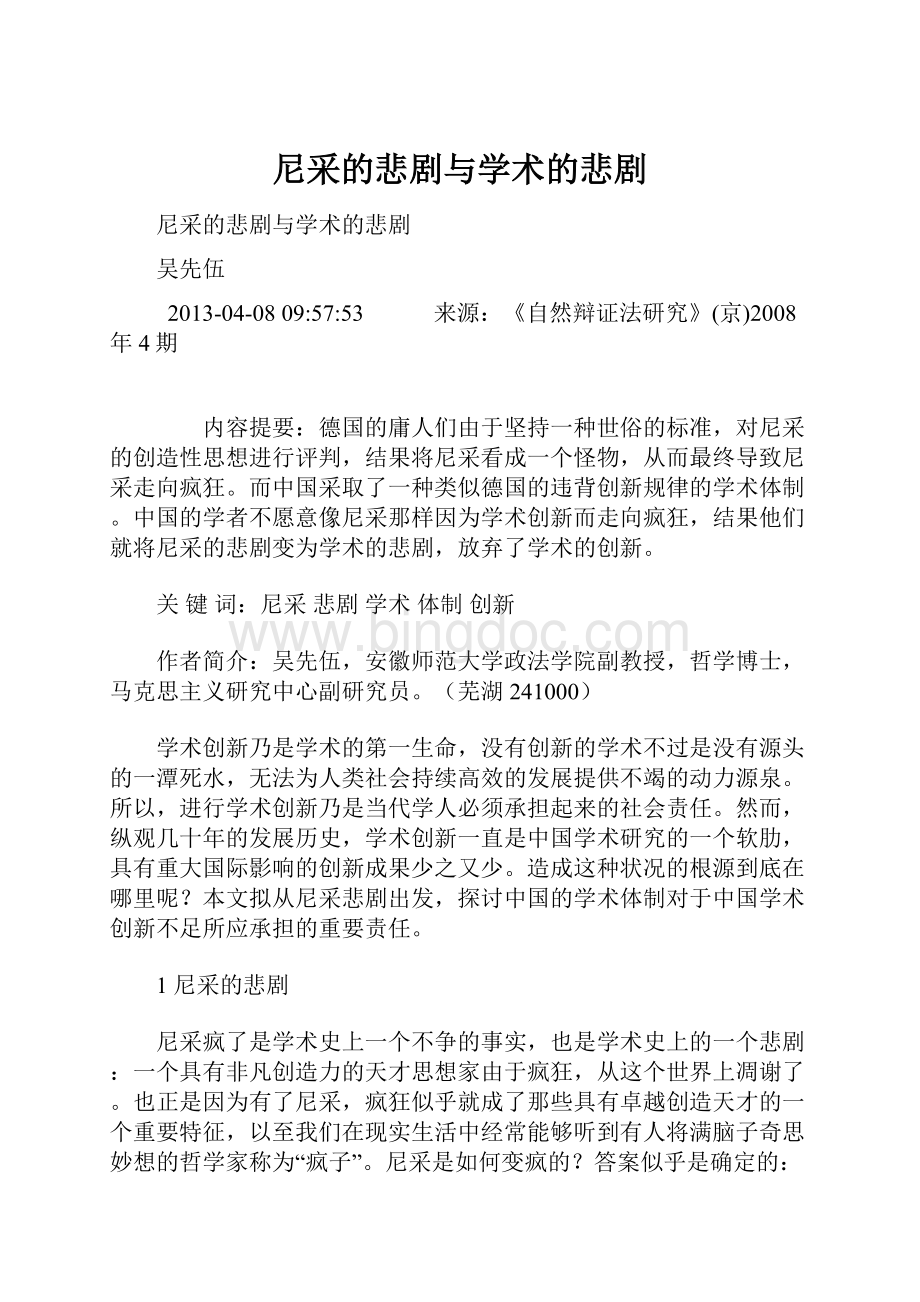
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
尼采的悲剧与学术的悲剧
吴先伍
2013-04-0809:
57:
53 来源:
《自然辩证法研究》(京)2008年4期
内容提要:
德国的庸人们由于坚持一种世俗的标准,对尼采的创造性思想进行评判,结果将尼采看成一个怪物,从而最终导致尼采走向疯狂。
而中国采取了一种类似德国的违背创新规律的学术体制。
中国的学者不愿意像尼采那样因为学术创新而走向疯狂,结果他们就将尼采的悲剧变为学术的悲剧,放弃了学术的创新。
关键词:
尼采悲剧学术体制创新
作者简介:
吴先伍,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芜湖241000)
学术创新乃是学术的第一生命,没有创新的学术不过是没有源头的一潭死水,无法为人类社会持续高效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所以,进行学术创新乃是当代学人必须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
然而,纵观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学术创新一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软肋,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创新成果少之又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本文拟从尼采悲剧出发,探讨中国的学术体制对于中国学术创新不足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1尼采的悲剧
尼采疯了是学术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个悲剧:
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思想家由于疯狂,从这个世界上凋谢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尼采,疯狂似乎就成了那些具有卓越创造天才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有人将满脑子奇思妙想的哲学家称为“疯子”。
尼采是如何变疯的?
答案似乎是确定的:
由于生理上的疾病。
著名的尼采研究者、存在主义大家雅斯贝尔斯说,“这样一种病态只是作为精神病才突然爆发的,它同官能性大脑疾病有关,极有可能同渐变性脑软化有关。
”[1]93著名的尼采传记作家哈列维,甚至有意在《尼采传》中提及尼采的父亲“患了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以暗示尼采后来变疯具有家族遗传因素[2]1。
而中国的尼采专家陈鼓应则猜测,“他的病,也许和他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短期的军中生活有关”[3]28。
由于这些研究都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确实可信的。
不过在笔者看来,仅仅从生理上分析尼采变疯这个悲剧是片面的、不充分的。
虽然尼采悲剧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但尼采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什么样的人应当归属于疯子一类?
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些具备了所谓疯子必备的繁杂的病理性特征的人,而是那些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不太正常的人。
当我们说尼采或一个哲学家疯了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尼采或那个哲学家是否具备了疯子所必备的病理性特征,而是看尼采或那个哲学家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否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相同。
如果相同,他们就是正常人;如果不同,他们就是不正常的人,甚至是疯子。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言行方式符合常规,与普通大众保持着高度一致,那么这个人就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言行方式不合常规,与普通大众迥然不同,一旦超出人们所能接受或容忍的范围,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甚至会被冠以“疯子”之名。
实际上,这种人并不是病理上的疯子。
譬如耶稣,在基督教征服西方之后,他就被当成了人类的英雄、智慧的顶峰,但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由于他的行为超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而被时人看成是不正常的、彻头彻尾的疯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与疯癫的体现”[4]71。
当然,耶稣可以不顾世人的讥讽而从容地走上十字架,因为他会用复活来教育世人,使人们对他做出重新认识与评价。
但对于一个凡胎肉身的人来说,他永远也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能够从别人的冷嘲热讽、鄙夷不屑当中摆脱出来,他将会因此而蒙上巨大的心理阴影,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
所以,当一个正常人因为世人的不理解而被冠以“疯子”之名以后,这种心理上的压抑很有可能转化为生理上的疾病,将他由一个“所谓的”(行为不合公众标准)疯子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生理疾病)疯子。
而尼采悲剧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符合众人的口味,不符合公众的标准。
毋庸置疑,尼采是一个难得的富于创造性的天才,他在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了过人之处,其老师李奇尔由衷地发出赞叹:
“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然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文学家。
他如今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俱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文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是个奇迹”,“无论什么,只要他想做,就能做到”[1]28。
他能在24岁的时候就在精英云集的巴塞尔大学担任教授,就是其创造性天才的明证。
然而问题在于,尼采是个创造性的天才,而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则是由因循守旧的“庸人”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尼采与世人之间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尼采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高出于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我是从高处下来的,而这个高处高到连飞鸟也飞不上去;我认识那些人类足迹从未到过的深处”[5]44,73。
庸人与天才之间这种巨大的差距,决定了庸人从那些保守的思想观点出发,永远也无法理解尼采这个天才的创造性思想。
然而问题在于,在一个由庸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尼采及其思想都必须接受庸人根据陈旧的思想观念所制定出来的是非标准的检验,结果在这些标准面前,尼采由于“出生得太早了”,“我的时代也还没有来到”,其思想也因此而显得“不合时宜”,有点不正常、有点疯狂[5]40,56。
或许正是出于对当时德国思想界的这样一种认识,尼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才思想——“上帝死了”,是借助于疯人之口表达出来的。
尽管尼采在学术上是个天才,但尼采毕竟也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人,他同样需要密切的人际交往来获得感情上的慰藉。
根据记载,在现实生活中,尼采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广交朋友,并且在朋友面前尽力表现得谦虚谨慎、举止得体,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平由学术所造成的自己与别人之间的距离,从而将自己很好地融入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当中去。
有时为了保持与朋友(如瓦格纳)之间的友好关系,尼采甚至会放下自己桀骜不驯的天性去屈尊逢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尼采并没有因为他的谦虚谨慎和对他人的友好态度,得到社会的接纳,庸人们由于无法理解尼采的新颖思想而将其视为怪物、疯子,并纷纷与他分道扬镳,离他而去。
尼采感叹自己在一个由庸人构成的世界里,无法找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与自己一起思考人类未来的志同道合的友人,“凡我所研究的、所关心的、强调的东西,我都未寻找到知情人与友人”,“我摔倒在你们的平庸之岸上,就像一层汹涌的波浪不由自主地渗透进沙土之中”[1]90。
世人的疏远使尼采成了孤家寡人,他开始感受到心灵上可怕的孤寂,“我需要人们,我寻求人们——我找到的始终只是自己——而我已不再需要自己”,“我很少还能听到友人们的声音。
此时我形影相吊,荒谬地形影相吊……多年来没有一点儿振奋精神的事情,没有一丝人情味,没有一丝爱的气息”[1]90-91。
这种状况对于尼采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摧残,他开始逐渐变得阴沉忧郁,甚至有点厌倦生命,“当我们孕育了自己的想法时,却根本没人支持我们,在艰难的分娩时刻也没人帮助我们:
这种时刻是那么的阴沉和忧郁。
我们只能将那些还很沉重和不成形的思想产生在某个黑暗的洞穴里。
友谊的阳光永远不会照耀到它们的身上”[2]53,“爱我的人都没有活下来,我怎么还能热爱生命呢!
”[1]91然而问题在于,尼采并没有因为世人的离去而改变自己的学术观念,而是在庸人的冷嘲热讽中艰难地承担着自己的学术使命。
当尼采由于创造性彻底崭露而导致朋友全部离他而去时,他的情感创伤最终将他引向疯狂。
尽管尼采拒绝承认自己精神失常,但他还是被疯狂所击中,并最终因此而丧命。
因而对于尼采而言,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则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一套正确评价独创性思想的体系,也没有为创造型思想家提供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2学术的悲剧
当然,尼采悲剧是学术史上的一个极端事例,现在可能没有人会因为其独创的学术思想而被逼上疯狂的绝境,但尼采悲剧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为尼采是一个创造的天才,是进行思想创新的学术典范,我们可以从尼采天才陨落的悲剧中获得如何对待创造性思想的有益教训,以便更好地为学术创新服务。
众所周知,缺乏学术创新一直是困扰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问题。
虽然近年来各级部门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鼓励学术创新,但成效甚微,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性学术成果都难觅其踪,“作为科学技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生命科学类的‘优秀论文总量仍不到世界的百分之一’,‘有些当代科学重要研究方面,中国达不到世界的千分之一’,学术创新成果之少可见一斑”[6],代表着学术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人将责任归咎于学术研究主体,认为当今中国的专家学者存在着“底蕴不深、眼光不敏、胆力不足、治学不勤”等等先天不足[7]。
不过在笔者看来,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有些人在国外就做出了大量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创新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也不乏其人,而在国内的就创造力全无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学术环境、学术体制,而这与尼采悲剧发生的根源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如前文所述,尼采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用一些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作为标准去对尼采的思想观念进行评价,结果尼采的独创性思想就成了疯人呓语、精神失常之人说出来的胡话。
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学术体制使用的是一套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它所使用的是一套与学术创新格格不入、至少也是一套不适合于学术创新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学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贯穿于学术研究过程始终。
选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
对于我国的学者来说,选题不取决于有所创新,而在于能否立项,因为选题被立项就意味着名利双收。
且不说“跑项目、买项目、卖项目”(何祚庥语)的普遍情况严重损害了立项的公正性,而这种立项本身就严重妨碍了学术创新。
为了能够立项,学者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术领域,去追逐一些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且不说自己对这个热点并不熟悉,而且追逐热点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在炒别人的剩饭了,那么,去研究这样的项目还能有什么创新可言。
另外,项目都是规划性的,有些规划可能要长达几年的时间。
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学术创新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邹承鲁院士在谈到自然科学研究时说:
“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又有它的不可预见性。
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领域、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
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精心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
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计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
[8]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亦然。
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说,在写出一部作品之前,就连作者自己都无法预料将要写出来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
当代英国闻名全球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也说,自己完成了一本著作之后,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研究什么主题、写出什么样的著作来。
这些都说明,所谓严密的研究规划恰恰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对创造性的扼杀,因为学者们最终无法跳出规划的魔咒进行研究。
难怪李醒民研究员不无忧虑地指出:
“须知,除了某些应用性和针对性较强的课题可以拟定规划外,大多数学术研究是无法计划的。
学术研究是探索性极强的活动,欲达目标和最终结果事先难以预料,研究过程变化多端,计划反倒容易忽视突发的灵感,坐失启示的良机,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
”[9]
任何一个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都是人们长期探索的结果,虽然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阿基米德原理,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故事暗示着有些重大的理论发现源自于人们的灵光乍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机遇性,但是机遇只会青睐那些有所准备的人。
这也就是说,学术创新离不开长期的积累和艰苦的探索。
然而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再也无法容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古老遗训。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每年都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考核、评估,每年都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论著来完成所谓的科研工作量,而这些又是与利益分配、职称等挂钩。
学术界为了适应这种学术体制而变得日益功利、浮躁,没有人再能潜心于学术了,无人再甘愿忍受寂寞去坐冷板凳了。
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去炮制文字垃圾以求滥竽充数之功效。
因而我们国家经常会产生大量一年发表几十篇论文、一辈子发表几百篇论文和几十本著作的文章高手,但他们对于学术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他们没有一篇文章、一段文字能被别人记起。
即使有些学者忍受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寂寞,劳精伤神地做出了一些创新成果,但它仍然极有可能会被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所扼杀。
因为既然是创新成果,那么它就是一些“人所不知、人所未讲的东西”(李醒民语),就会与传统的思想观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决定了我们要对它做出准确认识与判断,就殊非易事,即使我们是某个领域当中的顶尖级人物,恐怕也未必能对一个创新成果有准确的认识与判断。
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已经适应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人们(包括那些专家们)就觉得无法理解;当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那些在革命弟兄情谊中熏陶长大的人们就忍不住斥之为法西斯主义。
不但学术创新成果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人们难于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那些大权在握的评价者自身的素质也决定了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学术创新成果。
当今负责进行学术评价的,似乎并不是一些埋头于研究的纯粹的专家学者,而是一些喜欢拉关系、跑关系、四处露脸的“学术明星”(李醒民语)和大权在握的行政人员。
所以,邹承鲁院士批评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一方面,一线科技工作人员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表达。
虽然在决策前也通常经过所谓同行评议,但整个过程接受广大科学界的监督不够,如同在评议中从同行的‘选择’开始,一些懂行而不听话的专家常常被推到不参与评审,并且没有发言权的位置。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个人因素,科技界的专业标准就会被人际政治所代替。
另一方面,同行评议既然流于形式,服务人员就反而成了统治者”[8]。
既然这些主持学术评价的学术明星和行政人员本身对于学术没有精深的研究,自己又缺乏创新精神,那么他们只能拿着一些陈旧的学术标准去对那些创新成果进行评价。
那么,就不难想像,那些富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必然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无稽之谈,恐怕永远要被埋没在故纸堆中,再也没有得见天日的时机了。
这样一种僵化的学术体制,必然会限制人们的学术创新,至少会遏制人们学术创新的积极性,因为进行学术创新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极有可能使学者名利双损。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能否创新关键还在于研究者自身,尼采生活的时代,学术创新的环境也是非常恶劣的,但尼采还是贡献了大量创造性的成果,所以研究者应该在自己的精神境界上下功夫,自觉地排除一切外在干扰,坚定地走学术创新之路。
李醒民研究员就强调:
“学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诸如自由而宽松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必要的经济支持,健全的信息资料等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人要保持内心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墨守成规,不迷信古人、洋人和权威,不在乎权力和金钱,不随风赶潮流追时髦,不做某些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和代言人。
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境界,加上你的知识基础、治学经验和才气,再下它一二十年的真工夫,我就不信你在学术上搞不出一点新名堂来。
”[9]虽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下,这种愿望极有可能落空,因为中国与德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学者不会像尼采那样,以疯狂为代价进行学术创新。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每个学者都自觉地承担着一种学术使命,因而德国的学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特点,具有一种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
正因如此,尼采才能不顾世俗的标准,进行学术创新,即使以变疯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然而中国人向来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实用理性”(李泽厚语),“立言”总是被排在“立功”之后,著书立说总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连孔子也是在周游列国、求官不得之后,才开始整理《诗》《书》,删修《春秋》,做一些纯粹学术性的工作。
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专家学者不可能为了学术而去牺牲自己的名利,更不会为了学术创新而甘愿成为社会的另类,甚至将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很少有人像尼采那样为了学术而甘愿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况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进行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著书只为稻粱谋”乃是学者们的真实人生处境。
如果一些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能够为学者铺就一条鲜花遍地的人生坦途,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责备学者不去走一条充满坎坷与荆棘的创新之路呢?
既然学者们不愿尼采的悲剧变成自己的悲剧,那么学者们就会将尼采的悲剧转化为学术的悲剧,也就是说,大家为了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宁愿顺应潮流而放弃学术创新。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想使创新成为学术界的一种风气的话,就不能寄希望于学者自身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应该从变革学术环境,尤其是从变革学术体制入手。
第一,增强学术的包容性,使各种学术观点都能充分地得到表达和关注,尤其关注那些与通行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
第二,鼓励自由探索。
在集中人力和物力于少量热点、重点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大对于自由探索的投入,激发人们的研究、创新热情。
第三,完善评价体系,使评价系统符合学术规律,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要使真正的学者加入到评价过程当中,降低非学术人员在学术评价当中的作用。
如果学术创新变得有百利而无一害,能够达到社会与个人双赢的效果的话,那么专家学者们就能静下心来进行学术研究,学术创新就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涌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卡尔•雅斯贝尔斯.尼采其人其说[M].鲁路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M].谈蓓芳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3]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尼采.尼采文集[C].楚图南等译.北京:
改革出版社,1995.
[6]秦国民.教师的学术创新成果为什么少了?
[N].科学时报,2003-04-15.
[7]乔松楼.到底是什么影响了科研和学术创新?
[N].北京日报,2003-09-29.
[8]邹承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N].科学时报,2006-06-16.
[9]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N].光明日报,200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