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docx
《《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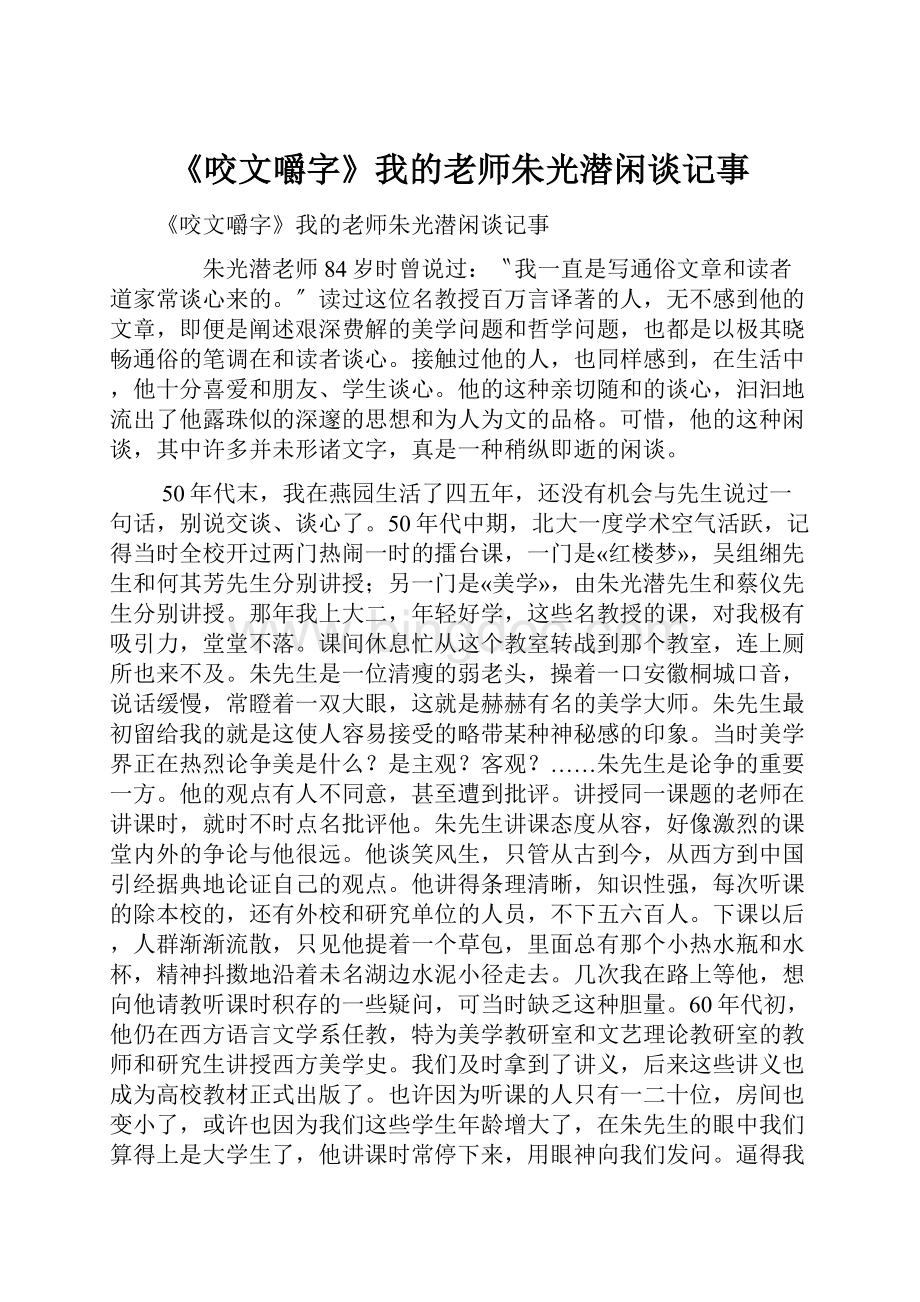
《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
《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
〝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
〞读过这位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
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
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
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别说交谈、谈心了。
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
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
课间休息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
朱先生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
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
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
是主观?
客观?
……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
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
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
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
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
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
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
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也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
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
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
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
那时他还住在燕东园,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
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
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
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
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
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
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
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
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
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
10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
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比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
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10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
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
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
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
20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
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
〝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
〞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
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
他常开玩笑说:
〝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
〞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
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
〝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
〞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
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
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
〝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他,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
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
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
我叫他:
〝朱老师!
〞他从遥远的想象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
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
他说:
〝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
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
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
〞我说:
〝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
〞他说:
〝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
走,回家去。
〞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
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
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50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
这很可惜。
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
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
50年前他写谈美12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
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
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
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在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体也锋利,自如活泼。
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写信给朱先生,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点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做结论。
他说:
〝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
他把他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
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
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
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
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
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
〝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
〞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
他想了一会,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
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
自传就要如实地写。
〞时下人们写回忆录,写悼念文章,写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溢美的多,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
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
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朱先生这篇«自传»。
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
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先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
说着说着,他突然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的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
他有篇文章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论述的一些理解。
他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研究,他期待有认真的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文章发表。
他说后来读到一篇批评文章很使他失望。
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清多少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对,应该如何理解,主要的论据是说关于这个问题某个某个权威早就这样那样说过了。
朱先生说,这样方式的论争,别人就很难再说话了。
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
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次他提出要我替他找一本浙江出版的«郁达夫诗词抄»。
他说他从广告上见到出版了这本书。
恰巧不久我去杭州和郁达夫家乡富阳,回来送他一本。
他很高兴,说达夫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过去读过一些,想多读点。
过后不久,有次我去,他主动告诉我这本书他已全读了,证实了他长久以来的一种印象:
中国现代作家中,旧体诗词写得最好的是郁达夫。
他说他有空想写一篇文章。
我说给«文艺报»吧。
他笑着说:
肯定又要引火烧身。
不是已有定论,某某、某某某的旧体诗词是典范吗?
他说郁达夫可能没有别人伟大,但他的旧体诗词确实比有的伟大作家的旧体诗词写得好,这有什么奇怪?
他强调对人对作品的评价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要因人的地位而定。
顺此他又谈到民初杰出的教育家李叔同,他认为李在我国近代普及美育教育方面贡献很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
他说李后来成了弘一法师,当了和尚,但并不妨碍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
他说现在有些文学史评价某某人时总爱用〝第一次〞的字眼,有些真正称得上第一次,有些那么因为编者无知而被误认为是第一次的。
他说很需要有人多做些历史真实面貌的调查研究。
我在«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朱先生看后建议我为北大出版社美学丛书写一本小册子,专门介绍李叔同在美学上的贡献。
我答应试试。
为此还请教过叶圣老,他亦鼓励我完成这本书。
朱先生这几年多次问起这件事。
他说:
〝历史不该忘记任何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人。
〞
朱先生虽然长期执教于高等学府,但他主张读书、研究不要脱离活泼生动的实际。
他很欣赏朱熹的一首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多次熟练地吟诵起这首诗。
1981年我请朱先生为我写几句勉励的话,他录写的就是这首诗。
他在递给我时又说起这首诗的末句写得好,意味无穷。
有次他谈起读书的问题,他强调要活读书。
他说现在出书太多,连同过去出的,浩如烟海,一个人一生不干别的,光读书这一辈子也读不完。
这里有个如何读和见效益的问题。
他认为认真读书不等于死读书。
他说,要从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范围出发,一般的书就一般浏览,重点的书或特别有价值的书就仔细读,解剖几本,基础就打牢了,20多年前他曾建议我们至少将«柏拉图文艺对话录»读三遍。
他举例说,黑格尔的«美学»是搞文艺理论、评论的人必须钻研的一部名著。
但三卷四册的读法也可以有区别,重头书里面还要抓重点,他说«美学»第三卷谈文学的部分就比其它部分更要下功夫读。
他说搞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必须对文学中某一样式有深入的了解和欣赏。
他个人认为诗是最能表达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
他喜欢诗。
他最早写的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文字,多举诗词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写过一组赏析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
40年代他在北大讲授〝诗论〞,先印讲义后出书,影响很大,前年三联书店又增订出版。
他在后记中说:
〝我在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
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做了探索分析。
〞他说我们研究文学可以以诗为突破口,为重点,也可以以小说、戏剧为重点。
总之,必须对文学某一样式有较全面、历史的把握。
否那么,写文艺理论和写文艺评论文章容易流于空泛。
朱先生很讨厌盲目吹捧,包括别人对他的盲目吹捧。
他希望读到有分析哪怕有尖锐批评的文章。
香港«新晚报»曾发表曾澍基先生的«新美学掠影»一文,我看到了将剪报寄给朱先生看,不久他回信说该文〝有见地,不是一味捧场,我觉得写得好。
〞他常谈到美学界出现的新人,说他们的文章有思想,有锋芒,有文采,他现在是写不出的。
他感叹岁月无情,人老了,思维也渐渐迟钝了,文笔也渐渐滞板了,他说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朱先生的记忆力近一二年明显有衰退。
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
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
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
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
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
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
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
〝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
〞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
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
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
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
最近忙不忙?
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
他说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
你提100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
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
他说:
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
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2019字一篇。
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写了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
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
他说,外国有一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
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
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
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
你再提98个题目便成了。
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谁的影响大?
这又是一个题目。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我不同意,为什么?
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
他笑着说:
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
我们约好冬天开始,叫我一周去一次。
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
朱师母说:
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
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吴泰昌)
(选自«梦里沧桑»,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