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讲给儿子的最短世界史讲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餐桌上讲给儿子的最短世界史讲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餐桌上讲给儿子的最短世界史讲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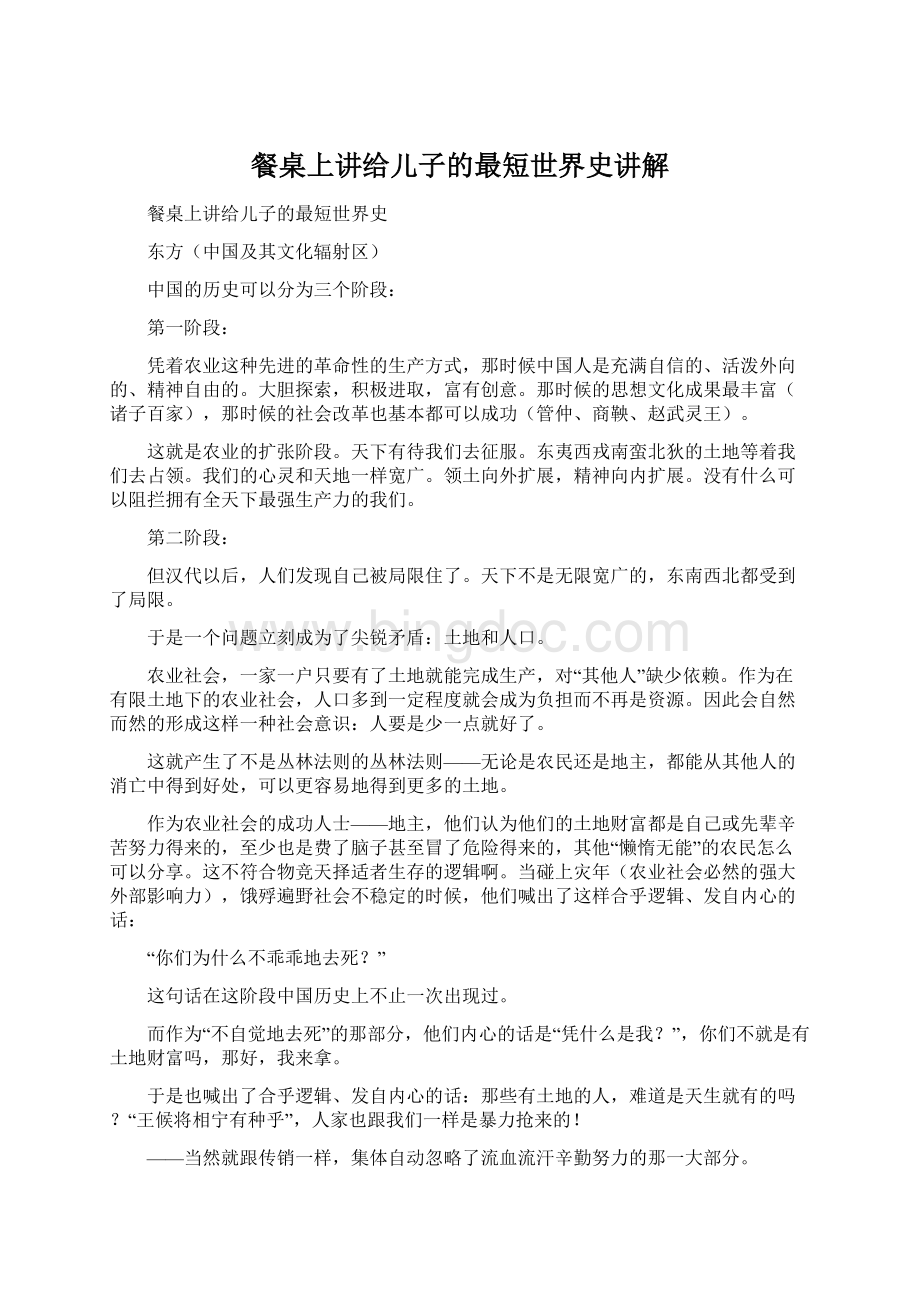
那些有土地的人,难道是天生就有的吗?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人家也跟我们一样是暴力抢来的!
——当然就跟传销一样,集体自动忽略了流血流汗辛勤努力的那一大部分。
丛林社会里头好人都不长命。
经过不断淘汰掉好人,逐步形成了“死道友莫死贫道”这样一种地区性格或精神。
秉着这种精神,农民们总是希望别人先出头,然后自己捡便宜。
(最好的情况就是,率先闹事造反的农民和地主同归于尽,那么大量的无主土地就归自己了)
于是农民们就相互比赛看谁先忍受不住——于是就形成了闻名天下的“中国人的温良忍让性格”。
被这种美好性格给惯出来的地主们,越发的肆无忌惮。
各种兼并和剥削,加上天灾人祸,终于到了让所有农民都忍不下去的地步。
于是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身份转换运动,从无土地人士转变为有土地人士。
造反、革命,形成新的以皇帝这个大地主为顶尖的土地分配金字塔。
于是又开始新一轮循环。
区别是上一轮的无土地人士变成了这一轮的有土地人士。
新循环开始时,因为经过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主要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此社会呈现和谐安定一团和气的面貌(土地有的是,抢什么抢!
)。
而且人们还普遍都残存着嗜血满足后的暴力因子,所以各方面都小心翼翼。
于是王朝兴盛了,人们富裕文明了。
于是人口又增加了。
矛盾又激烈了。
所以与其说这阶段是个死循环,不如说是个永不停息的翘翘板,今天你(或你的后代)在上面,明天我(或我的后代)在上面,社会就在这样的土地所有权互换的一起一伏中前进。
呃不对,是原地玩翘翘板。
任何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和变化(就连科技也在战争中湮灭),只有一些老掉牙的治国经验和生存智慧在反复——因此也节省了我们的时间。
至于中间的异族,多数是来搅局的,翘翘板的两端都不认。
蒙元直接把土地拿去放牧,让大家谁都玩不成,只好合力把他赶跑。
而女真人之所以两次成功*,是因为迅速地自觉融入了这个农业社会的游戏,当起有土地人士的代表,本质上跟起义成功的农民们,并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不是丛林社会的丛林社会。
它是随着人口数量而动态变化的。
土地有限,产出有限,而人口持续增长,于是就逐步丛林化。
这阶段的文化特色就跟上一阶段截然不同。
文化是服务于是社会,是服务于需要。
在上一个总体扩张的阶段,文化也是自由和扩张的。
而这一阶段的文化,其最主要功能就是协调内部矛盾。
各种伦理纲常,各种文明守则仁爱自制,都是为了试图扭转、延迟、缓和这个一阶段一阶段的丛林化趋势。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调和的、甚至是要人们自阉的文化——而最终都是必然要失败的(除非能忽悠得人们真的自阉)。
这样一种整体令人十分无奈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们普遍失去了扩张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自信心和安全感。
这阶段的社会改革也基本都是失败的(王安石、张居正),因为上一阶段的社会改革,是为了向外抢盘子,而这一阶段是为了对内分蛋糕,当然结果天差地远。
如果没有外部巨大因素(比落后异族还大),那么这个死循环将会永远继续下去,直到地球毁灭。
虽然听起来很冷酷,但不得不说,这种翘翘板游戏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消亡,是对中国的延续至关重要的。
否则的话,同样是完全封闭环境的复活节岛居民(最近岛屿在2000公里外),就是中国的样板。
人口增长,资源耗尽,最后全体毁灭。
但是阶段性的战乱,却使中国的自然资源有了喘息之机。
比如,在南明的抗清队伍中,有一支榆园军在千里平原的山东河南与满清骑兵周旋了很久,因为这支高达十万人的队伍,有一片庞大的榆树林作为根据地——而之前这里原本是耕地。
经过起义军、政府军和满清军队对居民的来回梳理,大自然蓬勃复苏了。
推而广之,全世界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持续有益的。
非洲牛羚每次大迁徙过后,都会感觉环境变好了许多。
不管人还是牛羚,大规模减少种群数量的不自觉行为,根子上都是出自对环境资源的本能担忧。
有些战争真的不是野心家故意制造和推动的,而是群体的焦虑担忧所不可挽回地促成的。
那么,除了这种原始野蛮残酷的减丁口方式,还有没有别的、更温柔一点的方式?
有的。
计划生育。
自觉地通过抑制动物性的生存繁衍冲动,抑制与身俱来的本能,来达到群体的幸福与持续,就是(我所作的)文明的定义。
不管外国舆论怎么看,个体怎么感受,这一场自觉有意识地进行的计划生育运动,是迄今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
真心说,能把这场运动一直组织下来的政府,是很了不起的。
第三阶段:
可以说,有识之士、有能力人士也认识到这个循环,但总体上能忍受。
意思是说,总有一部分人能坐在翘翘板的上头那端不是?
也许哪天就轮到我了呢。
虽然每次换庄都哀鸿遍野,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中国还在,社会还在,总体秩序还在。
特别是文明还在,乱来的异族都被打跑,服从潜规则的异族都被同化。
有些家族仍然可以千年屹立,另外一些也抱着在下次换庄时上位的希望。
总之在不安全感之中又有某些安全感。
而作为最底层的大多数,那些失去了或者说压抑了上位希望的、“还过得下去”的农民,早就习惯了换天下、交公粮,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民族,统治者们总得吃饭穿衣。
只要小心些不让自己倒霉卷入兵灾,作为男耕女织的基层细胞,也是有安全感的。
但是外国人来了!
以前怎么说也是窝里斗,有土地人士和无土地人士斗,大家轮流坐上面那端,现在全体都坐到了地板上。
文化意识同化不了,土地经营模式人家不稀罕,想要象满清一样拉进来一桌打麻将都做不到。
地主老财跟着受剥削,而底层细胞们小农经济破产(洋布又好又便宜)。
整个国家沦为了“殖民地”。
这个两千年不变的死循环终于被打破了。
说到这里就要把眼光转向西方。
*注:
总体而言女真人是个非常善于学习和适应的聪慧民族。
骑射玩得比蒙古人还精,火炮用得比明军还熟。
两次建立正统中原王朝(金和清)且都在统治区获得了极高的忠诚度,并且在东方世界唯一成功进行了利益分配改革(清雍正官绅一体纳粮)。
此外,一般来说越稳定越成功的社会,其应变反应就越迟缓越颟顸,作为最成功的农业社会,它甚至还有声有色地搞了洋务运动。
西方(地中海周边及英伦)
“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个好地方——那里谷物堆成山啊——男人都不会打仗。
埃及对于西方文明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尼罗河给埃及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就连中国与之相比都显得十分暗淡。
他的农业条件便利得令人发指,成为西半球天然的大粮仓(另一个粮仓是迦太基,也位于地中海南岸)。
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除了粮食,几乎什么都缺。
没有森林,没有矿产,只有无穷无尽的石头和砂子。
他的宿敌已掌握了铁制兵器,他还只有少数青铜兵器。
那么,握着丰富的粮食,这个古代世界最硬的硬通货,当然就要满世界易货贸易,采购必须品。
这个饥不择食的土豪,缺的只是一个商业服务中介。
于是克里特岛文明诞生了。
希腊文明的始祖克里特岛文明,就是依靠风平浪静的东地中海,加油站式的天然岛链,通过远比陆路更快捷、运货量更大的海洋运输渠道(远古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就是个悲剧),与埃及进行物资换粮食的交易,而发家致富的。
前面说埃及的军事装备就是个渣,另外生活富裕舒适到了几乎不劳而能获的地步,也没人愿当兵,宁肯去又有面子又有收入的修金字塔。
不过不要紧,咱有硬通货啊。
于是埃及又多了一个显著特色:
外籍雇佣兵。
主要靠着辉煌的建筑奇观,次要靠着雇佣兵的作战,这个文明震慑了周边落后愚昧的世界。
但要论到真实战力,以及战斗决心,它废柴到了连手无寸铜的希伯莱人都对付不了,只能看着摩西出埃及干着急。
一旦被人戳穿真相,埃及就是一头肉乎乎的肥猪。
搞不清(也记不住)谁是第一个戳穿这点的,反正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都在埃及建立过王朝。
之后亚历山大的部将希腊人托勒密,也稳稳地在埃及统治300年,最后是败给罗马人。
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好征服了。
(迦太基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也差不多,让汉尼拔欲哭无泪)
外强中干又富得流油的埃及被各个外部势力轮流征服。
而每一个征服了埃及这块西方最大、最稳定粮仓的国家,都依靠每年十万吨小麦的输入创建了辉煌的文明。
包括罗马这只台伯河上的野狼,也摇身一变成为文明的代表。
没有哪个欧洲人对此有任何指责。
——因为离了对北非的征服,欧洲就什么也不是。
这个环境和这段历史,构成了西方社会理念的核心:
一、通过商贸串联起各个功能单一、独立分布的资源产地;
二、通过契约保护商贸(只要不是牛叉到能自给自足的国家,都得遵守契约);
三、为征服资源产地、为保护商路而进行的战争,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
——即所谓“执剑行商”是也。
这跟东方“一切为了农业土地”、“moremore土地”,完全不同。
而商贸依靠海洋,征服也通过海洋。
这就是所谓的“海洋文明”。
国土可以不大,资源产地和市场不一定领有,但船强则国强,比如威尼斯一个小城邦就牛叉了很久。
自从罗马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之后,就不好用西方这个概念来统一描述了。
失去了粮仓和地中海贸易通道的西部欧洲,上演的是东方农业王朝内部斗争的翻版剧情,硬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东方是嘴巴太多,而西欧是蛋糕太小*,结果都一样(也同样节约了我们的时间)。
这个“黑暗时代”跟东方一样也依靠无奈的、调和的、自阉的文化来缓和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大家都要做好人,死后才能上天堂。
(基督教跟儒家文化一样,都是需求催生的产品。
教会和神职人员履行着东方士人阶层差不多的职能,统领着意识形态建设)
——换句话说,此时的西欧,实际上是东方文明!
外语版。
而西方文明的“正宗”在东罗马。
一度辉煌的东罗马以“拜占庭帝国”留名于世。
但自从被阿拉伯人夺去埃及后他就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到了借贷度日的地步,是历史上最苦逼的“皇帝”之一。
他象打不死的小强,挣扎着在保加利亚人和穆斯林的围殴中坚挺了一千年,直到被土耳其的超级大炮轰垮。
这中间不仅要承受威尼斯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偶尔还要挨西边那位表兄的背后一刀。
但东罗马的存在对西方文明却是至关重要的,从克里特岛文明以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海洋文明”,靠着这支风中残烛才总算得以延续,并使西边那位表兄后来得以“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后的西部欧洲才总算是有点人样了,而不再是人见人怕的穷亲戚、恶邻居)。
发生于穷恶邻居之间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海上资源抢掠战(以及东方致富航路争夺战),日益凸显了火炮的作用。
英国率先开始使用水力机械进行炮膛加工,打得又远又准。
吃了亏的法国、荷兰、西班牙开始效仿,开始竞争,于是工业革命开始了。
跟把抢掠来的第一桶金挥霍浪费掉的大陆国家西班牙不同,缺乏安全感的岛国英国,决心把每一个便士都投入到工业建设里去。
让每一个便士都成为资本。
(投入扩大化生产的便士才是资本,否则就只是钱)
资本对于生产资源的合理调配,对于促进工业生产,从而强国富民,其作用是十分神奇的。
于是资本成为了大家的“主义”。
(人既是资源又是负担。
在资本驱动的工业化爆发之下,人的资源属性提升了,而且工业化大幅提高土地承载力,人的负担属性也同时下降了,合二为一,个人受到了尊重,而不再单纯被看为过度繁殖的兔子)
但是世上几乎所有东西都一样,一旦成为“主义”,成为除了它之外什么都不考虑(也不能考虑)的意识潮流,就不好玩了。
就象“民族”这种朴素美好的情感,一旦成为“民族主义”就会要人命一样。
在“资本主义”引领之下,工厂主们用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效益,恨不能用不要钱的原料、不开工资的工人、翻倍的虚高价格卖出所有产品。
但经过痛苦的无序竞争,大家只能理智地接受了约束:
追求效益得合理一点,同志!
但这个“大家”是指的工厂主和银行家们,即资产阶段,不包括工人。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工人运动(或者已经被拍熄),还没有让“大家”体会到足够的痛苦。
所以在不能够无限地压低原料和抬高售价上面努力时,集体把多赚一点的希望寄托在了减少工资(提高劳动强度也是相对的减少工资)上面。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广大的工人,但是工人没钱,拿什么来买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产品卖不动,怎么办?
当然是降低价格压低成本。
压谁?
当然是压工人工资。
于是产品更卖不动了。
就跟东方的农民们一样,大家都希望别人先出头,先给工人加薪,但是先出头的那个肯定先死。
这是“不能考虑”的。
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恶性循环持续发展下去。
于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却只能堆在仓库里烂掉。
资本家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互为因果地持续降低。
最终产生了经济危机。
那么,经济危机有没有解决办法?
有。
第一个办法:
提高广大消费群体的购买消费能力。
注意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暴富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那只是推动了奢侈品消费。
所以,得是穷人们突然全体都有钱了(不是纸钞,是真金白银)。
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办法,居然真的出现了!
淘金潮。
这是地球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又一次拨弄。
在面对数以百万的带枪牛仔时,没有哪个富人有能力独占金矿,于是都变成了穷人们手里的财富,于是商品盘活,工厂开工,经济危机安然渡过——工人运动家们只好捶胸顿足。
当然这只是暂时缓解,根本矛盾还是没有解决。
好在地球足够大,这里的人买不起,不等于别处的人也买不起。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拉起铁锚,架起大炮,向着据说钱多人傻的东方前进。
之前他们满世界这么干是为了掠夺原料和劳动力(短视的是掠夺黄金),而现在是为了虔诚地追寻上帝——顾客消费者。
这就是第二个办法:
帝国主义。
(这个名词十分奇怪,因为明明跟封建帝国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上帝所在之国的统治者一开始肯定十分奇怪,为什么这些凶巴巴的家伙没有象我们经常干的索要“宝贵的”土地,费尽周折居然只是为了开放几个城市卖东西?
早说嘛。
而且条约一订立刻就换成满脸的讨好。
真是让人足够错乱的,统治者们纷纷表示理解不能:
喂喂,我明明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是最大的地主,为什么你把我揍得鼻青脸肿,却去讨好那些奴隶?
合着在你们白人眼里,我堂堂政府只是条看门狗,那些所谓消费者才是主人?
没错儿,人家“海洋文明”就是跟东方文明不一样。
当然了,入乡随俗,当帝国主义者们逐渐认清东西方的差异,明白原来不需要跟消费者直接对话,只需要跟他们的主人——政府打交道就能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心里面,自幼形成的公平商贸的节操哗啦啦碎了一地。
唉,被东方人带坏了。
16世纪英国人口仅仅400万,但已经为“无所事事的贫民大量充斥”而苦恼,并催生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东方和西方的第一次相遇
在帝国主义的推动下,西方跟东方就这么相遇了。
为解决当时必然的经济危机,西方的工业生产把东方的农业土地变成了殖民地。
(这又是一个不当的名词,因为人家压根就不是为殖民来的)
东方那些迟钝的统治者,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的变化。
但有个别机灵点的,很快学会了这一招。
原来资本这么神奇,原来它就是这么运作的,一点也不难嘛。
看看咱这岛国跟英国有多么象啊,咱也仿照着来!
于是东方也崛起了一个帝国主义。
但问题是,这里是东方!
是视土地为生命的东方。
你跟英国什么都象,就是脑袋瓜子不象!
于是不管怎么违和,这个国家居然把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市场的需求,把东方的翘翘板游戏和西方的“海洋文明”,两者给结合起来了。
在一群“农民资本家”的率领之下,形成了怪异的“农业式的帝国主义”。
(既要强占人家的土地,又要卖出你的产品,这怎么可能呢?
你拉了天大的仇恨,还指望中国人当你的上帝?
)
结果把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变成了真正的殖民。
问题是,殖民以后你的国民就有钱买你们的产品,解决你的经济危机了吗?
仍然还是没有。
顶多只是降低了资本家的生产成本,而没有解决穷人们的购买能力。
国内经济危机仍然无法消除,相反殖民还要占用大量资金,导致他的财政从来就没有好过。
那些普通下层殖民者的生活也很悲催,本来可以依靠先进生产力,向中国出售产品让大家日子很滋润(就象他们后来做的那样),结果一个个在异乡的冰天雪地开垦土地,挖掘矿山,向国内输送生产资料,让资本家们受益!
日本政府,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对着一帮工人和知识分子,政府实在给不出理由,只好搬出“大义”:
这一切是为了天皇陛下!
不服?
请到军部喝茶。
(以暗杀天皇的名义处死了工人运动领袖)
这个国家的政府自己也被搞错乱了。
反映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也是一塌糊涂的混乱。
一会要土地,一会要市场;
一会要占领,一会要亲善;
一会想撤军,一会又不想;
这个想要培植市场,那个只想高效掠夺;
刚刚树起傀儡政权,转头就签合并条约;
农民为主的陆军渴望土地,小资格调的海军没有兴趣;
这边进行着和平谈判,那边准备着武器弹药;
侵略掠夺是赤裸裸的,而共存共荣也是很真诚的……
——凡是相信了日本政府的诚意和承诺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感到了后悔。
混乱到最后,日本只好跟着感觉走了,谁更有说服力就听谁的。
当然,各种因素中,子弹最有说服力。
它成功地“说服”了犬养毅首相等几位坚持走“纯粹帝国主义道路”的政治家。
(据说,反对日韩合并、支持中国改革的“走纯派”伊藤博文,也可能是被说服的)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军队利用矛盾犹豫的统治阶层无力监管和纠正的时机,发动一次次对内对外的冒险,最终压倒了文官集团,夺取了最高权力。
于是人类历史继“农业帝国主义”之后又盛开了一朵奇葩:
和平条件下由军队主导的文官民主政府。
接下来。
殖民和侵略得来的资源,农作物和石油矿产等等,如果不能成为卖出去了的产品,只不过把经济危机的仓库堆得更高而已。
如何把这笔死财盘活不让它成为负担呢?
唯一的选择似乎只剩下:
变成子弹打出去。
至少这能换来表面的繁荣,地图的美丽,政客和民族主义分子不就要这个吗?
顺便还满足了农民们的土地幻想(对付工人有西方可以参考,有“反共”这个伟光正理由,至于知识分子则向来不用担心)。
于是打出去的子弹带来了更多的殖民地……然后是更多的仓库堆积以及更贫苦的国民……然后是更多的打出去的子弹……。
至于把全世界都变成殖民地后会怎么样,陆军马鹿们不负责任地表示暂且不考虑。
解决西方经济危机的新办法
放下东方的狗血,眼光重回西方。
西方还没说完。
因为解决经济危机还有第三个办法。
前面说过,经济危机是日益发达的工业生产和日益萎缩的群众购买力之间的矛盾。
而矛盾的起因在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已经成为了一种“主义”。
看起来只要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矛盾,但问题是,资本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还叫资本家么?
不是大家都停不下来的行为意识,还能叫“主义”么?
就算有人天良发现,理智清醒,想要采取行动停止这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的利润追求,但结果是谁这么做谁死。
这就是“主义”的可怕之处。
除非大家共同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终于能共同行动停止固定的行为趋势,否则任何“主义”都是无解的。
很遗憾这种机遇一直没有降临。
但是有位天才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资本家在中间追求利润,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很可能实现的。
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有合理的产业布局,有便捷的交换渠道,有训练有素(特别是有协作意识)的工人,有富有经验的组织管理者,这不已经够了吗?
工人们互相为了彼此生产,你要什么你告诉我,我要什么也告诉你,何必还要通过资本家和商人?
而且我们还可以提前统计各自的需要,结合各自生产能力,进行合理计划,这把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也免了,节约了多少浪费?
我们大家都知道离了对方机器开不动,工厂玩不转,我们谁也没本事独自生产出全部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懂得配合,不会相互拆台捣乱,多吃多占。
那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实现。
对于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资本家已经是多余。
既然多余而且形成无法解决的危害,那就应该去掉。
当然他的办法绝不真的只是灵机一动那么简单就出来了。
他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学术演算——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人类迄今为止,对认识我们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最重大的思想革命,这才使得这个道理如此简单明了。
(打比方说,就好象今天谁都知道E=MC²
,却几乎谁都不知道其推导过程一样)
但得注意,马克思是纯粹从书房中的哲学思想推导出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跟多数纯粹学者一样,他觉得这样做“合理”、“应该”,对社会有好处,那么就值得去试。
“凡是合理的就必然会存在的”,是他的哲学的重要观念。
他本人可能都没有好恶,最多就是学者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实施的关切。
但是他的好基友兼赞助商恩格斯不同。
恩格斯是出自资产阶级家庭,对工人状况有深切了解体会,甚至情感上也有联结。
他用切身体会对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施加影响,使之不单纯是书呆子的呓语,而是填充进了丰富的情感,明确的立场,以及人味儿。
同时鼓动他去亲身实践,组建共产国际。
——但是,永远不要指望哲学家能成为一个合格领导。
他立刻就面临一个挠头的问题:
你从对整个社会好、或者纯粹是从理论洁癖完美主义的角度,觉得“合理”“应该”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的那些人,他们不愿意退出,怎么办?
——贪婪到失去理性的毕竟是少数。
作为大多数资本家的一员,我承认你马克思说得很对,我也可以接受这个更加公正理性的社会,只不过,对你来说这只是学问,但对我来说却是身家性命!
在这辆没有刹车的资本主义列车上,我一下车就死定!
凭什么让我为了这个社会的美好而这样牺牲?
阶级斗争神马的,好象并不能解决问题?
马克思陷入了苦恼与困惑之中。
这个问题被战斗民族的列宁同志回答了。
他只用了一个字:
杀。
——既然你们谁都不敢先下车,那就把整列车上的所有人都干掉。
马克思哲学隐含的冷酷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大家的意识都是物质决定的,就像工厂批量生产的机器人,那何必还讲什么“对你来说对我来说”,这世上既没有“你”,也没有“我”,只有对环境的反应、对物质的代言、对阶级的认同。
总之,你不是人(当然我也不是)。
如果不能在你的脑袋里打上“madeinCP”,那你就是可以报废的残次品。
这并不是在臧否,因为哲学本身就是冷漠的学问。
这种冷漠的学问教导我们,大规模的肉体消灭反对者,十分有助于建设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美好的社会。
这也让那些“有太多小资情调”的西方知识分子闻“共”而色变。
一段时间内也把自己的同志吓得不轻。
——万幸的是没有谁真的完全遵从一门哲学来建设管理一个社会。
是否欢欣鼓舞地为建设科学合理美好的社会挥起屠刀,最终取决于,你身上儒家仁爱中庸精神还剩多少(可以肯定红色高棉没有剩多少)。
或者,一直以来约束野蛮本性是依靠的有神论,而当接受无神论的信仰时,约束也就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