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人体试验中以安慰剂治疗之法律问题.docx
《药品人体试验中以安慰剂治疗之法律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药品人体试验中以安慰剂治疗之法律问题.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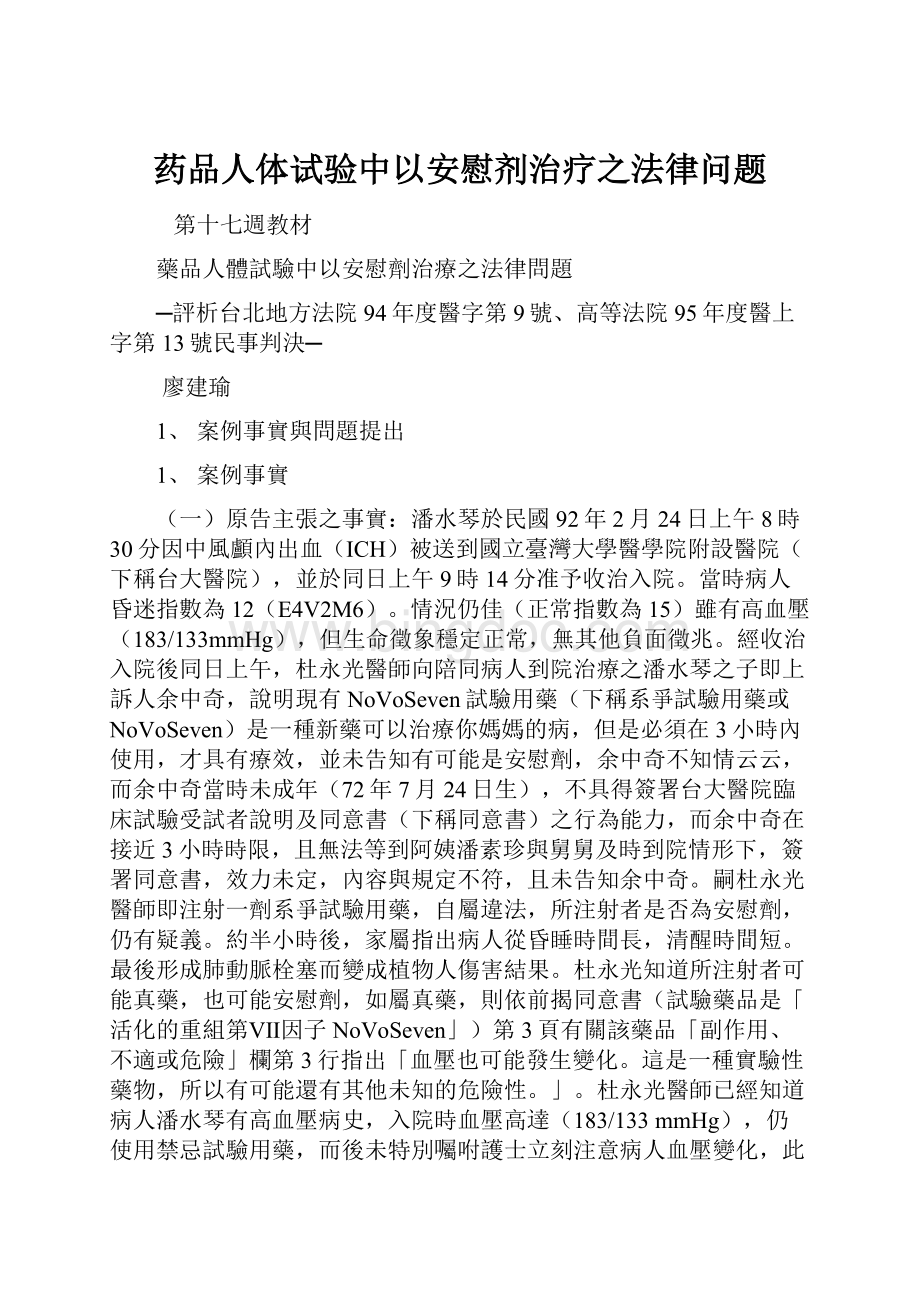
药品人体试验中以安慰剂治疗之法律问题
第十七週教材
藥品人體試驗中以安慰劑治療之法律問題
─評析台北地方法院94年度醫字第9號、高等法院95年度醫上字第13號民事判決─
廖建瑜
1、案例事實與問題提出
1、案例事實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
潘水琴於民國92年2月24日上午8時30分因中風顱內出血(ICH)被送到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台大醫院),並於同日上午9時14分准予收治入院。
當時病人昏迷指數為12(E4V2M6)。
情況仍佳(正常指數為15)雖有高血壓(183/133mmHg),但生命徵象穩定正常,無其他負面徵兆。
經收治入院後同日上午,杜永光醫師向陪同病人到院治療之潘水琴之子即上訴人余中奇,說明現有NoVoSeven試驗用藥(下稱系爭試驗用藥或NoVoSeven)是一種新藥可以治療你媽媽的病,但是必須在3小時內使用,才具有療效,並未告知有可能是安慰劑,余中奇不知情云云,而余中奇當時未成年(72年7月24日生),不具得簽署台大醫院臨床試驗受試者說明及同意書(下稱同意書)之行為能力,而余中奇在接近3小時時限,且無法等到阿姨潘素珍與舅舅及時到院情形下,簽署同意書,效力未定,內容與規定不符,且未告知余中奇。
嗣杜永光醫師即注射一劑系爭試驗用藥,自屬違法,所注射者是否為安慰劑,仍有疑義。
約半小時後,家屬指出病人從昏睡時間長,清醒時間短。
最後形成肺動脈栓塞而變成植物人傷害結果。
杜永光知道所注射者可能真藥,也可能安慰劑,如屬真藥,則依前揭同意書(試驗藥品是「活化的重組第ⅤⅡ因子NoVoSeven」)第3頁有關該藥品「副作用、不適或危險」欄第3行指出「血壓也可能發生變化。
這是一種實驗性藥物,所以有可能還有其他未知的危險性。
」。
杜永光醫師已經知道病人潘水琴有高血壓病史,入院時血壓高達(183/133mmHg),仍使用禁忌試驗用藥,而後未特別囑咐護士立刻注意病人血壓變化,此由92年2月24日入院至同年3月2日止,均無每日血壓紀錄可證,嗣至3月3日才有血壓高達200/130mmHg、4日血壓180/110mmHg及210/130mmHg的記載,顯有未密切監控潘水琴血壓,俾適時採取必要措施之過失行為,所注射者如果是無療效之安慰劑,杜永光竟未作應有的備位緊急補救措施(如開顱),喪失治療黃金時間,而有延誤治療責任。
且在92年2月24日注射試驗用藥後至3月2日止均未作血壓監測,疏未控制高血壓,及緩和腦出血的黃金時間。
遲至92年3月11日杜永光才為潘水琴作「顱內血腫」的開顱手術,開顱太晚,終於造成植物人,應有過失,造成植物人的原因是中風而非肺栓塞,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諾和諾德公司)提供試驗用藥,引起病人遭受至大傷害,應與台大醫院、杜永光負連帶賠償責任。
醫療行為有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之適用,並得依消保法第51條請求懲罰性賠償金。
(二)法院認定之事實
原告潘水琴於92年2月24日上午8時30分因入廁時,感到右肢無力,接著說話不清,接著由子余中奇陪同至台大醫院急診,經作電腦斷層掃描而顯示有左側顱內出血(intracranialhemorrhageatleftganhlia)現象,入院時血壓為183/133mmHg,而由台大醫院收院治療,潘水琴當時47歲(44年6月20日出生),醫師依余中奇告知,潘水琴有高血壓症狀,惟未以藥物控制,由被告杜永光醫師診治。
被告杜永光醫師見此顱內出血病症與其受被告諾和諾德公司委託主持系爭試驗用藥有關,隨即向余中奇說明,為抑制潘水琴顱內出血,以具凝血藥理作用之系爭試驗用藥作為治療,由余中奇簽署同意書,並經證人吳益嘉即台大醫院醫師、蔡翊新即台大醫院醫師在旁見證,杜永光醫師並在同意書內註明「當日進行對病人家屬之溝通時,本人亦在場。
確實在家屬同意簽字後才給藥,當時病人之昏迷指數為12分,無法簽署同意書」等語惟未顧慮及余中奇尚未成年。
又為配合潘水琴病情與系爭試驗用藥特性,系爭試驗用藥須在發病時3小時使用,此為余中奇在無法等待阿姨與舅舅及時趕到醫院情形下,而不得不簽署同意書原因,當余中奇簽署後隨即由杜永光醫師注射使用被告諾和諾德公司提供經行政院衛生署許可之試驗用藥NoVoSeven藥品,但因採隨機雙盲試驗,分配予原告潘水琴所注射之藥物,係由葡萄糖、澱粉等組成無藥理作用之安慰劑(placebo)。
另系爭試驗用藥得為人體試驗,業經行政院衛生署91年9月13日衛署藥字第0910062482號函准審核通過,此有行政院衛生署覆本院函可證;且系爭試驗用藥是為對顱內出血之抑制,而有凝血因素存在,與血管栓塞須採用抗凝血劑(antico-agulation)或血栓溶解劑(thrombolytics)等治療情況,彼此藥理作用相反,固有相當之衝突。
惟如前所述,原告潘水琴自92年2月24日中風跡象入台大醫院治療,至92年3月6日上午9時25分之前,與腦部斷層攝影顯示顱內並無增加新的損傷情形,且在此期間尚以復健方式治療;再者,潘水琴所受分配到之試驗用藥為不具藥性作用之安慰劑,因之,其引起之肺動脈栓塞,並非系爭試驗用藥所造成。
再查系爭同意書雖由余中奇(72年7月24日出生)於92年2月24日上午11時45分簽署,並由見證人吳益嘉、蔡翊新於當日上午11時20分見證。
然余中奇於92年2月24日簽署當時未滿20歲,而系爭同意書關係其母潘水琴的治療內容,潘水琴將其對使用系爭試驗用藥後狀況,供為判斷藥品之療效,依前揭醫療法第57條應得受試驗者書面同意。
如受試者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本件原告潘水琴於入院當時昏迷指數12分(中度),其本人並未簽署書面同意書而被告杜永光醫師當時未察余中奇之年齡狀況可否簽署系爭同意書。
另根據行政院衛生署91年8月間訂頒之「藥品優良床試驗規範」,其中第143條規定:
「如在緊急情況下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同意,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當無法預先取得受試者的同意且其法定代理人不在場時,為維護受試者的權利、安全、與福祉,且確保其符合相關法規的規定,必須在試驗計畫書中和/或其他地方有納入緊急事件處理方法,並得到人體試驗委員會/獨立倫理委員會的書面核准/贊同意見。
此臨床試驗相關訊息必須盡快告知受試者或其法定代理人,並徵得繼續參與臨床試驗的同意和其他相關事宜的同意。
」,依此,關於藥品試驗的緊急情況下,上開規範設定有須在計畫書中設立緊急事件處理方法,但被告杜永光醫師並未舉證符合前揭緊急取得同意之要件。
本件原告潘水琴成為植物人狀態結果,係因92年3月6日上午餵食早餐噎到(或嗆到)所致;而杜永光醫師在徵求受試者過程中,對於處在緊急狀況下有無未符合上開規範之作法,雖未提出證明,然此項徵求過程或未符上開規範,但此非造成原告潘水琴肺動脈栓塞之原因,應認2者不具因果關係。
最後原告主張被告諾和諾德公司與被告台大醫院間具有臨床試驗藥品協議契約關係,依協議書第1條規定,委託人所提供之NoVoSeven藥品因臨床治療使用後引起病人傷害或死亡,委託人應負全責等語,因被告諾和諾德公司提供之實驗用藥為安慰劑,尚不足認係造成原告潘水琴肺動脈栓塞之成因,故原告敗訴。
2、問題提出
1、人體試驗中藥廠、醫院(教學醫院或有特殊專長醫療機構)、醫師(計劃主持人)及患者(受試驗者)之四角關係。
從本案例中患者對於諾和諾德公司即藥廠以及醫院、醫師孰該實驗用藥NoVoSeven所進行之人體試驗所主張之請求權均為特殊侵權行為類型,究竟患者與藥商、醫院、醫師就該藥品所進行人體試驗有無另外成之契約關係,抑或四方關係僅由醫療法、醫療法施行細則、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藥品臨床試驗一般基準等法規所建構法定義務作規範。
2、人體試驗雙盲實驗中醫師以安慰劑為治療手段之告知義務與衝突。
人體試驗中對於以雙盲設計之以安慰劑作為對照組,於實驗過程中,醫師所擔任執行人之角色為確保實驗數據之正確性是否與其擔任醫療契約中醫師之角色產生衝穾。
例如本案中實驗藥物顯然無治療療效時是否應告知而改以替代治療。
3、醫師或試驗機構對於人體試驗違反說明義務之效果。
在違反人體試驗之法律規定或實驗計劃書中應說明事項所進行之藥品人體試驗,關於法律效果是否可依人體試驗契約或侵權行為請求賠償以及進行人體試驗之行為是否得適用民法第191之3之範疇。
2、藥品人體試驗法律關係之架構
1、藥商、醫院、醫師、患者四角關係現行操作模式
關於藥品人體試驗可能之當事人主體,依醫療法第78條第1項限定為教學醫院或有專長之醫療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故就實施人體試驗之機構(即試驗機構),法律明文規定其當事人能力,若有非屬上開教學醫院或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醫療機構而他人締結人體試驗契約,應認為當事人能力不符,非屬適法之契約行為,此乃為確保人體試驗執行能力之當然要求,屬於當事人能力之積極要件。
再從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中第五條規定,試驗機構須有一名試驗主持人負責取得受試者之進行人體試驗同意,又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四十條規定試驗主持人係由試驗委託者甄選,且依該準則第三條第八項規定所謂試驗委託者係臨床試驗之發起及管理者,因此在醫療法及施行細則、藥事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出現之試驗委託者,在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五章四十條至八十二條專章規範其權利義務。
由於人體試驗之主要法源為醫療法,在醫療法中未規範之試驗委託者,在人體試驗實際操作中往往亦被忽視,特別是在與受試者間之法律關係,往往如同附件一、二、三,出現於其中一委託單位之欄位以及損害賠償部分註明如臨床試驗計劃發生不良反應或傷害由試驗委託者依法應損害賠償責任而已,至於兩者間有何權利義務,受試者在書面文件均難以知悉,最後,再如附件四由試驗委託者與試驗機構簽訂承諾書,如試驗機構依照所訂計畫,臨床治療使用該藥品或醫療器材因而引起病人傷害或死亡,試驗委託者應負全責,並確認病人(包括其法定繼承人及其他法定請求權人)對試驗委託者有直接請求權。
是以,在實行操作下,要認為受託者與委託試驗者就人體試驗有何契約心要之點合意,實屬牽強。
因此現行藥品人體試驗模式及法律規範如下:
(一)外部關係
1、人體試驗委任監督關係:
試驗委託者試與試驗主持人、試驗機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三條第八項、四十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四條等)
2、人體試驗取得同意關係:
試驗主持人與受試者(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五條),惟實務操作藥品人體試驗同意書上均會表明試驗機構名稱
3、人體試驗損害之債務承擔:
受試者、試驗機構與委託試驗者
(二)內部關係
1、人體試驗內部監督:
試驗機構與試驗主持人,藉由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三章以下規定由試驗機構設置人體試驗委員會對於試驗主持人所進行之人體試驗為審查
2、藥品人體試驗與醫療契約之相互關係
1、僅存人體試驗契約之法律模式。
在藥品人體試驗第一階段(PhaseI),為藥品完成動物實驗後,因為主要目的為確認人體所能忍受的劑量範圍、了解藥物對人體的毒性及在人體之吸收、分佈、代謝、排除情形,所以試驗對象為健康志願者,此階段之研究通常並無治療性之目的,故並無患者係因就醫或罹患某種疾病而納入受試者之情形,故僅有人體試驗之法律關係存在。
而可能進行於自願之健康受試驗者或某些特定受試驗者族群。
在藥品人體試驗第二階段(PhaseII,最典型的試驗為治療探索)一般認為第二階段起始於以病人進行療效探索為主要目標的試驗。
初期療效探索試驗可使用各種試驗設計,包括使用同步對照組(concurrentcontrols)及基準狀況(baselinestatus)之比較,後續試驗則通常為隨機、同步對照組的試驗,以對某一適應症的療效和安全性進行評估。
第二階段的試驗通常執行於一群由嚴格條件篩選出同質性高的病患族群,並進行嚴密監測作業。
此階段之另一重要目的為決定第三階段試驗所使用之劑量及治療方法。
此階段中,早期的試驗通常採用逐步劑量增加的設計,以進行劑量-反應初步之估算,後期試驗則可經平行劑量-反應設計(亦可延至第三階段執行),以確認該適應症之劑量-反應關係。
劑量-反應確認試驗可在第二或第三階段進行。
第二階段所用的劑量,通常(但非絕對)低於第一階段所用的最高劑量。
第二階段臨床試驗的目的還包括:
評估其他可能試驗指標、治療方法(包括併用藥品)、目標族群(如輕微或嚴重疾病)等,以供第二階段後續試驗或第三階段試驗之需。
為達成上述目的,可藉由探索分析、研究數據。
藥品人體試驗第三階段(PhaseIII,最典型的研究種類為治療確認)一般認為第三階段起始於主要目的為顯示或確認治療效益之試驗。
第三階段試驗主要目的,為確認於第二階段中所得藥品用於目標適應症及受試驗者是安全及有效的初步證據。
這些試驗的目的在提供核准藥品上市之適當依據。
第三階段試驗可更進一步地探索劑量-反應關係,或探討將此藥品使用於更多族群、或用於疾病之不同階段、或與不同藥品合併使用。
對需長期給藥的藥品而言,雖然第二階段可進行長期給藥之臨床試驗,但此類臨床試驗通常於第三階段進行,第三階段所執行之試驗提供完整資訊,以支持藥品的適當使用說明。
因此,在第二、三階段受試者同時存在患者之身份,而第三階段往往亦伴隨較長時間給藥試驗。
契約締結目的而言,受試者與試驗機構於同意書均載明係為特定藥品臨床試驗之研究目的、試驗方法(包括試驗治療及每個治療之隨機分配機率、治療程序)、試驗預期之效益、試驗進行中受試者之禁忌、限制與應配合之事項,亦即受試者與試驗機構係基於藥品效果研究目的而為締結,至於會有何效果,是否因此產生療效,並非人體試驗契約締結目的,是以在藥品人體試驗,非單純僅該新藥品為試驗,就併用藥品所產生效果、用藥後之非治療檢查亦屬於在研究範疇,故一但締結人體試驗契約患者之身份將轉換為受試者,對待給付亦由試驗醫療費用給付免除,改由受試者應受限制之受試勞務,至於患者中止試驗後或試驗產生損害之醫療照護,均屬於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22條第10項、第112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法定義務,或者從人體試驗契約之後契約義務可導出,是以,在藥品人體試驗契約中並無醫療契約併存之空間及必要,對於受試者之保護已足。
2、僅存醫療契約之法律模式
從藥品人體試驗第二、三階段中受試者必定為患者以觀,往往係患者與醫師(試驗主持人)或醫院(試驗機構)先成立醫療契約後,因符合藥品人體試驗計劃中受試者之資格而獲選成為受試者,而患者之所以願意成為受試者或者願意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往往係基於治療之目的而非成為藥廠或學者研究目的下的白老鼠,因此從患者之角度所謂人體試驗同意僅在於同意醫師之使用非常規用藥(就藥品試驗而言)而言,並無另外成立人體試驗契約而使醫師因成立人體試驗契約同時扮演著試驗計劃執行人角色,並使醫師在此種不同角色扮演取得最有利之地位,例如:
在長期人體試驗下患者的疾病,因分配至安慰劑之組別,毫無進展甚至延誤治療試驗,醫師即遁逃成為試驗計劃執行人,主張藥品之人體試驗主要目的並非在於治癒病患云云,為確保患者就醫最大利益,應認為患者與醫院或醫師僅成立一醫療契約,就藥品之人體試驗,僅為患者同意醫師非常規之用藥,而對於該用藥患者有權隨時中止,對於該用藥引起之損害,醫師本於醫療契約之附隨義務即有繼續治療之義務,至患者用藥後之檢查,可認為係患者之協力義務,而就該用藥之費用得以減免,但對於一般治療所生之費用仍須基於醫療契約支付。
3、患者最佳利益考量─人體試驗契約與醫療契約併存之法律模式
醫療契約之締結,醫師主要義務乃係基於專業知識及經驗,不經篩選針對患者之疾病作出以治癒為目的就已知風險最小、副作用最少之治療方針、用藥。
而人體試驗契約,則係試驗機構之試驗計劃執行人受試驗委託者之委託,主動選擇符合試驗計劃之患者,受限於試驗計劃,使用風險與效益均不明確之藥品了患者身上,以取得研究數據為目的。
就單純以人體試驗之法律模式,容易使患者純粹成研究之對象,而忽略患者就醫之目的乃係為治癒疾病,而其所以願意簽署同意書亦認為除了接受風險不明之藥品外,亦同樣能受到良好的醫療照護,特別是在法律所未規定保護受試者之義務以外,例如在實驗組與對照組部分,患者是否受到足夠的醫療照護,抑或為取得精準之研究數據(或者稱新藥療效)而採取安慰劑使用。
再者,在人體試驗中所強調乃在資訊的完整揭露與對不確定風險的自願承擔,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讓試驗有關資訊有必要更詳細揭露的需求成為主軸,已非屬於一般醫療契約上之說明義務可以涵蓋,在醫療契約中患者自主決定權在於醫師就已確定用藥風險告知或替代方案,而於人體試驗時,醫師就所使用之藥品究竟有何療效及風險均處於未知之狀況,足認此時已非一般醫療契約中患者自主決定權所能解釋,因此是有承認受試者與試驗機構或試驗計劃主持人間有人體試驗契約存在之必要。
特別在於有醫療契約之存在可以導正執行試驗計劃之醫師純綷以試驗計劃為考量以及將患者純粹成為研究之數據,而人體試驗契約存在亦比較能說明患者之非治療之協力義務,如用藥後之抽血檢查以及試驗中止後後契約義務之產生。
然而,存在二個契約間之醫師或試驗機構,難免會發生義務衝突,例如:
試驗計劃之保密義務與治療上之說明義務,此時即應以患者最大利益作為解決之道,而非當然向一方傾斜,以確保醫藥發展與患者權利之平衡,本文即持此一看法為以下之論述。
3、醫師於藥品人體試驗契約及醫療契約中以安慰劑治療之說明義務
1、醫師於藥品人體試驗及醫療契約中說明義務之內容及例外
(1)就一般醫療關係而言,我國法主要係在侵權責任下去架構醫生之說明義務,其法律依據為醫師法第十二條之一及醫療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八十一條之規定,亦即認為醫師之說明義務係為取得侵襲性治療行為之侵權行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前提,基於避免侵害每位病人自主決定權而產生之說明義務,其意義在於所謂病人自主權的說明義務係針對疾病本身可能的發展以及疾病治療的可能風險和副作用,治療行為對於病人身體的完整性與健康所帶來利害得失,醫師應該向病患說明,讓病人係在對於疾病和治療擁有充分的醫療資訊下,由病人自由考慮疾病與治療間的風險而作自主的抉擇,並由病人自己承擔自主決定下的可能風險,大致上包括診斷檢查、治療過程、治療風險及其他治療方式之說明。
至於從醫療契約中另外可從保護交易當事人的觀念所產生之說明義務,傳統契約法中保護的是契約當事人之履行利益,此部分即在醫療契約中所稱「安全說明義務」,其意是指「對於整個治療施行過程、治療過程需要病人配合之部分以及如何避免危險產生」的說明。
安全說明義務與醫師的治療行為是一體的,如果醫師未盡安全說明義務,導致病人疏於未注意而產生治療失敗,屬於醫療過失的問題。
(2)人體試驗契約之說明內容
人體試驗之說明依據醫療法第79條第二項規定說明之內容為試驗目的及方法、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預期試驗效果、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52條規定說明內容亦同。
在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第22條規定應說明內容為:
1、臨床試驗為一種研究。
2、試驗之目的。
3、試驗治療及每個治療之隨機分配機率。
4、治療程序,包含所有侵入性行為。
5、受試者之責任。
6、臨床試驗中尚在試驗之部分。
7、對受試者或對胚胎、嬰兒或哺乳中幼兒之可預期危險或不便處。
8、可合理預期之臨床利益。
9、其他治療方式或療程,及其可能之重要好處及風險。
10、試驗相關損害發生時,受試者可得到之補償或治療。
11、如有可獲得之補助,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12、如有應支付之費用,應告知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
13、受試者為自願性參與試驗,可不同意參與試驗或隨時退出試驗,而不受到處罰或損及其應得之利益。
14、經由簽署受試者同意書,受試者即同意其原始醫療紀錄可直接受監測者、稽核者、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關檢閱,以確保臨床試驗過程與數據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並承諾絕不違反受試者身分之機密性。
15、辨認受試者身分之紀錄應保密,且在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下將不公開。
如果發表試驗結果,受試者之身分仍將保密。
16、若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臨床試驗之意願,受試者、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會被立即告知。
17、進一步獲知有關試驗之資訊和受試者權利之聯絡人,及與試驗相關之傷害發生時之聯絡人。
18、受試者終止參與試驗之可預期情況及理由。
19、受試者預計參與臨床試驗之時間。
20、大約受試者人數。
(三)兩者說明義務之差異
1、受試者與一般病患自主性不同
如同前述,患者在成為受試者之過程中,由於主動者係執行試驗之醫師,在具有相對依賴關係之醫病關係中,由治療之醫師主動要求患者成為受試者,要說出「不」之自主性,與一般常規治療下之醫病關係顯較不可能。
再者,患者在長期疾病壓力下會常成為受試者,往往係對於常規治療已失去信心,是否接受試驗之自主性,自難預期與一般患者相同。
特別是有生命威脅之情況下,容易對於人體試驗之危險性低估而對於新藥療效高度期待而作出錯誤之判斷或根本喪失自主判斷之能力。
再加上受試者與患者之地位與角色不同,受試者原則上只是試驗計劃之施行客體,對於試驗計劃內容本身並無決定之權利,只能選擇是否進行或中止,因此在人體試驗契約中受試者,實質上並無像一般患者就治療方針與醫師進行討論或有無其他替代性治療。
受試者能自主決定範圍,嚴格來說實在有限。
故在醫療法中人體試驗說明必須包括其他可能之治療,在人體試驗契約中實屬無意義。
2、執行試驗者與醫師對於藥物已知之風險掌握不同
藥物之人體試驗目的在取得藥品之療效與副作用,因此執行試驗之醫師,對於新藥之風險基本上亦處於未知之狀況,特別是第二階段之人體試驗,除了一般藥動學及第一階段累積之安全性外,事實上對於藥品可能之副作用及療效均無從掌握,因此,醫療法上人體試驗說明應包括副作用及預期之效益,是否能屬實,甚至構成不實之說明而取得同意,實值研究。
3、人體試驗之說明在於資訊之揭露而非風險之分散
在一般醫療契約中醫師本其專業醫學知識,對於前來就診之病患,說明診斷之病情與目前醫學的可能治療方式或不治療之風險,使病人瞭解自己所面對的人生風險,然後自主決定個人所願意承擔的風險,對自己的決定負責任。
以法律觀點而言,法律要求每一個權利主體對自己的決定與行為負責任,無法要求權利主體承擔他人所做決定的結果,當然此前提是相信有自由決定能力之人必能做出符合個人利益的決定。
但在人體試驗中受試者自主性被限縮,執行試驗對於藥品之風險掌握亦有限,已如前述,在如此風險不明、自主權有限之情況,自難僅以人體試驗契約之締結,即認任受試者自干冒險,而將藥物試驗風險不明之結果要求受試者承擔,因此,在人體試驗之說明著重乃在試驗資訊之公開,特別是動態之試驗結果公布,至少讓受試者有知悉不良事件而得以中止試驗之可能。
(四)醫療契約與人體試驗契約說明義務之例外
醫療契約說明義務之例外第一種情形為緊急情況(emergency),所謂緊急情況意謂醫生基於病程的發展在時間上無法合理期待醫生達成及時說明,若先說明對於患者將產生更嚴重之損害,大致須具備疏於提供治療對於患者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及必須包括患者當時是無意識能力或無能力做出決定,或者無其他患者授權之代理人可表示決定時,且須在此相同情況下理性患者將會同意或有同意可能性時才完全符合緊急情況之說明義務例外。
第二種為治療特權(therapeuticprivilege)醫療特權其意義醫生基於向患者說明傳遞醫療資訊後,可能會造成對患者無論在病者生理、心理或情感上潛在傷害或者造成對治療行為不良效果因此准許醫生基於上開醫學考量無庸對患者說明。
第三種為病人之放棄(Waiver)在醫療實務有時病患希望醫生去替他決定適當的治療即可而放棄被告知的權利,被美國最高法院定義為自願且有意的讓渡已知權利。
第四種為已知風險,在德國法上承認說明義務之例外尚有當病患在某種疾病因特定醫師長期治療下就此部已被充足解釋,即所謂久病成良醫的情形下,針對閱歷豐富的老病號,就該長期就診的疾病上,至少在細節上無庸再說明。
在人體試驗說明義務之例外,最常見者為缺欠決策能力,所謂決策能力是指受試者本身欠缺同意能力,一種是從年齡上所謂無行為能力及限制行為能力人,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