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docx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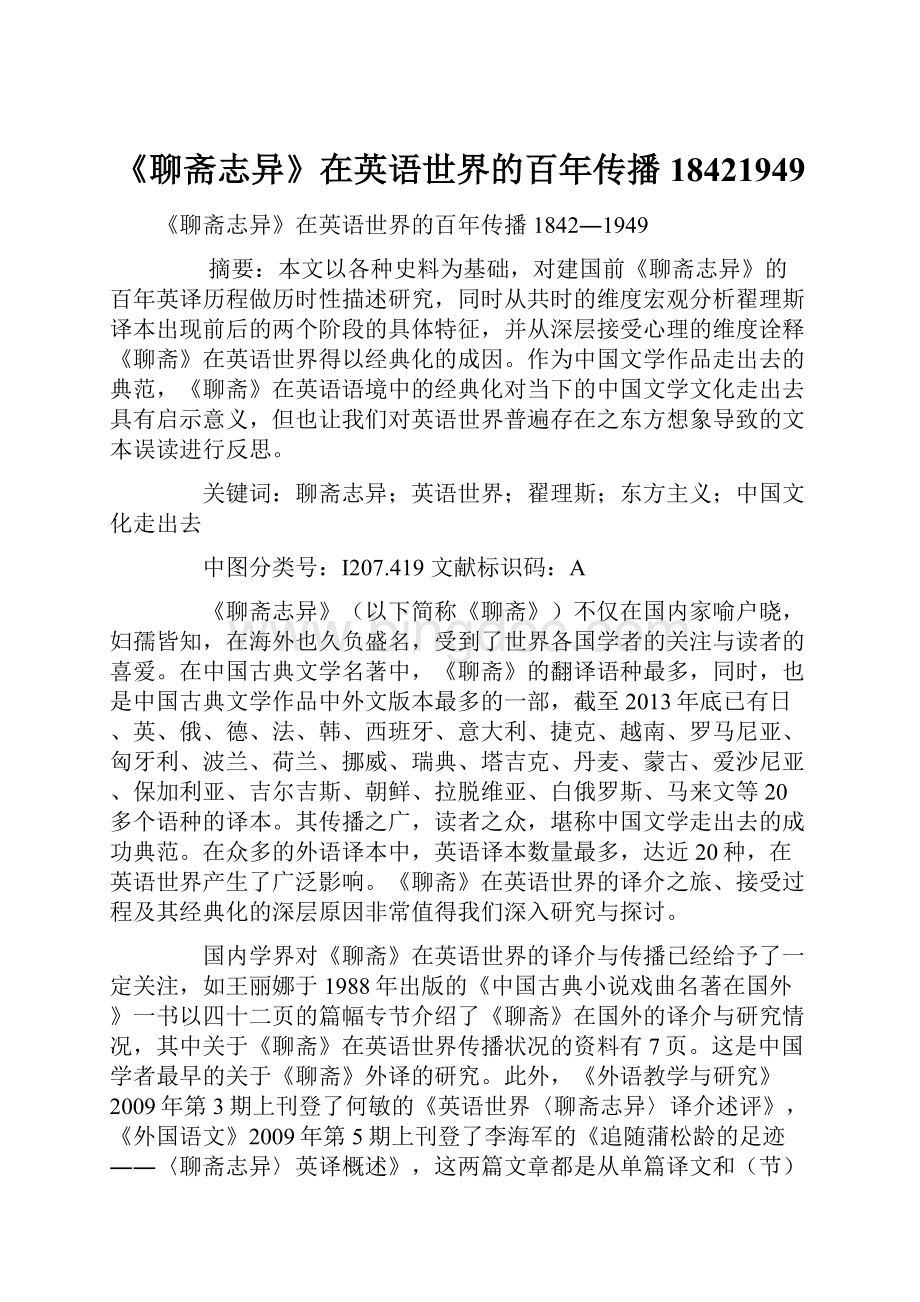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
摘要:
本文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对建国前《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历程做历时性描述研究,同时从共时的维度宏观分析翟理斯译本出现前后的两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并从深层接受心理的维度诠释《聊斋》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
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在英语语境中的经典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反思。
关键词:
聊斋志异;英语世界;翟理斯;东方主义;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I207.419文献标识码:
A
《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海外也久负盛名,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与读者的喜爱。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聊斋》的翻译语种最多,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截至2013年底已有日、英、俄、德、法、韩、西班牙、意大利、捷克、越南、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荷兰、挪威、瑞典、塔吉克、丹麦、蒙古、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吉尔吉斯、朝鲜、拉脱维亚、白俄罗斯、马来文等20多个语种的译本。
其传播之广,读者之众,堪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典范。
在众多的外语译本中,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达近20种,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之旅、接受过程及其经典化的深层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国内学界对《聊斋》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已经给予了一定关注,如王丽娜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以四十二页的篇幅专节介绍了《聊斋》在国外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其中关于《聊斋》在英语世界传播状况的资料有7页。
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的关于《聊斋》外译的研究。
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上刊登了何敏的《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外国语文》2009年第5期上刊登了李海军的《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英译概述》,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单篇译文和(节)译本两个角度分别评述《聊斋》的英译历程。
三位学者的研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聊斋》的译本情况,为研究者了解《聊斋》的译介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随着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研究的不断深化,学界应该更深入探讨《聊斋》英译历程中译入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范式以及赞助人等影响译本接受的超文本因素,找出《聊斋》被广泛接受并经典化的深层原因,从而为我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献计献策,是当务之急。
鉴于1949年前《聊斋》的英译在译介模式、译者身份、意识形态、传播路径以及译本接受上都迥异于建国后的译介。
本文主要就建国前一百余年的翻译活动进行评述,从历时性的角度纵向考察建国前《聊斋》的英译历程,以1880年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的首个《聊斋》节译本的出现为界,将这一长达百年的译介过程分为两个时期;同时,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在评述个体译文(本)的基础上对《聊斋》英译历程进行宏观观照,分析各个时期译介的总体特征,总结《聊斋》在英语世界获得接受的经验,为当下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始于歧见,但终成贡献(1842-1879)
1842年到1880年的近四十年是《聊斋》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第一阶段。
虽然《聊斋》早在1768年的昭和时代就传入了一衣带水的日本,其后不久也传入朝鲜,对两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由于日本与朝鲜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汉学功底深厚,具备无障碍阅读汉语原文的能力,因此日朝两国迟迟没有出现《聊斋》的译本,反而是与中国语言文化差别悬殊的英语世界最先出现了《聊斋》的译介。
这一阶段始于184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Gutzlaff,1803-1851)分别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聊斋》,讫于1880年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的首个《聊斋》节译本问世。
关于《聊斋》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学界至今仍存有不同说法。
王丽娜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中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卫三畏。
他的两篇英译文《种梨》和《骂鸭》,收录在他1848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1848)的第一卷中”[1]214。
此说法长期以来被广泛接受,但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燕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顾钧等学者提出了商榷的意见。
王燕在2008年第2期的《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了《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一文,认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第一次将《聊斋》介绍到西方。
据王燕考证,1842年,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第十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名为“ExtraordinaryLegendsoftheTaoists”(《道家之非凡传奇》)的评介文章,把《聊斋》归为宣传“异教信仰”的宗教读物。
除了介绍《聊斋》外,这篇文章还简要讲述了其中九则故事的情节,分别为:
《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
作者未署名,只说是某通讯员评论(reviewedbyacorrespondent)。
经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韩南(PatrickHanan,1927-2014)考证,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聊斋志异》的阐述性文字”[2]80,“郭实猎①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关于《聊斋志异》的阐述性文字”[2]80。
王燕据此推论郭实腊应是本文作者。
王燕还将郭实腊的评介译为汉语,题为《〈聊斋志异〉西传第一文》,发表在2007年第2期的《蒲松龄研究》上。
顾钧则对王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他于《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3期上发表《也说〈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认为1842年卫三畏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1842)中包含的三篇《聊斋》故事译文应被视为是《聊斋》西入英语世界的首次尝试。
基于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顾钧否定了王丽娜认为卫三畏于1848年在《中国总论》中首次译介《聊斋》的说法。
《拾级大成》是卫三畏于1842年编订的汉语学习教材。
在文选部分,卫三畏选择了三篇《聊斋》的故事,分别是《种梨》、《曹操冢》和《骂鸭》。
1848年,卫三畏出版了汉学著作《中国总论》,在第二十三章“雅文学部分”介绍了《聊斋》,并附录了《种梨》和《骂鸭》两则故事的英译文。
除了在《拾级大成》和《中国总论》中收录《聊斋》的故事译文外,1849年卫三畏还在《中国丛报》第十八卷第八期上发表了《商三官》的译文。
① 这一时期是《聊斋》在英语世界走向经典化的关键时期,其中翟理斯的译本功不可没。
翟译本收录了164篇《聊斋》故事,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聊斋》节译本,“其后数度重刊,更兼转译欧洲诸文,于西方代表蒲松龄百年之久”[9]xxxii,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译本。
首先,翟理斯把《聊斋》当作严肃的文学作品看待。
翟理斯对蒲松龄和《聊斋》的极度推崇,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即可见一斑。
翟理斯编撰的《中国文学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1901)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首部从历史发展上系统阐述中国文学源流传承的著作①。
全书446页,仅专项介绍蒲松龄与《聊斋》的篇幅就达20页之多,而介绍李白和杜甫的内容加起来不过6页。
他在书中说,“观满清一朝文学肇始,实在一志异之人”[10]338。
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与渊博学识也推崇备至,“文尽简约,几无一可删略之词”。
他说:
“观满清一朝文学肇始,实在一志异之人。
”[10]338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与渊博学识也推崇备至。
“文尽简约,几无一可删略之词,且词工新意,妙处横生,非文章宗匠如蒲松龄者不可为也;文尚用典,经典引据含千年之辞文诗赋,且隐喻甚丰,广饰修辞,唯卡莱尔可与相媲。
其文精润纯雅,中国文士皆引以为宗……”[11]xxiii,将蒲松龄与19世纪的英国文体大家卡莱尔(ThomasCarlyle)相提并论,足见翟理斯对蒲松龄的推崇。
选译《聊斋》中他认为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篇章译为英语,也是由翟理斯对蒲松龄的敬仰所促成。
其次,翟理斯翻译《聊斋》的目的是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
这在19世纪中国面临西方侵略瓜分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翟理斯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翻译的初衷:
“增我人民之见闻,使中华帝国礼仪风俗闻诸英伦。
”[11]xxii为此,仅在译书书名的选择上,翟理斯就用心良苦。
他先后否定了卫三畏的“PastimesoftheStudy”和梅辉立的“TheRecordsofMarvels,orTalesofGenii”,认为两者只着眼于鬼神精怪而忽略了《聊斋》的文学性及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太过狭隘,不适合作为书名。
最后他敲定书名为“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
翟理斯在译序中说,“‘聊’字韵义甚广,实不可译,窃以‘中国’代之,此亦可表此书之要旨也”[11]xx。
书名中重点突出了原书名中并没有的“中国”,足见翟理斯认为译书是为了增进英国读者对中国的认识。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背景文化,翟理斯在译文后添加不少译注,每篇后几条至十几条不等,有不少译注对译文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各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描摹。
这些注释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丹方风水之术,葬丧婚娶之礼,不老长生之药,龙蛇狐怪之崇”[11]xxii都在其内。
翟理斯译注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证。
有时他援引西方学术著作对原文涉及的问题作补正或将西方的文学作品相互印证。
如在《画壁》的一文中,翟理斯将朱孝廉飞升入壁和在英国妇孺皆知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记》的场景作对比,很容易唤起英语世界读者的文化认同感,给读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翟理斯的译本出版之后风靡英语世界,拥趸众多,在将《聊斋》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聊斋》的欧洲其他各种语言译本大多由是翟理斯译本转译。
虽然20世纪后一些翻译理论家对翟理斯的翻译策略颇有微辞,但翟理斯译本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译本。
这一时期的译介成果蔚为壮观,几个译本看似冗乱纷繁,实则都表现出译作在被经典化、被接受过程中的特征。
首先,从发行渠道和流通范围上看,与发轫之初的“侨居地汉学”截然不同,这几个译本全部都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由英国的德拉律(Thos.delaRue)公司出版;索利的译本StrangeStoriesfromtheLodgeofLeisure由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霍顿?
米夫林?
哈考特(HoughtonMifflinHarcourt)公司出版;邝如丝的译本ChineseGhostandLoveStories由纽约的万神图书(PantheonBooks)公司出版。
这些译本发行量较大,翟理斯和邝如丝译本其后又几度重刊,拥有众多读者,影响深远。
其次,这一时期译介的目标读者为普通读者,译本追求可读性,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大多文笔晓畅,优美耐读。
最负盛名的翟理斯译本文笔优美典雅,虽然进行了一定改写,但仍在最大限度上保存了蒲松龄原本的文风。
他的《聊斋选》出版后受到了学者和评论家的赞扬,与翟理斯同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的著名汉学家理雅阁(JamesLegge)在《学术》(“TheAcademy”)上发表书评,称赞“翟理斯先生的译文质量很高”[12]185。
当代著名汉学家闵福德(JohnMinford)充分肯定了翟理斯的翻译成就:
“……迄今尚无译者能超越翟理斯。
翟理斯毕生浸淫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对蒲松龄古雅简约的文风颇有领悟,并诉诸其英文行文中。
”[13]1翟理斯译本的另一个特色是删去了原著中的性描写和评论性文字“异史氏曰”。
翟理斯在序言中说,“中间有大不宜于当世者,其文粗劣低俗,颇似十八世纪本国庸俗小说家之貌”[11]xxix,意即《聊斋》中大胆的情爱描写“大不宜于当世”。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尊奉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对两性之间的行为规范标准要求很严格,任何与性有关的话题都成为禁忌。
《聊斋》中大量不加隐晦的性爱描写在当时的英国读者看来不堪入目,翟理斯译本中对此一律予以删除或改写。
例如《画壁》中,朱孝廉入画之后见到一貌美少女,“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于狎好”[14]4。
此处翟理斯竟译为一段婚礼仪式,让朱孝廉和少女拜堂成亲,并且煞有其事地添加译注,描述中国婚礼场景;下文的“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方乐未艾”,翟理斯也选择直接略去。
另外,英国小说发展到维多利亚晚期,摒弃了早期小说中作者使用插入式评论夹叙夹议的传统,因此《聊斋》篇末的“异史氏曰”不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习惯。
因此,翟理斯对性描写和“异史氏曰”进行了删改以更好地为英语世界读者所接受。
另一位译者索立认为,《聊斋》是文学作品,因此他希望“读者能从英译文中得到读原著的感觉”。
他反对逐字逐句的对译,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学都存在于其独立的传统、文化与信仰中,每个单词都有其文化蕴涵,不了解这种文化的人得不到正确的含义”,一旦追求字句的对等则“所有的魅力、美感和趣味都荡然无存”[15]3。
他还举出意大利谚语“tradutoretraditore”(翻译即叛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索立基本采取了意译的方法,因此,他的译本通顺晓畅。
对于读者较难理解的中国文化典故,索立大多以英语国家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化意象取代,做了一定改写。
自幼受家学熏陶的邝如丝则选择了《聊斋》中40篇最为凄婉动人的狐鬼爱情故事译成英语,译本语言优美动人,可读性非常强,引起了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致力于《聊斋》全本翻译的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聊斋》译本。
除了毛继义、陈途宏译本至今无迹可考外,其余三个译本都把《聊斋》当做文学作品看待,译笔优美,文字晓畅,可读性很强,但同时改写的痕迹也很明显。
第三,选篇上倾向于故事性较强的短篇小说。
纵观翟理斯译本中的164篇故事,不难发现这些故事大多情节跌宕,故事性很强。
而索利的译本也是如此选择,尽管由于改写过多,使得他的译本读起来像是“英国文化中略带东方色彩的哥特故事”[16]150。
邝如丝译本则选择了《聊斋》中40篇狐鬼爱情故事,成书后大受好评。
这一时期的《聊斋》译本不仅在普通读者中获得好评,更成为汉学界关注的重点。
翟理斯本人即英国汉学界的三大巨星之一,《聊斋志异选》作为他的重要译著,在英国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1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以20页的篇幅介绍《聊斋》一书并予以高度评价,正式把《聊斋》纳入欧美汉学研究的范围。
其他三个译本和和数十个单篇译文陆续面世,使得《聊斋》成为广受欢迎的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为汉学界所认可。
至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聊斋》的英译也走入低谷。
但彼时《聊斋》已经走过经典化过程的关键一步,成功走入了英语世界学者与读者的视野。
三、《聊斋志异》走出去的当下启示
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在特定时代的经典化,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查明建曾撰文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做出如下定义:
翻译文学的“经典”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canonized)了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品[17]87。
《聊斋》被英语世界读者接受、走向经典的过程可以说是这三种“经典”合力促成的结果。
《聊斋》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地位自然毋庸置疑,其文学魅力、其文化价值、其机趣、诙谐、智慧及其普世价值都是其得以在英语世界畅行的主要原因,因此才能成为“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
翟理斯的节译本《聊斋志异选》文约质美,“于西方代表蒲松龄百年之久”[9]xxxii,作为经典译本在《聊斋》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而在当下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宏观背景下,《聊斋》作为“第三种经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这一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聊斋》故事大多记述花妖狐魅和畸人异行,在文类上与英语文学中的“哥特文学”相契合。
英语民族对超自然之神秘体验的钟爱在洋洋大观的哥特小说中就可见一斑。
“尽管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许多惊险、恐怖的故事,但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英美文学那样不仅创作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影响广泛的哥特传统”[18]90。
此外,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拨使得作家冲破了克制情欲的理性主义框架,转而挖掘人的精神世界。
探索想象、直觉与神秘体验等非理性因素成为文学的主潮。
无论是英语民族对阴森恐怖的超自然因素的接受心态,还是彼时英国的社会文化语境,都为《聊斋》创造了有利的接受环境。
《聊斋》在19世纪中后期进入英语世界并非偶然。
19世纪末英语世界对中华帝国的奇异的东方想象也是《聊斋》获得普遍接受的另一重要因素。
“东方、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东方不是东方,只是被西方‘东方化’了的东方”[19]49。
自13世纪《马可?
波罗行纪》中描绘了一个遍地黄金的富饶之邦起,无论是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还是启蒙运动时期将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作为尊崇理性道德、排斥异教迷信的权威与楷模,抑或是18世纪末起将中国贬损为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作为“本我”的西方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19世纪末英语社会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处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鼎盛时期,“日不落帝国”的殖民辉煌使不列颠上下产生一种虚妄的文化优越感。
在英国人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形象,而隶属于东方的中国则被描绘成是非理性的、堕落的、野蛮的、不正常的,是堕落腐朽、需要西方文明征服和拯救的异国。
在《聊斋》中,化身人形与书生交媾的狐女,死而复生穿衢过巷的老妪,能行奇术入云偷桃的艺人,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偏见相吻合。
在阅读《聊斋》故事的同时读者固有的期待视界在花妖狐魅、畸人异行的文本形象中得以吻合。
在19世纪欧洲人的眼中,东方除了是愚昧腐朽、野蛮落后的代名词,还意味着神秘迷人的异域风情。
赛义德认为,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的地方、异国情调的存在,难忘的风景、回忆和非凡的经历。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与各种商贸的频繁往来,英美等国民众对中国社会文化与风土人情也开始逐步了解,留长辫子叩头作揖的男人和穿旗袍裹三寸金莲的女人无不刺激着英语世界民众的猎奇心理。
出于对陌生事物的好奇,他们渴望获取对中国这一远隔重洋的古老国度的奇异传闻。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等关于中国之内容玄异、情节跌宕、充满异域风情的翻译文学作品自然就广受欢迎。
《聊斋》也褪去了在本土语境内讽世大作的光环,在英语语境中的作品形象转而成为《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①,并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接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聊斋》以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等译本为载体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是不争的事实。
这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还要有精品意识。
《聊斋》在海内外均获得广泛接受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蒲松龄吸收了“文人小说”与“市人小说”两种传统的营养,使《聊斋》成为“融雅文学与俗文学于一炉”[20]14的集大成之作,呈现出审美趣味的多层面性,“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在‘思想感情和态度上’与自己一致、并能引起共鸣的作品”[20]14。
如莫言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绝不仅仅是因为葛浩文、陈安娜等人翻译的原因。
莫言以其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这样葛、陈等人的翻译顺水推舟,才能锦上添花。
可见,在当下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尤其要有精品意识,甄别遴选真正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译介到全世界读者的面前。
其次,为了获得接受而刻意迎合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则是不可取的。
在当今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固有的他者想象,扭曲化甚至妖魔化中国的阅读倾向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只有关于政治和性的中国当代小说在西方才有市场”的说法,西方的图书市场上关于中国的小说中,颇不乏以暴力、淫秽、政治等虚构元素为噱头的作品。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深层目的是为了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真实的认知与了解,而非向异国读者传达歪曲的中国形象,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误读。
中国的译家和有关部门有必要选择能够传达真实中国形象的作品进行译介,以避免适得其反的结果。
作为成功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被严重误读,从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讽世大作沦为传达扭曲的中国形象的《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幸耶?
悲耶?
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