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上.docx
《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上.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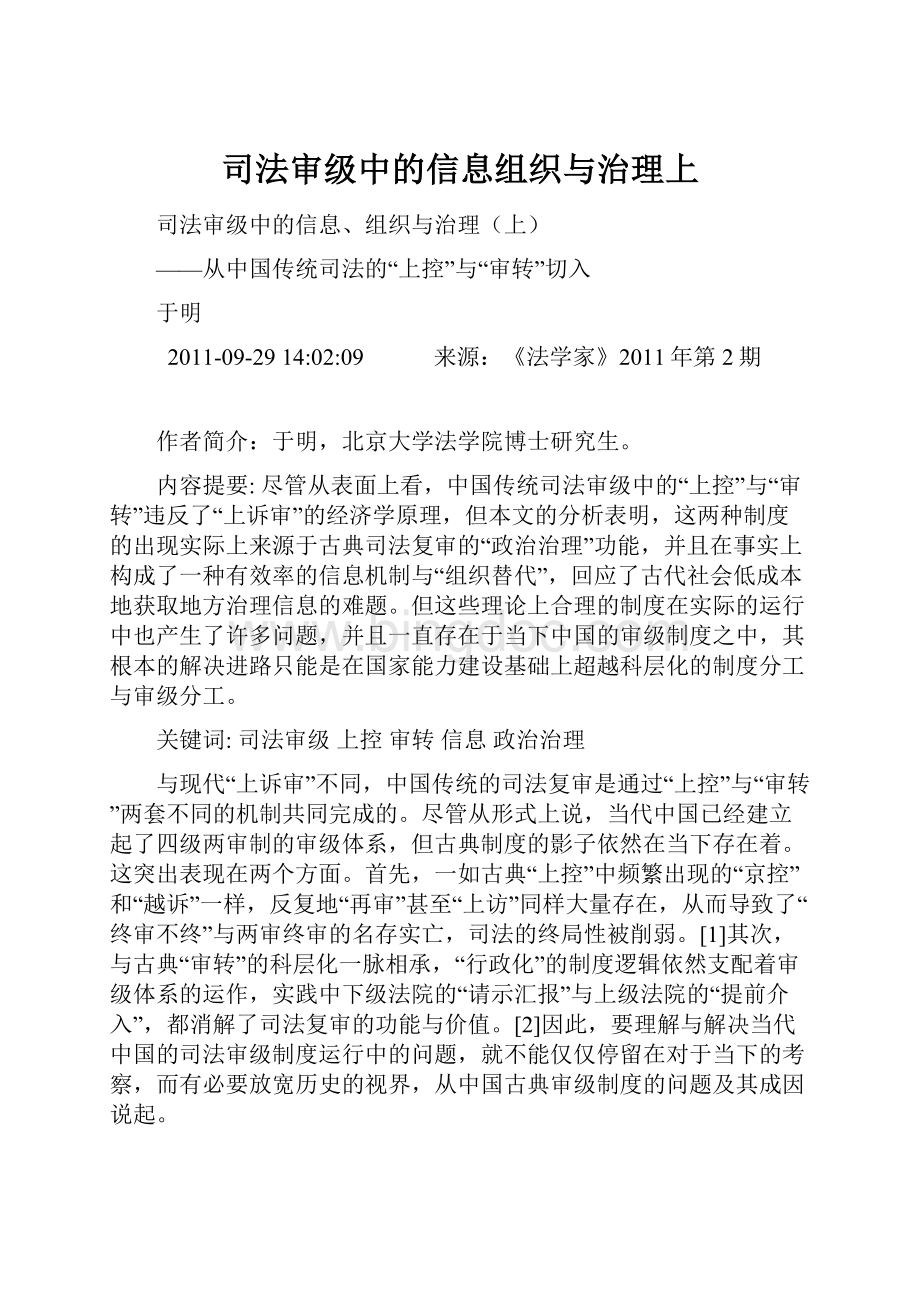
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上
司法审级中的信息、组织与治理(上)
——从中国传统司法的“上控”与“审转”切入
于明
2011-09-2914:
02:
09 来源:
《法学家》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于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司法审级中的“上控”与“审转”违反了“上诉审”的经济学原理,但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来源于古典司法复审的“政治治理”功能,并且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有效率的信息机制与“组织替代”,回应了古代社会低成本地获取地方治理信息的难题。
但这些理论上合理的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并且一直存在于当下中国的审级制度之中,其根本的解决进路只能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基础上超越科层化的制度分工与审级分工。
关键词:
司法审级上控审转信息政治治理
与现代“上诉审”不同,中国传统的司法复审是通过“上控”与“审转”两套不同的机制共同完成的。
尽管从形式上说,当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四级两审制的审级体系,但古典制度的影子依然在当下存在着。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一如古典“上控”中频繁出现的“京控”和“越诉”一样,反复地“再审”甚至“上访”同样大量存在,从而导致了“终审不终”与两审终审的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被削弱。
[1]其次,与古典“审转”的科层化一脉相承,“行政化”的制度逻辑依然支配着审级体系的运作,实践中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与上级法院的“提前介入”,都消解了司法复审的功能与价值。
[2]因此,要理解与解决当代中国的司法审级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当下的考察,而有必要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中国古典审级制度的问题及其成因说起。
但本文又并非只是对于历史的梳理。
在回顾了中国古典司法复审的特点后,我将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原理重新解读帝制时代的“上控”与“审转”。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古典的制度都并不符合现代“上诉审”的效率原则,但研究将表明,由于制度目标与关注点的不同,帝制时代的司法审级制度依然包含了成本与效率的考量,并同时构成了基于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
最后,本文还将指出,传统制度也带来了科层制的“反功能”与“目标替代”的不良后果,根本的解决进路,只能是超越科层化的制度分工与审级分工;而这一结论,对于现在的改革,也依然适用。
一、帝制中国的司法复审[3]
中国的帝制始于秦汉,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乞鞫”与“奏谳”等复审制度的雏形;但真正制度化的司法复审确立于隋唐时期。
[4]从这一时期开始,直至晚近的清代,帝制中国的司法发展出一套完备的复审制度,并创造出了与现代的“上诉审”迥然有异的审查机制。
尽管历代的制度各有损益,但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一般化的社会科学的解说,因此以下只是以清代的“上控”与“审转”为例,说明中国传统司法复审的具体运作机制。
清代的地方审级分为县、府、司、院四级。
[5]与现代的上诉一样,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基于当事人请求的“上控”制度,其适用的对象是所有州县审理的案件,既包括重大刑事案件(“命盗”),也包括轻微刑案(“笞杖”)与全部的民事案件(“民间细故”)。
依据清律,只要当事人对于裁判结果不满,就可以经由“控府、控道、控司、控院”,直至提起所谓的“京控”—即向在京衙门乃至皇帝本人提起上控。
“京控”的具体形式,除向都察院或步军统领衙门等呈递状纸外,还包括“击登闻鼓”与“迎车驾”等特殊形式。
[6]
但清代的司法复审又不等同于现代的“上诉审”。
较之“上诉”的终局性,“上控”不具有明确的终审审级。
在现代司法中,上诉的层级往往设有终审限制,案件至多经过两到三次审理即告终结(即两审或三审终审)。
然而,依据清律,无论案件是否结案,也无论结案后的时间长短,均可提起“上控”;且只要当事人对复审结果不满,所有州县受理的案件,均可层层“上控”,直至“京控”,乃至于皇帝本人。
甚至于“京控”之后,仍可再次翻案与反复申诉。
[7]
与此同时,清代的“上控”还深受“越诉”问题的困扰。
当事人往往不遵循审级的科层而直接上诉到更高的审级,从而导致了所谓“京控”大量增多。
尽管在清律中对于“越诉”和“京控”有明确的禁止,[8]但在实践中,对于“越诉”的这些限制似乎又并不严格;[9]尤其是对于“迎车驾”与“击登闻鼓”等非常“京控”手段,案件的性质与真实往往成为法定的免责理由。
[10]甚至即便是对于一般的“越级上控”,只要案件本身确实关系重大,“笞五十”的惩罚也往往在实践中被免除。
[11]总之,在事实上,清代的做法不仅未能阻止越级上控的发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纵容甚至鼓励的作用。
其次,“上控”又并非清代唯一的复审形式,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形式。
与之并存的,是另一种案件自动逐级复审的“审转”制度,其适用的对象限于可能判处徒、流、死的重大刑事案件(往往是“命盗”案件)。
具体而言,对于徒刑案件,由州县完成侦查与初审,并在拟定罪刑(“拟律”)后,将案犯与卷宗上报府、司两级复审。
但无论州县还是府、司,都并无判决之权,真正的生效判决只能在上报后由督抚本人做出。
而对于流刑案件,即便督抚也无权判决,而是对案卷审核后上报刑部,最终由刑部作出生效判决。
最后,对于死刑案件,程序最为复杂,由督抚具题后上报刑部核拟,并经三法司会签,最终呈请皇帝批准。
而皇帝的批示又可分为立决与监候;对于后者,仍需交押等候每年的秋审复核。
[12]
总之,在“审转”制度中,案件均由各级自行上报,无需当事人申请。
这种逐层的“审转”与官员的责任相联系。
对于基层的州县官而言,无论是否存在偏私或腐败,任何“错案”都可能带来严厉的惩罚,不仅可能殃及仕途,还可能因此而丧命。
[13]这种责任又是连带的,一旦错判被发现,不仅州县官本人,而且所有承担“审转”责任的府、司、院等各级官员,都可能因而受到连带。
尤其是负有“亲提审讯”之责的知府,如果未能“辨明冤枉”,即便毫无“贪赃”或“徇私”,也同样可能被“革职处分”,甚至处以刑罚。
因此,在严格连带的“审转”责任之下,即便简单的错案平反,其背后因此受到牵连的“官犯”群都可能是难以计数的。
[14]
在简要描述了帝制中国的司法复审之后,我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困惑与疑问:
在传统司法中,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了“上控”与“审转”并存的二元复审体制?
又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越诉”的屡禁不止和科层化“审转”的存在?
但本文并不打算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设问的本身可能就值得推敲。
这些疑问不仅“先入为主”地预设了现代“上诉审”的“天然”合理性,而且隐含地将一切有别于“现代”的制度都视作值得怀疑的“异端”。
为了避免这种“现代性”带来的主观偏见,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暂时从历史的语境中走出,首先对于“上诉审”的一般原理做些理论上的论证与分析,同时也为本文之后对于古典复审制度的分析提供一个尽可能客观中立的理论框架。
二、“上诉审”的经济学
一般认为,上诉审的基本功能是“错判纠正”与“法律统一”;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校正功能”(correctivefunction)和“预防功能”(preventivefunctions)。
[15]前者着眼于“事后”的“纠纷解决”,旨在通过纠正错判来确保公正与减少“错误成本”;[16]而后者的出发点在于“事前”的“规则之治”,试图通过上诉案件的审理来实现法律解释与适用的统一,甚至必要时创制规则(司法造法),从而实现法律的规则化“治理”。
以下,本文将这两类功能简称为“纠错”与“规则治理”。
但问题随之而来。
首先,既然是“纠错”,为什么又总是设定上诉的终审审级?
毕竟,真相的发现是无穷的,终审的存在本身可能构成“有错必纠”的障碍。
其次,如果上诉审包含了国家的“规则治理”,它的启动为什么又只能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呢?
国家的“主动出击”难道不是更有利于规则统一的实现么?
对此,传统的回答,可能诉诸某种理念或“大词”,比如将终审的设定视作“程序正义”的体现,或是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视作“权利话语”的胜利。
这些解说都有道理,但依然停留在概念的层面,在我看来,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解释。
首先,就终审的存在而言,表面上看这似乎会导致一些错判无法得到纠正。
但司法的追求并不只是正确。
诉讼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制度设计还必须建立在效率的考量之上。
而实际上,无论是对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上诉审较之初审的新增收益都十分有限,并呈现出边际效益的递减,但为此付出的成本却是巨大的。
因为事实的认定更多地取决于信息的多少,而非裁判者的智识;仅仅增加审级,不仅无助于纠错,且随着时间流逝与法官亲历的减少,还可能导致新的错误。
至于法律的解释,本身即是一个“权威”的问题,同样与智识无关;任何的法律问题一经终审,问题本身即告终结,反复重审的收益也必然为零。
[17]因此,现代的审级大多限定在两审或三审终审,以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成本。
其次,“上诉”的启动之所以基于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从中获得解说。
有如前述,上诉审的首要功能是“纠错”,但这一功能的实现同样须付出相应的成本,尤其是甄别与发现“错判”的“信息成本”。
因此,上诉审制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在于如何有效地识别潜在的“错判”,以尽可能减少对于正确判决的复审。
[18]而既有的研究恰恰表明,基于当事人请求的上诉审,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回应了信息成本的问题,构成了一种低成本的信息机制。
毕竟,由于自身的亲历和利益的相关,在发现可能错判的问题上,当事人较之法官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与利益驱动,相应的成本也更低。
[19]
在这个意义上,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构成了当事人与法院共同承担信息成本的分摊机制。
当事人对于错判案件的初次甄别,相应地减少了上级法院甄别错判与复审案件的范围与数量,从而有效降低了上级法院的信息费用。
[20]相反,如果是由上级法院自行甄别错案,由于信息成本的高昂,势必导致大量资源投入的浪费;而考虑到真正的错判往往只在全部判决中占据较小的比例,这种低收益的成本耗费更是难以估量。
正是基于这种明显的比较优势,我认为,由当事人承担信息成本的上诉机制,更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不过,这一信息机制的适用还隐含了一个“分化”的前提:
错判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倾向于提起上诉,而正确的判决则一般不再进入复审。
相反,如果无论判决正误,当事人都不上诉(无人上诉)或都上诉(人人上诉)的话,那么上诉的信息机制将是彻底失效的。
但正如萨维尔(StevenShavell)指出的,由于上诉的“私人成本”(privatecost),这样一种“分化”机制往往会自发地出现。
因为如果我们假定法官审判的基本公正,则上诉中推翻错判的概率将明显高于正确判决被推翻的概率;相应地,对于错判上诉的预期收益也将明显大于正确判决的上诉。
如此一来,在上诉成本一定的情况下,错判的当事人将具有更大的激励提起上诉,而正确判决的当事人则会发现得不偿失,从而选择放弃。
[21]换言之,这里存在着类似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
但萨维尔同时指出,这仍然是理想的状态。
在真实情形中,由于上诉成本过高或过低,很可能导致自发“分化”机制的失效。
[22]因此,在许多时候,面对自发机制的失灵,还有必要通过“费用’(fee)或“补贴”(subsidy)的设置来确保“分化”的实现。
[23]比如,要减少正确判决的上诉,可以提高上诉收费与缩小上诉理由的范围;反之,则可以考虑降低收费或是放宽受理标准,甚至给予上诉人某些许诺,比如刑事的“上诉不加刑”,或民事的“利益不变更”,都可能为错判当事人提供更多的激励。
用“市场”的比喻来说,自发的上诉“市场”的失灵,同样离不开国家“有形之手”的补充。
不只是“纠错”,基于当事人请求的上诉,对于“规则治理”也是有意义的。
有如前述,“规则治理”的内涵是规则的统一与创制,这就要求上诉审法官能够识别与发现那些更有效率的规则。
而正如波斯纳(RichardPosner)指出的,正是由于上诉制度的存在,使得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规则的识别”上较之立法者具有更大的优势,法官创造的“普通法”也因此更有效率。
因为一般说来,当某一规则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时,被迫承担低效率成本的一方,往往更多地具有上诉的激励,从而使得对于低效率规则的上诉总是超过对高效率规则的上诉。
也因此,较之立法者的“盲目”,“上诉市场”(appealmarket)的存在,最终将导致越来越多有效率的规则为上诉审所接受。
[24]
以上就是“上诉审”的经济学分析。
这些研究表明,现代上诉审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司法的效率原则,因而具有可证成的合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审级中的“程序性”缺失和自行“审转”的存在,都似乎有悖于审级制度的效率追求。
当然,这仅仅是似乎。
面对一种在历史上长期存续的制度,我们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同情的理解”,审慎地考察它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与合理性。
因此,有必要从既有的理论出发,对于帝制中国的司法复审作出新的理论解说。
三、“上控”与政治治理
首先讨论“上控”。
传统审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上控”的“程序性”缺失,不仅缺乏审级的限制,而且即便是对于“越诉”的控制,在实践中也往往是“模糊”的。
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简单地归因为传统法律的“简陋”,或是统治者的“恣意”和“专断”。
但这只是概念化的解说,在我看来,这可能更多地源自古典的“上控”与现代的“上诉审”在制度目标与功能上的差异。
上诉审的基本功能是“纠错”与“规则治理”,这在古典“上控”中也有所体现。
“刑名违错”的纠正或是“冤抑”的平反,甚至于律例解释与适用的“齐一”,都可能是统治者的制度初衷。
但“上控”的功能又不仅限于此。
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到帝制中国的政治架构与核心关注之中,就不难发现,整个“上控”制度最初的逻辑起点,并非只是“纠错”或“规则治理”,而更多地旨在实现对于地方吏治民情的监督与控制,以确保社会治理的有序。
他们追求的同样是“治理”的功能,只不过与侧重法律统一与创制的“规则治理”不同,传统“上控”更多地是通过等级化的政治控制而实现的。
因此,我们或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政治治理”或“行政化治理”。
这一机制源自帝制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
严格说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并非不存在分权,至少在中央以至省级机关,已经出现了行政与司法的分开。
[25]但考虑到数量上占大多数的州县衙门,以及行政长官对于司法的影响,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古典司法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与司法合一”;[26]又由于在州县衙门的职权中,以司法和征税为主,因此,甚至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司法兼理行政”。
[27]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作为地方司法机关的州县衙门,其基本的职能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中央政权对于地方的控制与治理,而决不只是单纯地依据法律做出判断。
不仅是州县官,整个等级制的官僚体系也都服务于这一目标。
正如瞿同祖指出的,清代的政治架构,只有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即负责实际事务的“治事之官”;而他们的上级,无论是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还是巡抚或总督,都不过是监督官,即负责监督官员的“治官之官”。
[28]整个行政等级的目标都旨在实现对于最底层的州县官的监控;而与之相应的,作为附着于行政科层的中国古典司法审级,其最重要的职责也就不仅是为了“纠正错判”,或是“统一规则”,而更主要地是为了实现对于州县官的监督和地方秩序的稳定,是对于地方的“政治治理”的延伸与扩展。
[29]
基于这一目标,诉讼人的“上控”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尽管“上控”本身只关乎具体的个人与事件,但同时也蕴藏了有关底层社会的丰富信息;尤其是考虑到“上控”总是来自于地方官员的“审断不公”与“徇私枉法”,又往往包含了官员是否“清慎”的吏治信息。
因此,对于底层民众的“上控”,尤其是“京控”,统治者无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期维系帝国治理的“下情上达”,这从历代帝王近乎“苦口婆心”的言辞表达中亦不难看出。
比如,清代嘉庆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指出,“朕勤求治理明目达聪,令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接到呈词即行奏明申理,以期民隐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
[30]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上控”所提供的社会信息,就好比地方社会状况的一个“生理切片”,较之其他的信息机制,可能更“真实”地反映有关地方治理的“不良”信息。
[31]
这里,我们也就发现,传统的“上控”同样构成了特定的信息机制。
只不过,与“上诉”的信息传递集中于案件的本身不同,“上控”机制的目标,更多是为了传递有关地方社会的综合“治理”信息。
但两者的本质,都在于将发现信息的成本部分地转移给案件当事人,或者说是由当事人与法院共同分摊信息成本。
[32]又由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与当地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这样一种成本分担也是有效率的;尤其是考虑到帝制中国的信息传递成本的高昂,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与技术手段的欠缺,这一机制无疑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从“政治治理”的视角切人,我们也重新理解了“上控”的程序性缺失。
现代“上诉审”之所以设置终审审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复多次的复审在事实查清上的低效率。
但经济学的理论又告诉我们,考察效率的前提是“效率对谁而言”的问题。
[33]一旦制度目标发生转换,其效率的逻辑也必然改变。
获取地方治理信息的制度目标,也就决定了传统“上控”中审级的缺失未必是无效率的。
毕竟,在传统社会的条件下,面对信息的有限与传递的滞后,统治者关心的更多是如何确保这些原本脆弱的信息渠道的畅通,以尽可能获取地方吏治失败的重要信息,至于事实的查清与规则的确定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
考虑到帝国时代信息成本的高昂,[34]最大限度地减少“上控”的限制(成本),以求治理信息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许构成了一种有“效率”的选择。
四、“越诉”的禁与不禁
帝制中国在对待“越诉”上的禁与不禁的“模棱两可”,也同样可从中获得解说。
只不过,与单纯的效率解读不同,对于“越诉”问题的解说,我将更多地回到“上诉审”的理论模型,尝试从“上诉市场”与国家调节的视角重新解读帝国统治者“模糊”态度的成因。
尽管两者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与“上诉审”基于当事人请求一样,“上控”的启动也以利害关系人的控告为前提。
因此,“上控”制度运作的结果,可能构成一个类似的“市场”,并离不开“分化”机制的参与;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机制的关注点并不只是所谓的“错判”,而更多地旨在发现那些事关地方吏治与秩序稳定的“重要”信息。
之所以需要“分化”机制的原因,还在于传统国家能力的有限,以及政治治理的“秩序”导向。
[35]统治者往往只能有选择地激励那些事关“稳定”的重大“上控”(往往是“命盗”案件),而同时抑制“细故纷争”的复审请求。
从理论上说,这种信息的“分化”具有自发形成的可能。
帝国统治者也倾向于假定“命盗”案件更多地关系到个人生命与家族安危,因而比“细故”具有更大的“上控”激励。
除非是“冤抑”深重且无法伸张,小民也断不会承担巨大成本而不断“上控”(“非实有沉冤,谁肯自投缧绁”)。
[36]也因此,在这些看似不计成本的上控行为背后,往往隐含了地方吏治失败的重要信息,甚至于社会秩序动摇的征兆。
同时,由于上诉成本的失衡,当事人的“分化”往往无法自发地形成,而必须借助于相应的国家干预。
而回到帝制时代,类似的激励失效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可能表现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时间富余,以及可替代财富来源的匮乏,使得一些“上控”的机会成本极低,从而可能诱发百姓采取“缠讼”、“图赖”、“越级上控”等“小事闹大”的诉讼策略,以达到“以时间换利益”的目的;加之讼师的挑唆与闲散人员的参与,更是使得许多“细故纷争”进入到“上控”之中。
[37]而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制约因素,还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交通与信息的不便,以及帝国地域的广大,因而又往往导致小民的“上控”成本过于高昂[38](“川资旅费,需用浩繁,旷业废时,生机坐困,故凡牵连拖累者,莫不受害无穷”)[39],以至于将许多重大案件也挡在了统治者的视野之外。
因此,面对“上控”成本的不确定与“市场”的失灵,与萨维尔的“干预”理论一致,帝国统治者也需要通过设置额外的成本与收益来确保“上控”诉讼人的有效“分化”。
从这一视角进入,我们发现,所谓禁止“越诉”的程序性规定,实际上构成了国家对于上诉成本的“费用”设置,是为了隐性地提高“上控”的诉讼成本,以抑制可能的“细故纷争”的进入。
考虑到古代社会的交通与信息成本,每一级审级的增加,都可能导致成本的激增,因而可能构成制约潜在上控人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京控”,由于地方审级的多重,“逐级上控”的制约所带来的成本负担更是难以计数的。
同时,即便对于成功的“京控”,依照清律,上控人也将处于长期的羁押中。
显然,在统治者的眼中,这些措施都旨在增加当事人的上控成本,以确保能将有限的财力与精力用于重大案件的处理。
但在帝制中国,最为根本的制约依然来自于信息成本的高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理解统治者在对待“越诉”问题上的模糊态度,及其采取“选择性执法”(selectiveenforcementoflaw)[40]的原因。
毕竟,对于统治者而言,限制“越诉”的目的,原本在于确保有限的能力被用于地方的政治治理,但如果越级“上控”的案件最终被证明确实关乎地方吏治,甚至可能危及统治秩序时,这种限制本身就不再具有意义,案件本身的性质也当然地成为事实上的“免责理由”。
[41]正是通过这种“例外”,统治者事实上为重大案件的上控人提供了一种隐性的“额外收益”,从而可能激励此类案件的“越诉”和治理信息的传递,并最终实现统治者孜孜以求的“下情上达”。
用沈之奇的话来说,这些行为尽管在表面上“由越诉连及言之”,但在立法原意上却“意各不同也”。
[42]
以上的分析还只是初步的。
事实上,在王朝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统治者在对待“上控”(尤其是越级京控)的态度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即便是同一统治者,在控制的宽与严、放与禁的问题上,也往往呈现出阶段性的断裂与转变。
[43]但这些分析已经表明,帝制中国的“上控”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上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同样构成了一种特定的信息机制。
所不同的,只是对于“信息”的关注点存在差异。
尤其是在“分化”机制的问题上,帝国的统治者采取了成本与收益的调节,以确保“上控”信息功能的发挥和政治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注释:
[1]参见傅郁林:
《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参见贺卫方:
《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76页;苏力:
《司法解释、公共政策与最高法院》,载《法学》2003年第8期。
[3]现代意义的“上诉审”仅限于上级法院基于当事人请求对下级法院未生效裁判的重新审查。
但本文讨论的“司法复审”的含义更为宽泛,不仅包括基于当事人请求的复审,也包括案件的自行上报复审;复审的对象,既可能是未生效的判决,也可能是已经审结的案件,甚至可能是已经多次重复审理的案件。
[4]关于古代司法复审的一般性介绍,参见张晋藩主编:
《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5]其中州县为第一审级,“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府为第二审级,凡在州县“或有冤抑,审断不公”,即应向上一级“府”具控。
第三审级的“司”,即各省按察使司,实践中充当“府”的上级复审机关。
“院”即总督和巡抚,是地方的最高审级。
此外,中央还设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构成了清代司法的第五审级。
参见注[4],第389-404页。
[6]参见那思陆: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范忠信、尤陈俊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6页。
[7]参见赵晓华:
《略论晚清的京控制度》,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所谓“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
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诉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
又所谓“遂行来京控告者,交刑部讯明,先治以越诉之罪”。
《大清律例·诉讼·越诉》。
[9]参见[美]欧中坦:
《千方百计上京城:
清朝的京控》,谢鹏程译,载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主编: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
[10]如清代沈之奇强调,“击鼓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