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后裔与科学史.docx
《神的后裔与科学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神的后裔与科学史.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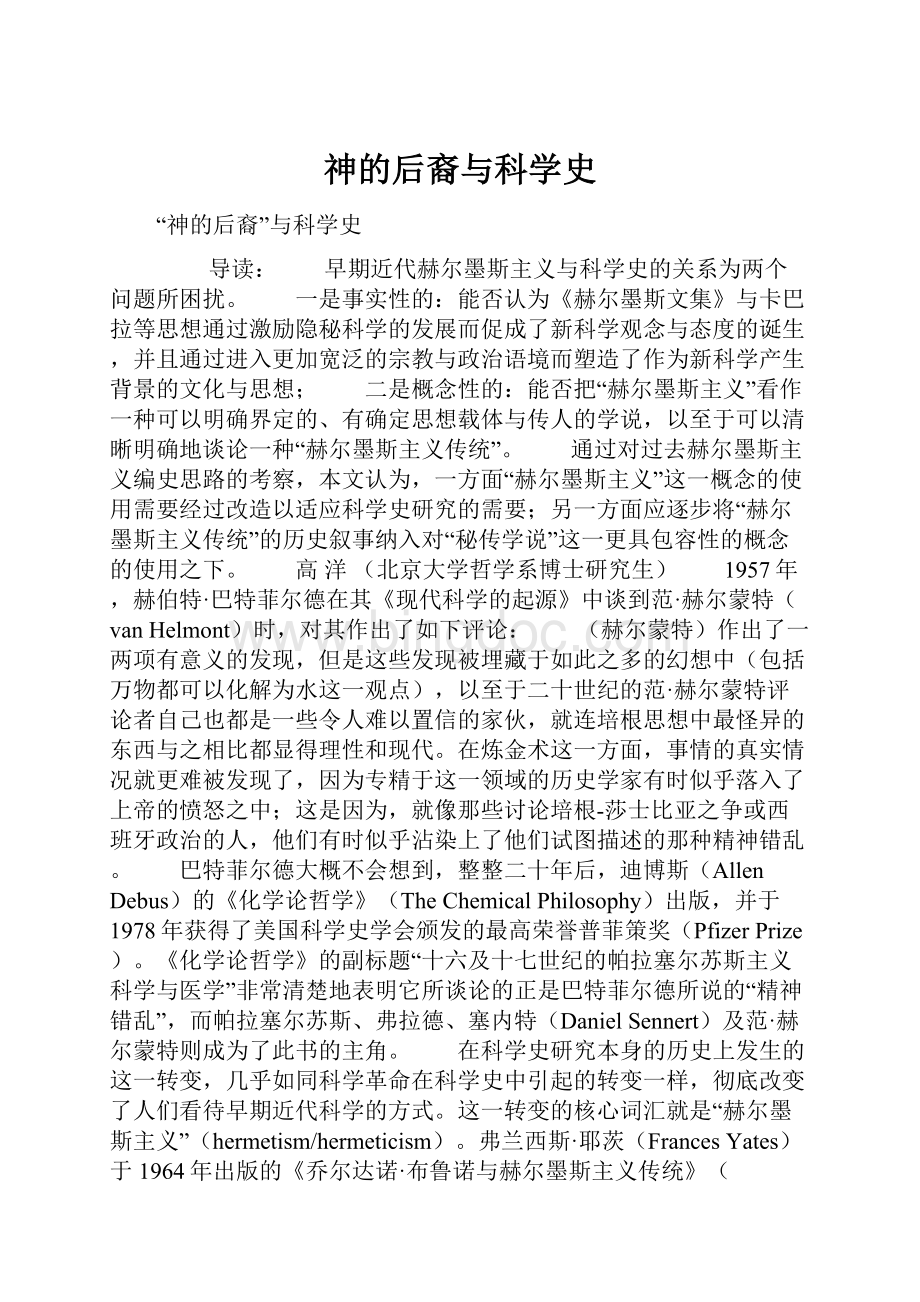
神的后裔与科学史
“神的后裔”与科学史
导读:
早期近代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史的关系为两个问题所困扰。
一是事实性的:
能否认为《赫尔墨斯文集》与卡巴拉等思想通过激励隐秘科学的发展而促成了新科学观念与态度的诞生,并且通过进入更加宽泛的宗教与政治语境而塑造了作为新科学产生背景的文化与思想; 二是概念性的:
能否把“赫尔墨斯主义”看作一种可以明确界定的、有确定思想载体与传人的学说,以至于可以清晰明确地谈论一种“赫尔墨斯主义传统”。
通过对过去赫尔墨斯主义编史思路的考察,本文认为,一方面“赫尔墨斯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需要经过改造以适应科学史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应逐步将“赫尔墨斯主义传统”的历史叙事纳入对“秘传学说”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的使用之下。
高洋(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1957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其《现代科学的起源》中谈到范·赫尔蒙特(vanHelmont)时,对其作出了如下评论:
(赫尔蒙特)作出了一两项有意义的发现,但是这些发现被埋藏于如此之多的幻想中(包括万物都可以化解为水这一观点),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范·赫尔蒙特评论者自己也都是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就连培根思想中最怪异的东西与之相比都显得理性和现代。
在炼金术这一方面,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更难被发现了,因为专精于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有时似乎落入了上帝的愤怒之中;这是因为,就像那些讨论培根-莎士比亚之争或西班牙政治的人,他们有时似乎沾染上了他们试图描述的那种精神错乱。
巴特菲尔德大概不会想到,整整二十年后,迪博斯(AllenDebus)的《化学论哲学》(TheChemicalPhilosophy)出版,并于1978年获得了美国科学史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普菲策奖(PfizerPrize)。
《化学论哲学》的副标题“十六及十七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科学与医学”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所谈论的正是巴特菲尔德所说的“精神错乱”,而帕拉塞尔苏斯、弗拉德、塞内特(DanielSennert)及范·赫尔蒙特则成为了此书的主角。
在科学史研究本身的历史上发生的这一转变,几乎如同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中引起的转变一样,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早期近代科学的方式。
这一转变的核心词汇就是“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hermeticism)。
弗兰西斯·耶茨(FrancesYates)于1964年出版的《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GiordanoBrunoandtheHermeticTradition)使这个词进入了科学革命研究的核心,她不仅将斐奇诺、皮科、阿格里帕、约翰·笛等人引入了科学史的叙事,而且鼓励学者重新将自然魔法、占星术及炼金术等“隐秘科学”(occultscience)纳入科学史的正当研究范围,同时还迫使人们对哥白尼、培根、牛顿等科学革命中的传统人物作出新的思考与评价。
对于耶茨来说,这一切都起始于《赫尔墨斯文集》(CorpusHermeticum),她相信这部著作及相关思潮的传播为早期近代科学思想的转变与形成提供了关键的动力。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科学史家已在耶茨开辟出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早期近代的赫尔墨斯主义”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的认识与反思。
对相关领域研究的考察将使我们发现,“赫尔墨斯主义”所提供的思想史资源并未枯竭,并且它将成为一个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秘传学说”(esotericism)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领域对于科学史研究富有启发意义。
从“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到“赫尔墨斯主义传统” 1.谁是赫尔墨斯?
赫尔墨斯主义所尊崇的核心人物“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Trismegistus)是一位据信生活于远古时代的埃及智者,而实际上他来源于埃及的托特神(Thoth)与希腊本土信仰中的赫尔墨斯神(Hermes)的杂糅与融合。
早在公元前5世纪,托特神与赫尔墨斯神就被混同为一,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称埃及流行托特神崇拜的城市为“赫尔墨波利斯”(Hermopolis),即赫尔墨斯之城[2]。
托特神首先是埃及的月神,而月亮是“众星的统治者,区分着季节、月份和年岁”,因此他也自然成为了时间之神及个人命运的统治者。
由于月相变化与埃及民众的生活节律息息相关,托特神又进一步成为宇宙秩序与宗教机构的创始者。
据说他还是计数与书写的发明者,因而他又被尊崇为知识、语言及科学之神,且尤其是一位伟大的术士(magician)。
无疑,古希腊人看到了托特神与赫尔墨斯神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冥界引导者和神使的身份,以及某些技艺的发明者。
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托特神被尊崇为世界的创造者,人们认为他用思想与言辞创作了世界;而在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哲学中,赫尔墨斯逐渐被等同于逻各斯(Logos),“已生成、在生成和将要生成的万物的创造者(demiourgos)和阐释者(hermeneus)”。
“三重伟大的”(trismegistos)这一称号被加于赫尔墨斯之上,最早见于公元2世纪晚期雅典那格拉斯(Athenagoras)的著作。
学者相信,这个称号实际上来源于埃及语言中形容词最高级的表达方式以及希腊人对这种表达方式的误解:
埃及语言将一形容词重复两至三次来表达其最高级的意义,如“伟大且伟大的(且伟大的)”即指“非常伟大的”或“最伟大的”。
希腊人将其按字面方式译为“megaskaimegas”,进而又转化为“megistoskaimegistos”,最终缩写为现在的形式。
在古代晚期的希腊罗马世界,“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已不再具有明显的神性,他的形象转变为一位拥有关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丰富知识的智者,并且他还是一位能使灵魂与其神圣起源恢复和谐的精神导师。
然而他仍然被当做神的后代,因此生活在极为遥远的古代:
奥古斯丁认为“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是阿特拉斯神(Atlas)的后代,因而是摩西的孙辈,他远在希腊哲人之前就在埃及讲授哲学。
一份日期不明的、被归于埃及历史学家马内托(Manetho,约280BC)名下的文本宣称托特神即是第一位赫尔墨斯,他将各种知识以埃及圣书体铭刻于石柱之上,大洪水过后,第二位赫尔墨斯(即“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发现了这些石柱,并将其中的知识译成希腊文保存于埃及神庙之中。
因此,尽管有些基督教思想家并不认为被归于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的教义是正确的(如奥古斯丁),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的存在,并且相信他具有古老和智慧的特征。
2.赫尔墨斯式的著作及学说 由于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只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方面,从古代到中世纪有许多作品挂靠在他的名下传播,另一方面,这些著作的内容与品质也极其复杂多样。
二十世纪研究赫尔墨斯式文献(hermetictexts)的两位重要学者斯科特(WalterScott)与费斯图基埃(André-JeanFestugière)将其分为两类,即流行的/技术的(popular/technical)与哲学的/理论的(philosophical/theoretical)赫尔墨斯式文献。
前者包括归于赫尔墨斯名下的魔法、占星术及炼金术等著作,后者的内容则较为确定,它包括一部由17篇长短不一的希腊文著作组成的文集、拉丁文著作《阿斯克莱皮乌斯》(Asclepius)、由斯托拜乌斯(Stobaeus)辑录的若干希腊文段,以及以科普特文和亚美尼亚文等保存的一些残篇。
迄今为止,学者尚未将所有所谓的技术性文献整理为一部可靠的文集,但哲学性文献则已有诺克(ArthurDarbyNock)与费斯图基埃所编辑的批判性文本,包括了所有已知的以希腊文与拉丁文形式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
哲学性文献普遍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中混杂有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犹太教、灵知主义及埃及本土思想等特征,它们并不是纯粹的哲学或宗教性著作,而更接近于神智学(theosophy)式的思辨与启示。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文献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流传于15-17世纪西欧的也正是这同一批著作。
尽管那时欧洲学者仍然普遍相信赫尔墨斯的古老性,现代研究则表明这些文本可能形成于公元1-3世纪,虽然在此之前其学说可能流传已久。
就内容而言,两类赫尔墨斯式文献最为明显的共同特征在于,相信一种无法直接经验的、然而又普遍存在的“交感力”(sympatheticpower)的存在,这种力量贯穿于一切现象、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领域,并将其联系为一,而人可以借助隐秘知识(occultknowledge)使这种力量为己所用。
技术性文献很少解释这种“交感”究竟是什么,而在哲学文献中,它被解释为由作为“一”的神所散发出的创造性和维护性的能量。
神之下为理智世界,理智世界之下为可感世界,太阳正处于这一可感世界的中心,恒星与行星的诸天球围绕它旋转,而人则是整个被造世界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microcosm)。
恒星与行星同样散发着能量,这些能量所组成的交感织体对万事万物发挥着影响。
星界中的众多精灵(daimon)则是这些能量的人格化,它们能够穿透身体而影响人类,从而构成其命运(heimarmene)。
赫尔墨斯式文献所表达的终极理想即在于修炼灵魂以超越命运所统治的地域,直到与神合一。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赫尔墨斯被作为一位伟大的术士和占星家崇拜的原因了。
在希腊化时期,术士被认为能够基于对交感力的知识而操纵这种充斥于宇宙间的力量,而埃及术士则最先具有利用魔法操纵神灵这一观念。
许多属于那一时期的希腊魔法纸草记录了这些实践,这些纸草的部分内容也被认为反映了赫尔墨斯主义的影响。
对斯科特与费斯图基埃来说,技术性文献的意义与价值完全无法与哲学性文献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两类文献必然有完全不同的来源。
晚近的研究则试图修正这种极端的看法,福登(GarthFowden)在其著作中力图证明,在赫尔墨斯主义的起源地埃及,魔法在宗教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费斯图基埃由于过分强调赫尔墨斯式文献的希腊特征,而无法接受魔法与炼金术等“非理性”的内容。
在福登看来,技术性文献是对哲学文献的“先行教授”(propaideia);而对相关文献作出“技术的”“哲学的”等等模式化的粗糙划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虽然如此,对两类赫尔墨斯式文献之间关系的探讨仍然充满争议,并无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表明历史上这两类文本的作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尽管谈论“赫尔墨斯主义”似乎容易使我们相信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以赫尔墨斯为信仰中心、以其著作学说为指导的宗教团体,但就当前证据而言,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
费斯图基埃与多利(H.D?
rrie)并不相信它曾在实际生活中发挥过影响,他们认为赫尔墨斯主义仅仅是一类哲学或宗教文献的代名词而已。
福登在其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念,并深入研究了赫尔墨斯主义在当时社会与历史情境下的实践。
勃洛克(vandenBroek)则指出,“赫尔墨斯主义”一词可用于指代相关文献中所表达的一套复杂的观念与实践,然而这一“主义”却并不说明实际上存在着人们所设想的融贯性与一致性。
我们将会看到,赫尔墨斯主义这种模糊暧昧的特征也影响到了它在早期近代思想史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3.耶茨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 当斐奇诺于1471年出版包含14篇拉丁译文的《赫尔墨斯文集》时,基督教欧洲并非早已忘记了赫尔墨斯的名字。
拉克坦修、奥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中对赫尔墨斯时有引用,《阿斯克莱皮乌斯》则自公元4世纪起就在拉丁欧洲广泛流传。
自12世纪起,自希腊文及阿拉伯文翻译而来的赫尔墨斯式文献与拉丁西方所产生的托名赫尔墨斯著作共同影响了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其中包括罗吉尔·培根、大阿尔伯特、托马斯·布拉德沃丁、埃克哈特大师及库萨的尼古拉。
自东方翻译而来的赫尔墨斯式文献主要是魔法与占星术等技术类著作,而《二十四位哲人之书》(LiberVigintyQuattuorPhilosophorum)和《论事物的六本原》(DeSexRerumPrincipiis)这类以拉丁文写成的托名赫尔墨斯文献则主要讨论神学与哲学问题。
这些著作的传播使基督教世界对待赫尔墨斯的态度重新充满了张力,这可以追溯到教父时代的意见分歧:
拉克坦修将赫尔墨斯尊为最为博学的上古智者及预言基督教诞生的先知,而奥古斯丁则将其谴责为运用魔法传播异端的异教徒。
斐奇诺聪明地同时利用了两者,他借助奥古斯丁确立了赫尔墨斯在“古代神学”(priscatheologia)阶梯上的崇高地位,又借助拉克坦修宣扬了赫尔墨斯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
斐奇诺的“古代神学”代表一种有学说传继意义的思想传统,他在其《赫尔墨斯文集》译本的序言中排出了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俄尔甫斯、阿格拉奥菲莫斯(Aglaophemus)、毕达哥拉斯、斐洛劳斯(Philolaus)及柏拉图的师承顺序。
尽管后来对其中人物有所修正,这种“古代智慧”(priscasapientia)的真理性却为早期近代欧洲普遍接受。
因此,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在文艺复兴世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广泛地尊敬和引用,并深刻影响了基督教欧洲的文化与思想。
斐奇诺的拉丁文译本影响巨大,流传广泛,到16世纪中叶已印行二十四版,并促使了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译本的问世。
1505年,勒费弗尔(Lefèvred’Etaples)首次将《阿斯克莱皮乌斯》加入《赫尔墨斯文集》。
1557年图尔内(AdrienTurnebus)出版了第一部使用完整希腊文手稿编辑而成的《赫尔墨斯文集》,此版本包含编号为I-XVIII的18篇文章,后人将不属于原始文献的第15篇删去,于是流传至今的标准《赫尔墨斯文集》实际上包含编号I-XIV及XVI-XVIII的17篇希腊文“论说”(logos)及《阿斯克莱皮乌斯》。
约五个世纪之后,耶茨以“赫尔墨斯主义传统”(hermetictradition)一词概括描述了这段思想流传的历史,并由此将“赫尔墨斯主义”引入了早期近代科学史研究的视野。
“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始于斐奇诺对《赫尔墨斯文集》的翻译,它与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kabbala)思想的引入与传播一同影响和塑造了文艺复兴学者思考人、自然及神的方式。
这一传统从15世纪末延伸至18世纪以外,斐奇诺、米兰多拉的皮科、阿格里帕、特里塞米乌斯(Trithemius)、布鲁诺、法国的宗教赫尔墨斯主义者和后来的玫瑰十字会运动,以及约翰·笛与罗伯特·弗拉德都是其中的显著代表。
这些人物及其思想著作构成了耶茨“赫尔墨斯主义”历史叙事的核心。
耶茨论述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史关系的主要作品包括1964年的著作《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1968年的论文“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中的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及1974年的著作《玫瑰十字会启蒙》(TheRosicrucianEnlightenment)。
她的主要论点是围绕四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即:
《赫尔墨斯文集》、新柏拉图主义及卡巴拉等思想传统;魔法、占星术、炼金术等隐秘科学;“玫瑰十字会”运动;以及科学革命。
在《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中,耶茨对《赫尔墨斯文集》的地位最为推崇,认为它对文艺复兴时期自然观的转变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耶茨看来,借助作为预言基督教真理的上古先知这一权威身份,《赫尔墨斯文集》庇护了归于其名下的魔法、占星术与炼金术研究,从而使各种隐秘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普遍的复兴,并且赋予了人利用魔法操控自然和通神的观念。
这种观念进而赋予了人从理论到实践的操纵意愿,从而使术士与希腊与中世纪的哲学家区别开来。
她认为,《赫尔墨斯文集》造就了斐奇诺以赫尔墨斯主义为核心的新柏拉图主义,使人们对作为魔法力量来源的太阳产生了关注,并且还培养了从数学研究出发探究自然奥秘的热诚,这些都使得十七世纪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在后来的著作中,耶茨更加突出强调“玫瑰十字会”运动在科学史中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了约翰·笛、罗伯特·弗拉德、弗兰西斯·培根及皇家学会与“玫瑰十字会”的可能联系。
她认为,受斐奇诺影响较深的文艺复兴术士传统与受帕拉塞尔苏斯影响较深的“玫瑰十字会”运动是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的两大主要潮流,它们与17世纪现代科学的诞生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科学革命”。
另外,耶茨还认为赫尔墨斯主义-卡巴拉思想所培养的宗教态度对探索世界的新科学态度有重要影响,这种宗教态度的本质则自然应追溯到《赫尔墨斯文集》的内容。
科学史中的早期近代赫尔墨斯主义 1.早期争论 耶茨的著作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界围绕“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革命的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拉坦西(PiyoRattansi)与迪博斯是支持耶茨观点的主要人物。
拉坦西在几篇文章中分别指出,首先,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在17世纪英格兰的传播与当时的政治宗教情境交织在一起,在有关当时大学课程改革的争论中,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作为机械论哲学的竞争者,一度成为取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要力量;而清教革命则可被看作是英格兰自然魔法传统影响的顶点。
其次,通过分析威廉·佩第(WilliamPetty)、弗拉德及波义耳等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的智识背景,他认为赫尔墨斯主义自然哲学在这一圈子中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由赫尔墨斯主义思想催生的乌托邦著作(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与安德烈亚的《基督城》)则在社会、宗教及教育改革方面帮助塑造了皇家学会的主张。
拉坦西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采取一种偏向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他支持耶茨的观点,即“玫瑰十字会”运动对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与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迪博斯则在《化学论哲学》中充分肯定了赫尔墨斯主义与魔法的兴起及自然研究态度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自然魔法的复兴导致了对作为自然之匙的数学的兴趣。
同时他也承认,这种兴趣一方面培养了利用数学阐释自然现象的研究精神,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约翰·笛等柏拉图主义-数秘主义的思想。
另一些学者则对“赫尔墨斯主义”持完全相反的态度,黑塞(MaryHesse)与维克尔斯(BrianVickers)是这一派的代表。
黑塞在七十年代初与拉坦西展开了一场论争,她反对拉坦西的科学社会史书写方法,而为作为“内史”(internalhistory)的科学史进行辩护。
维克尔斯对这些辩论的评论是,这些争论既没有对主要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也没有对相关文本进行详细考察。
他正确地指出,耶茨过于简单地将数学魔法中对数的操纵与自然的数学化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一些观点也同样建立在某种未经反思的偏见之上:
他认为耶茨对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阐发仅仅揭示了这种哲学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折中主义传统的最终阶段。
另外,由于《赫尔墨斯文集》及新柏拉图主义文本中包含将物质世界描述为邪恶存在的段落,而且新柏拉图主义者并未表现出对量化世界和实验的积极兴趣,维克尔斯认为它们并不能激励人们研究世界,而是会相反地导致逃离。
对于《赫尔墨斯文集》或新柏拉图主义著作中缺乏真正的数学或实验科学的指责实际上是毫无深度的。
这种批评希望在被考察的文献中直接看到科学革命的两大经典特征,即自然的数学化与实验态度,因而是一种过于辉格的观点。
并且,这种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所考察的问题:
耶茨追溯赫尔墨斯主义-卡巴拉传统的目的是回答为什么数学化与实验态度会出现,而不是这二者是如何出现的。
这种对“为什么”的回答揭示的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它所探索的是科学革命得以发生的可能性条件。
将《赫尔墨斯文集》、新柏拉图主义著作以及隐秘科学的内容归为与现代科学不同的“心态”(mentalities),不仅扭曲了这些著作发挥影响的前现代科学语境,而且对于理解现代科学在这一语境中的兴起并无助益。
在一篇长文中,维克尔斯详细地批驳了耶茨的《玫瑰十字会启蒙》一书,指出它对历史证据的运用和推断的方式不够严密,进而完全否定了“玫瑰十字会”运动与科学史的任何关联。
虽然维克尔斯指出了耶茨著作中的漏洞,然而他并未就此证明“玫瑰十字会”运动与科学史毫无关系,相反,他只是在文末以修辞手段来表达这一观点。
2.“赫尔墨斯主义”的编史学问题 在这些争论中,关于“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革命之间可能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澄清。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1)事实性问题:
《赫尔墨斯文集》与卡巴拉等思想是否通过激励隐秘科学的发展而促成了新科学观念与态度的诞生,并且通过进入更加宽泛的宗教与政治语境而塑造了作为新科学产生背景的文化与思想?
这个问题所问及的是耶茨历史叙述的真实性。
(2)概念性问题:
“赫尔墨斯主义”究竟是否一种可以明确界定的、有确定思想载体与传人的学说,以至于可以清晰明确地谈论一种“赫尔墨斯主义传统”?
这个问题所问及的是耶茨编史思路的概念基础。
这些问题是由于韦斯特曼(RobertWestman)与麦圭尔(J.E.McGuire)的相关研究而逐渐明确的。
韦斯特曼在其1974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耶茨论题”(Yatesthesis)一词,并从他所定义的“论题”开始讨论问题
(1)的内容。
他写道:
“耶茨论题”的中心在于两个论断:
首先,经由哥白尼天文学改革后的宇宙被布鲁诺及其他术士(magi)理解为一个魔法符号,而对其恰当的理解会导致社会中政治与宗教领域的改革;其次,通过采用和“赫尔墨斯主义化”(Hermeticizing)哥白尼的理论,布鲁诺等人为新宇宙在17世纪的数学化与机械化准备了道路。
韦斯特曼并不赞成这两个论断的真实性。
他证明,除布鲁诺之外,没有任何术士将哥白尼的宇宙理解为魔法符号,并且赫尔墨斯主义者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接受程度各异,例如弗拉德对日心说就持完全反对的态度。
此外,尽管韦斯特曼承认赫尔墨斯主义的传播有可能导致某些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物理观念出现,但他认为这些观念更有可能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而且必须通过与当时所流传的其他希腊哲学观念相比较而澄清。
最后,韦斯特曼完全否认赫尔墨斯主义可能对开普勒或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方法有任何影响,他认为赫尔墨斯主义传统本身与这种方法是背道而驰的。
麦圭尔则通过对牛顿自然哲学的考察,对牛顿自然哲学的“赫尔墨斯主义”解释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赫尔墨斯主义”一词合法的使用方式包括:
首先指一种建基于“古代神学”观念之上的使话语合法化的手段,其次是指17世纪早期提倡一种虔敬式社会改革的千禧年运动,最后则指炼金术传统。
麦圭尔认为这三者对光、以太及主动性本原(activeprinciple)等牛顿自然哲学观念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此外,他认为对赫尔墨斯主义独立地位的强调是言过其实的,这一高度混杂而折中的文本在形而上学核心方面属于新柏拉图主义,而新柏拉图主义与斯多亚主义更有可能是牛顿思想的来源。
韦斯特曼的“耶茨论题”实际上极端简化了耶茨的思想。
在研究布鲁诺的著作中,耶茨从未将哥白尼与天文学置于中心地位,而且在耶茨看来,赫尔墨斯主义的影响在于它遍及哲学、政治、宗教等多个领域,而非仅仅与科学史相关。
以现代学科划界后的狭隘科学史观点去考察赫尔墨斯主义现象,既无法公正对待赫尔墨斯主义,也无益于增进科学史本身对那一时期的理解。
麦圭尔合理地强调了《赫尔墨斯文集》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然而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他一方面没有与讨论相关问题的主要人物韦斯特福尔(R.S.Westfall)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则过于强调牛顿哲学观念性的来源,而忽视了炼金术文本可能的直接影响。
毋宁说,韦斯特曼与麦圭尔的贡献在于对科学史界对“赫尔墨斯主义”一词的混乱使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这与上述问题
(2)直接相关。
施密特(CharlesB.Schmitt)与柯本哈维(BrianCopenhaver)提供了对这些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和解答。
施密特认为,一方面,很难说耶茨本人提出了一个“论题”,即使这样的“论题”存在,它也必须综合考虑赫尔墨斯主义在布鲁诺政治、宗教、哲学等各方面思想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韦斯特曼的“论题”揭示出一个许多使用“赫尔墨斯主义”一词的学者都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赫尔墨斯主义”本身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概念,而且它与俄尔甫斯教义(Orphism)、琐罗亚斯德教义(Zoroastrism)、新毕达哥拉斯主义(Neopythagoreanism)及卡巴拉等都是附着于新柏拉图主义这一思想主干上的分支。
与其说赫尔墨斯主义具有某种独立的影响,不如说它被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