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docx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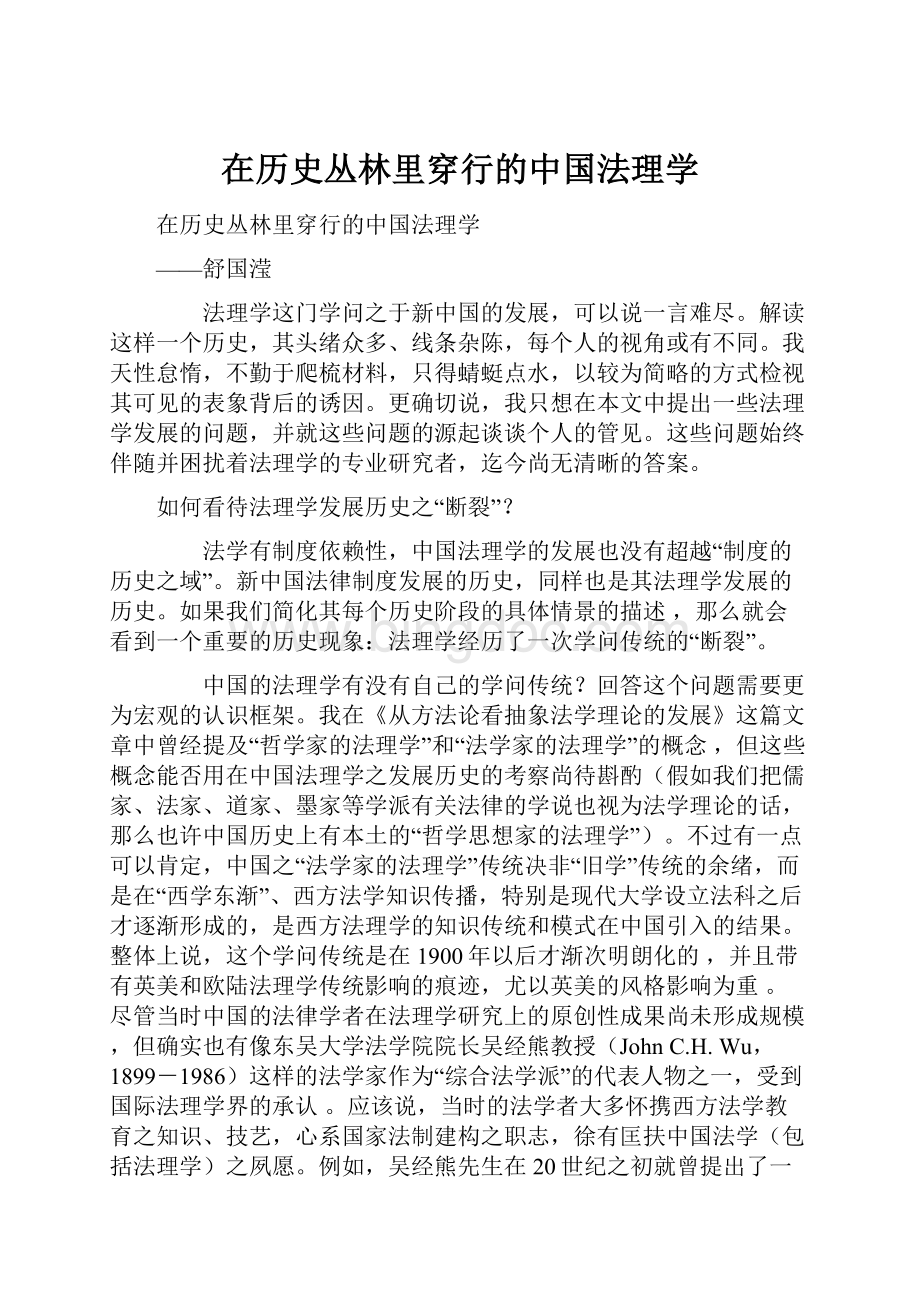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舒国滢
法理学这门学问之于新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一言难尽。
解读这样一个历史,其头绪众多、线条杂陈,每个人的视角或有不同。
我天性怠惰,不勤于爬梳材料,只得蜻蜓点水,以较为简略的方式检视其可见的表象背后的诱因。
更确切说,我只想在本文中提出一些法理学发展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源起谈谈个人的管见。
这些问题始终伴随并困扰着法理学的专业研究者,迄今尚无清晰的答案。
如何看待法理学发展历史之“断裂”?
法学有制度依赖性,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也没有超越“制度的历史之域”。
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其法理学发展的历史。
如果我们简化其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情景的描述,那么就会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
中国的法理学有没有自己的学问传统?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为宏观的认识框架。
我在《从方法论看抽象法学理论的发展》这篇文章中曾经提及“哲学家的法理学”和“法学家的法理学”的概念,但这些概念能否用在中国法理学之发展历史的考察尚待斟酌(假如我们把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有关法律的学说也视为法学理论的话,那么也许中国历史上有本土的“哲学思想家的法理学”)。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之“法学家的法理学”传统决非“旧学”传统的余绪,而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知识传播,特别是现代大学设立法科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是西方法理学的知识传统和模式在中国引入的结果。
整体上说,这个学问传统是在1900年以后才渐次明朗化的,并且带有英美和欧陆法理学传统影响的痕迹,尤以英美的风格影响为重。
尽管当时中国的法律学者在法理学研究上的原创性成果尚未形成规模,但确实也有像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经熊教授(JohnC.H.Wu,1899-1986)这样的法学家作为“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国际法理学界的承认。
应该说,当时的法学者大多怀携西方法学教育之知识、技艺,心系国家法制建构之职志,徐有匡扶中国法学(包括法理学)之夙愿。
例如,吴经熊先生在20世纪之初就曾提出了一个踌躇满志的设想:
“中国法学家也能够很快有在法学上普遍被承认的贡献,这门学问的中心为什么将来不能在中国呢?
”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吴经熊依靠个人的努力在英美世界展现中国法律思想之文化特性,在法理学领域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当时大学法学院的法学专业刊物也有同样的志向,秉承法律学问之严谨求实的精神,注重务实,倡导学理研究,介译西学,为民国时期的法学传统及风格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笔者在翻检1923年(民国十二年)创刊的朝阳大学《法律评论》(江庸创办)时发现,该刊在80年前刊出的文章和论题(如法学方法论)在今天看来仍属无人涉猎的领域。
譬如,在《法律评论》第9卷第134号(1933年)上就曾发表过德国法哲学家、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及其会刊创立人之一(另一位是新黑格尔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柯勒〔JosefKohler〕)的伯罗茨海默(FritzBerolzheimer)的文章。
我相信,目前法理学界了解IVR组织及其职能的中国学者不少,但真正知晓伯罗茨海默的人则寥寥无几。
此为后话,容他处再议。
回到正题上:
尽管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们积极努力,我仍然把当时的法理学传统看作是“过渡形态的”——一种发展中的法理学传统:
其表现为由介译西学为主的法理学向原创性法理学研究的转变,由法理学家个人独立的研究向由若干法学家共同承续之稳定的学术传统转变。
照此路径发展,中国形成若干法理学学派,与国际上相应的法学派构成平等对话、相互补益,甚至实现吴经熊“法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理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历史并未按照学者们的想像来发展,也不依学者个人的主观好恶和个人的意志来推进。
1949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律历史及法学历史的走向。
该指示第5条明确规定: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
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
……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令、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新型的人民政权采取革命的方式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法统”,连同在这个“法统”之下生成的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亦一并消解。
新政权亟待确立新的国体和政体及其正统性地位,需要建立新的革命的法律制度,这种迫急的形势不允许当时的革命家们过多地考虑废除旧法统与保持法学传统连续性之间多重复杂的关系。
政治和政策上的“经济思维原则”主导着政治家们的决策,“一边倒”的政策使新中国的整个制度建构、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想的资源不得不借鉴和倚重苏联的模式。
就这样,民国时期刚刚开始确立的法理学传统随着旧法统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后,随着195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学院系调整、“司法改革运动”及“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清除旧法人员等活动,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传统就彻底解体,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旧政权时期即成规模的大学法科不复存在,旧时代的法理学专业人员销声匿迹,甚至连图书馆保存的法理学专业书籍、资料亦散失殆尽。
所以,我们在中国法理学发展过程中发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学问传统的历史断裂。
这种断裂的直接后果表现在:
(1)所谓“维辛斯基法学”或“斗争法学”大行其道,一切根据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复杂的法律现象,法理学的智慧之光被简单的斗争理论所取代和遮蔽,僵死的教条成为评价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2)法理学者的身份被制度区隔为“左”“右”两个阵营:
两派的学者都在新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寻求其进击对手的政治资源和解释资源。
故此,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左右着法学理论争论的方向,注释政治会议、党报社论的精神及领导人的讲话成为法学理论工作之要务。
而且,法学上的“禁区”层设密布,学者们几乎没有多少动用思想的动力和机遇。
久而久之,其政治敏觉性超过了学术和思想的敏觉性,法学的思想创造能力则陷入委顿的境地。
“思想的慵懒”现象流行于法学的各个领域。
(3)旧政权统治时代已经学有所成的法理学者被停止专业工作,其智识的活动无人接续。
当时人们对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还略知一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理学则几乎无人系统研究。
法学理论限定在人为堆设的“孤岛”之内。
所以,当1977年我国恢复法学教育之时,我们的法学教育者、研究者和学习者其实都很清楚:
我们实际上是在法学理论的不毛之地上艰难地行进,所面对的是周遭世界的“无知之幕”。
(4)法学理论研究者对法律学问应有的真诚和良知遭受挫折。
“斗争法学”强化了学者的“斗争”意识,而使学者多少丧失了对法理学之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对学问之本真的虔诚。
这种后果其实影响至远,后来法理学界内部的所谓“思想交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分辨真假学术、重新寻获学术良知和真诚的过程。
至今,这样的交锋仍时起波澜,重建法理学传统过程还不得不时断时停,花费精力去应对学界内部一些非学术的纷争,以期形成较为理想的“言谈情境”和无扭曲的“交往共识”。
可以想见,当一个民族抛弃了法学理论家们的思考和智识工作,其理性的法律文化的实际力量会显得多么衰弱,而其非理性的制度力量又会多么无序地强化,以至于造成主张革命的政治家们亦始料不及的损失。
既然如此,人们也许会问:
这种历史的“断裂”是否有必要?
这种“断裂”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上述提问者大都是历史的“事后诸葛亮”,他们往往在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之后才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则未必对正在流经的“当下历史”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判断。
黑格尔说,自古以来还未曾有人能大致认识其本身的文化或时代。
如果说人最难认识的是他自己,那么一个时代最难做到的是发现这个时代的问题,深刻认识其自身的本质。
应该承认,在新中国打碎“旧法统”建立人民法制的过程中,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都遮蔽在“即时政治”的夜幕之下,看不太清楚历史之本真的面目,于是只好依靠战争年代的政治经验、策略和革命的惯性力量来推动历史按照自己主观划定的方向发展。
如果真正要反思,依靠“革命的全能意志”来整体改变历史的改制方案确实是值得谨慎对待的。
因为这样一种努力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两种结果都会造成历史之渐进发展链条的断裂。
即使成功了,判断成功的标准有时也难以确立。
而假如它失败了,其所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量,可能要让几个世代的人遭受苦难。
从“长时段的历史观”角度看,对一些历史事件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社会变迁才能揭示其意义和影响。
但就法理学学术传统“断裂”这一点而言,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历史判断,其负面的影响和代价已经显现在我们的制度建构之中,显现在现下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过程之中。
如果说在法理学的发展中还有什么“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我们当下面临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样一个峡谷。
然而,完成这样一个跨越的使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法学者们所要做的可能是根治由学术传统“断裂”留下的后遗症(如思想委顿,学术失范,理性论辩障碍等)。
如何认识法理学之“学”?
中国法理学50余年之进进退退,可能还与人们对法理学的晦暗面目没有清晰的认识有关。
这里有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是法理学自身的学问性质及功能为何;二是人们对法理学学问有何先在的想像和期待。
就后者而言,又有“内部的观点”和“外部的观点”之分,即:
法理学研究者对法理学的体认和企盼;政治家们和普通的民众对法理学的想像和期待。
上述不同的群体对这同一个学问领域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但在特定的时期(比如在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力量形成专断判准的时期),法理学者的认识与其他群体的认识孰是孰非、孰主孰次很难鉴别,亦难以区分。
在政治话语主导的语境里,学者也会改变其精英的知识立场和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当时流行的话语作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和分析的工具。
一旦这些话语和分析框架纳入其学问体系之中,就会以“科学”或“知识体系”的面相生存和繁衍,一代一代地加以传承,形成“学术制度”的力量。
后来的法理学研究者必须面对这一知识体系,甚至必须将其作为思想的平台和工作的出发点,否则他就必须将自我放逐,作为“思想的浪子”在主流的法律思想话语的边缘徘徊。
“法理学到底有什么用?
”——这始终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以简单作答的问题。
不同的提问者对这个问题的视角和兴趣是不一样的。
学者们关心法理学之独立的学问(抑或“科学”)的性格,普通民众想知道法理学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难题有否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政治家们则更看重法理学在实现政治意图上的实用价值。
不可否认,中国法理学兴衰之制度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政治家的态度依赖性。
上文说过,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左右着法学理论争论的方向,也是法理学沉浮起落的风向标。
法理学之学术传统的“断裂”与当时政治家们的观念不无关联。
从新中国的革命政治家角度看,法理学这门学问的面目是不甚清晰的:
它是“有用的学问”,还是“无用的学问”?
是“有益的学问”,还是“无益的学问”?
是“有害的学问”,还是“无害的学问”?
如果它有用、有益,它们的用益表现在哪里?
如果有害或无害,那又表现在什么方面?
当时的革命者无暇就这些细节问题过多地思考,则依其是否有益于新的政权建设而采取了简单的二分判准:
凡是对新政权有利的法律理论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法律理论,凡是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不相兼容甚或实用效益不明的法律思想学说,就被归结为“旧法观点”,属于批判和清除的对象。
董必武在1952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表达了当时政治领导人的担心:
“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对敌人斗争的锐利武器,不可操在不可信赖的人手中。
……把武器交给不可信赖的人(不管他有多大才能和学问),那是要犯错误的!
”这种不信任当然也包括对“资产阶级所谓法律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荒谬理论”的看法。
基此,领导者们坚持认为:
新中国的革命的法制是在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不断斗争中建立与健全起来的。
“国家和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成为诠释一切法律现象的终极根据,是法理学上唯一正确的结论。
这样,“斗争法学”自然就确立了其在新政权之法学理论中的正宗地位。
苏联的理论家们(尤其是安•扬•维辛斯基)为“斗争法学”曾经做过“学理精致化”的注解,因而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引介苏联版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就正好迎合了新制度对法学理论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由于批判和清除“旧法观点”而造成的思想空缺感。
但这种“充饥式的理论填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
法理学到底是一门具有自身独特研究对象、发展规律和相对自治的学问,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阶级斗争的法律哲学或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理论工具?
苏联版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对此以理论的话语作了说明:
“法律科学是研究国家和法的科学,……法律科学的使命是科学地解释阶级社会中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中的大量的社会现象。
”维辛斯基说得更直白:
“如果不以政治前提为出发点,就不可能解释法律。
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体现政治的形式,法律本身也像全部法一样是实现政治的工具。
”于是,法理学就在“政治挂帅”、“政策高于法律”的话语空间寻求其学科的合法性根据,在大学的法理学教科书和研究者们的法理学论文中大量充斥着流行的政治语言,学者们以寻章摘句方式引证马列、领导人的讲话为论述之根本。
法理学之学术性格顿失,沦为贫血的、空洞的、暴力的词语堆积体,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学说、专政的国家理论和政党的政治宣教毫无二致。
从执政的政治领导人的角度看,这样的“法理学”也许真正服务于政治,是实用的,至少是“无害的学问”了。
但其代价是昂贵的,一旦国家真正需要进行法治建设的时候,上述被政治阉割的法理学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其苍白的理论分析框架根本不能胜任政治的重托:
它不能清楚而有说服力地解释法治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更无从设计建构的方案。
当政治再次可能需求理论的时候,法理学反而不能担当职任了。
现实的政治摧垮了理论的身骨而又指望理论以其羸弱之躯担负无法承受之重,这种尴尬是令人深省的。
那么,在新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中,学者到底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法理学之学问性质及功能,学者之中难道就无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回答这个问题,要对不同时期的学者们所处的诸种环境作具体的分析。
其中(上文已提及)有一点是肯定的:
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和现实政治的诉求,法理学者们实际上被制度化力量区隔为不同的群体,他们的立场、理论兴趣和方法论存在着分化的状态。
这主要表现为所谓“新”“旧”、“左”、“右”的差别。
随着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和以及“旧司法人员改造”和批判“旧法观点”运动的开展,法学者的身份大体上都贴上了制度区隔的标签。
旧法学出身的人由于得不到新政权的信任而被停止了各自的专业工作,即使他们对法学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对法理学之学科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但由于不再有从事专业研究的资格、条件和环境,不再有自己发言的讲坛,他们事实上逐渐淡出法学历史的舞台,无声无息地了却余生,有些可能还受到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悲愤而殁。
当然,在那个年代,也不乏一些正直、勇敢、头脑冷静的学者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法理学学问,为守护理论的尊严做出最后的努力。
比如,曾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杨兆龙教授于1956-1957年间发表《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等文章,试图以理论的语言讲清楚“法律规范的本身是正义的”,“法律继承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政治性不应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等等现今看来属于常识性的观点,但这种理性的论辩很快就被随即而来的“反右”运动的鼎沸之声淹没了。
杨先生本人及其家庭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人扼腕叹息。
面对“舆论一律”的政治形势,更多的法学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通过“教育”、“反省”、“检查”、“批判”等方式迅速站到“斗争法学”的行列,用“斗争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左派”的行列,以便在争夺法学理论之话语霸权的斗争中处于较为优越的地位。
而一旦这种话语权的争夺与政治运动的展开扭结在一起的时候,学者们其实都在“知”与“行”的选择上迷失了自己的角色定位,谁也不再为法理学之“科学性”担负道义之责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成为政治评价的准则,整个法学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几乎被运动的声浪所吞噬,大学法律学系和各政法学院遭到解散,法学教研人员纷纷改行另谋生路。
法理学之学问的火种几乎就此熄灭,至少“法理学”的名称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即弃之不用,而恢复使用此概念则是较晚的事情,其间经历了20余年并非平静的重新认同过程。
毋庸置疑,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变化同样是意义重大的。
特约评论员文章所依凭的仍然是“真理”话语,但它所追问的是“真理的检验”而不是“谁言真理”,并且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归结为社会实践。
尽管“唯一标准”的提法容易给人一种话语霸权的感觉,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无疑是矫正混乱的思想路线的“技术性策略”。
事实上,真理之检验诉诸于“实践性”(实践是一种未定式和“试错”的努力),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和不断探索的认识旨趣。
这种态度和认识旨趣,不仅打开了法学理论界的思想禁区,为法学理论的争论提供了思想动力资源,而且也结束了中国法理学浑浑噩噩、混乱无序、徘徊不前的历史。
应当说,相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法理学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回应总体上显得是较为滞后。
在1980年以前,中国各政法院校、综合大学法(律)学系的法理学教科书仍然沿用50年代前苏联法学教材的体系,称作《国家与法的理论》,其内容的相当大一部分讲授国家理论。
其法学理论之核心部分(如关于“法的概念”、“法的作用”的阐述)仍然照搬“维辛斯基法学”的基本论点。
在法学研究方面,由于法理学界长期受“左”的思想的束缚和过去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知识准备和有效的进路突破理论上的禁区,即使对一些法学基本问题(如“法的继承性”、“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等)有所讨论,但多限于对党和国家文件的诠释和法律基本知识的普及,其中真正有理论突破和学术价值的论著并不多见。
在此方面,学者们所作出的第一次有价值的贡献,是1980年后法理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对“维辛斯基法学”体系在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解构的努力。
在学科建设方面,政法院系教材的体系和主要内容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标志。
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1981年)和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1982年)相继问世,在体例上打破了《国家与法的理论》旧有框架,凸显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多年以来法理学家们把法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信念、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确认。
所以,不难理解,上述两种教材成为其后同名教科书之蓝本,影响达十余年之久。
1983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法学理论讨论会,以“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为讨论主题,对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框架作了新的理论化的检讨。
学者们通过讨论而在学科定位等诸多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就为法理学学科的进一步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氛围。
然而,从法理学观念和思想层面看,其实质性的变化主要还是通过一系列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突破来实现的。
表现在两方面:
(1)关于敏感性理论问题的争论。
1980年前学者们在讨论法的敏感性理论问题时总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缩手缩脚。
《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周凤举的文章《法单纯是阶级斗争工具吗?
》,理论锋芒直指“法的阶级性”这一传统的理论命题。
周文所提出的论点激活了法理学者们沉睡的心智和理论争辩的热情,于是也才有了后来关于“法的阶级性”、“法的社会性”、“法的共同性”长达数年之久的辩论。
这些辩论的主题及方法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看来也许是“幼稚的”,甚至受到了来自其他法学学科的学者们的鄙视。
但参与讨论的人们明白,正是法理学的这场争论才为中国当代整个法学的发展争得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也正是有此争论,法理学界才会在80年代中后期讨论诸如“法的本位”(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人权与法制”、“法的价值”、“法律文化”、“法的精神”、“法制与法治”等等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法学基本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更新。
面对亟待回答的一系列法学难题,“困惑的法学家们”带着焦躁的情绪在法学研究中接引各种流行的科学方法,就构成80年代法理学发展的一大景观。
一时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
尽管这一波“方法论更新”的呼声随着研究者热情的冷却而渐趋沉寂,但它所提出的观察法律现象的独特视角,它在传统的法理学研究领域引进各种新方法论的大胆尝试,以及它所透出的对法理学认识之解放旨趣的渴望,均对法理学之陈旧、僵化的观念和理论产生不小的震动。
而它那蕴藏着的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想象力和冲击力,也是后来的法理学讨论和研究中所不曾再现的。
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学术的时代”。
这一判断既包含对当下较为成熟、理性的精神和研究品味的肯定,对学术传统的承继和回归的褒扬,也包含对80年代之“思想喷涌”景象的依恋。
就法理学发展而言,90年代出现的较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成熟的法理学论著的出版和法理学研究者之新生代的迅速成长。
人们曾做过这样一个比较乐观的估量,认为:
由于中青年法学家群体的崛起,中国的法理学已走出多年进退维谷的窘境,取代了其它法学学科在学界的影响,形成愈来愈强劲的发展势头。
笼统地讲,这一议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近几年,法理学界确实呈现出繁荣活跃的气象,表现在:
(l)法理学教研队伍增强,群体参与课题研究的活动比过去频繁。
自1978年以来,中国各大学、科研机构已培养了几百名法理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具体数字尚待统计),还有一大批法律本科毕业生充实到法理学教学科研岗位。
这样一批新生代的成长,从整体上改变了法理学教研队伍的结构,他们的新观念和新视野,为当今中国法理学的更新和发展注入了催进的动力。
而且由于这一代人尚未沾染各立门户的陋习,他们之间的相互协助与合作变得相对轻松一些。
尤其是在需要集体攻坚的科研课题和翻译外文书籍的工程方面,群体合作已显示出个人力所不逮的优势。
(2)法理学研究日渐深入,其质与量均有增益。
如果概括地划界,那么我们可以说:
90年代以前,中国法理学的任务主要还是澄清一些理论是非问题,为培育良好的学术环境做准备。
此后,由于极“左”思潮渐次失势,法理学界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在相对平和宽容的气氛中探讨法学范围以内的问题(如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学范畴、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法制与法治、法与人权、法律解释等)。
这一转向的结果,就是一批高品位的法理学论文和专著发表或出版,从而使中国法理学研究由意识形态的论辩转变至理论论证的阶段。
(3)注重法理学“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法理学的“请进来”有两种方式:
一是邀请国外的法理(哲)学家到国内访问、讲学;二是组织力量翻译国外法理(哲)学名著。
特别是,近年由一批中青年学者主持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西方法哲学文库”的编译工作,弥补了法理学研究文献上的不足,使学界能够阅读到国际法理(哲)学界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如萨维尼、霍姆斯、卡多佐、拉德布鲁赫、哈特、德沃金、考夫曼、拉伦茨、拉兹、波斯纳、塞尔兹尼克、麦考密克、阿列克西等人)的学术著作。
另一方面,法理学界多年来也较注重“走出去”的努力。
一批学人先后被派往英美欧陆诸国留学或讲学,他们在中外法学的交流与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