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参考文献.docx
《网络文化参考文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网络文化参考文献.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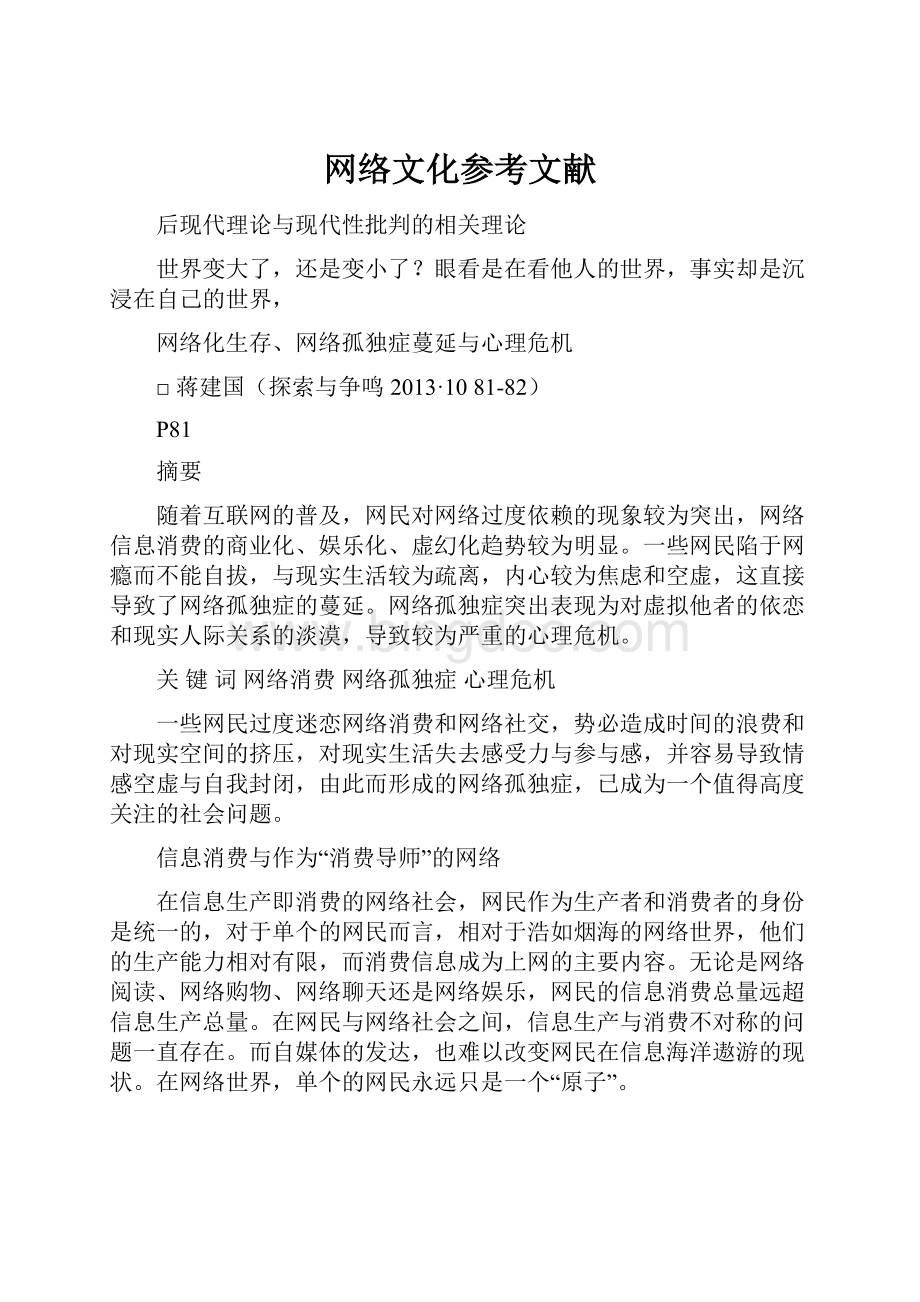
网络文化参考文献
后现代理论与现代性批判的相关理论
世界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眼看是在看他人的世界,事实却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网络化生存、网络孤独症蔓延与心理危机
□蒋建国(探索与争鸣2013·1081-82)
P81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对网络过度依赖的现象较为突出,网络信息消费的商业化、娱乐化、虚幻化趋势较为明显。
一些网民陷于网瘾而不能自拔,与现实生活较为疏离,内心较为焦虑和空虚,这直接导致了网络孤独症的蔓延。
网络孤独症突出表现为对虚拟他者的依恋和现实人际关系的淡漠,导致较为严重的心理危机。
关键词网络消费网络孤独症心理危机
一些网民过度迷恋网络消费和网络社交,势必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对现实空间的挤压,对现实生活失去感受力与参与感,并容易导致情感空虚与自我封闭,由此而形成的网络孤独症,已成为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信息消费与作为“消费导师”的网络
在信息生产即消费的网络社会,网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是统一的,对于单个的网民而言,相对于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对有限,而消费信息成为上网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网络阅读、网络购物、网络聊天还是网络娱乐,网民的信息消费总量远超信息生产总量。
在网民与网络社会之间,信息生产与消费不对称的问题一直存在。
而自媒体的发达,也难以改变网民在信息海洋遨游的现状。
在网络世界,单个的网民永远只是一个“原子”。
与传统社会的劳动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比,劳动的实践已经从田间地头转向于网络的空间生产。
不仅如此,网络促进了工作、消费、休闲、娱乐、社交的一体化,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现代神话。
尤其是对于一些网瘾者而言,网络世界是生活终极意义所在,网络消费是证实自我存在的方式。
我们在电脑屏幕上不断点击,信息似乎在发出奇异的味道,激发我们的消费欲望。
在网络社会,网络消费成为指导文化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价值所在,上网不仅是工作的需求,消费网络和网络消费已经合为一体。
如果说鲍德里亚将工业社会描写成为消费社会,那么,网络社会就是信息消费社会。
在工业社会,丰盛的物质生活推动了消费方式的多元化,消费成为证实人生价值和进行社会区隔的意义所在。
而在网络社会,信息消费本身就是证实自我存在的方式,如果你不是网民,意味着你已经“脱域”,被信息化浪潮所抛弃。
上网行为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规定动作,没有网络,无法生存,消费网络,就是消费社会和人生。
而网络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教堂”,指导着网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活动,充当着消费导师的角色。
网络虚拟生活与社会性焦虑
P82
网络欢迎每一位网民的加入,并对他们的身份和消费习惯进行诱导性识别。
尤其是商业性网站五花八门的消费性指引和分类栏目,不断地将消费者进行分流和归类,并进行具体的消费指导,网页的设计者总是在网页上不断增添强烈的刺激元素,并及时地通过广告进行消费劝说。
“满足你的消费个性”是商业网站的口号,但是,所谓个性是在被类型化的过程中附加了消费符号,点击率是网络了解消费市场的最佳方式。
“我点击、我存在”是网络社会个人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恰恰是网络消费的价值指引。
在Web2.0时代,网民的互动极大推动了网络消费市场的发展。
网络社会是一种“他人导向型社会”,正如《孤独的人群》作者大卫·理斯曼(DavidRiesman)所言:
“所有他人导向性格的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均把同龄人视为个人导向的来源,这些同龄人无论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
……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
”[2]
与内在导向型的人不同,他人导向型网民的生存方式与亲友的关系日益疏离,网络化生存更多地体现了网民自主和标新立异,在网络上寻找知音和追逐消费潮流已经成为新社交方式的意义所在。
他人的评价对于网民的自我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自我出位,有些博主还将自己的微博自我转发、自我阅读和自我消费,其畸形的博名心理可见一斑。
显然,网络自媒体仍然受到“消费导师”的干预和引导,让许多网民在“博名”和“出位”的狂欢中建构虚幻的自我意识。
而网络运用微博进行商业营销,或者利用名人微博进行广告与商品推销,更表明了其引导消费和制造消费悬念的意图。
随着网络化生存的发展,网络消费已无处不在。
与物质消费不同,网络消费本质上体现为时间消费,或者说上网本身就是在消费时间。
在网络空间,信息的过度泛滥与时间的稀缺形成明显反差。
网络浏览的即时性消费淡化了时间概念,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无序性和超链接性,使点击型消费的价值难以实现,过目即忘的浏览难以保存信息,更难以产生深刻记忆。
消费信息已成为网络时代最广泛、最流行的方式。
“我上网,故我在”。
我们迫不及待地消费每一条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信息的意义所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如何抵制诱惑,而在网络消费过程中,“虽然我们一直在含食,却处在永远的饥饿之中”[3]。
网络化生存已成为证实网民物理存在的方式,而网络消费所造成的记忆缺失、精神空虚和价值迷茫,则是网络社会病的表征。
P83
由于长期依赖网络和缺乏深度思考,一些网民对于现实问题往往视而不见,尤其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以逃避和拖延回归网络世界,形成心理学所描述的“习得性无助”状态,并以随意的信息搜寻和娱乐麻痹自己。
而冷漠的信息灌输进一步加大了网民的麻木状态,网民不断收取邮件、QQ聊天、刷新微博,生怕错过每一条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其中绝大部分信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是网民的信息依赖症却不断蔓延,由于过度迷恋于网络生活,一些网民不断发展自私和自恋的人格,他们过度关注网络中的自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置之不顾,一些网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共同语言和情感交流,各自在网络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而对于现实的朋友圈子,往往疏于联系。
许多网民上网交流,并非是真情的互动,而是由于无聊和寻求刺激。
这种功利性诉求,恰恰也是网络情感世界的共同表征。
因此,无论是网络阅读、网络购物还是网络社交,许多网民都在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他者的世界对于他们十分遥远,上网不过是满足自我的生活方式而已。
但是,“自我迷恋并不会产生满足,它导致了对自我的伤害”[6]。
所以,尽管网络世界极为宽广,而许多网民的内心世界极为狭小。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网络世界游荡,没有原因、没有结局,漫游已成为生活的意义所在。
但是,一旦离开网络生活,住房、升学、婚姻、工作等问题却无法回避,许多年轻网民以“屌丝”自居,以犬儒主义武装自己,以网络泄愤作为生活方式,不断在网络上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借以引起网民的围观和议论。
但是,这种发泄以遁世为前提,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不是期待美好的明天,以自我破坏、自我作贱作为解脱的方式,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域,许多毫无价值的话题很快就消失于信息海洋之中。
尽管“屌丝”现象折射了现实生活的无奈,但网络“屌丝”族群的聚结并没有形成共识和行动方案,更谈不上对建设性的集体决策。
即使是一些以交友、购物、娱乐为目的而形成的网络族群,也难以长久地坚守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网络集体生活的短暂性聚集,难以使网民遭到归宿感和认同感。
喧嚣和流行过后,许多网民感到无比寂寞和空虚,产生被“控制”、被“抛弃”、被“淹没”的感觉。
P84
虚拟性他者与孤独症的蔓延
麦克卢汉用补偿性媒介理论论述了新媒体的优势,网络媒体既聚合了传统媒体的优势,又进一步推动了媒介的人性化发展。
但是,网络工具理性的高度膨胀,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网络价值理性的发展。
尤其是Web2.0时代带来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文化,使许多网民在信息的海洋中找不到上岸的途径,更不知道如何集中精力和有效安排宝贵的时间。
由于网络化生存方式的流行与传播,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受到媒体的影响。
当下,中国有近一半的民众已成为网民,作为在网络影响下生活的个体,学会运用网络解决生活和工作的难题,是适应现代生活必然趋势。
但是,过度依赖网络生活,造成网络对现实生活的挤压、曲解和抛弃,则是网络生活留下的巨大隐患。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上网仅仅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旦产生网瘾,网民就将上网视为生活意义的价值所在,挤占本应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上网过度就是以网络空间排挤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行为,导致网瘾者对时间敏感度和现实关注度的缺失。
网瘾者下线之后,脑海里一片空白,在现实空间,又难以被人接受、被人邀请、被人喜欢,因此茫然而无聊,沮丧而内疚,成为孤独的漫游者。
这又进一步驱使他们更经常地上网,期待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寻求医治孤独的灵丹妙药,进而患上网络孤独症而不能自拔。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2年5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5.0%的受访者表示周边存在很多“网络孤独症”的青年,其中22.9%的人表示“非常多”。
34.4%的人坦言自己就有“网络孤独症”。
[7]由此可见,网络孤独症已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病。
然而,网络孤独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孤独,网络孤独是以刻意逃避现实社会和疏远人际关系而形成的单向性孤独。
网瘾者陷于孤独,是因为他们痴情于网络这一虚拟伙伴,他们将网络视为生活伴侣和社交对象,而现实生活中的孤独症患者是由于缺乏交流,没有社交对象而造成的自闭。
他们没有倾诉的对象,没有被社会关注。
但是,网络孤独症患者却运用网络在关注社会,关注他者,并运用网络社交工具建立了极为广泛的社交网络。
他们是网络交流的活跃分子,也是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的活跃分子。
但是,网络交流是虚拟而缺乏“凝视”的交流,网络孤独的产生,就是网民预设了逻辑前提,以网络社交替代人际交往,以“陌生人社会”替代“熟悉人社会”。
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矛盾、人际纷争、社会乱象让许多网民心灰意冷,从而产生逃离的心态,他们希望从网络消费和交流中获得理解、尊重和满足。
因此,网络孤独症患者从自我需要出发,期待通过网络解决生活中的焦虑和无奈。
而网络的他者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是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对象,他们是在线的交流对象,但并不是心理大师和慈善大使,这些虚拟的他者,是心情涣散的游客,在网络上的邂逅,只是他们漫长旅程中的一个节点。
他们的网上交流,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偶遇,没有前设,没有相识,没有深入,没有主题。
这是一种交流的无奈,并非真正意义的情感沟通。
所以,“向网络说话”与“向天空说话”一样,难以形成深刻的情感互动,更难以体现人文关怀精神。
但是,网络社区却日见火爆,网络聊天也魅力无穷。
对于许多网民而言,“被邀请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他们并不孤独的一种证明”[8]。
网民们热衷于“被邀请”,也不断寻找虚拟的“邀请对象”,许多网民都习惯于“潜水”,隐瞒自己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婚姻状况等基本信息,大家都戴着“面具”聊天,而且许多内容都是“大话”,是一些时政传闻、流言蜚语、名人隐私和娱乐八卦。
然而,即便这些“大话”,也没有主题,没有共识,对于许多问题,都各自表述,先入为主。
狂聊过后,没有结论,没有记忆,没有共享。
在很多情况下,网络社区
P85
聚集的是“乌合之众”,但是大部分网民不愿自己被“污名”,认为自己的参与已经在网络“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实,偃旗息鼓之后,除了聊天过程之外,网聊上瘾者并没有留下让人深思的见解,更谈不上增进彼此的友情。
他们在无聊之后,在孤独中踏上新的网聊旅程,期待下一站有“美丽的邂逅”。
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可见,“习惯性网聊”已经成为心理病态的表现,就像一些盲目的相亲者,上百次的相亲已经使他们疲惫而麻木,相亲对象已成为考察的一个模糊概念。
狂热的网聊者陷入话语贫困和主题缺位的状态,已经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凉之感。
网瘾者的孤独是一种比一般孤独者更为危险的孤独。
他们意图通过电脑与无数人建立联系,解决交流的困惑和情感的空虚。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人机对话,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丧失人性,而人性的光辉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
对于大多人而言,我们孤独的根源在于不被接受、不被喜欢、不被赞赏,因此,我们需要融入现实社会。
对于网络孤独症患者而言,也只有走出网络迷恋的误区,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关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积极参与各种群体生活,在工作和生活中培养信任、友谊,才能走出情感误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参考文献:
[1]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6:
192.
[2]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0.
[3]弗兰克·施尔玛赫.网络至死.北京:
龙门书局,2011:
136.
[4]、[5]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0:
171、96.
[6]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07.
[7]83.2%受访者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中国青年报,2012.5.24.
[8]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
新闻界ISSN1007-24382013年第15期
中日大学生掌媒使用比较研究项目论纲
胡翼青
考虑到兼顾研究的信度与效度,也考虑到在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困难,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辅以半结构式访谈的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课题组希望通过问卷调查证明的如下假设:
1.掌上智能终端可能降低大学生课堂效率并占用其课后学习时间。
2.它可能减少大学生的现实社交或降低其质量,增加其孤独感。
3.中日学生在掌媒使用行为与使用方式上有一定的差异。
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研究者又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分别对南京大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交换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其中,南京大学共2组,每组各6人,文科、理、工科学生各2人;南京大学日本交换生2组,每组各6人。
此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本次研究中所进行的访谈形式是半结构式访谈,因而所有的访谈问题仅仅作为一种框架或参照系而出现。
从现实的访谈结果的反馈来看,访谈者新观点的提出为课题组对于现象的解释提供了颇有趣味的新视角。
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焦点小组访谈的优长。
对被访谈者进行了编号:
中国大学生编号为Z1、Z2等,日本则为R1、R2等,下列两篇文章中出现的采访对象均以此方式呈现。
通过以上的研究,项目组确实发现,日本与中国在大学环境、社会化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致使中日大学生在掌媒使用行为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
总地来说,日本大学生对掌媒的依赖度要轻一些,使用方式也较为多元。
但也应当看到,在信息时代,传播环境正在越来越趋同,中日大学生的掌媒使用行为的差异正在逐渐消弥,大家都在越来越依赖这一有史以来渗透力量最为强大的私媒体,后者已经成为我们克服现代性焦虑最重要的一种心理治疗工具。
而对这一工具的依赖则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现代性焦虑之中。
新闻界ISSN1007-24382013年第15期
离不开的“黑镜”:
中日大学生对便携式智能媒体的依赖
周梦媛周昱含
摘要通过对中日两国大学生对“便携式智能媒体”依赖程度的比较研究,作者发现,社会化方式的不同以及对大学生活态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日两国大学生对待便携式智能媒体的态度。
不过,越来越相似的传播环境正在抹平中日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中日大学生;便携式智能媒体;依赖
通过对中日大学生进行一个比较性的经验研究,(具体方法参见《中日大学生掌媒使用比较研究项目论纲》),本文试图考察:
便携式智能媒体对大学生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在这方面到底有何不同?
他们之间的依赖程度或性质是否有差异?
这些媒介又是如何影响中日大学生的课堂和课余学习的?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社会原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黑镜”一词来源于英国4台迷你剧,试图表达“便携式智能媒体”对人性的利用、重构与破坏。
所谓“便携式智能媒体”,通常就是指我们使用的iphone、ipad、电子书这类除了发挥其自身功能,还能实现网络连接的便于携带的媒体终端。
“黑镜”存在于几乎每个当代大学生的手掌间和双眼前。
生活在校园中,任何人都不难发现大学生与便携式智能终端之间一种依赖关系的存在。
通过对中日大学生进行一个比较性的经验研究,(具体方法参见《中日大学生掌媒使用比较研究项目论纲》),本文试图考察:
便携式智能媒体对大学生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在这方面到底有何不同?
他们之间的依赖程度或性质是否有差异?
这些媒介又是如何影响中日大学生的课堂和课余学习的?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社会原因?
我们看到中日大学生的三个共识:
其一是对“黑镜”的依赖是周围同学中常见的现象,其二是这种依赖造成了“荒废时间”;其三是问题出在个体缺乏自控力,但又无可奈何。
三、结论与分析
数据的统计以及访谈记录让我们观察到显然“黑镜”对中日大学生均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且中日大学生都逐渐离不开它。
但是中日大学生受到的影响具有差异,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我们尝试根据访谈作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
(一)中日大学生差异来源于社会化方式不同
社会化的不同第一点源于同为“90后”的中日大学生分别来自的是独生子女家庭和多生子女家庭。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
目前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和比例都是最多的,中国独生子女达1亿2000万,独生子女在青少年时期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特定的社会环境。
家庭规模的缩小,家长角色的变化,学校教育方向的偏离,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
社会变革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化环境必然会在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从社会化发展的具体方面看,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懒惰”是独生子女的明显不足。
此外,“动手能力差”、“责任心差”也是其弱于非独生子女的方面[1]。
独生子女的“蛋壳化”现象,将自我封闭在一个固定空间里,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兄弟姐妹之间相模仿的条件,朝夕与成人相处,来自成人世界的语言行为的刺激,使独生子女丧失了孩子气而过早成人化。
在人际交往上,已习惯于一种实用功利、互相交换的“平面交际”[2]。
我们的问卷数据也表明中国大学生与大学同学联络均分达4.45,接近每日交流。
虽然急剧的都市化促进了日本小家庭的增加及少子化。
现在的日本大部分仍然是多生子女家庭,我们的访谈中也发现从小在同辈环境交流中长大的日本大学生,在与同辈磨合过程中,很小就懂得谦让、分享的意义。
应该承认同辈群体由于年龄结构相仿,在社会化过程中既是施化者又是受化者,它为社会化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提供了最初的比较正式的角色承担的机会。
66
67在日本,小学和初中为义务教育阶段,并且学校都坚持4个基本方针办学通过全部教育活动,根据儿童的成长阶段,选择相应的科目,目的是达到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坚强的意志重视培养学生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欲望。
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注意培养个性的同时,保持从幼儿园到高中各科目内容的一贯性在培养尊重日本文化和传统态度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3]。
高中教育普通高中的是根据文部省公布的指导要领制定的,由各学习科目及特别活动组成其学习的科目中包含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程,与中国不同其中还设有家政课,特别活动包括学生会活动、社团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日本高中生都会在初高中参加起码一类社团,每日参与训练、交流等。
我们的问卷统计也中发现,日本大学生与高中、初中、小学同学的联络次数明显高于中国,分别是1.90(每周2次)1.38(每周2次)3.37(每周5次)。
日本杜会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利低出生率时代,持续的低出生率使得日本劳动力不足,计时工非常普遍给高中生、大学生们创造了大量的打工机会[4]。
综上所述,中日大学生的社会化方式不同成为便携式智能媒体对中日大学生的影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大学生的依赖相对较低,也就不难理解。
(二)中日差异来自于对大学生活的差异67
如前所述,学校的满意程度会影响大学生对便携式智能媒体的依赖,便携式智能媒体使用倾向与中日大学生对所在读大学的满意程度的关系存在较明显关系。
可以说对学校满意度越高,受到智能媒体带来的影响和问题就越小。
中国大学生访谈中大部分人都带有不满意的情绪进入本专业就读。
……我们发现,在中国,“大学生”概念之下所包含的个体相较于日本要更为复杂,中国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所抱有的期待也比日本大学生丰富得多。
这种情况势必造成中国大学生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后,对于本专业的认同甚至整个大学生涯所作出的评价和反馈的态度也更为多元。
按照道理来说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应该让大学生感觉到了不再受到应试教育,幸福的“大解放”。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多年的高强度压力式学习到放任不管其中的巨大反差,显然让大部分学生不能适应。
犹如弹簧般突然弹起,让很多学生无法自然收回。
Z3说“课上课下两级分化都比较严重。
认真学习的同学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很认真学习的,并且自觉性极高;而其它的同学平时几乎不自习,上课的时候也是敷衍了事,基本上靠考前突击应付期末考试。
”再加上课程设置的死板等多重原因,中国部分大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了高度不参与性,不听课,不发言,不互动,执着于手间的“黑镜”。
访谈中z2说“尽管从道理上讲大家都明白这样做时不应该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上课太无聊了。
”之前的大多文献认为是科技造成的依赖与沉迷,然而除了便携式智能媒体技术的快捷便利,中国大学生更多的出一种功能性依赖。
即借助“黑镜”,逃离课堂。
逃离空间上“教室”这一固定的场所,到达一个与同学,家长,陌生人都可以沟通学习“自由之地”。
(三)相似的传播环境导致中日大学生差异趋同
中日大学生对便携式智能媒体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同时我们发现差异并不是非常大,或者说很多地方很相似,如何解释这种相似呢。
或许越来越相似的传播环境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
p68
数据显示大学生每周的闲暇时间达70.7小时,休闲时间几乎被媒体所填满。
而娱乐活动也逐渐趋同,聚餐(日本为饮酒会)、卡拉OK、体育运动等。
对于闲暇时间的安排:
Z3同学:
“就我周围同学而言,形式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聚餐,看电影,唱歌等等”Z4认为大学生活动的形式比较的多样,其中聚餐和唱KTV估计是最普遍的形式。
有时候“请客”“几乎每周都聚”等现象太过普遍,与大学生的学习任务有时形成了冲突。
应当节制。
Z2觉得:
“实话说,就我个人而言,就深度而言,比高中要深刻的人不少(精神交流),就人数而言,比高中少了。
主要通过课程实践小组、球队、校园社团、学生会(聚餐、联谊)等方式。
我基本都有参与,认识的同学也不少,但总体而言,泛泛之交为多。
还是接触机会不多的缘故。
应该说随着虚拟社交的发展,传统社交在大学生社交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大学生深交能力的发展的。
”
[1]风笑天.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社会适应[J].教育研究,2005(10).
[2]袁潇、风笑天.青少年手机需求及使用行为研究现状[J].中国青年研究,2011(4)
[3]橋元良明,「若者の情報行動と対人関係」,正村俊之編,『情報化と文化変容』,ミネルヴァ,2003.
[4]三得利次世代研究所,http:
//www.suntory.co.jp/culture-sports/jisedai/active/report/media/index.html
[5]许敏.大学实践教育与大学生的社会化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09(3).
新闻界ISSN1007-24382013年第15期
群体性孤独:
针对掌媒使用依赖的中日比较研究
张婧妍周惠懋
摘要近年来媒介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融合与革新,使我们越来越容易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一种与周围人“亲密无间”的感觉。
然而现实呈现的却是专注于各自手中掌媒的沉默的人群。
本文对中日大学生掌上媒体和SNS技术的使用及其对现实社交的影响进行考察,针对数据和访谈中呈现出的中日技术依赖共性和依赖程度的差异,尝试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进行解释,并从差异中发现现代性兴起过程中陌生人社会出现对两国原有社交结构的冲击。
P71
受访者R1的话来说,她对于技术的态度是“都会接触,但绝不沉迷”,而对于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御宅族”、“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