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docx
《《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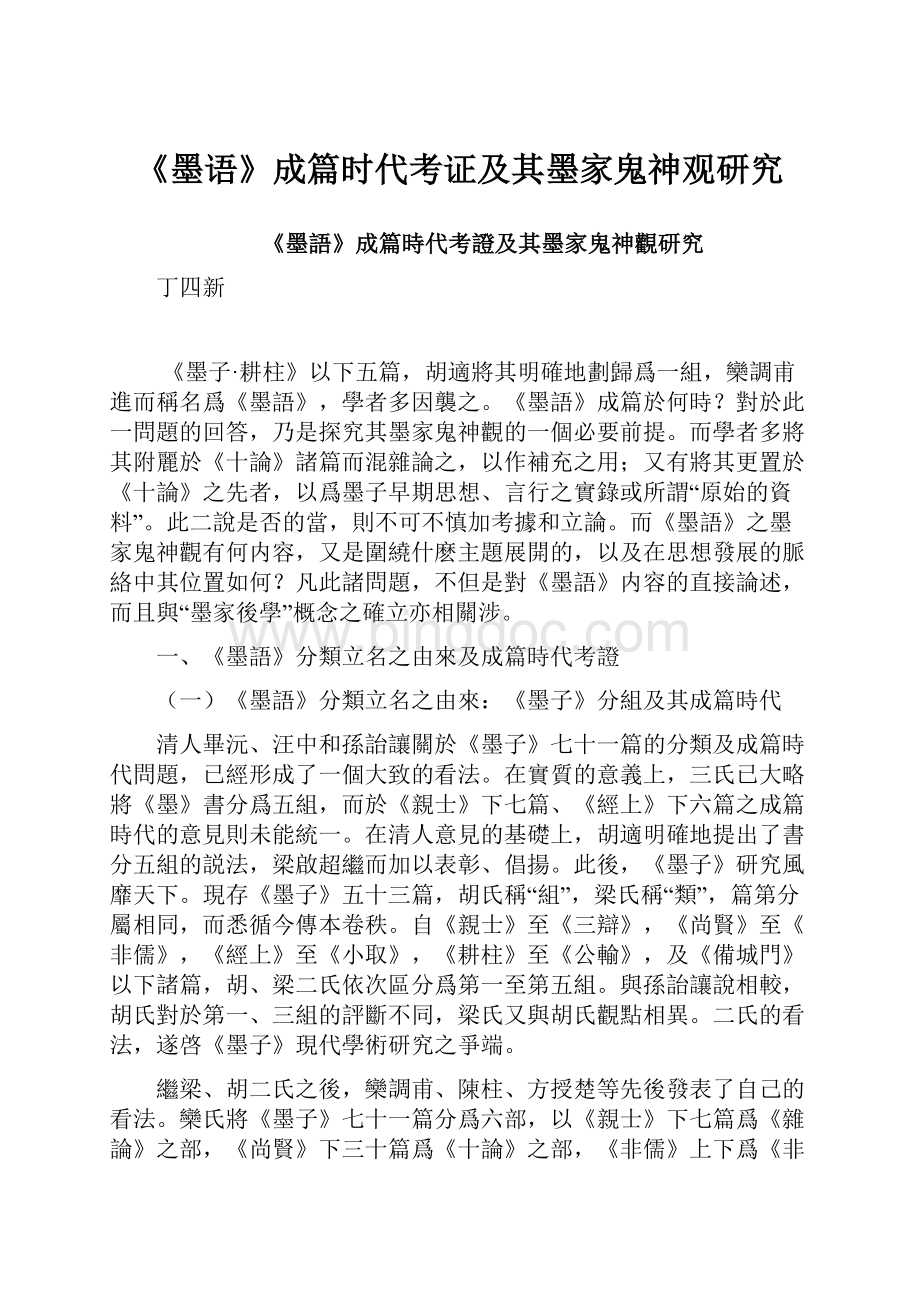
《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鬼神观研究
《墨語》成篇時代考證及其墨家鬼神觀研究
丁四新
《墨子·耕柱》以下五篇,胡適將其明確地劃歸爲一組,欒調甫進而稱名爲《墨語》,學者多因襲之。
《墨語》成篇於何時?
對於此一問題的回答,乃是探究其墨家鬼神觀的一個必要前提。
而學者多將其附麗於《十論》諸篇而混雜論之,以作補充之用;又有將其更置於《十論》之先者,以爲墨子早期思想、言行之實錄或所謂“原始的資料”。
此二說是否的當,則不可不慎加考據和立論。
而《墨語》之墨家鬼神觀有何内容,又是圍繞什麽主題展開的,以及在思想發展的脈絡中其位置如何?
凡此諸問題,不但是對《墨語》内容的直接論述,而且與“墨家後學”概念之確立亦相關涉。
一、《墨語》分類立名之由來及成篇時代考證
(一)《墨語》分類立名之由來:
《墨子》分組及其成篇時代
清人畢沅、汪中和孫詒讓關於《墨子》七十一篇的分類及成篇時代問題,已經形成了一個大致的看法。
在實質的意義上,三氏已大略將《墨》書分爲五組,而於《親士》下七篇、《經上》下六篇之成篇時代的意見則未能統一。
在清人意見的基礎上,胡適明確地提出了書分五組的説法,梁啟超繼而加以表彰、倡揚。
此後,《墨子》研究風靡天下。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胡氏稱“組”,梁氏稱“類”,篇第分屬相同,而悉循今傳本卷秩。
自《親士》至《三辯》,《尚賢》至《非儒》,《經上》至《小取》,《耕柱》至《公輸》,及《備城門》以下諸篇,胡、梁二氏依次區分爲第一至第五組。
與孫詒讓說相較,胡氏對於第一、三組的評斷不同,梁氏又與胡氏觀點相異。
二氏的看法,遂啓《墨子》現代學術研究之爭端。
繼梁、胡二氏之後,欒調甫、陳柱、方授楚等先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欒氏將《墨子》七十一篇分爲六部,以《親士》下七篇爲《雜論》之部,《尚賢》下三十篇爲《十論》之部,《非儒》上下爲《非儒》之部,《經上》下六篇爲《墨辯》之部,《耕柱》下四篇爲《墨語》之部,《公輸》下諸篇爲《備守》之部。
其所命部名,爲多數學者所襲用。
與胡、梁相較,欒氏雖亦循傳本篇目次第,然在歸屬上小有不同:
其一,欒氏將《非儒》上下篇單獨列爲一部,胡、梁則與《十論》同組並類;其二,欒氏將《公輸》連下,與《備城門》諸篇同部,胡、梁則上屬之《耕柱》諸篇。
今案,《非儒》二篇與《十論》諸篇不類,宜單獨析爲一部,欒說可從。
《隋書·經籍志》曰“《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又宋人所見三卷本與今傳本卷次合,則今傳本次第其所由來者久矣。
今傳本《耕柱》與《大取》、《小取》同卷,《公輸》與《魯問》同卷。
據此,欒氏以《公輸》入《備守》之部,殆與古人分卷之意難相吻合。
不過,由於該篇在思想上與鬼神無涉,故本文使用《墨語》一名時,多就前四篇而言之。
(二)《墨語》成篇時代諸看法述評
欒氏等人關於《墨子》分組劃分的意見,同代及後輩學者少有更動,歐美和日本的漢學家其分法大抵相同。
畢沅曾指出《耕柱》篇“並稱子禽子”,則以該篇成於禽子弟子或其後學之手。
畢氏、孫詒讓又曾引《魯問》篇子墨子對魏越所言之“十義”,並以爲“通經達權”而不可訾議的墨子本旨,則二氏以所云“十義”爲墨子思想之概括,並以該篇出自《十論》之後,此殆可推知矣。
民國以降,爭論蠭起。
胡適云:
“《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子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起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
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爲重要。
”胡適的觀點有三,其一,認爲此五篇爲“墨子後人”所輯;其二,認爲此五篇乃“墨子一生的言行”之輯聚,體裁與《論語》相同;其三,認爲此五篇有許多材料比《十論》還更爲重要。
梁啟超云:
“這五篇是記墨子言論行事,體裁頗近《論語》。
”與胡氏相較,梁氏評語較爲平實,似乎並不贊成胡氏第三點意見。
隨後,欒調甫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云:
“按《墨語》四篇……爲墨者記述墨子應答門弟子及時人之語,猶儒家《論語》爲記孔門之語者也。
篇中記述墨子弟子,或稱名氏,或稱氏子,惟禽滑釐稱子禽子。
據何休《公羊傳注》云: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本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
’則此四篇之作,當出禽子之門。
”其說,孫氏《閒詁》已發其端。
於《所染》“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句下,《閒詁》已引何《注》爲說;又引《列子·天瑞》篇張《注》曰: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據此,畢、孫二氏當已知《耕柱》篇爲禽滑釐弟子之作,特注中未明言之耳;所不同者,欒氏將《墨語》四篇設爲一個整體,故謂此四篇皆“出禽子之門”。
又,欒氏指出:
“篇(指‘墨語’四篇——引者注)中記墨子稱其弟子曰‘子’,弟子則稱之曰‘夫子’,與《論語》子汝之稱已不同。
而弟子自稱吾我,亦與孔門稱名者異。
”由此可知,《墨語》四篇所倚待的師生觀念已發生了某些較大變化。
欒氏發見於此,實有助於嚴儒墨之别。
羅根澤繼而認爲《耕柱》五篇爲墨子再傳弟子記墨子言行之作,並提供了兩條理由:
其一,篇中不惟對墨子稱子墨子,對墨子弟子亦時稱子,如耕柱子、高石子、高孫子、弦唐子;其二,對禽滑釐更進而稱子禽子,故作者或爲禽滑釐之弟子。
要之,羅說與欒說相合,而與畢、孫之說無違。
當代研《墨》學者一般認爲《墨語》成篇於墨子弟子或再傳弟子之手,即屬於此路看法。
與畢、孫、欒諸氏之主張相對,蒙文通等另起新說,以《耕柱》五篇爲《墨》書之最先者。
蒙云:
《耕柱》至《公輸》此五篇又一類。
……《耕柱》等篇似《論語》、《孟子》,爲條記墨子言行,殆《墨書》之最早者。
……竊謂《耕柱》五篇,於《墨書》爲最先,《親士》七篇次之,《尚賢》終《非儒》最晚。
先者雜記言事以見義,次之采集言談類次之,篇爲一義,最後則以十大義爲目,綴集而敷陳之。
意者,《耕柱》五篇次於《大、小取》後,而下連《備城門》諸篇,倘秦之墨所傳乎?
秦之墨重行而不重言,傳墨子言行,即依最先之本以說以教,無所損益改作,而所究力者,專在守禦之事。
據蒙氏所云,此論乃伸其故友唐迪風之說。
蒙氏據《耕柱》篇子墨子答治徒娛、縣子碩問之語,分墨氏爲談辯、説書、從事三派,並云三派即三墨也。
所謂“三墨”,本自《韓非子·顯學》“墨離爲三”之語。
俞樾曾據《十論》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推測此三篇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
欒調甫云:
“余疑‘十論’上篇出於秦之墨,中爲東方之墨,下爲南方之墨也。
”蒙氏斥俞說爲“戲論”,而謂三墨爲南方之墨、東方之墨、秦之墨。
秦之墨爲從事一派,伯夫氏、唐姑果是也;東方之墨爲説書一派,相里氏、謝子是也;南方之墨爲談辯一派,苦獲、己齒、鄧陵子是也。
又據此三墨之分,蒙氏將《經上》至《小取》六篇屬之於南方之墨,將《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係之於秦墨,將《親士》下七篇及《十論》歸之於東方之墨。
從引文來看,蒙氏以《耕柱》五篇爲最早,並猜測其出於秦墨之傳。
蒙說大意,葉翰、黃建中等已先發之。
楊俊光曾對近人所謂“墨離爲三”之說作了批評,認爲所謂“説書”、“談辯”、“從事”三者均是“爲義”之大務,“只是同一學派内部的不同分工”,不能據此而判定爲《韓非子》所言之“三派”。
楊氏緊扣《耕柱》原文,其說有據。
“説書”、“談辯”、“從事”三者雖可相分“爲義”,然而確實不含《顯學》篇所謂“取舍相反”之意。
而學者徑直將此分工協作之不同看作分派之不同,則其中難免存在謬誤的可能。
今補充一證,《貴義》云:
“子墨子曰:
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此正與《耕柱》篇“爲義”之三大務相環,亦乃修身成義之說。
據此,可知學者以三大務爲三大派之劃分標準,殆有郢書燕説之迷妄。
蒙説頗富構想力,文字亦繁,後學者又據之演繹不絕,今特就其言以辟之。
其一,彼既以《耕柱》五篇於《墨》書最先,又以篇中所言談辯、説書、從事三者爲三墨,則直以三墨起自墨子生前矣,然此與《顯學》所謂“自墨子之死也”而“墨離爲三”之語大有乖違。
其二,南方之墨者,說見《莊子·天下》;東方之墨者,說見《說苑·雜言》;秦之墨者,說見《說苑·雜言》、《淮南子·修務》。
三方之墨,於典有徵,——然此三方之墨即是韓非所謂“三墨”者乎?
是不可以不辨。
《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鄧陵子之屬”云者,與所謂“三墨”有二者相合,——然韓非有謂此相里氏乃東方之墨者,伯夫氏乃秦之墨者乎?
蒙氏以“相里勤爲東墨”而持“伯夫自應爲秦墨”之說,實出於自家臆斷,冀其或是也。
其三,《天下》云: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
”從句法結構來看,相里勤、五侯二人爲師徒,五侯與南方之墨者并時,相里氏與鄧陵氏相别而時有先後。
據《莊》書,相里氏一派(主要爲五侯之徒)亦與南方之墨者相訾應也,如此,則何能將相里氏之墨置於“談辯”之外,而臆斷其必爲“説書”之“東墨”邪?
其實,請循其本,以地域與以學行分派,本當爲二,何可輕易將二者混同起來?
其四,蒙氏云:
“《耕柱》等篇似《論語》、《孟子》,爲條記墨子言行,殆《墨書》之最早者。
”所謂“似《論語》、《孟子》”者,本於胡、梁二氏。
然而,第使甲書與乙書之體裁相似,亦不能據此由甲書之早作而斷定乙書必當早作。
此二者之間實無必然聯繋。
以《耕柱》等篇與《論》、《孟》相似,而推斷其爲“條記墨子言行”則可,然而據“條記墨子言行”之說進而斷言其爲“《墨書》之最早者”則不可。
其實,先秦子書的形成非常複雜,《耕柱》諸篇既可能爲墨子生前言行之信實記錄,亦可能爲後人追記、增益甚至託言寄論的結果。
故僅據“條記墨子言行”以立說,是無法得出《耕柱》等篇“殆《墨書》之最早者”的判斷的。
相反,我們應當根據語言、文獻、思想等多種因素來推斷《墨語》諸篇的製作時代。
此外,蒙氏既云“或秦墨之起稍後,非莊子所知”,則以南墨先起矣;後又云“南墨成書最晚”,則殆以秦墨先起矣。
前後二語疏於照應,至於自相矛盾而不自覺也。
蒙氏又將其“心得”推廣於七十一篇而求“三墨”之跡,其中或有偶合於實際者,然其大率實本自妄臆之測。
至於方授楚《墨學源流》,考證始見繁縟,然其立說尚有未必允當之處。
方氏以《貴義》下四篇爲“墨家後學”的著作,晚於墨子弟子,以《耕柱》篇作於秦漢之際。
方云:
第四組各篇,遲早頗不一律,但早者亦在第二組以後,蓋其言均辯而不多也。
《公輸篇》文甚辯而無盈辭,視《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爲早……惟《耕柱篇》又云:
“昔者夏后開使蜚蠊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孫云當作益
雉以)卜於白若之龜……乙又言兆之由,曰:
饗矣。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此以“國”“北”爲韻而句不順,王樹枬、劉師培、張純一並改“國”爲“邦”,則東邦韻也。
按邦而爲國,此漢人避高祖諱改之;夏后啓作開,亦漢人避景帝諱改之也。
此雖不能斷定《耕柱》爲漢景帝以後人所作,最少此一節爲景帝以後人所加,則無可疑,蓋他篇“邦”“啓”字均未改也。
《耕柱篇》又有“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之語,則此篇必爲禽滑釐派之後學所述者也。
然則由《耕柱》至《公輸》五篇,或起於第二組以後,至漢而始完成之也。
方氏認爲《墨語》五篇的形成雖有遲早之分,然皆在《十論》之後,說與鄙意相合。
不過,他疑心《耕柱》篇爲漢人著作,而以避諱爲說,殆非。
篇中“夏后啓”之“啓”字作“開”,固因避諱。
他篇“啓”字僅一見,見《非樂上》引《武觀》文。
據《墨》書體例,《武觀》乃佚《書》。
依漢人抄書通例,經書文字並不避諱。
王引之曾據《太平御覽》等改“一西一東”爲“一東一西”,又移此句於“一南一北”上,而致雲、西與北、國四字兩兩協韻。
劉師培等人以避諱爲說,“國”乃“邦”字之改,而邦、東爲韻。
此爲一種可能。
而將“一西一東”移於“一南一北”句上,以北、國爲韻,則又爲一種可能。
邦、國二字,先秦俱有;郭店竹簡《老子》乙組即有“國”字,由此可知,人們不能僅據通行本作“國”,即因避諱爲說,反推簡本《老子》此字必作“邦”。
而《墨子》全書作“國”字者多矣,其是否咸由避“邦”字諱所致,顯然不可一概而論。
方氏依避諱之說進而懷疑《耕柱》篇爲秦漢之際或漢初著作,殊爲粗率。
相反,設若此“國”字確實由避諱所致,那麽據此可以推斷該篇當不遲於漢初而作,然而無法由此斷定衹可能撰作於漢初或秦漢之際。
總之,方氏以《耕柱》爲秦漢之際著作,其說殆不可信。
嚴靈峰氏曾將《貴義》與《十論》相並,列入彼所謂“本論”,而以爲《非攻上》脫文。
嚴氏一方面認爲“非攻”是“貴義”,另一方面又以“‘貴義’實即‘非攻’之主要内容”,說甚不清,未足與辯。
《非攻》與《貴義》二篇皆以“義”爲中心,這是毫無疑問的,然後者並非以“非攻”爲論述之根本目的。
又,二篇文體不類,猶牛頭不對馬嘴。
因此,嚴氏以《貴義》爲《非攻上》之脫文,其說殆流於感想之類,不足取信。
最近,鄭傑文拓展了胡適等人之說,而作了所謂詳細的考證。
他說:
“《墨子》中《耕柱》等5篇,是比胡適所謂的‘第二組’即從《尚賢》到《非儒》24篇(又稱《墨子》‘十論’)更爲重要、更爲原始的墨家資料。
”不過,與胡氏相比,鄭氏有兩點不同:
其一,將胡氏的特稱判斷變爲了全稱判斷。
胡云“其中有許多”,這是特稱判斷。
而“許多”一詞在漢語中其含義頗爲模糊。
其二,胡氏衹用了“更爲重要”四字,鄭氏又衍生“更爲原始”一語。
因此,胡適的看法比較籠統,尚在疑信之間;而將《墨語》五篇全部看作比《十論》諸篇更爲重要、更爲原始的墨家資料的觀點,則大抵出自鄭氏之意。
又,鄭氏此一觀點,蒙文通其實已先說之。
不過,在蒙氏那兒,構想的成分較重。
鄭氏與其不同,而力圖以所謂考據來作論證。
他一共提出了六條理由,其中第五條以文章及對話之長短爲據,說甚無稽,毋需置議。
其第一、二、三條理由分别認爲《耕柱》等五篇多次記載了“某些人士對墨子學説的質疑”、“學生對他家學説的傾慕和對於所學内容的疑問”、“學生對於墨子的批評,甚至有反叛墨子者”,並舉出了一些例文加以評論。
然而,對於墨子學説之質疑、懷疑或者批評,此即已預先承認了墨子具有了自己堅定的思想主張。
且從原文來看,《墨語》五篇實已包括了《十論》所涉諸内容。
因此,鄭氏用作論證而列舉的《墨語》五篇例子,它們到底是發生在《十論》思想基本形成以前,還是在其後?
這不是憑藉揣測式的解釋即可輕加回答的。
大概鄭氏在論證之先即已預先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假定,以《十論》爲成熟時期的墨家著作,而在其成熟之前則必定有一個不成熟的時期。
就目的來看,鄭氏的此一考證乃完全是爲了尋找墨子學説之初創内容;從結果來看,鄭氏以爲《墨語》五篇即是。
這在其所云第四條理由中完全表露了出來:
“如此等等的例子,呈現著由《耕柱》等5篇到《墨子》《十論》諸篇所承載的墨家思想學説由初步、不成熟,到複雜、成熟的發展過程。
”此爲明證。
不過,問題正在於這些看似“不太成熟”,甚至有違墨子“十義”之《墨語》内容,難道真的只可能先於而不可能後於《十論》而提出嗎?
實際上,鄭氏已意識到了自己的觀點及其論證在很大程度上處於窘迫的境地之中。
鄭云:
其六,但有一問題需要澄清。
《墨子·魯問》載魏越問“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時,墨子說:
“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與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即語之兼愛、非攻。
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墨子在此明確講到《墨子》《十論》的十大主張,那麽是否是墨子在世時,作爲墨家主導社會學説的《墨子》《十論》就已完成並且十分完善?
若果如此,我們討論墨翟初創墨家學説時的最主要原始資料當爲此《墨子》《十論》。
但上舉《墨子·魯問》載墨子所言祭祀目的,與《墨子·明鬼下》載墨子言祭祀的目的,已明顯看出“初創學説”與“成熟學説”的差别;《墨子·魯問》所載墨子在魯的四次言談,與《墨子》《十論》所載墨家的成熟思想學説有較大差異;並且,這樣的例子在《耕柱》等5篇與《墨子》《十論》諸篇的對比中尚多。
那麽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墨子》《十論》是由墨子、墨子弟子、墨家後學逐步完善而形成的。
所以,我們討論墨子初創學説時的主要内容,當然應依據《耕柱》等5篇而不能依據《墨子》《十論》。
《魯問》篇對墨子十大主張(“十義”)做了完整而系統的概説,一般說來,應當據此推斷《墨語》諸篇出自《十論》之後。
然而鄭氏的觀點與此正相反對,故自云“需要澄清”此一問題。
從上述引文來看,鄭氏的辯解無非遁辭而已。
《魯問》、《耕柱》與《十論》諸篇的思想差異較大,此固如是;然而,到底孰先孰後?
這不是憑藉囫圇式的判斷即可隨意決斷的。
首先鄭氏將自己尚處於論證之中而需要他人檢討、認可的觀點作爲一個真實的大前提來對待,並進而據來其討論相關問題,此適有障目攫金之妄。
由答文來看,墨子的十大主張在《魯問》撰作的時候已是一個完整而又能應時發用的思想系統。
據此可知,此種形態的“十義”說必定是成熟的;而成熟形態的“十義”說,則表明在實質的意義上《十論》已經形成。
又,墨子高弟禽滑釐(亦早期弟子)本爲子夏弟子,而禽子何以後來捨儒取墨,心折於墨子之門?
蓋非徒爲個人崇拜,抑亦悅於墨道故也。
如果說禽子心折墨門之時,墨道尚處於初創階段,那麽在《墨語》撰作之時,則當已爲一成熟的形態。
《貴義》云:
“子墨子曰:
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
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同篇又云:
“子墨子南遊於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翟聞之:
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
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
而子何怪焉?
”《耕柱》曰: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
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
子墨子曰:
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
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
可譽而不譽,非仁也。
”這些“子墨子”所言之話,都是爲了努力維護已然之“墨道”本身,而與《魯問》一段完整、系統闡述十大主張的文本正相呼應。
據此,鄭氏之説殆不可從。
在日本和西方漢學界中,渡邊卓(WatanabeTakashi)、葛瑞漢(A.C.Graham)、白妙子(BrooksA.Taeko)、方克濤(ChrisFraser)和戴卡琳(CarineDefoort)等學者曾深入地考察和討論了《十論》諸篇的成篇時代問題,然而對於《墨語》諸篇的相關問題,他們幾乎皆沒有觸及或加以認真的探討。
職此之故,細緻地討論《墨語》的成篇時代問題,在當前的學術背景下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三)《墨語》成篇時代略考
《十論》諸篇,畢沅曾指出乃“門人小子記錄所聞”。
觀篇中“子墨子言曰”、“子墨子曰”之語習見,此固墨子生前講説,然弟子申論之言亦於其中顯而易見。
同時,由於古書成篇過程較爲複雜,其中包含了後學更進一步推衍、修飾的内容,此亦有可能。
前輩學者有謂每論之下篇較爲晚出,說疑是。
不過,從總體上來看,《十論》諸篇本爲墨子弟子申述之作,而主要爲了表達墨子本人的思想。
至於《墨語》諸篇,單純從文體來看乃是一種記錄或記述;不過,與《十論》相比,在形式上非常零散,乃所謂“語彙”,而非論文體式。
所謂“語彙”,必纂集而成。
而諸語彙於篇中又各以類相分,因此各篇之編纂當在記述者身後,去墨子之死殆有數十年之久。
這裏,首先設定了《墨語》諸篇乃是對墨子生前言行的忠實記錄,而非出自後人的依托。
不過,這些篇目究竟是對墨子生前言行的忠實記錄,還是出自後人的依托?
乃正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大問題。
今略爲考證如下。
《非儒》篇,畢沅認爲非墨子本說,乃純爲弟子所造。
孫詒讓更進一步,據《荀子·儒效》篇而認爲其所非者正乃“周季俗儒”。
據此,則該篇成於戰國末季。
孫說業已得到廣泛承認,學者少有異議。
而《非儒》與《墨語》諸篇存在文本上的關聯,其例較多。
例一,《非儒下》、《耕柱》篇皆有“道教”一詞,他篇俱無。
《非儒下》、《魯問》篇皆有“白公”典故,他篇俱無。
《尚賢下》“有道者勸以教人”、“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尚同上、中》“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兼愛下》“有道肆相教誨”,《天志中》“有道相教”。
“道教”殆從所徵諸語演化而來,然已完全獨立爲一詞。
例二,《非儒下》與《耕柱》篇對儒者“君子述而不作”之教皆作了批駁,他篇俱無。
例三,《非儒下》與《公孟》篇對儒者“君子必古言古服然後仁”之說皆作了批駁,他篇俱無。
《非儒下》:
“儒者曰: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應之曰:
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公孟》:
“公孟子曰: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
子墨子曰:
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
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
且子法商,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此二駁文雖觀點有異,然實相補助。
《公孟》孫氏《閒詁》:
“《孟子·告子》篇荅曹交曰: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公孟子之言同於彼。
”據此可知,此正當時儒墨相辯詰的流行話題,而公孟子與“子墨子”之辯當發生在孟子同時或稍後。
例四,《非儒下》與《公孟》篇皆有“君子若鍾”之譬,墨氏對此儒者之說並作了批駁,而他篇俱無。
《非儒下》云“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公孟》作“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
此譬喻,戰國中晚期文獻習見。
上博竹書《性情論》:
“金石之有聲,弗鈎不鳴。
”(後四字,郭簡《性自命出》殘)《莊子·天地》: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荀子·法行》:
“扣以其聲。
”《淮南子·詮言》: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
”據此而言,《公孟》篇此段文本不當早於《性自命出》篇之作。
而此篇竹書的撰作,據筆者意見,殆與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相近。
又,《公孟》篇云:
“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所謂不扣而鳴邪?
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詞鋒更爲苛酷、嚴厲,已深得儒墨相詆之風。
總之,據此四例可知,《墨語》諸篇當與《非儒》作於同一時期。
從《墨語》與《十論》相比較來看,前者在總體上亦當晚於後者。
其一,《十論》諸篇有著重於立論者,亦有著重於駁論者,然持論猶且穩健,而無染磽薄、苛厲之風;《墨語》諸篇則好爲剽剝之論,而遣辭尖酸、刻薄,時具譏諷之意,且又多用設譬、歸謬之法,此正戰國中晚期諸子好辯時代之特徵。
其例衆多,今不引。
又,《墨語》專門針對儒者之駁議多見,而《十論》諸篇並未將所批駁者特指爲儒者,甚至連“儒”一字亦無。
這些看法,前代學者大概已指出。
除此之外,在《墨語》諸篇中,墨者具有強烈的自誇與矜辯風氣,此尤爲值得注意者。
《貴義》“子墨子曰”:
“吾言足用矣。
舍吾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
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此與《大取》篇“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猶在”同謂,將“子墨子之言”誇詡爲萬世不易之絕對真理,由此可見其一斑。
孟子亦好辯,然猶且以“予豈好辯也哉?
予不得已也”以自衛;至於《墨子·公孟》篇,“子墨子”則曰“告子毀,猶愈亡也”,其矜辯、標榜之跡昭然若揭矣!
其二,《非命上》有所謂“三表”,中、下篇謂之爲“三法”,《貴義》“子墨子”則曰:
“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
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此係以“三表”或“三法”爲基礎,而放之於言行者。
不但如此,《墨語》強調“合其志功而觀焉”的觀點,相對於“三表”之“儀”而言乃是思想上的一種轉進。
《魯問》云:
“魯君謂子墨子曰:
‘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
’子墨子曰:
‘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譽)爲是也。
魡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蠱),非愛之也。
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志功之辯,又見《耕柱》、《大取》篇,殆墨子後學之觀念,無疑。
其三,在《十論》中,“十義”乃分别著重論述之;而在《墨語》中,則綜合諸義之文本多見。
《公孟》載“子墨子曰”:
“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
”同篇記子墨子對儒者“四政”之批判,《魯問》篇又完整地載述了“十義”的系統,合此三者而言之,適足證明《墨語》當晚於《十論》而作。
其四,與《非攻下》相比較,《貴義》篇白黑之辯當爲晚出。
《貴義》:
“子墨子曰:
今瞽曰:
‘鉅者白也,黔者黑也。
’雖明目者無以異之。
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
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
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
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瞽所謂不知白黑者,非不知“白”、“黑”二名之别也,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