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苑科技大学101文档格式.docx
《高苑科技大学101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苑科技大学101文档格式.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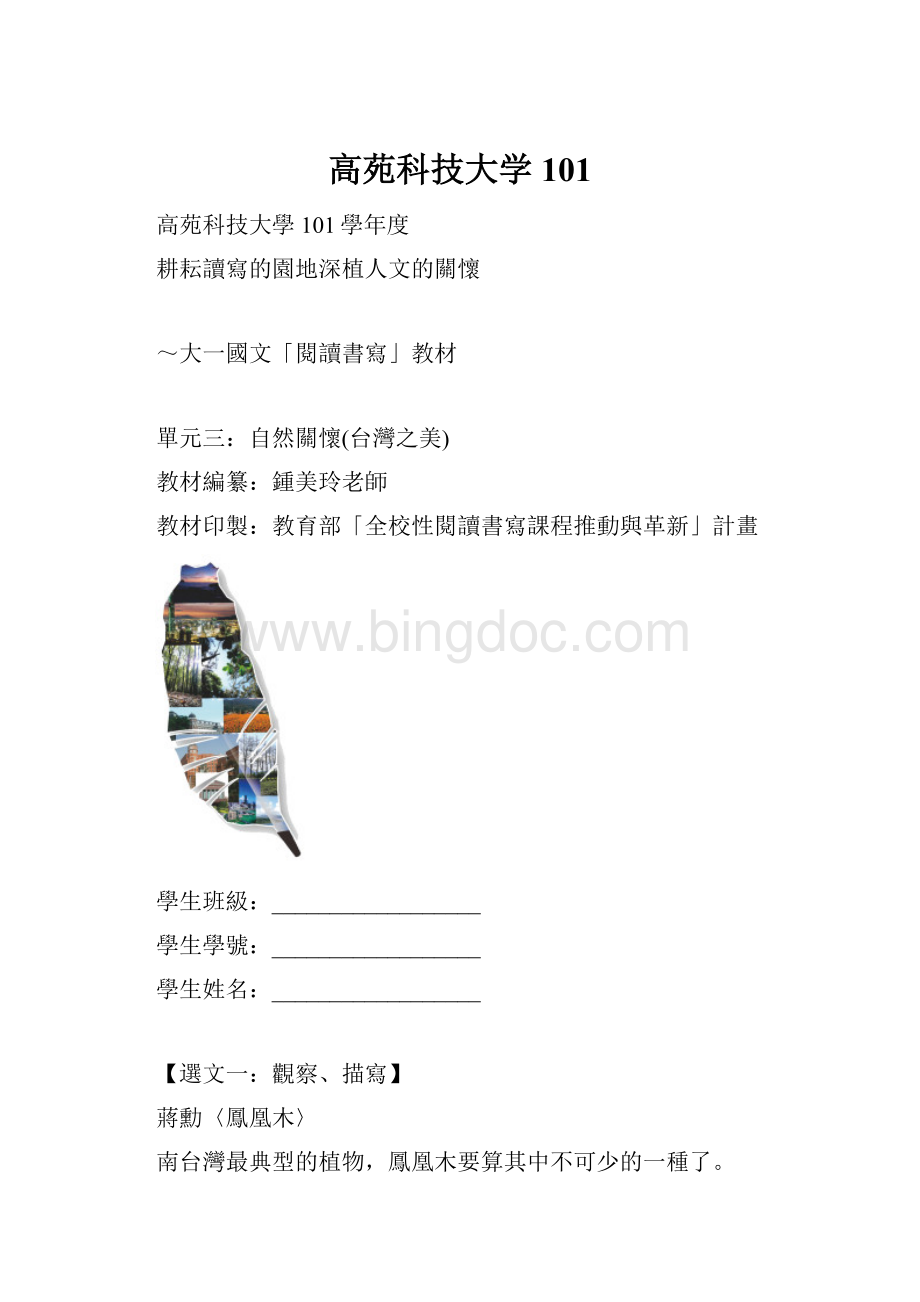
大抵在寒冷、艱困、貧瘠中生長的生命,為了抵抗惡劣的環境,都自然生長出一種堅實牢固的特性。
鳳凰木是熱帶地區受陽光、雨水驕寵的植物,它無阻礙地伸展肢芽葉脈,給陽光、給雨水,給一碧如洗的艷麗的藍天,而它,在享樂安逸中,也渾忘了憂患、災難。
鳳凰木的葉片很小,每一片只有米粒般大,點細如萍。
它們借著橫向伸展的枝莖分脈生長,連綴平鋪成如鳥翼一般薄而廣的葉羽,層層相覆蓋,受風時,上下昭展飛動,的確如鳳凰的停棲,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
「碧梧棲老鳳凰枝」,杜甫說的是梧桐,卻似乎更適合拿來歌詠這碧綠飛張如鳥羽的鳳凰木呢。
鳳凰木的綠是一種極俗艷的綠,青中帶黃,脆亮耀眼。
六月開花,花是一簇一簇冶豔的猩紅。
粉紅駭綠,完全是南國熱帶的嬌憨、野熾、俗艷之美。
今年的鳳凰木開得特別盛,整個大度山像火燒一樣。
那俗艷大膽的紅與綠,不含蓄、不收斂,是準備著,在這一季,用最狂烈的方式,把生命燃燒消耗殆盡。
我站在那紅如血的花前,看血點飄灑飛揚,不禁要驚叫起來。
原來生命是可以這樣揮霍的,它像是在嘲笑、不屑於世人的拘謹、小心翼翼,不屑於那樣畏縮的苟活,它要任情恣性,縱心所欲,給人間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夏日南國之花。
花季過後,枝梢上結了豆莢,逐漸長大,可以長到手肘般的長度,有三指寬,一稜一稜,露出厚實飽滿的種子的形狀。
到了成熟時,豆莢開時,種子四處散播,來年春天復進地上便可見小小鳳凰木的新苗。
豆莢形成的季節,同時葉瓣也要開始飄零凋謝了。
許多樹木的落葉十分驚人,一大片一大片,彷彿刻意誇張死亡的悲劇,秋後的山上,枯葉的瑟颯,頗使人驚心動魄。
鳳凰木的落葉幾乎全無感覺。
那米粒般的葉瓣,在風中變黃飄散,像蘇詞中說的「似花還似非花」,細細點點,迷離紛飛,一霎時變無影無踪。
只有低頭細心去看,才看到匯聚的葉瓣,點細如萍,也無須人清掃收拾,一場秋雨,便化為塵泥了。
冬天的鳳凰木只有光禿的槎椏,在空中飛張著,十分慘怖悽楚的姿態,垂吊著尚未落盡的長長枯黑的莢殼。
很少人注意這就是鳳凰木,在夏季曾經驕奢冶豔、濃麗野俗的鳳凰木。
蟬聲逐漸不見了,秋雨陡起,我看見點細的鳳凰葉瓣開始飄零,夏秋之交,心緒是特別繾綣難解的啊!
選自:
《大肚•山》,台北:
爾雅出版社,1987年
【選文二:
陳列〈玉山去來〉
崎嶇的碎石小徑在無邊的漆黑中循著陡坡面曲折上升。
我臨時隨行的一支玉登山頂觀日出的隊伍,自從出了冷杉林,進入海拔約三五五○公尺的森林界線以後,已因成員體力的不一而斷隔為好幾截;
我看到他們的手電筒或頭燈的微光點綴在上下的數個路段上,在黑暗裡搖晃。
那些不時閃現的人影、岩坡和低矮的圓柏叢,全如魅影般。
由於沒有了樹林的遮擋,風稍大了,夾著凌晨近四時的森冷寒氣,從難以辨認的方向綿綿襲滲而來。
裹在厚重衣服裡的身軀,卻因吃力攀爬而是熱的。
四周也仍相當安靜,只有偶爾從那寂寂黑色中響起的前後人員的傳呼應答,或是石片在暗中某處唰唰滑落滾動的聲音。
我一邊聽那聲音在我身邊漂浮懸盪,一邊聽著自己的心跳和踩在碎石上的跫音,一步步地繼續往那黝黑的高處摸索,彷彿是史前地球上的一個跋涉者。
經過幾小段碎石坡以後,矮樹也漸少了,風,去更強勁,陣陣拍打著身邊的裸岩,咻咻刮叫。
我斜靠在一處樹石間休息,腳下的急斜坡掩沒在黑暗裡,而很遠很遠的底下,是數公里外嘉南平原上和高雄地區依稀聚集的燈光。
天空仍是濃濃墨藍,只有很少的幾顆很亮的星。
路愈往上遇坎坷,呈之字形一在轉折,沿鬆脆的石壁而上。
我盡量調整呼吸,配合著放下每一個斟酌過的步伐。
而就在這專注中,天終於開始轉亮,晨光漸漸,在我身旁和腳下開始幽微浮露出灰影幢幢的巉嚴陡崖。
驚懼的心反而加重了。
到達位於玉山山脈主脊上的所謂風口的大凹隙時,形勢大改。
山野大地好像在我來不及察覺之際忽然在我腳下翻轉了半圈;
上坡時一路被暗暝龐大的嶺脈遮住的東邊景觀,轉瞬間出現在我一下子舒放拉遠開來的眼底裡。
大斜坡、深谷、北峯,以及從北峯傾斜東去的山嶺,都在薄薄的曙色風霧中時隱時現。
寒風囂叫,從娜屬於荖濃溪源頭的谷地吹掃過來,沿著大碎石坡,直像這個風口猛衝。
我緊緊倚扶著危巖,努力睜眼俯瞰錯落起伏的山河,心中也一陣陣的起伏。
然後,當我手腳並用地爬過最後一段睽巍巍破碎裸露的急升危稜,終於登頂後,我就看到那場我從未見識過的高山風雲激烈壯闊的展覽了。
這是四月初的時候,凌晨近五點,我第一次登上玉山主峰頂。
當我正是氣喘吁吁,驚疑的心神仍來不及落定時,山頂上那種宇宙洪荒般詭蹫的氣象,剎那間就將我完全鎮懾住了。
一片洪荒初始的景象。
大福大福成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絕從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灰褐乳白相間混,或淡或濃,瞬息萬變,襯著灰藍色的天,像颶風中翻飛的卷絲,像散髮,狂烈呼嘯,汹汹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我眼前和頭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如宇宙本身以全部的能量激情演出的舞蹈,天與地以及我整個人,在這速度的揮灑奔放中似乎也一直在旋轉中搖盪著,而奇妙的是,這些雲,這些放肆的亂雲,到了我勉強站立的稜線上方,因受到來自西邊的另一股強大氣流的阻擋,卻全部騰攪而止,逐漸消散於天空裏。
而在東方天際與中央山脈相接的一帶,在這些喧囂狂放的飛雲下,卻令有一些幾乎沉沉安靜的雲,呈水平狀橫臥,顏色分為好幾個層次,赭紅的、粉紅的、金黃的、銀灰的、暗紫的,彼此間的色澤則細微地不斷漫漶濡染著,毫無聲息,卻又莫之能禦的。
然後,就在那光與色的晃動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大的蛋黃,像橘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蹦跳而出,雲彩炫耀。
世界彷彿一時間豁然開朗,山脈谷地於是有了較分明的光影。
這時,我也才發現到,大氣中原先的那一場壯烈的展覽,不知何時竟然停了。
風雖不見轉弱,頭頂上的煙雲卻已淡散,好像天地在創世之初從猛暴的騷動混沌中漸顯出秩序,也好像交響樂在一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沉穩,進入了主題豐繁的開展部。
我找了一個較能避風處,將身體靠在岩石上,也讓震撼的心情慢慢平息下來。
啊,這就是台灣的最高處,東北亞的第一高峯,三九五二公尺的玉山之巔了,嶔奇孤絕,冷肅硬毅,睥睨著或遠或近地以絕壑陡崖或瘦稜亂石斷然阻隔或險奇連結著神貌互異的四周群峯,氣派凜然。
名列台灣山岳石峻之首的玉山東峯就在我的眼前,隔著峭立的深淵,巍峨聳矗,三面都是泥灰色帶褐的硬砂岩斷崖,看不見任何草木,肌理嶙峋,磅礡的氣勢中透露著猙獰,十分嚇人。
我想,在可預見的未來,我是絕對不敢去攀登的。
南峯則是另一番形勢:
呈曲孤狀的裸岩稜脊上,數十座尖峯並列,岩角崢嶸,有如一排仰天的鋸齒或銳牙。
白絮般的團團雲霧,則在那些墨藍色的齒牙間自如地浮沉游移,陽光和影子愉悅地在獰惡的裸岩凹溝上消長生滅。
而二公里外的北峯,白雲也時而輕輕籠罩,三角狀的山頭此時看來,相形之下就可親近多了,在綠意中還露出了測候所屋舍的一點紅。
中央山脈的中段在似近又遠的東方,大致上,或粉藍或暗藍,從北側到南一線亙,蜿蜒著起起伏伏,自成為一個更大的系統,兩端都溶入了清晨溶溶的天光雲色裡,中間的若干段落也仍被渾厚的雲層遮住了,但浮在雲上的一些赫赫有名的山頭,卻是可以讓我快樂地一邊對照著地圖一邊默默叫出它們的大名:
馬博拉斯、秀姑巒、大小窟山、大關山、新康山……。
它們一一來到我的心中。
我站起來,在瘦窄的脊頂上走動。
落腳之處,黑褐色的板岩破裂累累,永在崩解似的。
岩塊稜角尖銳,間雜著碎片與細屑,四下散置。
我就在這些粗礪又濕滑的碎石堆中謹慎戒懼地走著,辛苦抵擋著從西吹來的愈來愈強盛的冷風。
我勉強張眼西望,看到千仞絕壁下那西峯一線的嶺脈和楠梓仙溪上游的一段深谷,都蒙在一片渺茫淡藍的水氣裡。
阿里山山脈一帶,則遠遠地橫在盡頭,有如屏障一般,山與天也是同樣粉粉的淡藍,只是色度輕重不一而已。
實在非常寒冷。
我恍悟到耳朵幾乎凍僵了,摸起來麻麻刺刺的。
那支登山隊的幾位隊員在急勁酷寒的風中顫抖著身子。
有人得了高山症,臉色一陣白似一陣,呼吸困難,身軀直要癱軟下來的樣子。
我的溫度計上指著攝氏二度。
後來我才曉得,山有千百種容貌和姿色。
這一年來,我三次登上玉山主峰頂。
一月中旬,有一次我在雪花紛飛中穿過冷杉林之際,曾被那深厚濕滑的冰雪阻斷了最後的一段一公里多的登頂路成。
繼四月底的初登經驗後,六月底,我大白天二度登臨,只見濕霧迷離,遠近的景觀幾乎都模糊一片,只有偶爾在那霧紗急速地飄忽飛揚舞踊的某個瞬間,才隱約露出局部的某個斷稜或山壁。
但隔一周後摸黑再上山時,遭遇竟又迥然不同。
難得的風輕雲也淡。
最迷人的則是日出前後東北方郡大溪一帶的景色。
在那溪谷上,霧器印氤氳,濛濛寧謐的水藍。
層層疊置著一起從兩旁緩緩斜入溪谷地的山嶺線,便全都浴染在那如煙的藍色裡,彷彿那顏色也一層疊著一層,漸遠漸輕,滿含著柔情。
這個早晨,似乎仍是地球的一個早晨,永遠以不同的方式和樣貌出現的高山世界的早晨。
當旭日升起,在澄淨的蒼穹下,台灣五大山脈中,除了東部的海岸山脈之外,許多名山大嶽,此時都濃縮在我四顧近關遠眺的眼底,所有的那些或伸展連綿或曲扭摺疊的嶺脈,或雄奇或秀麗的峯巒,深谷和草原,斷崖和崩塌坡,都在閃著寒氣,變動著光影,氣象萬千,整個的形象卻又碩大壯闊,神色則一般地寧靜無比。
這個時候,光和風雲,以及其他什麼時候的雨雪雷電,都瞬息萬變地在這個山間世界作用嬉戲,讓山分分秒秒地改變著它的形色與氣質。
然而就在那捉摸不定的特性裡,透露的卻又是巨大無朋,如如不動的永恆的東西,讓人得到鼓舞與啟示的東西,例如美或者氣勢,動與靜的對立與和諧,生機與神靈。
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玉山頂來回走動,隱約體會著這一類的訊息,時而抬頭四顧巡逡,一邊在默默念起各個山峯的名字。
一種對天地的戀慕情懷,一種台灣故鄉的驕傲感,自我心深處汩汩流出,一次深似一次。
台灣,其實,不就是一個高山島嶼嗎?
或者更如陳冠學所謂的「台灣以整個台灣,高插雲霄」。
兩億五千萬年以前,當時的亞洲大陸的東方有一個海洋,來自陸塊的砂、泥等沉積物經年累月在路棚和路坡上堆積。
七千萬年前,大陸板塊與海洋板塊開始碰撞,產生了巨大的熱與力的作用,原來的沉積岩廣泛變質。
台灣以岩石的面貌初次露出水面。
此後的漫長歲月裡,這個區域漸回復平靜,台灣島與大陸之間的地槽再度累聚起厚厚的沉澱物,冰河的融化則使台灣又沒入海面。
四百多萬年前,一次對台灣影響最大的造山運動發生了。
菲律賓海洋板塊由東方斜著撞上了台灣東部,使台灣島的基盤急速隆起,地殼抬升,始岩層再次摺皺斷裂,變形變質。
這些斷裂,亦即近南北方向的斷層,是台灣一種出現頻繁的地質構造。
本島南北平行的幾個大山脈,也正是這種來自東西方向的劇烈擠壓造成的,台灣因此高山遍佈。
因此,台灣以拔起擎天之姿,傲立海中。
在這個島上,海拔超過三千公尺的名山,達三百餘座。
面積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一個海島,竟坐擁這麼多高山峻嶺,舉世罕見。
目前,這兩大板塊衝撞擠壓所產生的抬升起用,仍在進行。
我所站立的這座玉山,正就是地殼上升軸線經過之處。
我置身的玉山山脈和眼前的這一段中央山脈,也正是台灣山系的心臟地帶,座落在台灣高山世界的最高處。
我一次又一次走入山區,在玉山頂碎裸的岩石間踱步,時而環顧那些既殊形詭狀又單純重複疊置著淡入遠天或浮露魚閒雲間的峯巒,當世界遼闊清亮的時候;
而當風生雲湧,冷氣颼颼刺痛著我寒凍的臉孔,所有的景物和生命跡象又都急急隱沒了,甚或細密的雨陣排列著從某個方位橫掃而來,夾著風與霧,消失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谷和森林。
清明中見瑰麗,晦暗動盪中更仍是大自然無可置疑的巨大與神奇。
我於是開始漸能體會學者所說的台灣這個高山島嶼的一些生界特質了。
真的,假使沒有這些攅簇競立的大山長嶺,台灣的幅員將顯得特別狹小,不見高深,風景則變得平板單調,沒了豪壯氣勢與豐富的姿采,而人與其他生物也勢必有著迥異於目前的生息風貌的吧。
對於生界的特色,氣候是關鍵性的決定因子,而對於台灣的氣候,我眼際裡的這些重重高山,正有著莫大的正面作用,像一道道相倚並峙的屏障般,在冬夏兩季之間,分別攔下了來自東北與西南的季風氣流,使得島上年年都有充沛的雨水,孕育出蒼翠的森林,並將全島滋潤得難見不毛之地。
座落於島上中央地帶的整個玉山國家公園,也因而成為台灣最重要的集水區。
濁水溪、高屏溪和東部的秀姑巒溪這三條台灣島上的大水系,都以這裡為主要的發源地。
台灣山勢的崇高,也使溫度、氣壓和風雨都受到極大的影響而呈垂直變化,在海拔不同的地區造成明顯的氣候差異,使原屬亞熱帶短短距離瑋度內的台灣,出現了寒溫暖熱的諸種氣候型。
動植物的類型,當然也就隨海拔位置的不同而大有變異。
台灣垂直高度近四千公尺,從平原走上玉山頂,就氣候和草木的變化來說,微地形、微氣候和微生態系姑且不論,大略等於從此地向北行四千公里。
一個蕞爾小島竟有如此紛岐的氣侯型和生態系,這又是世界南有其匹的。
台灣就是一座山,一座從海面升起直逼雲煙且蘊藏著豐富生命資源的巍巍大山。
這是造化奇特的賜予。
我們大部分人大部分時間就在它的腳下生聚行住。
我在玉山地區三番兩次進出逗留,總覺得自己已走進它的源頭了。
這個源頭,基本上,卻相當荒寒。
設於海拔三八五○公尺之玉山北峰的測候所,測得的玉山地區年均溫度是攝氏三‧八度。
攝氏五度的等溫線大致與海拔三五○○公尺的等高線相合。
而三千公尺以上的地區,在冬季乾旱不明顯時,積雲期可連續達四個月。
一般而言,由於氣候的因素,加上岩石裸露,風化劇烈,土壤化育不良,海拔超過三千六百公尺的地帶無法形成森林,三千八百公尺以上的地區,更可以說是台灣生育地帶的末端,只能存活著少數的某些草本植物。
我先前幾次走過這個高山草本植物帶時,只覺得滿眼盡是光禿的危崖峭壁,岩層破碎。
勁厲的冷風,經常吹襲。
這裡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間或出現在石屑裡的小草,看起來毫不起眼。
我不曾為它們停留過疲累的腳步。
然而六月底再次經過時,我卻為它們展露的鮮豔色彩而大感驚訝。
荒冷沉寂的高山上突然出現了一片蓬勃的生機。
尤其是北峯周圍,可能因坡度較緩,土壤發育較好,花草甚茂,各種色彩紛紛將這個高山地域鑲飾得不再那麼冷硬:
紫紅色的阿里山龍膽,晶瑩剔透如薄雪般的雪山薄雪草,藍色的高山沙參,黃色的是玉山佛甲草、玉山金梅和玉山金絲桃,以及在北峯頂上盛開成一大片的白瓣黃心的法國菊……。
我開始帶著一本小圖鑑專程去進一步認識它們。
在長期冰封之後,這些高山草花,這時,正進入它們的生長季節。
它們正著氣溫回升的短暫夏日努力成長,在一季裡匆忙地儘量完成從萌芽至開花、結果以至散播種子的一生歷程。
不過另一方面,我這時卻也開始了解到高山野花之所以多為多年生,原來是有其苦衷的。
對許多高山植物而言,籽苗內的養份畢竟有限,無法同時供應成長與孕育種子之需,所以為了達成繁殖的目的,只得採取分年逐步完成生命循環的策略:
第一年全心全意發展根系,次年發芽,然後年復一年的儲存能量,待準備充足後,再驕傲地綻放出美麗的花朵來。
但即使是這麼堅韌的高山岩原植物,在玉山主峯頂上,也已少見。
我反而發現了兩棵玉山圓柏。
四月底的時候,這一簇出現在峯頂梢南絕崖陡溝中的綠意旁,仍留著一小堆殘雪。
它們是台灣最高的兩棵樹。
然而就植物生命而言,地衣則還高過了它們。
顏色斑駁地貼生在山巔裸岩上的這些地衣雖屬低等植物,但因不畏高山上必然強烈的風寒和紫外線,且能將假根侵透入岩石內,逐漸使之崩解,使高山上高等植物的生長成為可能,因此一向是惡劣環境中最強悍的先鋒植物。
至於動物,據說在溫暖的季節,仍會有長鬃山羊、水鹿和高山鼠類在此出沒。
但我三度登頂,卻只有在四月底的那一次看到一隻岩鷚。
只有一隻。
牠長得胖胖的,離我約僅一丈,在板岩碎屑上慢條斯理地走著,毫無怕人的樣子。
灰色的小小的頭,時而啄點的地面,時而抬起來四下顧盼,背部灰栗相間的覆羽在刮掃的冷風中不斷地張揚起伏。
這就是台灣陸棲鳥中海拔分佈最高的鳥類,而且是世界上僅存於我們這個島嶼上的台灣特有亞種。
可是為什麼只有一隻呢?
牠真的能在這麼高寒的裸岩間找到果腹的小蟲或植物種籽嗎?
興奮之餘,這些都不免令我疑惑。
我一再地攀爬跋涉於玉山頂一帶,後來彷彿覺得幾乎要成為一種迷戀式的追尋甚或膜拜了。
我逐漸察覺到,自己似乎愈來愈期待著要在每次的山野漫遊中,在某個時刻,通過高山世界那種亙絕千里的恢宏大氣勢,通過周遭或恆久或瞬息生滅的形色聲氣和律動,去和什麼東西連結起來,譬如土地,譬如時間,等等。
我是已體會到了我可以為之歡欣的某些什麼,但我仍貪婪的希望能確切地把握得更多。
然而,經過了一長段時日之後,玉山頂所有的那些經歷,在記憶中其實有一部分卻已混淆起來;
某些個別的興奮心情雖還在,但印象中所有的那些或美麗或偉大的色彩和聲音,形狀和氣質,所有的那些我曾有過的感動或震撼,領會或省悟,最終都混合成單純的某些繫念和啟示,留存在我心底裡。
當夏天過去,秋天來到,高山的花季迅速消聲匿跡,冷霜降臨,多刺的玉山小檗的葉子轉紅了,掉落了。
然後是冬天,一片皚白的冰雪世界裡。
那些裸岩、地衣、那兩株海拔最高的圓柏,以及全部的那些堅苦卓絕的高山草花們,都將一體覆蓋在厚厚的白雪下。
而那隻孤獨的岩鷚,應該也會往低處移居的吧。
然後,也許四個月之後,春天回來的。
然後夏天……。
好長好長的一再輪迴的宇宙的歲月,大自然的歲月,我目睹過的那個玉山地區高山世界的歲月。
我懷念這樣悠悠嬗遞著的歲月,同時相信這其中必然存在著可以超越時間的義理和秩序,一些既令人敬畏卻又心生平安和自在,既令人引以為傲卻又願意去謙虛認知的屬於高山、屬於自然、屬於宇宙天地的義理和秩序。
【選文三:
觀察、思考】
劉克襄〈北壽山與南壽山〉
北壽山
每次到高雄,都會去爬壽山(柴山)。
這回也不例外。
為了爬山,還特別選擇靠近山腳的旅社下榻。
很不湊巧,前往攀爬的日子正好是周日。
平時壽山的登山客就絡繹不絕,例假日時更像鬧區之街道般擁擠。
大清晨北壽山入口的龍皇寺,集聚了比平時更多的攤販,沿著狹窄的巷道,排列到山腰去。
原本打算半途時,靜靜地坐下來休息,但是小徑上人來人往,始終找不到適當的休息空間。
長住南部的自然生態作家王家祥跟我說過,自從山區開放以後,這條山路不只像中正路一樣熱鬧,時日一久,山路被踩寬,更被蹧蹋得禿裸、溜滑,有些山上的珊瑚礁石都已磨損殆盡。
不過幾年光陰,遊客在北壽山就留下了許多條像巨大疤痕般的小徑。
長此以往,這個山的生態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半路上,遇見了好幾隻臺灣獼猴。
牠們肆無忌憚地在半路上向遊客要東西吃,或者乾脆用抓了就跑的方式。
登山的民眾也以餵食獼猴為樂。
結果,造成獼猴在行徑上背離常情。
我自己在半路上尋找植物繪圖時,就遇到兩次。
當我打開背包時,一隻公猴還跳到我休息的桌前搜尋,以為我要取出東西來吃。
野生的臺灣獼猴裡,大概就是北壽山的這一群最親近人了。
但也因為不懼人,牠們的食物來源已經相當仰賴登山者的提供。
甚至於,養成奢華的習慣。
如果遊客給的食物不好吃,諸如番茄、麵包之類,往往咬了一口便棄置一旁。
唯獨花生、香蕉是最愛,總吃得一乾二淨。
我在休息時,也聽到一些登山人在抱怨,他們很不喜歡黃昏時,仍單獨在壽山逗留,免得披索取食物的獼猴干擾。
這種索討食物的行為長期下去,對獼猴在自然環境的生存並不見得好。
民眾們其實應該反省,減低這種餵食的樂趣。
前年來時,北壽山的步道只有一些地方鋪了木板棧道,架空於地面,讓動物爬行而過,植物能較自由地生長,減少被登山者傷害的機會;
對當地的珊瑚礁環境也更能減低衝擊。
這回來時,木板棧道又擴充了。
在臺北大崙尾山的自然步道,我見過類似的設計。
最新的枕木步道,不僅和地面契合,而且還鋪灑了鵝卵石。
至於,到底哪一種步道適合,恐怕還得視個別的環境去判斷,如果把臺北象山自然步道的石階小徑移到壽山,恐怕就是對珊瑚礁環境的大破壞了。
但是它在臺北的近郊出現時,對環境的衝擊,似乎就減少許多。
天氣頗為炎熱,梅雨季節好像還在南洋旅行,還未回來。
但我已經開始巴望,一如蒟蒻的渴望雨水。
優勢的構樹族群已經結出累累的青色果實。
我隱隱感覺,特有的臺灣鹿角金龜即將從地面羽化出來,快樂地飛上這些甜美的果實。
五月時,不僅鹿角金龜,朽木蟋蟀、大青叩頭蟲,還有一種橙紅色,至今我尚未鑑定出真正屬種的紅叩頭蟲,想必都會出來湊熱鬧。
接著是雄蟬大鳴。
但壽山的時序和季節,可不是我這種過客的旅行者所能一眼望穿的。
套一句流行的廣告,一九九七年,我在巴黎的左岸咖啡館,但不見得我認識了巴黎。
我只是藉由咖啡屋,感覺巴黎的具體存在,自然觀察亦是。
當感覺對時,每一種昆蟲鳥獸都可能帶來這種情感。
在步道上旅行時,我選擇了烏柑、咬人狗、龍船花和蟲屎等,此時較為常見的代表植物,做為繪圖的主要素材。
這些北部不常見的植物,傳遞著多樣的熱帶氣息,在我現階段的自然觀察旅行裡,有著親切的疏離之感。
它們不止是一種植物這樣單純的符號而已,當它青綠盎然地站在那裡時,背後的內容,還潛藏著相當複雜的人文和歷史意義。
我如是這般思索著,且自信而愉悅地面對每一種植物,小心地繪入筆記本裡。
相信長尾南蜥知道這種心境的。
這種有著手臂長,肥胖而巨大的蜥蜴,如巨蛇般吐露舌信,到處鑽探。
每當我久坐時,都會自草叢裡,或珊瑚礁上,露出滑溜的頭,曖昧地凝視,彷彿在質疑我對這個熱帶山區的情愫。
南壽山
在壽山旅行了兩天。
前一天,在北壽山自然步道觀察,隔天便到更接近海岸的南壽山去。
我沿著中山大學校園後面一條隱秘的步道,隨意信步而行。
這條路直通百年前英國的打狗領事館。
一邊走路時,不免想起博物學者郇和(R.Swinnoe)在此任職領事一職時,攀爬壽山的旅行,還有西方旅行家沿路走訪的景觀敘述。
我經過的範圍主要在靠領事館面海的山區。
原來希望看到此地特有的山毛杮,但一路上,多半是血桐、稜果榕和構樹為多。
猜想山毛杮喜歡棲息的環境可能更靠近隱秘的森林吧?
構樹無疑是這兒最為眾多的優勢族群。
寬葉的成熟樹種多半已長出青綠的漿果。
偶爾進入隱秘的林子時,還有盤龍木長出紅鮮的果實。
接近領事館時,長著漂亮紫花的蝶豆和紫紅花朵的珊瑚藤也出現了。
不知當年郇和走的路線是否就是這一條?
甚而,其他外國人也循此路到密林裡去。
我再度於駐英領事館前徘徊,回想當年的自然景觀。
這個地方是臺灣自然觀察和採集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往昔採集者的敘述,經常讓我充滿歷史情感和困惑?
譬如說最早記錄的蝶道吧,郇和當年在此看到的會不會是玉帶鳳蝶呢?
這種鳳蝶依賴的食草烏柑,正是林子裡相當優勢的植物。
還有,為什麼郇和常記錄的老鷹,現在幾乎難得一見。
一九八○年代,我在左營軍港服役,老鷹仍常低空盤旋。
百年來經常活動於此的鳥種,為何在這短短十年就難以記錄了?
再者,大家都熟悉的臺灣獼猴,一直局限在柴山這個地區活動,無法和其他山區的族群交往,會不會發展出不同的個體,或者延伸出某種變化?
海風從海峽徐徐灌進,我遠望著,彷彿看到百年前西方自然探查隊的船隻,繼續在入港、卸貨。
同時,領事館這邊,也有一些在內地採集到的珍稀物品,以及重要的自然科華文件,正在打包準備運回歐洲。
但我的煩惱和疑惑從那時起就末被運走,它繼續附生在這塊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