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docx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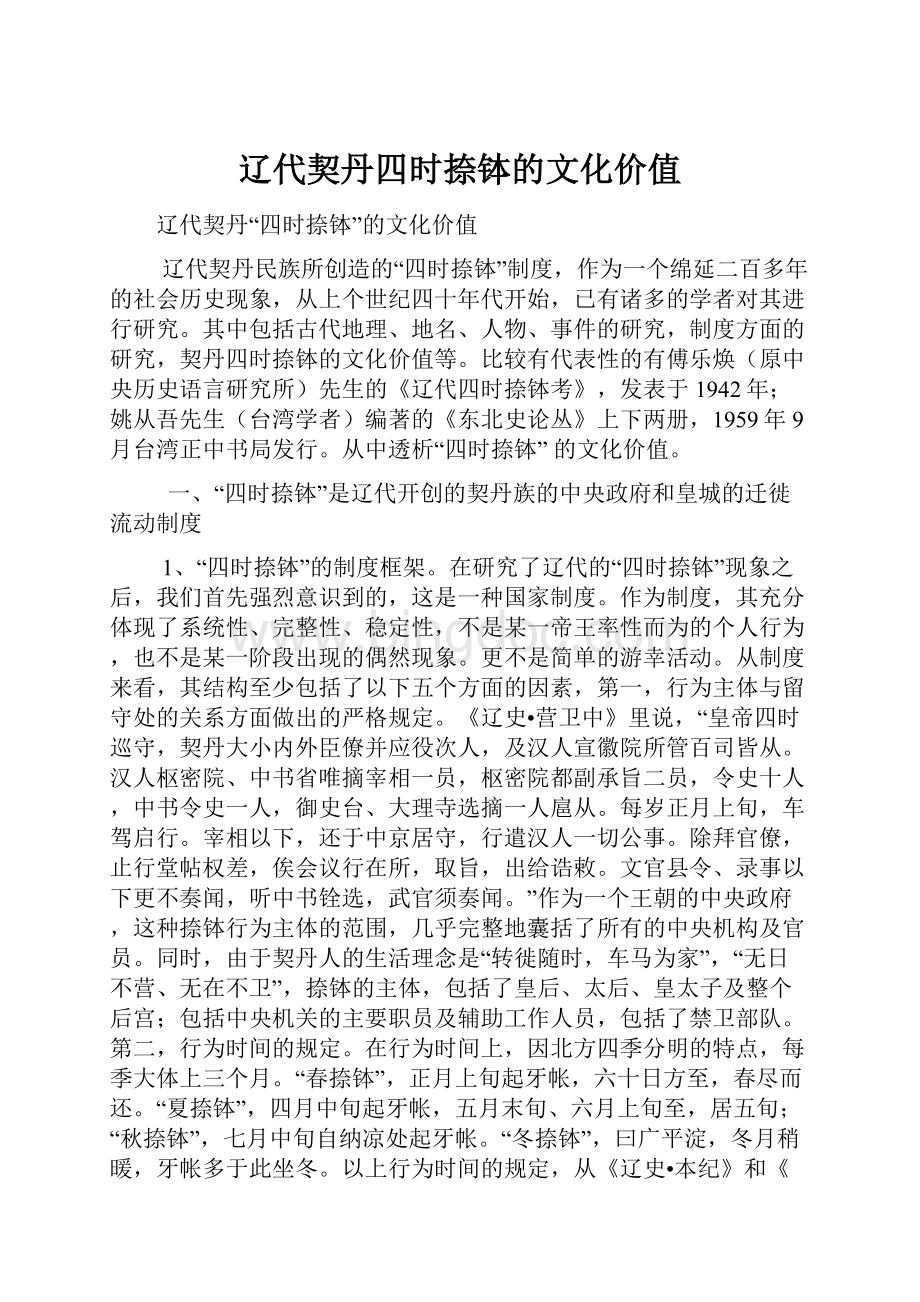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乐焕(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姚从吾先生(台湾学者)编著的《东北史论丛》上下两册,1959年9月台湾正中书局发行。
从中透析“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一、“四时捺钵”是辽代开创的契丹族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迁徙流动制度
1、“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
在研究了辽代的“四时捺钵”现象之后,我们首先强烈意识到的,这是一种国家制度。
作为制度,其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不是某一帝王率性而为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阶段出现的偶然现象。
更不是简单的游幸活动。
从制度来看,其结构至少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行为主体与留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
《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
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
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
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
”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
同时,由于契丹人的生活理念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捺钵的主体,包括了皇后、太后、皇太子及整个后宫;包括中央机关的主要职员及辅助工作人员,包括了禁卫部队。
第二,行为时间的规定。
在行为时间上,因北方四季分明的特点,每季大体上三个月。
“春捺钵”,正月上旬起牙帐,六十日方至,春尽而还。
“夏捺钵”,四月中旬起牙帐,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秋捺钵”,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
“冬捺钵”,曰广平淀,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
以上行为时间的规定,从《辽史•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主要是季节方面的规定,在各月的实际运行中有一定灵活性。
第三,行为内容的规定。
“春捺钵”的钩鱼猎雁,夏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
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
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
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
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
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
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理因素,如冬求暖,夏趋凉。
亦有关活动内容,如春水秋山。
还与治国安邦的其它因素有关。
第五,建筑方面的宏观规划与宫室布局。
这在《辽史•营卫制》中有具体的记载,一些宋使节出使辽和代辽而兴的金初营地,也做了描述,大略相同。
其中侧重在政治、军事、建筑方面做了记述,而于生活方面的皇城服务、保障设施方面仍显欠缺。
2、相关的制度出处。
“四时捺钵”制度,从《辽史》来看,主要出自《营卫制》。
其中,《营卫制》的上、中两部分的导语,集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了阐述,而在《营卫中》里,则对“四时捺钵”制度集中地做了制度概括。
除《营卫制》外,“四时捺钵”制度还反映在《本纪》中。
反映在《本纪》中的,带有对总体制度的完善、补充性质。
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
‘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
“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
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
《本纪》中,还具体地记录了历代辽君捺钵的实况。
在《辽史》以外,与捺钵相关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从《契丹国志》、《辽史拾遗》等史书中找到佐证。
二、“四时捺钵”以政治中心流动为属性。
考察“四时捺钵”的属性,最重要的前提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制度性流动迁徙。
因此,应主要抓住中央政府与皇城及四时流动这两个最主要特征。
1、不变的是中央政府的管理主体地位与皇城保障需求。
换言之,捺钵地转徙和捺钵地驻跸的依然是中央政府,其政治中枢与管理主体地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行政、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职能在捺钵过程中依然正常行使,而这种行使就使得捺钵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属性保持不变,管理者的地位依然保持。
2、处在流动和变换的是季节、地域,与之相关的资源和契丹民族。
驱使这种流动和变化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基础性原因,而使这些散在因素得以整合利用,使之成为捺钵的是契丹的精英,是契丹民族的特色文化。
因而捺钵在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制度化的安排,规划指导下的行为。
是契丹所特有的草原渔猎文化及衍生物。
在上述两点的结合中,主要突出了治国安邦的主题,体现了军事优先,军政、军民结合的特点。
比如讲兵习武的安排,营地的选择、布局、设置,对属国的弹压,由于外患和内叛而被迫中止的捺钵,变更驻跸地的情况等,均属此类。
其中变更驻跸地,一方面是澶渊之盟后的向东北迁徙,备兵主要为女真室韦,而皇帝、中央政府的君临及驻跸地的前移等同于坐镇指挥和亲自督军。
另一方面是每五六年一次的眷顾西南地区,明显带有巡视成分。
还有,就是天祚帝在完颜阿骨打起兵后被迫西迁,也主要出于避乱、避兵的考虑。
其次,是体现了亦官亦民、亦政亦经的特点。
贵为天子的皇帝,亲自捕鱼,亲执弓矢,放飞鹰鹘,一如汉天子春郊播种,对天下人是一种示范,其过程也带有练兵、示武、节庆性质。
再次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这种交流有与宋朝、属国间的情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有驻跸地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军队的交流,而最重要的是承接汉文化、农耕文化的辐射,汉民族城邦文化、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包括服饰、礼仪等方面的交流带动与互动。
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在大的和平环境之下,辽宋之间交往频繁、坦诚,交流主体、项目亦增。
除天子登基、驾崩之外,太后、皇后、皇子也在其例,如贺生辰,索要天子画像等内容;又如宋朝登科的知识分子名录也送契丹,《贞观政要》、《唐太宗、唐明皇实录》,白居易《讽谏集》等也在圣宗读书之列,而且宋朝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在担任和平友好的使者。
如圣宗太平六年宋龙图待制孔道辅使契丹,孔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契丹国志》70页);道宗咸雍是十一年,沈括使辽(《契丹国志》90页);张舜民、苏辙、欧阳修、刘敞等都曾使辽。
三、“四时捺钵”的主客观条件
“四时捺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基础和背景。
而应运而生的“四时捺钵”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精华。
1、基于北方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契丹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契丹所处的北方,较之宋朝所处南方,以及辽帝所辖汉族农耕区(《辽史》中谓“汉城”)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所谓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较少。
由于开发晚,人口稀少,多为草原,整体上属于植根于草原文化的渔猎文化。
与之相适应的,是契丹族内部社会结构还没有进入农耕阶段,游牧部落为主要治理结构。
这种情况在辽初尤为明显。
从太祖开始,所经略、并兼的主要是南方的汉人辖区,以俘掠汉人,兴建汉城,采农耕制度等方式来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内部统治和边防,而战争频仍,俘户迁民,斩杀无辜等行为又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辽史•兵卫上》导语部分,把契丹的兴起,人口的俘获,不从者的斩杀,攻城掠州的过程做了很好的、很全面的记述。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迟滞。
渔猎文化,从根本上是取之于自然的原生态经济结构,其利在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小,尤其是带有休养生息、轮作轮牧性质的捺钵,所体现的是有限、顺势、因时索取资源,但从负面来看,资源的加工、流通方面利用率低,生活资料的积累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压扁了文明进步的阶梯。
在这种情况下,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纵马于野,弛兵于民等,都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局限,也在客观上使得渔猎文化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保存下来。
而南北分治的契丹治理文化,又使得北方契丹渔猎经济结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从契丹民族社会进步自身发展逻辑看,文明的进步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到了圣宗一代,即契丹中叶,才可以发生对汉文化的心仪、仰慕和接受(见《契丹国志•圣宗纪》)。
到了圣宗时,才出现“禁诸屯田不得擅贷官票”等由军队耕种土地,支持战争,赈济灾民的记载(《辽史•圣宗纪》)。
到了兴宗重熙五年十月,才出现“御试进士自此始”等汉化的过程。
所以,从一定意义看,对于契丹人而言,由渔猎文化及氏族部落式管理,到农耕文化及封建式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2、“澶渊之盟”的签订。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捺钵出现了三个方面变化,或是为春捺钵发生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提供了外部环境。
第一,“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契丹政权在南方换来了相对安定的疆域,使得契丹帝王的捺钵地由漂泊不定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
“澶渊之盟”的签订,为辽宋两地的经济恢复,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喘息的机会,而捺钵就会在更为从容的外部环境中进行。
从《辽史•兵卫》中可知,辽国的兵制,一则全民皆兵。
而全民从兵事,在战争状态下,就使得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壮年不能依天时而从事农耕。
二则所有战争的负担几乎都摊到每一百姓身上。
而且战争的负担很重,殃及百姓和无辜。
如每一兵须配三匹马、两丁、甲胄九件,弓四,矢四百,以及各种兵器和军需物资,皆须自备。
而马草马料靠“四出抄掠以供之”。
在这样的兵役制度下,如果有战事,则无经济可言。
第三,“澶渊之盟”之后的捺钵,几乎所有四季的捺钵地,同时又是宋史觐见契丹君主的地方,这在客观上使捺钵地成为交流交往的平台和圣地。
3、契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关于《辽史》在哲学角度解释四时捺钵方面的贡献,很多专家都多有佳誉。
姚从吾先生认为《辽史》这方面有“很可喜的说明,而且保持了契丹人的立场”(见《东北史论丛》“契丹捺钵文化的由来”)。
那么。
什么是契丹人的立场呢?
一是因地制宜说。
《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
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
”这里所说的“三才”,当指天地人。
《周易•系辞下》: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
兼顾三才之间的关系而合理的结合,实际上就是要照顾到人的需求与经济地理条件,与资源条件,与气候节气等自然条件的结合。
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如今的环境理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具有共同之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精妙的依据天时地利实施王者治理之说,在史家看来,都是源于亘古的中原文化传统。
如《辽史•营卫中》,援引史书典籍为依据:
“《周官》土圭之法,日东,景朝多风;日北,景长多寒。
”再如《辽史•兵卫》上中,还援引上古圣贤的实践为解说:
“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
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暨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于兵卫,地势然耳。
”《辽史》的许多史论都以中华文化传统为自己民族创造的参照,而且都突出了因时、因地制宜的思想,使自己的创新找到了渊源,从而增强了说服力。
如《食货志》、《兵卫制》、《营卫制》、《游幸表》、《百官》、《地理志》等开篇都做了开宗明义的解说,《后妃传》也在结尾部分做了阐述。
而在如今看来,我们所能够从中发现的,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统与一脉相承。
二是合理地利用自然。
《辽史•营卫中》:
“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契丹民族是北方草原游走的少数民族部落。
“转徙随时”,所体现的是顺应由季节所决定的资源条件,这正是三才中的“有地道焉”,是经济地理的基本原理。
而“车马为家”,则体现出人口流动的主动性。
关于“车马为家”,《东北史考略》中引宋彭大雅、徐霆的描写“牛马骆驼以挽其车。
车上可坐卧,谓之帐舆。
”这是南宋使臣到元太宗窝阔时的描写。
“车马为家”,还包括财富必须转化为可以便于携带的浮财(这种转化,在客观上自然地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和交换过程,则直接促进了渔猎经济的瓦解),使整个辽代的财富,集中到皇家和中央财政、中央机关部分,完全集于车马之上。
所以车马为家,逍遥自在地游走生活,消磨时光,旅途的劳顿也就冲淡了许多。
三是兵民一体。
《辽史•食货志》中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
音洞,乳汁),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是以制胜,所向无前”。
这段话中,把草原,战马,契丹兵,与克敌制胜穿成一个链条,体现了对草原的依赖和敬畏,与汉民族耕战结合的思想如出一辙,其中还蕴含着以草原养马、以民济兵这些辩证思想。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鱼为生”(见《辽史•营卫制》),则是这种思想的深化。
而作为“有事”与“闲暇”的过渡又显得那样自然,四是组织化与半军事化。
《辽史•营卫制》中说:
“有辽始大,设制尤密。
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这里所强调的崇尚军事,重视防务,依靠组织化和严明的纪律,构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和中央机关。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捺钵的营地,既是办公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更是军事基地。
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自然会具有超于寻常的战斗力和竞争力。
四、独创性及影响
应当说,逐水草而居,以至于兵民结合、平战结合,甚至于官兵一致这样的作法和思想,是草原文化的共同特点。
“四时捺钵”的创新创造与特色在于,契丹人把这一作法上升到为国家形态,上升为皇家制度,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一以贯之,在外有宋朝,内有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仍得以保留。
其创新意义还在于,“四时捺钵”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始于辽,在有辽一代得以理论化、系统化、法制化,这是空前的,也是辽之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出其右的,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所能达到的高度。
捺钵文化在其掘墓人的金代,后来的元代,清代等,都有其影子(见傅乐焕先生《辽史丛考•辽代四时捺钵考》)。
辽捺钵制度的影响,主要及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基于北方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基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基于北方广袤的草原和众多的水资源。
而捺钵精神的习习相因,不仅源源不断地位北方少数民族提供活力,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创造动力,还使得北方的资源得以一代又一代地相对完好的传承给中华的子孙。
但捺钵制度在金元清的影响,主要是其文化的精髓而非制度的全部,因为随着农耕文化的影响,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促进了渔猎制度的瓦解。
而金元清对中原文化的消化吸收,尤其是对南方用兵,甚至是试图统一中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一步一步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
所以,捺钵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于其在流动中实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流动中实现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流动中促进各民族的竞争与融合,而不在于四时捺钵的制度、形式和内容本身是否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