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阅读109之一总11671人间有味是清鲜2茶与茶书档.docx
《星期六阅读109之一总11671人间有味是清鲜2茶与茶书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星期六阅读109之一总11671人间有味是清鲜2茶与茶书档.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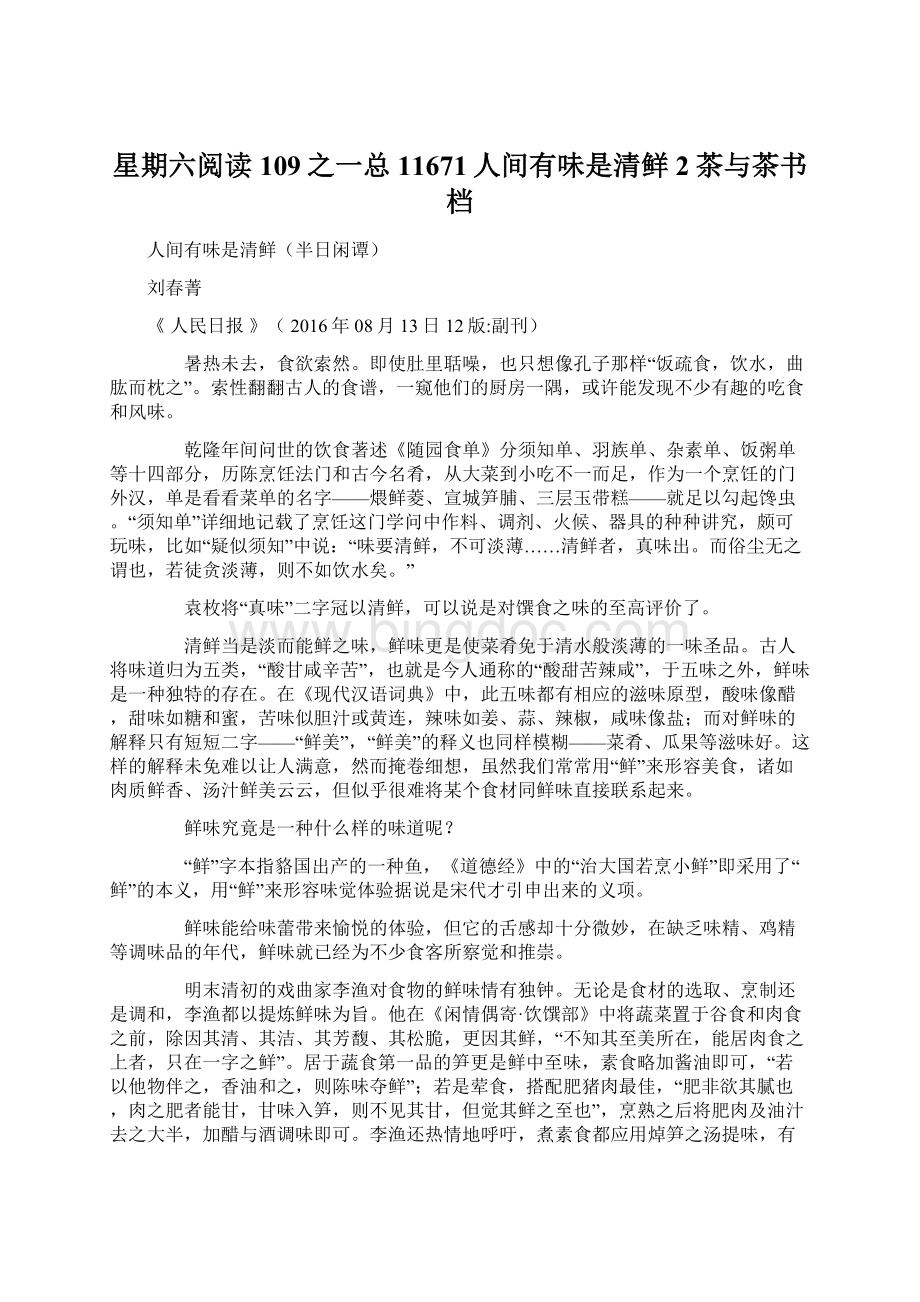
星期六阅读109之一总11671人间有味是清鲜2茶与茶书档
人间有味是清鲜(半日闲谭)
刘春菁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3日12版:
副刊)
暑热未去,食欲索然。
即使肚里聒噪,也只想像孔子那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索性翻翻古人的食谱,一窥他们的厨房一隅,或许能发现不少有趣的吃食和风味。
乾隆年间问世的饮食著述《随园食单》分须知单、羽族单、杂素单、饭粥单等十四部分,历陈烹饪法门和古今名肴,从大菜到小吃不一而足,作为一个烹饪的门外汉,单是看看菜单的名字——煨鲜菱、宣城笋脯、三层玉带糕——就足以勾起馋虫。
“须知单”详细地记载了烹饪这门学问中作料、调剂、火候、器具的种种讲究,颇可玩味,比如“疑似须知”中说:
“味要清鲜,不可淡薄……清鲜者,真味出。
而俗尘无之谓也,若徒贪淡薄,则不如饮水矣。
”
袁枚将“真味”二字冠以清鲜,可以说是对馔食之味的至高评价了。
清鲜当是淡而能鲜之味,鲜味更是使菜肴免于清水般淡薄的一味圣品。
古人将味道归为五类,“酸甘咸辛苦”,也就是今人通称的“酸甜苦辣咸”,于五味之外,鲜味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此五味都有相应的滋味原型,酸味像醋,甜味如糖和蜜,苦味似胆汁或黄连,辣味如姜、蒜、辣椒,咸味像盐;而对鲜味的解释只有短短二字——“鲜美”,“鲜美”的释义也同样模糊——菜肴、瓜果等滋味好。
这样的解释未免难以让人满意,然而掩卷细想,虽然我们常常用“鲜”来形容美食,诸如肉质鲜香、汤汁鲜美云云,但似乎很难将某个食材同鲜味直接联系起来。
鲜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鲜”字本指貉国出产的一种鱼,《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即采用了“鲜”的本义,用“鲜”来形容味觉体验据说是宋代才引申出来的义项。
鲜味能给味蕾带来愉悦的体验,但它的舌感却十分微妙,在缺乏味精、鸡精等调味品的年代,鲜味就已经为不少食客所察觉和推崇。
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对食物的鲜味情有独钟。
无论是食材的选取、烹制还是调和,李渔都以提炼鲜味为旨。
他在《闲情偶寄·饮馔部》中将蔬菜置于谷食和肉食之前,除因其清、其洁、其芳馥、其松脆,更因其鲜,“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之鲜”。
居于蔬食第一品的笋更是鲜中至味,素食略加酱油即可,“若以他物伴之,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若是荤食,搭配肥猪肉最佳,“肥非欲其腻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其鲜之至也”,烹熟之后将肥肉及油汁去之大半,加醋与酒调味即可。
李渔还热情地呼吁,煮素食都应用焯笋之汤提味,有此则诸味皆鲜;烹荤菜则首选虾汁,“以焯虾之汤,和入诸品,则物物皆鲜,亦犹笋汤之利于群蔬”。
在李渔的饮食哲学中,笋汤和虾汁仿佛已经具有了现代调味品的功能。
保证肉质的鲜美也是烹制鱼类的关键。
待客时,其他菜肴都可以提前备好,而鱼必须活养,待客人来后再行烹煮。
“鱼之至味在鲜,而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
若先烹以待,是使鱼之至美,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待客至而再经火气,犹冷饭之复炊,残酒之再热,有其形而无其质矣。
”
从舌尖到笔尖,李渔对鲜味的感知和追求一以贯之,充分展现出一位美食家的自我修养,其中想必也浸润着他的生活态度。
实际上,具有崇自然、尚鲜味的饮食品位的李渔,在当时可算是一股清流。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物产极大地丰盈,耽于饮食、奢侈铺张的风气盛行。
《五杂俎》中记载当时的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可谓水陆珍品毕陈,四方风物齐聚。
为满足口腹之欲,一宴杀物千余,一羹费至二万,日用鲫鱼三百之事比比皆是。
市民百姓深受此风浸淫,“宴会馈遗,民间张设,务崇多品,有山珍海错,蔬蔌多则二十品、十二品,少则八品”。
当时已有文士认识到无论从保本味的角度还是养生的角度,食之至味皆为淡,陆树声有言:
“都下庖制食物,凡鹅鸭鸡豕,类用料物炮炙,气味辛浓,已失本然之味。
夫五味主淡,淡则味真。
”陈继儒也说:
“日常所养,一赖五味,若过多偏胜,则五脏偏重,不唯不得养,且以伐矣。
试以真味尝之,如五谷,如菽麦,如瓜果,味皆淡,此可见天地养人之本意,至味皆在淡中。
”
想来,古人所说的“淡”应当不是索然无味的寡淡之感,而是有“鲜”的兴味在,好比作文,清新淡雅的文风中那一抹韵致最是动人。
“鲜”或许就是蕴含在食材的天然性状与本真质感中的韵味,难以言明却真实可感,轻抚味蕾,留下余韵悠长。
一笋一蕈、一虾一蟹本身就含有鲜味,只是其舌感接近于淡,不似酸味浓烈,也不及甜味馥郁,极易被忽略罢了。
因此,后天的烹调馔制不是为了破坏食材的天然之性,而恰恰是为了将其激发出来。
“淡而不失其味”便是“清鲜”,足可使食客余味绕舌、齿颊留香。
遍尝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方知人间有味是清鲜。
老来多交忘年友
柳萌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3日12版)
京城朋友聚会,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分职位高低,不看名气大小,均按长幼就座。
有次同席朋友中,有三位部级干部,还有几位文坛名家,论年龄数了数,主座竟然非我莫属。
就位如坐针毡,着实忐忑不安。
原来身居主位滋味并不好受,暗自感叹起来,这岁月连招呼都不打,就匆匆撞开耄耋大门。
不禁疑疑惑惑问自己:
我真的老了吗?
唉,真应了那句老话:
“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
”十多年前还能爬上十层楼,三年前还能步行三小时,两年前还曾一步跨俩台阶,怎么现在就倚杖而行了呢?
人呐,说老就老,毫无商量,你就得认。
是时光拖老的吗?
是生活催老的吗?
是磨难磨老的吗?
说不清。
反正是真的老了,不然,那主座位岂能轮到我坐?
那么,老了为何不觉老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有多位忘年朋友,有的五六十岁,有的三四十岁,正是人生好年华。
他们志向高远,神清气爽,无不透着蓬勃朝气。
跟他们相交相处,如同最佳天然补品,滋养着我枯老心灵。
来解闷儿读诗词,最喜欢苏轼这两句诗: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
”似乎高度概括我一生。
年轻时摊上政治运动,最好年月都毁弃了,简直比食蓼还苦涩。
跟我年龄相仿的人,生活经历大致相同,到一起难免说往事,这勾起来的痛苦,常常弄得人寝食不安。
我就闹不明白,都活到这把岁数,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何必再用往事折腾自己呢?
就是过去平顺的同龄人,现在的烦恼也是成堆数,疾病缠身、儿女不孝、下级不理、工资太少、世风不正、官贪商奸,如此等等,絮絮叨叨数落起来,听了让人心烦意乱。
其实这些烦恼谁没有呵?
问题是说了只求嘴快活,既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改变社会,只能让自己烦上加烦。
何必呢?
所以更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当然,说说也许心里痛快,只是千万不可伤心,把自己伤个好歹犯不着。
苏诗说的“老景清闲如啖蔗”,只是相对而言,老来仍然会有烦恼事。
比之自己过去,比之年轻朋友,老来还算省心、轻松,只要物质欲望不高,只要心里不搁闲事,日子就会过得安逸。
即使不像吃甘蔗那样甜,起码也不会感到忧愁,常言说的“知足常乐”,老年人应该容易做到。
人到老年应该学会,一不要争强好胜不服老,二不要强打精神不服输,这是两根铁丝绳子,缠绕上就会伤害老腿脚,让你天天受痛苦遭折磨,哪里还有颐养天年的幸福。
我之所以喜欢忘年交,看重的就是年轻人身上,那股清爽利索劲儿——没有太多抱怨,没有太多忧虑,洒洒脱脱地活在当下。
工作不顺心就跳槽,薪金给的少就走人,绝不把苦恼留在心里。
比之现在的职业青年,我们工薪层老年人,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只要自己不跟自己过不去,还有什么烦事在心头呢?
能吃能睡就是福气,少病少灾就是运气,忘仇弃怨就是和气,钱多钱少都要神气。
谁能如此谁就能拥有快乐,活脱脱一个人间老神仙。
说到结交忘年友,还有一个好处,年轻人不搬弄是非,不计较别人如何看待,在自己营造的自在世界,快快乐乐舒舒服服轻松地活,喜欢的事尽心竭力地做,合不来的人远远地躲,绝不活在别人嘴巴里视野中。
若真有什么烦恼事了,拉上哥们儿姐们儿,咖啡厅聊聊,歌厅里唱唱,回去睡个沉沉的大觉,醒来又是鸟语花香四月天。
被这样氛围感染着,自然而然心态纯净,仿佛自己还未真老。
再有就是年轻人不世故。
心不烦身不累神不劳,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哪有不快活的道理。
忘年朋友多,断不了应酬,只要无雾霾,无论距家多远,打车也要赴约。
有时一顿饭钱,还没有车钱多,有朋友不理解。
我说:
“钱再多能买来快乐吗?
”这就是我的生活经济学。
故此打油一首自嘲:
谁言暮年多寂寞,老来结交忘年友;无忧无虑度日月,天南地北随君走。
宗璞的南东西北
李冰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3日12版)
这个文题看起来有些“玄虚”。
何谓“南东西北”?
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
宗璞是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本名冯钟璞。
宗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其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
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
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
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等。
那年春节,我去给宗璞拜年。
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
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
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
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
宗璞不尚“家长里短”的闲聊,我与宗璞自然谈起她的《野葫芦引》。
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
抗战爆发后,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
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丰厚的生活基础。
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读宗璞的文字如读《红楼梦》,语言优雅蕴藉,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文趣,一种独特的风格。
说起来,宗璞的创作着实不易。
在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
她曾有感而作了首散曲: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
兵戈沸处同国忧。
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
悠悠!
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的女儿冯珏给我来电话,说“妈妈住院了。
”我赶忙去探望。
宗璞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
在问候中得知,最近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
是呀,《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都已面世,只剩最后一部《北归记》尚未完成,她着急呀。
我劝她不要太拼了。
她说:
“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
”我说:
“从长计议吧,现在少写点儿,是为了以后多写点儿。
”听这话,宗璞笑了,我也笑了。
我的笑是自己班门弄斧,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在大哲学家的女儿面前“卖弄”起哲理来了。
后来,宗璞在用药问题上遇到困难,我又和铁凝主席一起去找医院商量,请求给予照顾。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
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
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在格子里爬起来,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
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
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
她的回答很简单:
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又是一年春节,我又去给宗璞拜年。
这时她已经搬离住了六十年的“三松堂”老宅,住到昌平的一个新建小区。
宗璞告诉我,老宅已交给北京大学,作为“冯友兰故居”,准备修缮后供人参观。
宗璞坐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我,是在努力辨认。
我知其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零点三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
我挪过去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向她问安。
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
她说:
“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
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
”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部是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的。
看着她慈祥的面容和面前茶几上摆着的放大镜,不由心生敬意。
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在写小说。
与那些被市场牵引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草率急就文字相比较,一个如同陈酿的美酒、一个如同勾兑的汽水,文野高低自见分明。
面对宗璞,我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双目失明,身体瘫痪,却在病床上历时三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还想起了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病魔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她却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十四本著作,其中自传体的《我的人生故事》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的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史铁生是一个,还可以举出若干其他作家。
宗璞曾说过:
“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
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
”她还表示:
“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
书卷乃祛浮妙物
中国军网国防部网
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第07版:
迷彩书屋■张顺亮
曾有出版社进行过一项“死活读不下去的图书”的网络调查,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等中外名著悉数上榜。
这样的调查难免偏颇甚至沦为噱头,但被誉为“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经典名著,缘何遭受如此冷遇甚至被戏谑调侃呢?
原因很简单,不过“浮躁”二字使然。
心浮气躁是现代人的通病,“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静不下心,沉不住气,稳不住神,“口袋鼓鼓,六神无主;身体棒棒,东张西望”便是生动写照。
作家穆涛在《坐船和吃饭》里写到:
“读书如坐船,一种是游船,一种是渡船。
”而浮躁让读者登上的是“游船”,随处走走,随便看看,随意转转,狗熊掰棒子,舟过水无痕,是走过路过、打酱油的。
“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
过去,读书人敬惜字纸、爱书如命,秉烛夜读、凿壁偷光,一本好书常常数人传抄,那种“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的读书意境真是如梦如幻。
如今,数字化、网络化让阅读变得触手可及,足不出户便可坐拥书城。
但是,“互联网太好了,好到有点坏”,一部智能手机把我们的时间分割得七零八落,每天五彩斑斓、鱼目混珠的信息让我们无所适从、无力选择。
不妨看看四周,“有wifi吗?
”“密码是多少?
”“送流量吗?
”成为日常用语,“扫一扫”“摇一摇”“晒一晒”成为常用动作,“转疯了”“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成为高频词汇,“低头族”“手机控”“自拍党”成为人的行为常态。
于是,有的人3分钟不看手机便心神不宁,5分钟不刷微博便人心惶惶,10分钟不看朋友圈便坐立不安;长篇大论不受待见,“微言大义”充斥屏幕;转发代替了阅读,浏览代替了伏案,点赞代替了热议,XX代替了查书,收藏代替了购买,硬盘代替了大脑……
费尔巴哈说,人是他自己食物的产物。
粮食强壮人的肉体,书籍塑造人的精神。
阅读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
试想,如果在咖啡厅里点了一杯拿铁,但每次都只是把上面的奶沫给吃了,下面的咖啡却没有动,将是何等的讽刺!
军营是社会的一部分,军人也不可避免地被数字化卷入浅阅读的大潮,跌入微阅读的泥淖,陷入轻阅读的窘境,挤压了官兵读书的时间,分散了读书的精力,动摇了读书的信念,影响之剧,负面作用之大,值得警惕。
清代被赞为有“古大臣之风”的张英有句名言:
“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
”自古至今,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读有所得,必是心有所悟。
书籍是精神苦旅者的港湾,亦是心灵焦躁者的安处。
因而,宋代大儒朱熹说:
“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
”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应该有诗和远方”。
阅读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远离喧嚣、追寻灵境,可以看见无知和愚钝的自己,触碰到最深处生锈的灵魂,酣畅处犹如鱼入大海,畅快、惬意、美妙,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穷其一生,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心无旁骛似明镜,无风何处起涟漪?
夜已深,人未寐,一杯香茗,一部经典,心灵没有负载,涉猎止于索取,遇见高人的睿智,揣摩智者的洞见,感受著者的匠心,细品世道的冷暖。
此时此刻,繁华散尽,月上西楼,捧读的你仿若空谷幽兰、兀自芳菲,人在天涯外,心在咫尺间,庸常琐烦不能摇曳你,世俗扰攘不能裹挟你,自己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部厚重而经典的传奇大书呢?
茶与茶书
2016-08-13作者:
杨扬来源:
文汇报
盛夏来临,守在家里,喝清茶,看茶书。
有朋友打来电话问,喝茶就是喝茶,要看那么多茶书干什么?
想想也是,书案前又是书,又是茶,本来不大的地方,推来搡去,手忙脚乱,弄不好茶杯倒翻,不仅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清福,反而弄得一团糟。
不过,茶书犹如神助,有茶书和没茶书,究竟是感觉不一样;看过和没看过,更是不一样。
古往今来,喝茶的很多,懂茶的也不少,但能够将喝茶、品茶的经验凝结成文字,而这文字翻来覆去,又能敷衍成章,流传于世的,可谓少之又少。
茶书中,真正称得上经的,当然要数陆羽的 《茶经》。
陆羽之前的一千年,人们已经开始喝茶了。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但专家考证,九经之中,无茶字。
中国人的饮茶之风,起于战国和秦汉时期。
但那时的喝茶,在今天看来,有些匪夷所思。
茶叶煮熟之后,放些盐等佐料,和汤而食。
那情形,与喝菜汤差不多。
从喝茶之风的兴起,到陆羽 《茶经》 的诞生,这中间不知道产生过多少奇奇怪怪的喝茶方式。
有些人是宁愿喝酒,也不愿喝茶,因为喝茶与吃菜差不多,而且又苦又涩,真是活受罪。
一个专门形容喝茶为苦事的名词是“水厄”。
所以,苏东坡说“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
”《茶经》 问世之后,混乱的局面为之改观,很少再有人抱怨说喝茶是水厄。
此后的一千多年,正本清源,中国人的喝茶方式,虽经历了煎茶,抹茶乃至泡茶的变迁;也不断有文人墨客、风雅人士续写、补写和编写茶书,但也只是续写、补写和编写而已。
各种借题发挥的茶录、茶论、茶谱,不乏奇思妙想,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茶经》 的地位。
2010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收有中唐至清末的114种茶书。
以经为名的,只有陆羽的 《茶经》。
2015年出版的 《中国茶书全集校证》,下限放宽到民国初年,收有101种茶书,其中陆羽 《茶经》的正统地位,没有丝毫改变。
文物出版社即将出版的50册 《中国茶文献集成》,想来也将延续以往的茶文化传统。
茶书作为典籍的一种,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看看中国的历朝历代,茶书的兴盛,与文化的兴盛,应该是同步的。
上世纪80年代,陆定一在给吴觉农先生主编的 《茶经述评》 写序时,满怀希望能够看到20世纪的新茶经。
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过一部新编的 《中国茶经》,但是不是陆羽 《茶经》 意义上的新茶经,没人敢说。
30年过去了,喝茶的风气似乎越来越盛,喝茶的讲究程度也越来越高,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均居全球第一,其中茶叶出口量32.3万吨,名列世界第二。
喝茶需要茶书吗?
需要的。
这不仅是经验总结,也具有指导作用。
不妨讲讲我自己的体会。
今年5、6月间,去福州、苏州和常州,那都是有好茶的地方,季节也是春茶收获的时节。
在福州,去一所大学的茶艺实践基地。
那店老板听说我喜欢铁观音,就对我直言,现在我们福州人喜欢喝岩茶啦,岩茶不伤胃。
我不拒绝岩茶,但店商的话不太相信。
在那里工作的学生为我考虑,专门从茶叶基地选送来新炒的铁观音。
临别时,一再嘱咐,茶叶要放冰箱冷藏。
没几天,我去苏州开会,晚上进了苏州大学对面的一家台湾人开的茶叶店。
老板闲来无事,与我神聊,一边泡茶,一边告诉我他的喝茶心得。
其中有铁观音、乌龙茶放在紫砂茶叶罐里,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他见我面露疑问,就取出自己的所藏,专门挑了几种,当场沏泡,让我品尝。
的确,常温保存的铁观音、乌龙茶,茶味不失,十分纯正。
后来遇到一位苏州朋友,向我推荐碧螺春红茶。
碧螺春绿茶倒是每年都喝,但碧螺春红茶从来没有尝过。
茶商在西山,晚上过不来,让我回沪后等快递。
他特地关照,常温下放着,现在不要喝,等秋天再用。
回上海后,收到一包茶叶。
去了塑料外包装,连纸袋一起,动也不敢动,就照他的吩咐,常温下放着,等秋天再喝吧。
但我心里一直打鼓,会不会将一包好茶就这么糟蹋掉了?
6月到常州,去一位朋友的私人博物馆看他的紫砂壶收藏,随后喝茶。
茶是他家里的帮手泡的。
一上口,我说是宜红啊。
主人也喝了一口,回答说是宜红。
不过,他马上皱起了眉头说,这茶放久了,不能喝,换掉。
主人自己跑去里间取来新茶,重新沏泡。
有前后宜红的对照,新沏的宜红,的确味甘而醇香,别有一种甜美新鲜的滋味。
临到告辞时,主人送我两盒宜红,特别关照,这是有机茶厂定制的上好红茶,明前宜红。
我就问,是不是要常温保存?
他说不行,必须放冰箱,否则,几天一过,茶叶就没用了。
我知道绿茶的储藏一定要放冰箱,而且一般都是一年为限期。
新茶出来,前一年的绿茶基本就没用了。
但我也有意外的体验。
有一次清理冰箱,发现三年前的一盒温州三杯香绿茶忘记在冷冻柜里。
看看还没有拆过封,丢掉太可惜,于是,拆封泡了一杯尝尝。
茶水入口,那种清香,如陈年的美酒所有,几乎是贴着舌根一直往上窜,挡都挡不住。
陈年的绿茶,还有如此香味,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过了两天,拿来再泡,发现放在常温下的这盒绿茶已经不能用了,茶汤发黄,味道也变了,像一朵枯萎的花朵,神气全无。
所以,茶叶的藏与不藏;藏于常温下和冷冻室,真是大有讲究。
从实用的角度,茶书是可以给人以指导的。
茶书有实用的一面,茶书还有更高远的境界与格调。
回味一下读茶书的感受,最大的快乐,是作者别开生面的个人体会和绵绵不绝于耳的细声叙述。
茶书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小叙事,哪怕是帝王将相,一旦落笔,想对喝茶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时,朕啊臣的那一套,全都落幕,剩下的是有关汤汤水水、树木草叶和坛坛罐罐所引发的无边遐思。
大宋皇帝赵佶在《大观茶论》 中,谈及本朝的龙团凤饼,言语间充满了自豪,仿佛窥见了草木之灵,因而“啜英咀华”、“研究精微”,急于将自己的“所得之妙”,分享给天下同好。
明代的宁献王朱权,在经历了“靖难之役”后,以茶道为悟化对象,倡导茶道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
茶,在朱权眼中,不仅仅是游心于茶灶之间,而是“有裨益于修养之道”,它“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眼前这普普通通的一片茶叶,竟然有那么了不起的功用,他不能不感叹“茶之功大矣!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神奇饮品,但有哪一种饮品可以像茶那样引发如此多的形而上思考呢?
为什么茶会触发人们对道的追问与遐想呢?
或许,喝茶者的身份角色与茶和茶书之间有特殊的关联。
在古代,茶不是人人都能喝到的,至于名贵的好茶,更是一种奢侈品。
能够喝到好茶,又能够写茶书的,当然不是一般人士。
《三国志》 中,吴国国君孙皓,特别器重大臣韦曜,“密赐茶荈以代酒”。
茶,成为皇上礼待大臣的物品。
唐代的湖州紫笋茶,更是宫廷专供。
每年春天采茶,役工达三万人。
这一点点紫笋茶,普天之下,有多少人能品尝到呢?
那些有缘喝到神品者,又有几个人会想到茶与道的关系呢?
只有那些真正热爱茶,痴迷于茶,对茶有独到理解的问道者,才有可能由茶悟道,由一片绿叶,扩展到天地人生的玄思,在文字的书写中,体悟茶与天地人的关系,为后世来者,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录。
所以,每当翻阅茶书时,我总想知道前辈先贤中,都是什么人在写茶书。
有专家曾对114种古代茶书的作者进行统计,发现其中72部茶书的作者,籍贯是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其次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占22部。
河北、陕西、山西、山东占四部,但这四部茶书作者,虽是北人,但都长期出仕南方茶区。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