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绝句.docx
《夏之绝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夏之绝句.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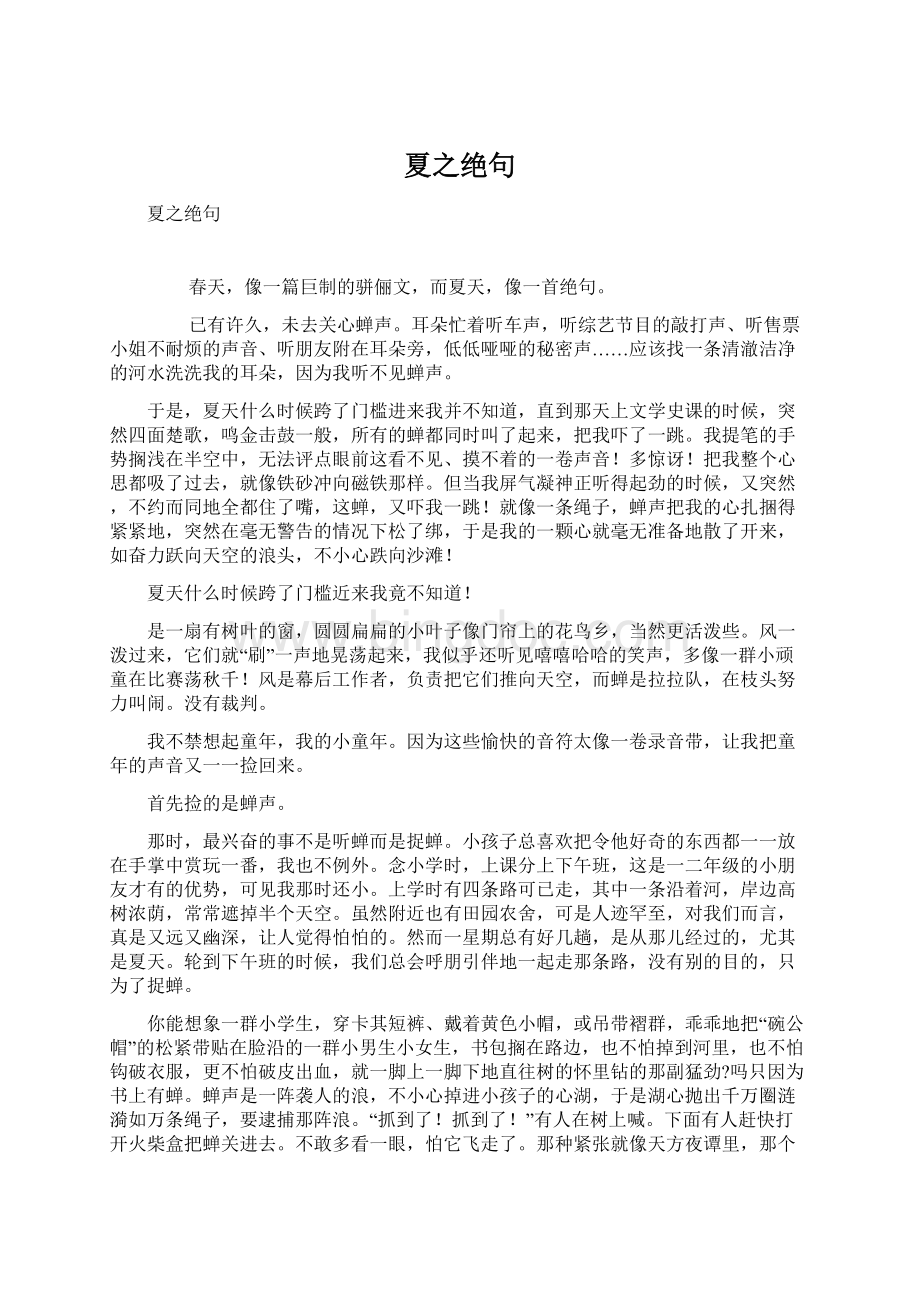
夏之绝句
夏之绝句
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
已有许久,未去关心蝉声。
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附在耳朵旁,低低哑哑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
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半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卷声音!
多惊讶!
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
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地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
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地,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
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近来我竟不知道!
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乡,当然更活泼些。
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刷”一声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
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
没有裁判。
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小童年。
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首先捡的是蝉声。
那时,最兴奋的事不是听蝉而是捉蝉。
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手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
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势,可见我那时还小。
上学时有四条路可已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
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
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几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
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
你能想象一群小学生,穿卡其短裤、戴着黄色小帽,或吊带褶群,乖乖地把“碗公帽”的松紧带贴在脸沿的一群小男生小女生,书包搁在路边,也不怕掉到河里,也不怕钩破衣服,更不怕破皮出血,就一脚上一脚下地直往树的怀里钻的那副猛劲?
吗只因为书上有蝉。
蝉声是一阵袭人的浪,不小心掉进小孩子的心湖,于是湖心抛出千万圈涟漪如万条绳子,要逮捕那阵浪。
“抓到了!
抓到了!
”有人在树上喊。
下面有人赶快打开火柴盒把蝉关进去。
不敢多看一眼,怕它飞走了。
那种紧张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个渔夫用计把巨魔骗进古坛之后,赶忙封好符咒再不敢去碰它一般。
可是,那轻纱般的薄翼却已在小孩们的两颗太阳中,留下了一季的闪烁。
到了教室,大家互相炫耀铅笔盒里的小动物——蝉、天牛、金龟子。
有的用蝉换条牛,有的用金龟子换蝉。
大家互相交换也互相赠送,有的乞求几片叶子,喂他铅笔盒或火柴盒里的小宝贝。
那时候打开铅笔盒就像打开保险柜一般小心,心里痒痒的时候,也只敢凑一只眼睛看一个小缝去瞄几眼。
上课的时候,老师在前面呱啦呱啦地讲,我们两眼瞪着前面,两只手却在抽屉里翻玩着“聚宝盆”,耳朵专心地听着金龟子在笔盒里拍翅的声音,愈听愈心花怒放,禁不住开个缝,把指头伸进去按一按金龟子,叫它安静些,或是摸一摸敛着翅的蝉,也拉一拉天牛的一对长角,看是不是又多长了一节?
不过,偶尔不小心,会被天牛咬了一口,他大概颇不喜欢那长长扁扁被戳得满是小洞的铅笔盒吧!
整个夏季,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强迫蝉从枝头搬家到铅笔盒来,但是铅笔盒却从来不会变成音乐盒,蝉依旧在河边高高的树上叫。
整个夏季,蝉声也没少了中音或低音,依旧是完美无缺的和音。
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声。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响,蛙声、鸟鸣、及蝉唱。
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
蝉是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司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它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
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诗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达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它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它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
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
晨间听蝉,想其高洁。
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
高踞树梢,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
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轻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
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
蝉亦是禅。
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
像一群吟游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它们的脚。
拉拉杂杂地,他们谈天探询、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压韵。
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
我喜欢一面听蝉一面散步,在黄昏。
走进蝉声的世界里,正如欣赏一场音乐演唱会一般,如果懂得去听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抱怨世界愈来愈丑了,现代文明的噪音太多了;其实在一滩浊流之中,何尝没有一潭清泉?
在机器声交织的音图里,也有所谓的“天籁”。
我们只是太忙罢了,忙得与美的事物擦身而过都不知不觉。
也太专著于自己,生活的镜头只摄取自我喜怒哀乐的大特写,其他种种,都是一派模糊的背景。
如果能退后一步看看四周,也许我们会发觉整个图案都变了。
变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我们的视野。
所以,偶尔放慢脚步,让眼眸以最大的可能性把天地随意浏览一番,我们讲恍然大悟;世界还是时时在装扮着自己的。
而有什么比一面散步一面听蝉更让人心旷神怡?
听听亲朋好友的倾诉,这是我们常有的经验。
聆听万物的倾诉,对我们而言,亦非难事,不是吗?
聆听,也是艺术。
大自然的宽阔四最佳的音响设备。
想象那一队一队的雄蝉敛翅踞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各自站在舞台上一般。
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
它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
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
它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
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
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幽游其中。
又如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见,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地攫走了你紧紧扯在手里的轻愁。
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段简残篇,徒留给人一些怅惆、一些感伤。
何尝不是生命之歌?
蝉声。
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选自《台湾艺术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渔父(简媜)
父亲,你想过我吗?
“虽然只做了十三年的父女就恩断缘尽,他难道从来不想?
”我常自问。
然而“想念”是两个人之间相互的安慰与体贴,可以从对方的眉眸、音声、词意去看出听出感觉出,总是面对面的一桩人情。
若是一阴一阳,且远隔了十一年,在空气中,听不到父亲唤女儿的声音;在路途上,碰不到父亲返家的身影,最主要的,一个看不到父亲在衰老,一个看不到女儿在成长,之间没有对话了,怎么去“想”法?
若各自有所思,也仅是隔岸历数人事而已。
父亲若看到女儿在人间路上星夜独行,他也只能看,近不了身;女儿若在暴风雨的时候想到父亲独卧于墓地,无树无檐遮身,怎不疼?
但疼也只能疼,连撑伞这样的小事,也无福去做了,还是不要想,生者不能安静,死者不能安息。
好吧!
父亲,我不问你死后想不想我,我只问生我之前,你想过我吗?
好像,你对母亲说过:
“生个囝仔来看看吧!
”况且,你们是新婚,你必十分想念我棗哦!
不,应该说你必十分想看看用你的骨肉你的筋血塑成的小生命长得是否像你?
大概你觉得“做父亲”这件事很令人异想天开吧?
所以,当你下工的时候,很星夜了,屋顶上竹丛夜风安慰着虫唧,后院里井水的流咽冲淡蛙鼓,鸡埘已寂,鸭也闭目着,你紧紧地掩住房里的木门,窗棂半闭,为了不让天地好奇,把五烛灯灯炮的红丝线一拉,田地都躺下,在母亲的阴界和你的阳世之际酝酿着我,啊!
你那时必定想我,是故一往无悔。
当母亲怀我,在井边搓洗衣裳,洗到你的长裤时,有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酸梅或腌李,这是你们之间不欲人知的体贴,还不是为了我!
父亲,你是一个大剌剌的庄稼男人,突然也会心细起来,我可以想象你是何等期待我!
因为你是单传,你梦中的我必定是个壮硕如牛的男丁。
可是,父亲,我们第一次谋面了,我是个女儿。
日日哭
母亲的月子还没有坐完,你们还没有为我命名,我便开始“日日哭”棗每天黄昏的时候,村舍的炊烟开始冒起,好象约定一般,我便凄声地哭起来,哭得肝肠寸断私的,让母亲慌了手脚,让阿嬷心疼,从床前抱到厅堂,从厅堂摇到院落,哭声一波一波传给左邻右舍听。
啊!
父亲,如果说婴儿看得懂苍天珍藏着的那一本万民宿命的家谱,我必定是在悔恨的心情下向你们哭诉,请你们原谅我、释放我、还原我回身为那夜星空下的一缕游魂吧!
而父亲,只有你能了解我们第一次谋面后所遗留的尴尬:
我愈哭,你愈焦躁,你虽褓抱我,亲身挽留我,我仍旧抽搐地哭泣。
终于,你恼怒了,用两只指头夹紧我的鼻子,不让我呼吸,母亲发疯般掰开你的手,你毕竟也手软心软了。
父亲,如果说婴儿具有宿慧,我必定是十分喜欢夭折的,为的是不愿与你成就父女的名分,而你终究没有成全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灵犀让你留我,恐怕你也以往了。
而从那一次棗我们第一次的争执之后,我的确不再哭了,竟然乖乖地听命长大。
父亲,我在聆听自己骨骼里宿命的声音。
前寻
我畏惧你却又希望接近你。
那时,我已经可以自由地跑于田梗之上、土堤之下、春河之中。
我非常喜欢嗅春草拈断后,茎脉散出来的拙香,那种气味让我觉得是在与大地温存。
我又特别喜爱寻找野地里小小的蛇莓,翻阅田梗上每一片草叶的腋下,找艳红色的小果子,将它捏碎,让酒红色的汁液滴在指甲上,慢慢浸成一圈淡淡的红线。
我像个爬行的婴儿在大地母亲的身上戏耍,我偶尔趴下来听风过后稻叶窸窸窣窣的细语,当它是大地之母的鼾声。
这样从午后玩到黄昏,渐渐忘记我是人间父母的孩子。
而黄昏将尽,竹舍内开始传出唤我的女声棗阿嬷的、阿姆的、隔壁家阿婆的,一声高过一声,我蹲在竹丛下听得十分有趣,透过竹竿缝看她们焦虑的裸足在奔走,不打算理,不是恶意,只是有一点不能确信她们所呼唤的名字是指我?
若是,又不可思议为什么她们可以自订姓名给我,一唤我,我便得出现?
我唤蛇莓多次,蛇莓怎么不应声而来呢?
这时候,小路上响起这村舍里唯一的机车声,我知道父亲你从时常卖完鱼回来了,开始有点怕,抄小路从后院回家,赶紧换下脏衣服,塞到墙角去,站在门槛边听屋外的对话。
“老大呢?
”你问,你知道每天我一听到车声,总会站在晒谷场上等你。
阿嬷正在收干衣服,长竹竿往空中一矗,衣衫纷纷扑落在她的手臂弯里,“口口(此二字过于生僻,‘日,月’加‘走之底’,大约是指黄昏)不知晓回来,叫半天,也没看到囝仔影。
”我从窗棂看出去,还有一件衣服张臂粘在竹竿的末端,阿嬷仰头称手抖着竹竿,衣服不下来。
是该出去现身了。
“阿爸。
”扶着木门,我怯怯地叫你。
阿嬷的眼睛远射过来,问:
“藏去哪里?
”
“我在眠床上困。
”说给父亲你听。
你也没正眼看我,只顾着解下机车后座的大竹箩,一色一色地把鱼啊香蕉啊包心菜啊雨衣雨裤啊提出来,竹箩的边缝有一写鱼鳞在暮色中闪亮着,好像鱼的魂醒来了。
地上的鱼安静地裹在山芋叶里,海洋的色泽未退尽,气味新鲜。
“老大,提去井边洗。
”你踩熄一支烟,喷出最后一口,烟袅袅而升,如柱,我便认为你的烟柱擎着天空。
我知道你原谅我的谎言了,提着一座海洋和一山果园去井边洗,心情如鱼跃。
我习惯你叫我“老大”,但是不知道为何这样称呼我?
也许,我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也许,你稍稍在自我补偿心中对男丁的愿望;也许,你想征服一个对手却又预感在未来终将甘拜下风。
你虽为我命名,我却无法从名字中体会你的原始心意,只有在酒醉的夜,你醉卧沙发上,用沙哑而挑战的声音叫我:
“老棗大,帮棗我脱鞋棗”非常江湖的口气。
我迟疑着,不敢靠近你那酒臭的身躯,你愤怒:
“听到没?
”我也在心底燃着怒火,勉强靠近你,抬脚,脱下鞋,剥下袜子,再换脚。
你的脚趾头在日光灯下软白软白地,有些冲臭,把你的双脚扶搭在椅臂上,提着鞋袜放在门廊上去,便冲出门溜去稻田小路上坐着。
我很愤怒,朝黑黑的虚空丢石头,石头落在水塘上:
“得拢!
”月亮都破了。
只有这一刻,我才体会出你对我的原始情感:
畏惧的、征服性的、以及命定的悲感。
然而,我们又互相在等待、发现、寻找对方的身影。
夏天的河水像初生育后的母乳,非常丰沛。
河的声音喧哗,河岸的野姜花大把大把地香开来,影响了野蕨的繁殖欲望,蕨的嫩英很茂盛,一茎一茎绿贼贼地,采不完的。
不上学的午后,我偷偷地用铁钉在铝盆沿打一个小孔,系上塑胶绳,另一头绑在自己的腰上,拿着谷筛,溜去河里摸蛤蜊。
“扑通!
”下水,水的压力很舒服,我不禁“啊啊啊”的呼气。
河砂在脚趾缝搔痒、流动,用脚趾一掘,就踩到蛤蜊,摸起来丢在铝盆,“咚!
咚!
咚!
”蛤蜊们在盆里水中伸舌头吐砂,十分顽皮,我一粒一粒地按它们的头,叫它们安静些。
有时,筛到玻璃珠、螺丝钉、纽扣,视为珍宝,尤其纽扣。
我可以辨认是哪一家婶子洗脱的扣子,当然不还她,拿来缝布娃娃的眼睛。
啊!
我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同伴,但拥有一条奔河,及所有的蛤蜊、野蕨、流砂。
这时候,远方竹林处传来你的摩托车声,绝对是你的,那韵律我已熟悉。
我想,我必须躲起来,不能让你发现我在玩水。
但这一段河一览无遗,姜叶也不够密,我只得游到路洞中去藏,等待你的车轮碾过。
我有种紧张的兴奋,想吓你,当你的车甫过时,大声喊你:
“阿棗爸啊!
”然后躲起来,让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偷看你害怕的样子:
你也许会沿着河搜索,以为我溺死了,刚刚是回魂来叫你,你也许会哭,啊!
我想看你为我哭的样子……来了,车声很近了,准备叫,“轰轰轰……”车轮碾过洞的路表,河波震得我麻麻的,我猛然从水中窜出,要叫,刹那间心生怀疑,车行已远……那两个字含在嘴里像含着两粒大鱼丸,喘不过气,我长长地叹一口气,把那两字吐到河水流走。
叫你“阿爸”好像很不妥贴,不能直指人心,我又该称呼你什么?
才是天经地义的呢?
一身子的水在牵牵挂挂,滴到水里像水的婴啼,我带着水潜回河中,不想回家帮你提鱼提肉,连对“父亲”的感觉也模糊了。
夏河如母者的乳泉,我在载浮载沉。
然而,为何是你先播种我,而非我来哺育你?
或者,为何不能是互不相识的两个行人,忽然一日错肩过,觉得面熟而已?
我总觉得你藏着一匹无法裁衣的情织锦,让我找得好苦!
迟归的夜,你的车声是天籁中唯一的单音。
我一向与阿嬷同床,知道她不等到你归来则不能睡,有时听到她在半睡之中自叹自艾的鼻息,也开始心寒,怕你出事。
你的车声响在无数的蛙鸣虫唧之中,我才松了心,与世无争。
你推开未闩的木门进入大厅,跨过门槛转到阿嬷的房里请安,你们的话中话我都听进耳里,你以告解的态度说男人嗜酒有时是人在江湖不得不,有时是为了心情郁促。
阿嬷不免责备你,家里酿的酒也香,你要喝几坛就喝。
也免得妻小白白担了一段心肠。
这时,阿姆烧好了洗澡水,也热了饭汤,并请你亲自去操刀做生鱼片。
一切就绪,你来请阿嬷起身去喝一点姜丝鱼汤。
掀起蚊帐,你问:
“老大呢?
”
“早就困去罗。
”
你探进来半个身子,拨我的肩头叫:
“老大的棗老大的棗,起来吃としみ!
”
我假装熟睡,一动也不动。
(心想:
“再叫呀!
”)
“老大的棗”
“困去了,叫伊做啥?
”
“伊爱吃としみ。
”
做父亲的摇着熟睡中女儿的肩头,手劲既有力又温和,仿佛带着一丁点怕犯错的小心。
我想我就顺遂你的意思醒过来吧!
于是,我当着那些蛙们、虫群、竹丛、星子、月牙……的面,在心里很仁慈的对着父亲你说:
“起来吧!
”
“做啥?
阿爸。
”我装着一脸惺松问你。
“吃としみ。
”说完,你很威严地走出房门,好像仁至义尽一般。
但是,父亲,你寻觅过我,实不相瞒。
手温
那是我今生所握过,最冰冷的手。
“青青校树,萋萋芳草”的骊歌唱过之后,也就是长辫子与吊带裙该换掉的时候。
那一日,正是夏秋之间田里割稻的日子,每个人都一头斗笠,一手镰刀下田去了。
田土干裂如龟壳,踩在脚底自然升起一股土亲的感情。
稻穗低垂,每一颗谷粒都坚实饱满,闪白闪白的稻芒如弓弦上的箭,随时要射入村妇的薄衫内,好搔得一驼红痒。
空气里,尽是成熟的香,太阳在裸奔。
父亲,你刈稻的身躯起伏着,如一头奔跑中的豹。
你的镰刀声擦过你的耳际,你的阔步踩响了我左侧的裂土,你全速前进,企图超越我,然后会在平行的时候停下来,说:
“换!
”然后我就必须成为你左侧的败将,目送你豹一般向前刈去,一路势如破竹。
但是,父亲,我决心赢你。
我把一望无际的稻浪想象成战地草原,要与你一决雌雄。
我使尽全力速进,刈声脆响,挺立的稻杆应声而倒,不留遗言。
我听见你追赶的镰声,逼在我的足踝旁、眉睫间、汗路中、心鼓上,我喘息着,焦渴着,使刀的劲有点软了,我听见你以一刈双棵的掌势逼来,刈声如狼的长嗥,速度加快,我不由得愤怒起来,撑开指掌,也以同样的方式险进,以拼命的心情。
父亲,去胜过自己的生父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能了解吗?
当我抵达田梗边界,挺腰,一背的湿衫,汗水淋漓。
我握紧镰刀走去,父亲,我终于胜过你,但是不敢回头看你。
日落了,一畦田的谷子都已打落,马达声停止,阿嬷站在竹林丛边喊每个人回家吃晚饭。
田里只剩下父亲你和我,你正忙着出谷,我随手束起几株稻草,铺好,坐下歇脚,抠抠掌肉上的茧,当我摘下斗笠扇风时,你似乎很惊讶,停下来:
“老大,你什么时候去剪掉长毛发?
”
“真久啰。
”我摸摸那汗湿透的短发,有点不好意思,仿佛被你窥视了什么。
“做啥剪掉?
”
“读中学啊!
你不知道?
”
“哦。
”
你沉默地出好谷子,挑起一箩筐的谷子走上田埂回家,不招呼,沉重的背影隐入竹林里。
我躺下,藏在青秆稻草里的蛤蟆纷纷跳出来,远处的田有人在烧干稻草,一群虎狼也似的野火奔窜着,奔窜着,把天空都染红了半边。
我这边的天,月亮出来了,然而是白夜。
父亲,我了解你的感受,昔日你褓抱中那个好哭的红婴,今日已摇身一变。
这怎能怪我呢?
我们之间总要有一个衰老,一个成长的啊!
但是,一变必有一劫。
田里的对话之后,我们便很少再见面了。
据说你在南方澳,渔船回来了,渔获量就是你的心事;据说你在新竹,我在菜园里摘四季豆的时候,问:
“阿嬷,阿爸去哪?
”
“新竹的款!
”
“做什么?
”
“小卷,讲是卖小卷。
”
“你有记不对没?
你上次讲在基隆。
”
“不是基隆就是新竹,你阿爸的事我哪会知?
”
基隆的雨季大概比宜兰长吧!
雨港的檐下,大概充斥着海鱼的血腥、批驳鱼商的铜板味,及出海人那一身洗也洗掉的盐馊臭。
交易之后,穿着雨衣雨鞋的鱼贩们,抱起一筐筐的鲜鱼走回他们自己的市场,开始在尖刀、鱼俎、冰块、山芋叶、湿咸草,及秤锤之间争论每一寸鱼的肉价,父亲,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激动的时候就猛往地上吐槟榔汁,并操伊老母……雨天,我就这样想象。
想到心情坏透了,就戴上斗笠,也不披蓑衣,从后院鸡舍的地方爬上屋顶,小心不踩破红瓦片,坐在最高的屋墩上,极目眺望,望穿汪洋一般的水田、望尽灰青色的山影,雨中的白鹭鸶低飞,飞成上下两排错乱的消息,我非常失望,嗫嚅着:
“阿爸!
”“阿爸!
”天地都不敢回答。
再见到你,是一个寤寐的夜,我都已经睡着了,正在梦中。
突然,一记巨响棗重物跌落的声音,改编了梦中的情节,我惊醒过来,灯泡的光刺着我的睡眼,我还是看到你了,父亲。
你全身爬进床上衣柜的底部,双拳捶打着木板床,两脚用力的蹭着木板墙壁,壁的那一面是摆设神龛的位置,供桌、烛台、香炉,及牌位都摇摇作响,阿嬷束手无策,不知该救神还是救人?
你又挣扎着要出来,庞大的身躯卡在柜底,你大声的呼啸着、咆哮着、痛骂一些人名……我快速地爬下床,我知道紧接着你会大吐,把酒腥、肉馊、菜酸臭,连同你的坛底心事一起吐在木板床上,流入草席里。
父亲,我夺门而去,夜雾吮吸着我的光臂及裸足,我习惯在夜中行走,月在水田里追随我,我抓起一把沙石,一一扔入水田,把月砸破,不想让任何存在窥见我心底的悲伤。
整个村子都入睡了,沉浸在他们箪食瓢饮的梦中。
只有田里水的闹声,冲破土堤,夜奔到另一畦田,只有草丛间不倦的萤火虫,忙于巡逻打更。
父亲,夜色是这么静谧,我的心却似崩溃的田土,泪如流萤。
第一次,我在心底下定决心:
“要这样的阿爸做什么?
要这样的阿爸做什么?
”
父亲,我竟动念绝弃你。
七月是鬼月,村子里的人开始小心起来,言谈间、步履间,都端庄持重,生怕失言惹恼了田野中的孤魂,更怕行止之际骚扰到野鬼们的安静棗在七月,他们是自由的、不缚不绑不必桎梏,人要礼让他们三分。
小孩子都被叮咛着:
江底水边不可去哦,有水鬼会拖人的脚,天若是黑,竹林脚千万不要去哦,小鬼们在抽竹心吃,听见没有?
第二天早晨去竹丛下看,果然落了一地的竹萚,及吸断的竹心渣。
鬼来了,鬼来了。
七月十四,早晨,我在河边洗衣,清早的水色里白云翠叶未溶,水的曲线妙曼地独舞着,光在嬉闹,如耀眼的宝珠浮于水面,我在洗衣石上搓揉你的长裤,阿爸,一扭,就是一摊的鱼腥水滴入河里,鱼的鳞片一遇水便软化,纷纷飘零于水的线条里。
阿爸,你的车声响起,近了,与我擦肩而过,我蹲踞着,也不回头看你了,反正,你是不会停下来与我说话的。
我把长裤用力一抛,“趴”入河,用指头钩住皮带环,两只裤管直直地在水里漂浮,水势是一往无悔的,阿爸,我有一两秒的时间迟疑着,若我轻轻一放指,长裤就流走了。
但我害怕,感觉到一种逝水如斯的颤栗,仿佛生与死就在弹指之间。
我快速地把长裤收回来,扭干每一滴水,把它紧紧地塞进水桶里。
好险!
捡回来了,阿爸!
但是阿爸,你的确是一去不返了。
那日,夜深极了,阿爸你还未回来,厅堂壁上的老钟响了十一下,我尚未合眼。
远处传来一声声狗的长嗥,阴森森的月暝夜,我想象总有一些声音来通风报信吧!
当我浑浑噩噩地从寤寐之中醒来时,有人用拳头在敲木门:
“动”、“动”、“动”……
一个警察,数个远村带路的男人,说是撞车了,你横躺在路边,命在旦夕,阿爸。
阿嬷与阿姆随后去,我踅至沙发上呆住,老钟“滴答”,“滴答”,夜是绝望的黑,虫声仍旧唧唧,如苍天与地母的鼻鼾。
我环膝而坐,头重如石磨,所有的想象都是无意义的暴动。
人生到此,只有痴痴呆呆地等待、等待,老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时间的咒语。
隐隐约约有哭声,从远远的路头传来,女人们的。
你被抬进家门,半个血肉模糊的人,还没有死,用鼻息呻吟着、呻吟着。
我们从未如此尴尬的面对面,以至于我不敢相认,只有你身上穿着的白衬衫我认得,那是我昨天才洗过晾过叠过的。
阿姆为你褪下破了的血杉,为你拭血,那血汩汩地流。
所有的人都面容忧戚,但我已听不见任何哭声,耳壳内只回荡着老钟的摆声及你忽长忽短的呻吟棗天就要亮了,像不像一个不愿回家的稚童摇着他的拨浪鼓在哭?
我端着一脸盆的污血水到后院井边去,才呼吸到将破的夜的香,但是这香也醒不了谁了。
上方的井水一线如泻,注乱下方池里的碎月,我端起脸盆,一泼,血水酹着这将芜的家园,“天啊!
”我说,脸盆坠落,咕咚咚几滚,覆地,是上天赐下来的一个筊杯吗?
我跪在石板上搓洗染血的毛巾,血腥一波一波刺着我的鼻,这浓浊、强烈、新鲜的男人的血,自己阿爸的。
搓着搓着,手软了,坐在湿漉漉的青石上,面对着井壁痛哭,壁上的青苔、土屑、蜗牛唾糊了一脸,若有一命抵一命的交易,我此刻便换去,阿爸。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再度将你送去镇上就医,所有的人走后,你呻吟一夜的屋子空了,也虚了,只剩下地上的斑斑碧血。
那日是七月十五日,普渡。
我在井边淘洗着米,把你的口粮也算进去的。
昨夜的血水沉淀在池底,水色绛黑,我把脏的水都放掉,池壁也刷洗过,好像刷掉一场噩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把上井的清水释放出来,我要淘米,待会儿家人都要吃我煮的饭,做田的人活着就应该继续活着,阿爸。
河那边的小路上,一个老人的身影转过来,步子迟缓而佝偻,那是七十岁的大伯公,昨晚,他一起跟去医院的。
我放下米锅,越过竹篱笆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