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docx
《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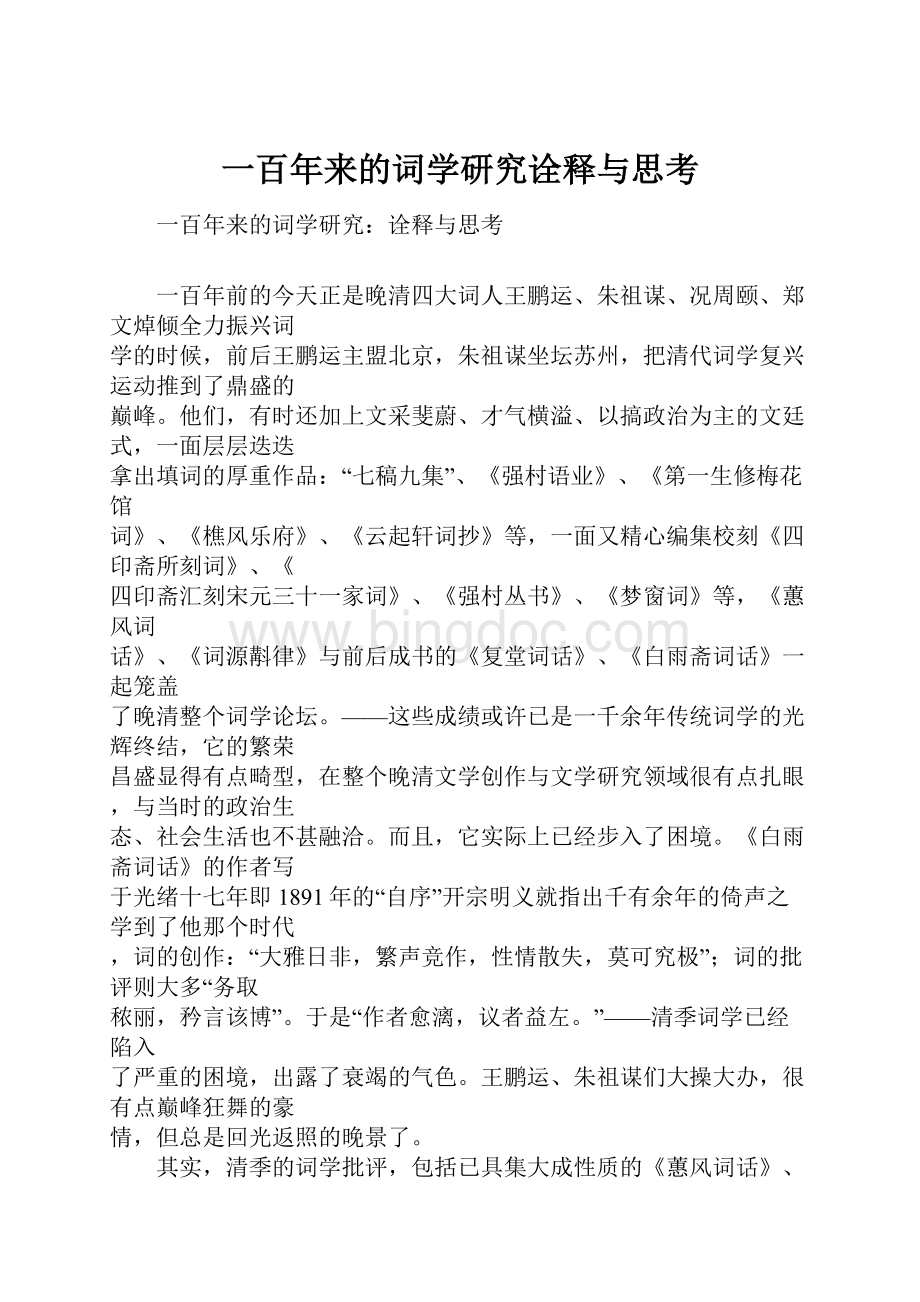
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
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
诠释与思考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倾全力振兴词
学的时候,前后王鹏运主盟北京,朱祖谋坐坛苏州,把清代词学复兴运动推到了鼎盛的
巅峰。
他们,有时还加上文采斐蔚、才气横溢、以搞政治为主的文廷式,一面层层迭迭
拿出填词的厚重作品:
“七稿九集”、《强村语业》、《第一生修梅花馆
词》、《樵风乐府》、《云起轩词抄》等,一面又精心编集校刻《四印斋所刻词》、《
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强村丛书》、《梦窗词》等,《蕙风词
话》、《词源斠律》与前后成书的《复堂词话》、《白雨斋词话》一起笼盖
了晚清整个词学论坛。
——这些成绩或许已是一千余年传统词学的光辉终结,它的繁荣
昌盛显得有点畸型,在整个晚清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很有点扎眼,与当时的政治生
态、社会生活也不甚融洽。
而且,它实际上已经步入了困境。
《白雨斋词话》的作者写
于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的“自序”开宗明义就指出千有余年的倚声之学到了他那个时代
,词的创作:
“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词的批评则大多“务取
秾丽,矜言该博”。
于是“作者愈漓,议者益左。
”——清季词学已经陷入
了严重的困境,出露了衰竭的气色。
王鹏运、朱祖谋们大操大办,很有点巅峰狂舞的豪
情,但总是回光返照的晚景了。
其实,清季的词学批评,包括已具集大成性质的《蕙风词话》、《白雨斋词话》在
整体构架上——本体立场和审美视野——与千有余年前发轫时期的两宋词学没有本质上
的区别。
宋人的词学工程大抵在作品编辑、曲调考证、韵谱整理、作家作品本事及批评
、词的理论探讨五个方面,但严格意义的词学概念似乎又不很有共识。
谢桃坊《中国词
学史》“引论”对“词学”两字历史源流有相当深细的叙述,大抵作为研究“词”的一
门“学”则是近代学者的观念。
1926年有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出版,1930年有胡云翼
《词学ABC》出版, 但这两部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研究对象的着作对“词学”的概
念范畴是不甚清楚明晰的。
1933年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1934年的《词学季
刊》1卷4号上刊出了龙榆生的《研究词学之商榷》,开始在学术意义上为“词学”立了
概念:
“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
,谓之词学。
”并为词学确定了八个研究范畴,其中后三个范畴即三门新学:
声调之学
、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实际上可以涵盖前五门旧学。
1981年的《词学》集刊第一辑里
发表了唐圭璋撰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将词学范畴厘定为十项:
词的起源、
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
。
刘扬忠在1989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之路》中为宋词研究实际上可以说是为词学研究设
计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图表,作者自云“未敢云全”,但词学的基本门类与具体内容应
该说是相当“全”的。
笔者这里做“词学一百年”的回顾考察,当然不能就词学的全范
畴发言,本文的词学讨论范围主要限于词的理论批评与史的流变把握。
理论批评大抵包
括内在的体制、方法、声律、格调,与外在的审美意识、精神取向、思想立场等人文内
涵;史的把握意在揭示词体流变轨辙真迹与词史兴衰及其潜伏于中的词的观念的演化变
革的文化史意义。
词的传统是“艳科”,是“小道”、“末技”,是“绮罗香泽”;词学的传统是“
别是一家”,是“本色当行”,是“诗词分疆”,是“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
谐凤律”。
——词学的历史更多的带有一种孤芳自赏和幽闭自
恋的倾向,五代北宋以来的正宗词家宁可承认“诗庄词媚”,宁可委屈自己称“薄伎”
,称“小歌辞”,却也要与诗划清界限,用严苛的音乐属性把自
己这一家从诗的王国里独立出来,成为自成体制的小邦下国。
到了清代,由于实际上的
词学已蔚为大国,不仅创作上一派繁荣,研究上也俨然国学一脉,与经史子研究,与以
诗文为骨干的集的研究平起平坐。
尽管清词早已与音乐分了家,已是胡适说的词的“鬼
”借尸还魂的时代,“本色当行”的口号叫不响了,他们便悄悄地把词的本体功能向诗
靠拢,常州派以来的词论,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一条思路出发,处处与诗论争平等,
争“正变”,争风雅比兴的言志功能与社会效益。
词学家也不再肯承认词的“小道”、
“未技”的地位了,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中云:
“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
词至
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
《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
”—一句“上与《风》、《骚》同旨”实质上已把词与诗
放在同一地位了,词也能在社会政治的大题目上与诗发挥同样的“风”、“刺”功能。
常州派一脉的寄托比兴的词与南社的革命排满的诗不是同样的质性,同样的功用,并应
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么?
这便是词的“尊体”运动的由来。
有清一代词学的历史任务似是要在本体观念上与两宋词学颠倒一下,常州派崛起后
,张惠言、周济直到清季谭献、陈廷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始终是把“尊词”
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们的核心工作、外围工作,以及理论宣传工作都围绕着“尊词”
这个中心任务转。
但是,由于千年传统的词“别是一家”的疆域牢宠,沉潜于音声韵律
用大力于内功锻炼,或追尚醇雅清空,或执意词情蕴藉,或留连“花草崇拜”,审美情绪上依恋婉丽侧艳的原教旨正宗人马誓不肯让出旗帜,修正
“诗余”的体制质性。
于是晚清的词学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在本体功能上努
力向诗靠拢,模拟汉儒说诗,讲求词的寄托比兴、《风》《骚》同旨,梦想“体益尊,
学益大”,力图把振兴词学落实在政治教化的挂靠上;另一方面,却又被宋以来传统的
“别是一家”守身如玉的思维所束缚,拒绝靠拢,拒绝合流,拒绝承担为社会政治发言
的体制外使命。
—清季词学的“繁荣”就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而两造的并辔齐驱,互
不相让,又使这种“繁荣”进一步加剧加重,实际上也使词学的“古色古香”进一步凝
固、僵化,生命机制停滞不前,慢慢透出一股腐朽的气息。
—这是清季词学大画面的主
要景观。
二十世纪初叶,这幅大画面上出现了新的亮色,新的景致,王国维的出现带来
了现代词学的第一线曙光。
二十年代:
现代词学的崛起
王国维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有天才的大学者,他在哲学、美学、经学、史学的研究上
都拿出过可观的成绩。
他文学研究上的成绩主要在词曲与戏剧,词学研究只是王国维学
术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多半还是他处于人生精神困境时的一种排遣与寄托的产物。
王
国维1904年在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聊以自慰,《人间词》的甲乙稿刊印
于1906年至1907年,1908年起从事词学研究,着名的《人间词话》也就在这一年开始在
《国粹学报》分期连载。
他的一些重要词学文章大都写成于1908
年至1913年间。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词学理论批评的专
着,关于《人间词话》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无需我再来赘述。
王国维的词学成就体现
在新的观念与新的手段上,而正是这种新观念与新手段使王国维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
化带来了生机。
首先王国维为词的“尊体”选择了另一条大路,抛却了“与《风》、《骚》同旨”
的儒家传统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民族文化精神”体现的见解。
词的真正
价值、它的文学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千年不辍的活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贯
穿了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与生命运动。
一种活泼泼的真情淋漓的文学往往展示了一个民
族文化的发达与精神的健康,这两点尤其体现在文学新形式的创造性上和表现形态的丰
富性上。
王国维在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自序》里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
“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
”他把“宋之词”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元之曲”相提并论,“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撇开了
风雅教化的尊体术,王国维把词学看作为一种“纯粹美术”,从而使她获得了普遍受尊
重的独立价值。
这种独立价值集中体现在反映现实的人生,尤其是忠实地表述现实人生
的精神痛苦、欲望与忧患上。
王国维论词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
剧意识,他称赞李煜词“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许多人认为提法荒诞
,但这话正孕育了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染过来的哲学的与美学的悲剧色彩
,也隐隐流露出他深重的人生悯怜和朦胧的拯拔意图。
他触到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
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深层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艺术真谛。
作为王国维的新手段,王国维在“词话”这种旧形式下采用了新的探索技术,他组
装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剖分析千年的倚声之学各块组织器官。
他的“境界”说以
及一套连环扣合的“有境界”、“无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
诗人”、“客观之诗人”、“造境”、“写境”、“隔”、“不隔”、“合乎自然”、
“邻于理想”等概念范畴为词学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中西文艺学合璧的思维术与方法论,
美感形式与悲剧意识替代了传统词学的陈旧理论框架,词学第一次染上了现代学术的色
彩,并且在思维与实践上产生了征服词学体制内人马的理性力量和帮他们解决问题的实
际能力。
传统的词学界即使不很理解王国维的全套词学思想,但对《人间词话》内闪烁
出的奇光异彩也不得不刮目凝视,有所思索。
然而王国维的词学理论体系显然有着不少局限。
局限并不是表现在他论词重五代北
宋,轻南宋,尤其是轻传统看好的白石、玉田。
——这可以说是一个主观偏见,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批评
创见。
真正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来看,王国维词学的局限还在“境界说”本身的模糊
影响与诸多矛盾难合之处。
其中重要概念范畴,他不肯认真界说解释;各概念范畴的逻
辑关系,他又不屑作细致严密的论述推演。
他往往用“摘句”的手法来表达理论认识与
美感觉悟,缺乏科学的精确性与理论说服力——这与他用“词话”作为新理论的载体一
样同样是缺乏一种自觉突破的先进意识。
还有他的重要词学论文多用力在考证功夫上,《人间词话》开启的先锋理论后继乏力
,几成绝响。
他的一些词录题跋,也往往率尔操觚,带有旧式名士的不良习惯。
他对周
邦彦的评价“前倨后恭”,虽被后来的研究家们誉为探索的真诚与渐进渐深,但似也不
能不看出他对词学的审美认识与把握存在着矛盾与困惑之处。
——总的看来,王国维的
词学研究前不如他的哲学、美学之理论锐气,后不如戏曲、经史之沉稳厚重。
然而他在
世纪初叶的独具只眼和理论新变则是现代词学崛起的信号,为现代词学奠立了理论基石
。
杨海明在《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一文中曾说,在现代词学的新
变中,如果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人物的话,那么胡适就足有资格被称为
此中的“革命党人”了。
他在此文中对胡适词学的“革命”性冲击,推动词学朝着现代
化的方向急速转型和迈进的所谓“澄清迷雾,振聋发聩”的历史功绩有相当全面的论述
。
胡适深具反传统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戴着“过激党”的帽子,他的词学理论对传统词
学的挑战与冲击带有更激烈的狂飙意义。
胡适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的求新变的呼声湮
没在晚清传统词学高涨汹涌的潮头里,孤军奋战,没有产生重大的响应。
胡适则在新文
学革命的事业中不仅杀出了一条血路,开出了一片新天,而且还传播了一套理论,带出
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一股奔腾向前的新潮,造就了一种改天换地、转换范式的大气候—
—收功效果大不一样。
关于胡适的词学研究的理论建树和狂飙突进,六年前我在《胡适
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一文中曾专门大写了一节,这里不想重复。
只是提纲挈领
提几条,并且着重谈一下胡适与王国维在现代词学崛起运动中的不同贡献,以点明这一
脉历史线索的行进轨迹。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史源流中的正宗与主潮,因而最有价值,最有生命,最
应受到尊重。
词正是白话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镇,既具典型意义又有影响力。
词的“尊
体”运动到了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认识在学界确立、普及才最终完成,并且一劳永逸歆享
供献。
民间源头论。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
”云云,胡适的这一段着名语录人所熟知,也有时时重温的必要。
基于上面认识,胡适推出了他的词史见解:
即着名的词的“本身”、“替身
”和“鬼”的三段论历史。
——有清一代的词学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
史搬演,虽然轰轰烈烈、气象壮观,然而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无一点生人的生意、生气
。
词本身的历史又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
——“歌者的词
”即是民间新创词的体裁,文人参加渐成“诗人的词”,而“词匠的词”即是“天才堕
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后的“小技巧”、“烂书袋”、“烂
调子”!
技术主义,工艺主义,典故与书袋代替、压倒了活的文学的创作与艺术的真美
。
——这一套理论把王国维在审美底蕴上贬抑南宋的思维扩展到了哲学、历史眼光的判
断,断然把南宋一批“词匠”开除出了文学的殿堂。
在词的内容风格上重豪放,轻婉约,为词的审美批评和风格流派的分野立出
了新的时代要求。
这个审美判断由一时的见识异化为特定的教条,由于诸种历史内容与
文化条件的原因,实际上的影响力笼罩了词学界半个多世纪,霸气十足。
几乎到了八十
年代初,才有了反拨的历史条件并由之酿成一场学术冤屈的历史控诉,一段时间内还结
成一条声势巨大的审美立场上“反豪放”的统一战线。
不过,笔者在这里又必须指出一点:
胡适对词发起的这场革命是留有一手的,或者
说是给出路的。
胡适同王国维一样,受时代大气候薰染喜欢做词,当然
绝不主张废词,即打倒词。
他掀起文学革命的“誓诗”即是写在了一首《沁园春》的词
里,新文学革命的心声正不妨用旧的词形式宣示出来。
当然风格声调变了,文字雅俗也
变了,“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内容意味更是大变了。
——白话进入了词,白话
词成了胡适创造的白话新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是他最满意的那部分。
有两点
最能看出胡适对词的给出路政策的优渥:
一是他自己填了不少白话词,而且平仄韵律大
抵合辙,并不违反“倚声填词”的基本原则;二是他始终不肯让新诗兼并了词,保持了
词文学体裁的形式独立。
正是由于首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主帅网开一面,“五四”新文学
的大洪流冲垮了《选》学的辞赋、桐城派的古文和同光体的假宋诗,唯独留下了词。
但
也冲掉了词的“常州”色彩属性,保留了它清新活泼、明白如话的纯洁体式。
胡适同王国维一样,也信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在形式递嬗上王国维更多地留
意诗的不同体制的替代演化,他曾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
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
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
由于此。
”这段话过于机械活溜,与他的“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至南
宋以后,词并为羔雁之具”等话一样,模糊影响,值得商榷。
但在外貌上很与胡适那段
着名的话相似。
不同的是主体:
胡适说的主体是民间文士,包括歌伶乐工;王国维的主
体则是文学上的“豪杰之士”,即大文人,着名作家诗人,很专业的。
——两人论断微
妙差异,可见一斑。
1935年7月胡适曾有一信给任访秋, 谈到他与王国维在论词上的分
歧。
首先胡适强调:
“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
”两人在词史上着眼点
不同,结论亦不同。
胡适又指出王国维的“境界”概念,“隔”与“不隔”的提法都说
的“不很清楚”。
胡适认为,王氏的“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而他理解中的
境界或意境应是“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
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
”王国维的所谓“隔”,其实只是“不能浅出”而已,并不玄
妙。
胡适还提到,“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
——大概王国维自己并不满意《人间词话》,胡适则深信自己的词史观是“根本不错”的,他的词学研究意在
历史的阐释与思想的前进,重在传授一种观念,锻炼一种眼光,培养一种意识。
三十年代:
两队人马各做各的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他提倡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建立起
了一套崭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史的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
转型,把词学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或者说开启了一个词学新时代。
胡适是
用中西学融合的文化哲学的批评手段居高临下,自外而内地解剖传统词学,他的手术做
得更先进,更大胆,“革面”居次,“洗心”为上。
胡适的词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带出了
一队人马,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洗心”为上的新潮流,中国传统文学
史上有关词的章节已被推倒重写。
这一队胡适派的新人马,重要成员和最新成果有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
史略》、《词学概论》,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柯敦伯《宋文学史》,薛砺若《宋词通论》,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他们的关于词和词史见解,间有细枝末节的不同,但贯通的
目光、演化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均打上胡适牌鲜明的印戳。
在词的现代学术史的演进上
,他们无疑是一条主线。
但他们几乎又全是词的本体研究体制外的人物,严格说来,他
们是体制外论词,安排词史,评估词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姑可称为“体制外派”。
——连同王国维也是“体制外派”的奠基人物,施议对《百年词通论》就说:
“王国维
论词实际尚未进入词体的深层结构,他的理论并非词的本体理论。
”——称“体制外派
”是相对于“体制内派”而言的,三十年代的中国词坛正活跃着一个声势巨大的词学“
体制内派”,也即是《词综》、《词律》以来一直绵延到“四印斋”、“双照楼”、“
强村”门下的正宗传统派的词学队伍。
这一派人马注重词的本体理论,词
的内部深层结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集中于词籍、词谱、词调、词韵、词史,也即是龙
榆生提出过的词学八项中的三项:
目录之学、声调之学与词史之学。
他们的代表人物有
夏敬观、刘毓盘、梁启勋、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
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集一时词学体制内精英,阵
营壮阔,大将如云。
他们的着作如《词调溯源》、《词学通论》、《词学》、《词史》
、《词曲史》、《词学研究法》、《词源疏证》、《校辑宋金元人词》等等均是词的体
制内研究的重要成果。
唐圭璋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的编辑印行更是这一队人马
中三十年代最辉煌的硕果,于千年词业功德无量,而龙榆生创办并维持了三年五个月的
《词学季刊》也是那段时期词学体制内派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传统的词学中人又忘不了传统词坛的雅事盛曲。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便
有结社填词的雅举,三十年代尤盛,如北京的聊园词社、趣园词社,天津的须社,上海
的沤社、午社、声社,南京的如社等等。
春秋佳日,或访花品茗,或揽胜寻幽,拈题限
调,放怀唱酬。
除了有组织的词社活动之外,三十年代各大学一时还都设置词学教授讲
座,如中央大学的吴梅、汪东、王易,中山大学的陈洵,武汉大学的刘永济,北京大学
的赵万里,浙江大学的储皖峰,之江大学的夏承焘,重庆大学的周岸登,暨南大学的龙
榆生,河南大学的邵瑞彭、蔡桢、卢前等。
一时还有“词学研究会”、“诗词函授社”
的发起,词学昌明,热闹非凡,“词的解放”的口号唱得很响。
从衣冠唐宋、雅词曲拍
里总难免透出阵阵发扬国粹、踵事增华的陈腐气息。
难怪进步的文化界与思想界要发出
严肃的批评之声,如郑振铎在《词的存在问题》一文中说:
“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
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
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的
产生!
……我将真为‘解放’两字一痛哭!
”又说: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
四印斋、双照楼、强村所刻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
为了
他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护皋比’而做‘大学教授’。
因此便梦想一个
‘词学昌明’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
”郑振铎指出:
“现在对
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帐的时代”,我们研究词,并不是为“昌明词道”,我们有必要用
“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才是词学研究的正道!
体制内外两派平行存在,各干各的。
体制外派忙于自己的旧文化批评与新文化建设
,相对宏观的文化眼光使他们的工作重心大都离开了词。
——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过
去仅仅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或山林雅士寄托怀抱的阳春白雪——词,这种狭隘的文学形
式呈开放型、大众型传播,变成为更多的人能制作运用并可充分反映时代新生活情趣的
文学样式,所谓“旧瓶装新酒”,旧瓶历久,酒则弥新。
体制内派依然严肃认真做着体
制内的功课,同声相求,音词切磋,职业情感涌起时也往往在词学刊物的“今词林”、
“今诗苑”栏目里陶写怀抱,锻炼技术。
不过体制内派的大学者也往往感受到了学术风
气的逼迫和时代精神的薰染,如龙榆生,他偶尔也移步出体制,站到了体制外的立场上
撰结诸如《两宋词风转变论》、《选词标准论》、《东坡乐府综论》之类的词学批评文
章。
又如赵万里,他精心完成了他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专门去请胡适作序,而胡适
在序中对体制内词学的优等功课表示了相当称赞的同时也对体制内作业的技术规格作了
相当严格的并且充满现代色彩的要求。
这也正可看出两派交流的历史痕迹。
胡适也正是在为赵万里作的序里提
出了“词与曲的分界”的宏观见解,又提出了“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的体制外口号。
其
实体制内外的人马早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表示出惊人的一致,如二十年代至三
十年代初有关敦煌旧藏唐人写卷《云谣集杂曲子》的校辑整理,王国维、胡适、朱祖谋
、龙榆生、刘半农、郑振铎都表示了一致的关心与重视。
胡适到晚年还在为这本写卷的
王国维、罗振玉、朱祖谋、龙榆生的“跋”写“按语”!
当然整体来说,在三十年代的大年历中,体制内外两派仍是各干各的,平行存在,
但是各自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想运行的轨辙倘作比较,其结论应该还是相当清楚的。
当
然“术业有专攻”,体制内派对词学的纯粹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术
影响一直保持到五十、六十年代,甚至八十、九十年代,成为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宗师
级人物,在诸个词学重镇,各领风骚。
五十、六十年代:
曲折演进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
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文化战线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
思想内容上的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估一切文学遗产的重
要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
服膺这些准则。
这些准则无疑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
新涌入词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厚今薄古”不仅是新思维
,而且是新机遇。
一批老词学研究家则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用旧思维、旧方法累积有年而
做出来的厚重成果,也开始尝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踉踉跄跄,左顾右盼地步入了
新的研究领域,企图跟上新时代。
——词学形成了一个曲折演进发展的新格局。
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五
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总结。
这篇文章对这个三十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估
价后指出了她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
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
这方面的问题暴露了文学评论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
并且直接导致了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泛滥。
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
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
尽管我们花了最大气力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