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尖措和他的舞团.docx
《万玛尖措和他的舞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万玛尖措和他的舞团.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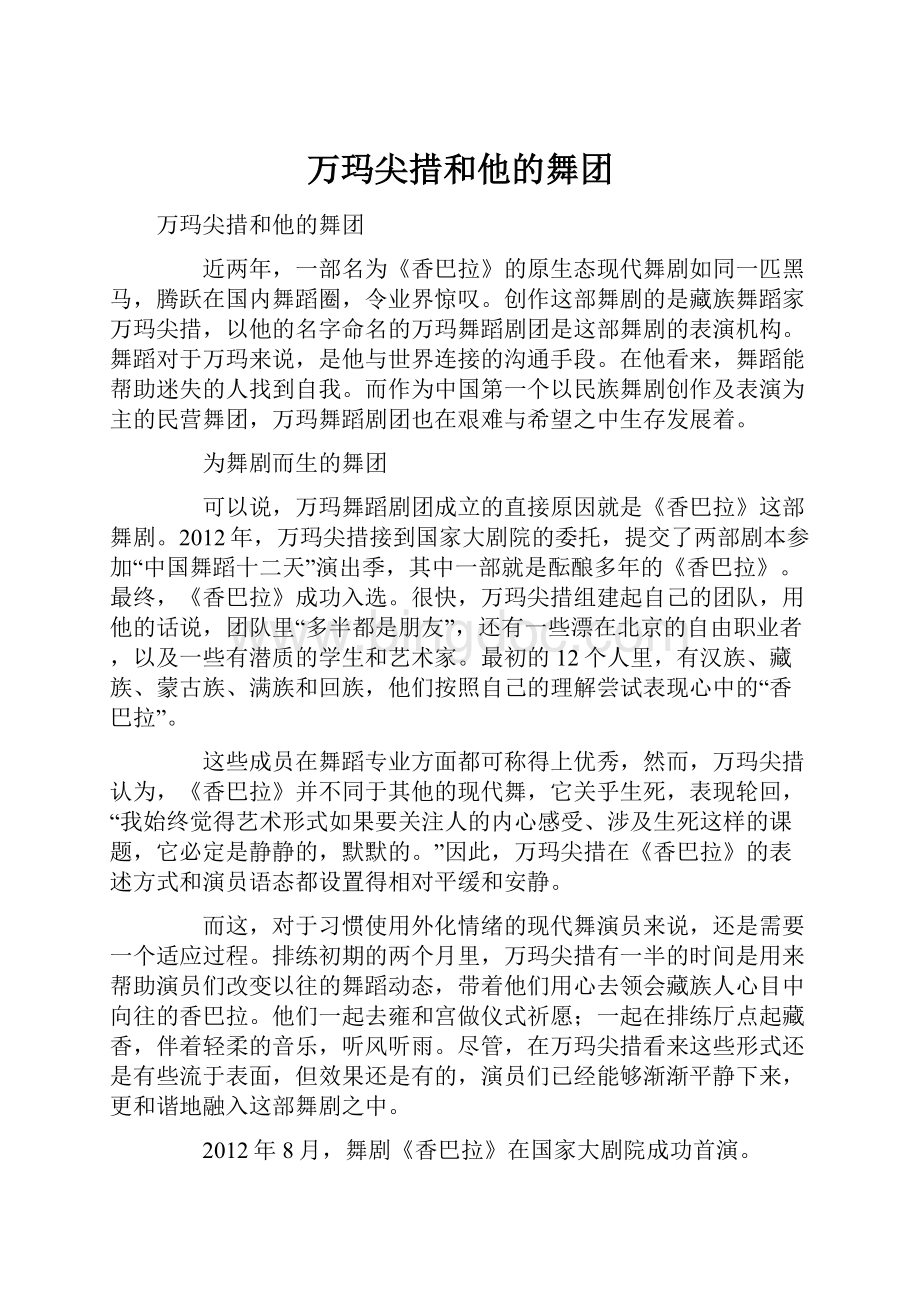
万玛尖措和他的舞团
万玛尖措和他的舞团
近两年,一部名为《香巴拉》的原生态现代舞剧如同一匹黑马,腾跃在国内舞蹈圈,令业界惊叹。
创作这部舞剧的是藏族舞蹈家万玛尖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万玛舞蹈剧团是这部舞剧的表演机构。
舞蹈对于万玛来说,是他与世界连接的沟通手段。
在他看来,舞蹈能帮助迷失的人找到自我。
而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舞剧创作及表演为主的民营舞团,万玛舞蹈剧团也在艰难与希望之中生存发展着。
为舞剧而生的舞团
可以说,万玛舞蹈剧团成立的直接原因就是《香巴拉》这部舞剧。
2012年,万玛尖措接到国家大剧院的委托,提交了两部剧本参加“中国舞蹈十二天”演出季,其中一部就是酝酿多年的《香巴拉》。
最终,《香巴拉》成功入选。
很快,万玛尖措组建起自己的团队,用他的话说,团队里“多半都是朋友”,还有一些漂在北京的自由职业者,以及一些有潜质的学生和艺术家。
最初的12个人里,有汉族、藏族、蒙古族、满族和回族,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尝试表现心中的“香巴拉”。
这些成员在舞蹈专业方面都可称得上优秀,然而,万玛尖措认为,《香巴拉》并不同于其他的现代舞,它关乎生死,表现轮回,“我始终觉得艺术形式如果要关注人的内心感受、涉及生死这样的课题,它必定是静静的,默默的。
”因此,万玛尖措在《香巴拉》的表述方式和演员语态都设置得相对平缓和安静。
而这,对于习惯使用外化情绪的现代舞演员来说,还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排练初期的两个月里,万玛尖措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帮助演员们改变以往的舞蹈动态,带着他们用心去领会藏族人心目中向往的香巴拉。
他们一起去雍和宫做仪式祈愿;一起在排练厅点起藏香,伴着轻柔的音乐,听风听雨。
尽管,在万玛尖措看来这些形式还是有些流于表面,但效果还是有的,演员们已经能够渐渐平静下来,更和谐地融入这部舞剧之中。
2012年8月,舞剧《香巴拉》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
一篇名为《madeinShambhala》的日记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称“香格里拉”,意为自由净土、极乐天堂。
万玛尖措表示,在每一个藏族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香巴拉。
而他从小就对这一概念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
万玛尖措出生在青藏高原青海省黄河岸边一个名叫卡里岗的小村庄,那里民风淳朴。
由于父亲是镇上文工团的团长,万玛尖措从小就在文艺大院里生长。
大院里的生活氛围在原本就民风淳朴的家乡显得更加单纯。
每个家庭的父母都是同事,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好像是所有家庭的孩子。
在万玛尖措最初的记忆里,自己可以随意到大院里任何一家去蹭饭,甚至住上一个星期再换一家去住,许久不回家父母也不会担心。
在大院里,人们都管万玛尖措叫“老天爷的儿子”,五岁时,他问父亲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叫他,父亲只说了一句“因为你生活在香巴拉里,你就是老天爷的儿子。
”那是万玛尖措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香巴拉”这个词,尽管对它的概念很是懵懂,但吃百家饭被众人宠的感觉让他直观地明白,“香巴拉”代表着幸福。
10岁那年,万玛尖措在父母的带领下参加了一场天葬仪式。
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人从有到无消亡的过程,那场景对于年幼的万玛尖措来说,算不上是触动,只是纯粹觉得恐怖。
回家的路上,妈妈的一句话安抚了受到惊吓的小万玛――“刚才那个被天葬的人其实很幸福,因为他去了香巴拉。
”对于“香巴拉”的憧憬,让之前经历的恐惧瞬间笼罩上一层美好。
最终,高中时代的一篇日记成为创作舞剧《香巴拉》的灵感。
“那篇日记名为《madeinShambhala》,记录了当时我的一些小情绪,其中涵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和责任感。
”万玛尖措回忆道,在2001年已经上大学开始进行舞蹈创作的他,偶然翻出了那篇日记,备受启发,于是,将自己对香巴拉意象的理解和那些小情绪整理成一个小文本。
从此,要创作一部有关香巴拉的舞剧就成为万玛尖措的愿望。
大学时代创作的小文本被他不断添加内容,扩充元素。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还不足以去触碰如此宏大的主题。
”因此,万玛尖措迟迟没有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践,他认为自己还需要更多的积累与沉淀。
直到十一年后的2012年,在国家大剧院,万玛尖措的夙愿总算得以了却。
回归“大地的舞者”
其实舞剧《香巴拉》的排练并非事事顺利。
中途,万玛尖措和演员们都陷入了追求表面平静的误区,每天通过各种形式去营造安宁氛围,这对习惯夸张表达、情绪外露的演员们来说已近乎一种枯燥的折磨。
而那时的万玛尖措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最初想要表达的主题,担心观众是否能接受。
这样的状态让他果断停下了排练,回到家乡。
或许,人在迷茫焦虑的时刻首先想到的都是回家,那里可能并不一定会为你提供解决方案,至少,能让你觉得踏实,有安全感。
回到家乡的万玛尖措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青海湖转湖祭,他开着车带着父亲沿着圣湖行驶。
一路上,父子俩默默无言,父亲当然知道儿子一定是遇到困惑了,然而他也知道,跟自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儿子同样固执倔强。
父子俩每次就舞蹈创作进行探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他明白,自己和儿子此刻需要的只是彼此的陪伴。
转湖的路程开了一半,万玛父子遇到了另外一对转湖的父子――父亲一步一叩首地磕着长头,儿子拉着装满家用的板车。
不管身旁的汽车如何飞驰而过,这位父亲始终平静地延续着自己的行为,儿子则快乐地赏花听鸟。
他告诉万玛,他们已经磕长头转湖两个多月了。
问他一路上苦不苦,答不苦,很开心很充实;问最怕什么,答就怕不能继续。
一问一答间,万玛尖措仿佛开悟了,他感觉自己看到了舞者的内心,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平静祥和,那是信仰的力量。
这次的偶遇让万玛尖措恍然大悟,什么是舞者?
在他看来,这位磕长头的父亲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舞者。
因为他心里有爱和信仰,而且他还有儿子和一路上帮助他们的人的爱跟随。
从技术层面来讲,他的舞台就是这片大地,他的背景就是蓝天白云,而他的灯光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
万玛尖措终于明白,只是从表面上要求演员动作要慢下来静下来,是治标不治本的。
最关键的是人的内心,你的心到底有没有真正平静下来,舞蹈是不会骗人的。
他把自己在青海湖边拍摄的那对父子的素材剪辑成一个短片,放给演员看过之后,那位“大地舞者”的身体力行远胜过万玛尖措一遍一遍的指导。
内心受到震撼,接下来的排练就顺畅了。
如抽象画派的静默舞蹈
在这部返璞归真的舞剧中,没有主角,甚至没有明确的主题。
唯一的隐性线索就是一位穿白衣的小沙弥,这个有着与生俱来善心的孩子成为串联着整部舞剧,而这条线索也是若隐若现的。
舞剧中有着这样的情节:
小沙弥用自己化缘得来的盘缠换回一条鱼,他想要将这条鱼放生,结果鱼却死在了半路上。
从此,小沙弥便走上救赎之路。
万玛尖措说这段情节的设置灵感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小他都要跟随父母把鱼放生,小时候是放生在家附近清澈见底的河流里,如今退休的父母搬到西宁去住了,每年放生的环节还是不能遗漏的,只是,面对城市中被污染的河流,万玛尖措实在想不通这究竟是对鱼的救赎还是对它们在造孽。
这样的思考被引入舞剧《香巴拉》,在人生路上类似的困惑让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小沙弥,永远走在探寻与思索的路上。
“《香巴拉》并不是一部传统的叙事性舞剧。
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深刻的信仰文化和生死观,传递的是人性共通的东西。
”万玛尖措希望与受众建立一种平等的观演关系,以开放式的结构引发受众自己的理解,从而完成对作品的解构。
“这部舞剧就像一幅抽象派绘画,你能看到浓烈的色彩和饱满的情绪,但它要表达什么,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在这部有别于传统藏族舞剧的《香巴拉》中,你看不到印象中夸张的动作、喧嚣的音乐、华美的服饰以及绚丽的布景,只有模拟传统藏族舞蹈的简洁动作、棉麻质地的素色藏服和直接取自牧区的道具,配乐也都是采自民间的音乐片段,很多时候音乐褪去,只听到舞者沉重的呼吸声和细碎的脚步声。
静静默默地,于无声处将人带入一种思索的情境。
舞台上最炫目的也就是在舞蹈之前就在绘制并贯穿舞蹈始终的沙画坛城,最终舞者在沙画上翻滚腾挪,将其毁坏殆尽,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藏族老百姓在田间地头跳的舞蹈并不像之前舞台上呈现的那么花哨,穿得也没有那么鲜艳。
”对此,万玛尖措解释说,“我只是把最单纯的藏族舞蹈带回它的本源。
”于是,西藏传统的弦子舞、金刚舞都能在《香巴拉》中觅到踪影。
而舅爷亲手做的面具、从藏地牧区收集来的生活用品、民间艺人提供的鹰笛都成为《香巴拉》的质朴道具。
民营舞团的尴尬
《香巴拉》继2012年应邀首演于国家大剧院,随即先后应邀参加美国纽约与芝加哥艺术节、香港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国际艺术活动,今年8月还亮相韩国国立剧场。
目前,该剧已在国内外多地演出近30场,观众反响热烈。
这让万玛尖措既骄傲又欣慰,然而舞台面临的困境还是不可回避的。
对于民营舞团来说,资金缺乏简直成为胸口永远的痛。
万玛舞蹈剧团在创办之初也时常为此焦虑。
即便发展至今,舞团已经积累了一些固定的受众群体,并且也有相关赞助扶持,万玛尖措和舞团其他成员依然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无论是演出道具还是各项支出,一律能省则省。
现代舞剧《香巴拉》借由万物生灵探讨生死轮回,通过朴素至极的本体表达,极美的舞台呈现和视觉冲击,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和对话中,传达深刻的藏传佛教哲学思辨。
剧中使用的很多道具都是万玛尖措直接从牧区收集来的,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道具不仅让宏大深刻的主题接足了地气,也节省了一笔开支。
此外,万玛舞蹈剧团的12名演员全部都采用项目签约制,既节省成本又提高效率。
舞剧中最经典的一个道具就是高大的九头神面具,万玛尖措说那是他80多岁的舅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亲手制作的。
万玛尖措也经常寻摸可以利用的物件自己做道具,他笑称这样:
“既省钱效果也好。
”整部舞剧中最大的成本就是贯穿全场演出的沙画坛城绘制,“那些彩砂每场都需要一两千的成本。
”
尽管动动脑筋也能适应资金缺乏的现状,然而万玛尖措的一些想要让《香巴拉》给观众留下更深刻印象的细节创意,却无力实施。
2013年3月舞剧《香巴拉》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时,工作人员为每一位观众发放了用传统藏纸印制的精美节目单,原本想将这一创意延续到以后的每一场演出,终因成本太高只得作罢。
万玛舞蹈剧团目前的主要收入是到各地商演收取的门票钱,用万玛尖措的话来说,“只能算少有盈余”。
2013年,舞剧《香巴拉》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多个城市进行了南中国巡演,总共25场演出,观众反响热烈。
正是这些观众对《香巴拉》的热情支持,也让一些商家有兴趣对这部舞剧进行赞助。
尽管缺钱,万玛尖措对于赞助商的筛选还是有自己的原则,“我愿意和跟藏文化相关的企业合作,或者至少它的负责人要对藏文化有基本的了解。
”万玛尖措认为,这样的企业才会对这部具有西藏元素的舞剧怀有尊重之意。
否则,他宁可自己东筹西凑,也不愿放弃原则接受赞助。
今年8月,舞剧《香巴拉》赴韩国交流与演出,通过了韩国国立剧院严格审核,获取在该剧院演出交流的宝贵机会,这意味着可以免除几十万人民币的场租费,让《香巴拉》在这座全亚洲最早的国立剧院上演。
这既让万玛尖措兴奋也让他犯愁,因为,场租费免除了,舞团里一大帮人往返韩国及在那里停留几日的费用还没有着落。
最终万玛尖措从几位朋友那里筹到了10万元的个人赞助,才得以成行。
“这些钱都是纯帮忙的,不具任何商业回报。
”万玛尖措对于朋友的慷慨解囊十分感谢。
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舞剧创作及表演为主的民营舞团,万玛舞蹈剧团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之中生存发展着。
《香巴拉》必须要归根
好在,舞剧《香巴拉》的大获成功让万玛和他的舞团看到了希望。
老实说,一开始,对于这样一部以原生态藏族文化元素结合现代舞艺术表现形式的舞剧,能够受到观众的认可,连万玛尖措自己心里都没底,他尤其担心自己的藏族同胞接受不了。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还是在韩国首尔,抑或是2013年《香巴拉》所进行的“南中国巡演”,观众的高度认同让万玛尖措倍感意外,也消除了他之前的顾虑。
此前,生长于青海的万玛尖措曾两次来到过西藏。
一次是2007年参与大型民族歌舞剧《幸福在路上》的创作,另一次是2010年到拉萨拍婚纱照。
万玛尖措说他要将人生大事完成在心中的精神高地。
在万玛尖措看来,每个藏族人心中,西藏,拉萨,都是香巴拉的具象呈现。
那里是心中的圣城,是幸福的所在。
“《香巴拉》也一定要到西藏去演出。
”今年下半年,万玛尖措的工作重点是创作筹备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部剧目。
此外年底到法国的演出也在洽谈中。
万玛尖措透露,《香巴拉》来西藏演出的计划定在明年,同时,还将在西藏、青海、云南等地拍摄这部舞剧的微电影。
他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打算将《香巴拉》在拉萨长期驻场演出。
尽管目前舞团还面临着很多艰难,但万玛尖措从来没有放弃过弘扬藏族文化,传承藏族文化遗产的想法。
在他创作的舞剧《香巴拉》中,藏式面具和鹰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纷纷呈现。
万玛尖措说他正在寻找合适的场地,准备在北京建一个非遗小剧场。
对于这个非遗小剧场,万玛尖措有着自己的设想,“白天用来做培训,从西藏、青海等地请来与藏文化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来教对这些感兴趣的人做藏式面具、鹰笛、藏纸等,还可以学唱格萨尔说唱,学画唐卡。
”晚上会有一小时左右的舞蹈及非遗项目展示的演出,演出之后还要开设小论坛,为观众提供交流平台。
万玛尖措说这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操作起来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就是资金的筹集,他打算采用申请艺术基金和众筹两种方式来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而请来西藏等地的老艺人,万玛尖措倒不觉得不好操作,“即便他们不习惯长期在内地生活,隔段时间请他们过来进行一次培训或演出还是可行的。
”
未来在万玛尖措心中始终还是充满希望的,《香巴拉》已经在那里了,慢慢将会打造成一个品牌力作,而心中的香巴拉永远都在指引着他向着梦想进发。
况且,目前在国际文化艺术领域,对非体制院团创作和演出的扶持已成为大国文化姿态,同时也是国家文化关怀和民族复兴的新趋势。
万玛尖措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