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农大 过去 未来与发展Word下载.docx
《川农大 过去 未来与发展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川农大 过去 未来与发展Word下载.docx(8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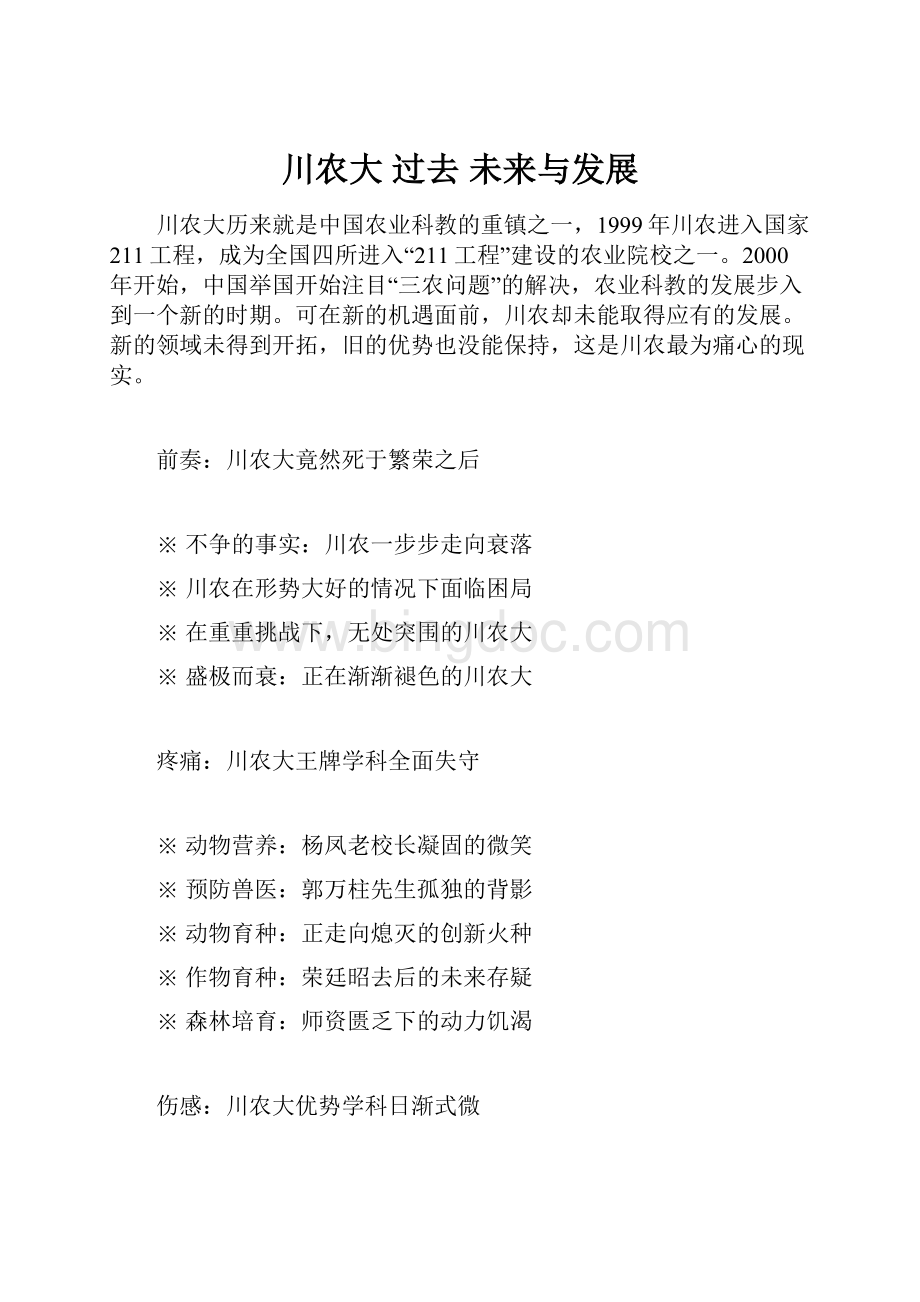
师资匮乏下的动力饥渴
伤感:
川农大优势学科日渐式微
※影子学科:
主流学科下的蜗行
※预备学科:
老而不强下的尴尬
※补充学科:
找不见真正的希望
※自设学科:
看不见真正的未来
※新兴学科:
在市场化下的亮光
※悲喜交加:
百年川农大的15个足迹
(1)不争的事实:
凡是了解川农发展史的人,如果看看今天的川农,再看看周围的环境,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够发现,川农大真的正在衰落下去。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无论我们辅以多美漂亮的数据,多么美好的说辞,也无法否认这个略显残酷的事实。
从上世纪初叶就一直引领中国农业科研和教育走向,并且在多个领域主导全国创新趋势的川农大,突然在进入新世纪后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很快陷入沉默!
作为一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学习、工作了较长时间的人,我们怎么能够继续保持沉默,继续过一种安身立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生活?
而且,随着山东农大、华南农大、湖南农大、福建农林、沈阳农大等后起高校进一步崛起的势头不断上升,那么,躺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复述上一代辉煌的川农还会更加悲剧。
当然,我无意、也不敢将老一辈人辛苦拼下的基业和辉煌全盘否定,我只是想更加深入地关注、揭示、思考和探讨眼前发生的事实,但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虽然凭借老一辈川农人为川农取得的积累,在未来很多年,川农仍将是农业科研和教育的重镇之一,虽然目前的川农依旧在有限的学科内保持着一定的优势。
但是面向未来,川农的这些优势能否长期保持,已经存在着巨大的疑问。
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川农不始终保持惊醒,那么用不了多少年,也许川农将成为一个“地大”(校园规模扩大)“物博”(学科数量增多)“人多”(在校学生规模庞大)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资本炫耀的高校。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的?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川农是一个“一次性”的产品?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川农和历史上的川农?
川农发生的一切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笔者一介村莽,在川农生活、学习、工作已有多年,我将力图用最全面、最深入,也是最尖锐的眼光来做一些描叙。
希望阅读此文的人,能够借助我粗鄙的笔法,了解和关注川农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现实、故事来自于笔者的了解和理解,尤其在事关部分学科或者翔实数据方面,难免有所纰漏。
但我的目标,只是为了进一步剖开我们的川农,使得人们真正认识川农,看清她的五脏六腑以及机体的真正运作。
眼下的川农,是个病得不轻的病人。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需要有勇气直面疾病。
川农不缺人才,不缺气魄,真正欠缺的,正是这种正视问题的勇气。
好在今天的川农依然有药可救,离真正的病入膏肓,还有很远的距离。
(2)川农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面临困局
1906年,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宣告诞生。
在随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这所成立诞生在仓库中的学堂在“兴中华之农事”的号召下,奇迹般地在短时间一举崛起为中国农业科研与教育的一面旗帜。
她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从中等学堂升格为高等学堂,并与法政学校、工业学校、外国语学校、国语学校一起成为省内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后来这五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在20世纪盛极一时的国立四川大学),之后与川大几度分合,却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
五十年后的1956年,在院系调整的风浪下,老一辈川农人从西南文化教育中心成都搬迁到偏僻的雅安独立建院,由此开始了川农长达五十年“拓耕荒陌,茹毛饮血”的创业之路。
川农一度被拆分为农、林两院办学,林学院甚至南迁西昌并中断办学,这些险些中断川农大的沧桑薪火。
但他们从未屈服,杨开渠、刘志农、夏定友、彭家元……在他们的呵护下,川农得以延续下来,撑到了文化的春天。
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借助老一辈川农人的积累,以作物遗传育种和动物营养为核心的学科体系开始得到重建和形成,并很快结出硕果。
在“解冻”后的第一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川农一举揽得五项科学大会奖,并在1981年作为合作单位与袁隆平一起取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这只是个开头,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川农在每年的国家三大奖项(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这代表着中国目前在硬科学方面的最高水平)方面屡传捷报。
在1988年、1990年更是历史性地实现了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蝉联。
与此相呼应,川农在1985年正式升格为大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校名。
此后,一大批农业科研与教育的大师开始向川农靠近,一大批科研院所得以建立和发展。
很快,川农的动物遗传育种、预防兽医、森林培育等学科再度崛起在传统的文化中心之外,在全国农业领域傲视群雄。
川农在1996年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正式步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
可此时的川农已经暮气沉沉,川农的第一批拓荒者或已不在人世,或已白发苍苍。
可以说,21世纪左右的川农步入到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进入211工程的余温尚未退却,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进入到新的热潮——然而川农在这样的浪潮中,却未能取得第二次辉煌,而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渐渐落寞。
当山东大学和华南农大通过学科建设逐步崛起,当西北农大和西南农大通过院校重组迅速突围,川农已经残酷地被边缘化。
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川农未能抓住机遇,却被挑战打败,陡然面临着困局。
千万条理由,千万条辩解,都无法掩饰川农在国内的地位逐步下滑的现实。
虽然时光荏苒,川农也在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但问题在于,我们发展的速度始终赶不上时代的步调,而结果只有一个,我们已经逐步落后于时代。
在科研成果方面,川农在老一辈川农人之外再也没能诞生任何一项拿得出手的成就;
在学科排名方面,川农的传统优势学科全面倒退,而新兴学科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在综合排名方面,川农早不仅被中国农大、华中农大等传统老校越甩越远,也被西北农林、山东农大等后起之秀逐步超越。
可以说,川农所面临的危机,并非一般的危机,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甚至是方向性的危机。
按照现在的状态,川农似乎不再给真正的创新力量以机会,而骄傲的创新力量自然也不会给川农任何机会——那些从20初就形成的良性增长周期正在走向衰亡。
似乎游戏就是如此简单,而规则竟如此明了。
川农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群朴实的农民改造并且征服自然的历史,是人们不断尝试、不断学习、彼此尊重、共同创新的历史。
实际上,川农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值得赞誉。
可惜,曾经朴实的农民在开辟出第一代的收获季节之后,却突然在风调雨顺的年月里失去了勤奋的精神,甚至变得懒惰。
难道川农是一座一次爆发的死火山?
或者是一座活火山,可是,她的休眠期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3)在重重挑战下,无处突围的川农大
川农的逐渐边缘化,我们首先可以从西部之争看出端倪。
长期以来,西北农大、西南农大、四川农大这三所农业院校,代表着西部农业研究与教育的最高水平。
二十年前。
在这三所院校的竞争当中,川农屡屡占据上风。
有人说“西北西南,都不比四川;
杨凌北碚,都难及雅安”——意思是在农业研究与教育方面,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农大与陕西杨凌的西北农大都赶不上位于四川雅安的四川农大——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却形象地说明了川农的分量。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川农在西部农林院校当中,第一个进入211行列。
而今天,时局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不要说西部第一,就是说第二都很难找到依据。
眼下的川农在西部只好勉强在新疆农大、甘肃农大、云南农大、内蒙农大等院校之上寻找优势,成为一个“与名称的地域所相称的地方农业院校”。
1999年,西北农大领衔七大院所重组,建立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并乘势闯进国家985工程、211工程,远远地将川农抛在了身后。
2006年,西南农大与西南师大实现合并,成立了西南大学,进而进入国家211工程。
在农业院校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下,杨凌凸起为“中国农业硅谷”,北碚整合为“西南高教航母”——而此时的川农,却拿着“九五”上亿的经费(四川省7500多万,国家划拨与自筹接近3000万),在雅安这座小城里日渐式微,逐渐平庸化。
如今的川农,居然沦为了一个靠着“四川唯一一所农业211工程院校”,“四川五所211工程院校之一”,“全国6所211工程农业院校之一”等广告自我麻痹的大学,日渐失去了进取心。
一步步成为了盆地中的老大,却成了全国的盆地。
当然,川农走下西部第一的神坛,对全国的农业科教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多校并进的多元化格局可以更好地优化教育与科研的链条,从而更好地推进农业科教的发展——但很显然,谁都不愿意是这个链条当中最“掉链子”的那一个。
对于川农的衰落,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慰藉自己,更无法找不到任何话语来为衰落开脱。
面对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压力,川农的回击居然苍白到无法言喻——最典型的便是在都江堰合并了省林业学校,成立了分校。
盲目求大,只会给科教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危险,这是教育发展的规律,川农却逆势而动。
如果说西南农大与西北农大的突围,得到了国家动力的强势注入和支持,使得他们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从而实现了对川农的现实超越。
那么,川农在省内的竞争又该作何解释?
2004年,四川大学爆出消息,将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在绵阳建立现代农学院。
这个消息让川农人倒吸一口凉气——此前已有先例,四川大学新建设的计算机学院,在国家重点学科的层面,居然将传统的电子科大挤掉——川农显然不愿意复制这样的案例。
作为某种回应,川农再度求大,宣布在温江开建科学研究院。
川农的成都科学研究院,至少成功地扼杀掉了川大试图蚕食川农的“地盘”的企图——但从长远来说,如今数年过去,川农的温江校区实际上也只是停留在图纸上,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实际上发展温江校区,川农已经力不从心。
新一届领导班子再次启动温江校区,我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是新一轮扩张的序曲。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
成都研究院的顺利开建,更多的是响应了当年成都市力图将温江建设成现代农业的“西南硅谷”的策略。
可是眼下温江早已不注目农业,而是发展第三产业,“农业硅谷”的口号已经成为历史,川农似乎也失去了出口。
当时的川农大舍近求远,雅安的农业科技园并没有引起川农的关注(当然,这与川农与雅安素来僵化的校地关系有关),如今雅安农业科技园虽然已经成为了川农与雅安合作的国家级高新园区,但这样的合作既缺少健全的机制,又缺少常态的平台,这样的合作显然没有实质性,只是徒有虚名。
川农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而且还将继续,川农身处困局,眼前是迷局,如不突围,将在第二个百年黯然失色,悄无声息。
追思川农的衰落,可能会列举出很多的原由,如地理环境条件制约,学校性质,经费投入,管理体制机制等。
地处雅安,是川农的隐痛,56年迁雅,非川农人所愿,但扎根50多年,失脱几次搬迁机遇的川农也很难有什么大的动作;
至于学校性质,更是难以改变,不管改成什么校名,除了花哨,恐怕本质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川农仍是以农为本的院校,其实,学科没有贵贱,只有水平分高低,贡献分大小。
与其怨人尤人,不如冷静思考,真行实干。
上帝从不喜欢怨儿,机遇从不降临自弃之人。
川农要发展,关键是靠自己,这是百年川农历史的经验,也是川农精神的核心,艰苦朴实和奋斗创造,一直是川农人的强项。
(4)盛极而衰:
作为一名在川农生活、学习、工作了多年的人,我不能不对川农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忧虑。
如果眼下的川农不猛醒,老一辈川农人辛苦拼下来的传统和基业,或将消失殆尽。
并且那些可能让川农重新迸发生机的源泉,也将很快枯竭。
在东北,东北农大的脚步已经超越川农;
在华北,中国农大已经彻底将川农抛在脑后;
在中原,山东农大已经将川农扔在身后;
在华东,浙江农大已经并入浙江大学并走向坦途;
在华南,华南农大已经将与川农的差距缩小;
在华中,华中农大已经将川农抛开;
在西北,西北农林已经跟川农拉开档次;
在西南,西南农大也早已实现突围——试问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脸面去擎起“兴中华之农事”的大旗?
回望历史,川农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
在动物营养、作物遗传、动物育种、预防兽医、森林培育甚至是原子能农业这样的领域独步天下,睥睨群雄——而今天,在群雄逐鹿华夏的时代,曾经小而精的川农却在盲目追求大而全的过程中倒下,并且逐步走向衰落。
不进则退,如果川农依然不为所动,沿着同样的思路和心态继续坐在盆地的小城里望着头顶巴掌大的天空而沾沾自喜,那么川农注定为成为夜郎之国,井底之蛙!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出了出了两位院士,六位国家杰青,六位长江学者;
全川的基层乡镇领导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从这里走出;
在国家历年来在三大奖项的评选结果中,川农大占有其中的16项(仅计算二等以上)——这完全是让人咋舌的数据。
曾几何时,我们敢号称动物营养学的黄埔军校,也敢号称中国西部(南部)育种研究中心,同时也能在兽医、林学领域叫板任何一个院所。
让人忧虑的是,今天的川农却在一步一步走向虚无,甚至是虚伪!
随着进入211之后的大规模扩张,使她离真正的学术圣地越走越远,也一步一步滑向世俗的深渊。
近些年来,川农的三大趋势让人痛心疾首:
大楼越建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学生越来越多,大器越来越少;
官员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这些因素都严重阻碍着川农大进步入一流水平,如不改进,川农或将盛极而衰,草草收场。
今天的川农,面对着太多太多的问题,市场化的冲击,行政化的捆绑,僵化的运行机制,自大的盆地意识,严重的人才断层,生硬的师生关系——一环套着一环,如今的川农大已经面目全非。
今天的川农大不再是优秀学子追求的朝圣地(学生稀缺),更不是农业大师云集的根据地(大师出走),甚至也不是农业市场的首选依托(就业难题)——那么,川农大究竟能够成为谁的川农大?
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大事的离去和后继无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川农不给人才甚至是偏才、怪才以任何机会,如果……没有太多的如果,今天的川农,似乎已经沦为一座充满了沮丧、失望、抱怨的“围城”,与当年对川农趋之若鹜的人才流相对比,眼下的川农“逃离”竟然成为了最为热闹的场面。
二十三年前,我的恩师如此给予我告诫:
“川农的未来终究还要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待。
这样的期待并不高,我们只希望你能再有一天真正以川农为豪。
只要你愿意为川农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能量,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
在这样的愿望之上,我们似乎从大一进入学校那天开始就充满了斗志,甚至老师的卧室都能够成为我们相互交流、沟通甚至是论战的场所,进而真正明了自身对于知识的潜质,以及对于学校的历史和未来的关注。
让人伤痛的是,在今天,一个充满希望和创新的川农却在褪色甚至消失。
可是这样的色彩一旦褪去,或许将永远不能归来!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描写了一个神秘、怪诞而又似曾相识的地方,城堡既不神奇,也不高贵,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
但文中的主人公对此却可望而不可及,直到死也没能进入城堡的核心。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川农大,但它的传统却没被我们继承,她依旧是我们的城堡,可望而不可及。
(5)动物营养:
在川农的拓荒者中,有一位至今健在的老人,他的名字在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当中,已经十分陌生。
他的名字叫杨凤,川农终身名誉校长,在他的90寿辰的时候,学校还专门为他举行了学术研讨会。
杨凤先生是国家级杰出专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动物营养研究的学者之一,更是国内动物营养学科的奠基人。
在第一代进行动物营养研究的学者当中,杨凤先生的能力处于巅峰。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所领导的川农动物营养学从一诞生就光华夺目,熠熠生辉。
川农的动物营养学科早在1984年就成为博士点,在1989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的动物营养学类国家重点学科,也是唯一的一个。
于是,川农的动物营养学走上“天下第一”的宝座,并号称领域内的“黄埔军校”。
到目前为止,川农的动物营养学科依旧是最为强大的学科之一。
这个学科实力很不错,目前有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中心、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名教育部“百千万”工程人选、1名教学名师、1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由长江学者雷新根领衔组建的未农中心,对动物营养学科的整体带动力十分微弱,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窗口。
只是川农的动物营养学在学术近亲繁殖和地狱偏离文化中心的情况下,逐步走向衰落。
杨凤先生超越学术建树期淡出后,一度出现后继无人的尴尬。
失去杨凤之后的动物营养刚刚失却“人和”,接着在争取动物营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过程中负于“地利”——最后被后起的中国农大和东北农大超越。
负于中国农大的表征比较显著,尤其以2005年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中国农大(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为甚——那标志着动物营养研究中心的北移。
此时,该重点实验室的主要领导者张子仪已经成为院士。
实际上,中国农大对川农的超越首先得利于“地利”,这是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
至于东北农大,川农更多地失却于人和。
在“后杨凤时代”,新一代接班人未能接下杨老先生留下的重任。
除了在1997年作为第二单位获得了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之外,十多年中,稀有建树。
而东北农大则不一样,在第一代人(以许振英为代表)谢幕之后,单安山教授很好地担负起了责任。
东北农大的动物营养学2002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实现了对川农营养学的追赶甚至是超越。
因为就川农的动物营养学科而言,眼下几乎没有人能够与单安山的科研能力相抗衡。
虽然陈代文是个很棒的学者,而且他在受命后也的确给川农的动物营养学科带来了很多非常积极的影响,也初步扭转了川农动物营养学倒退的趋势,但长远来看,营养学科的发展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在川农之后,南京农大、浙江大学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下一个谁会实现对川农的又一次赶超?
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在杨凤先生的90诞辰的时候,晚辈专门拜会了杨凤先生。
难以想象,这位开拓了川农的动物营养学的历史并且创造了辉煌的老人,在这样的高龄对动物营养学的学科发展状况依旧了若指掌。
他说,现实来说,中国农大已经领先,但我们还有机会,因为四川是个生猪养殖的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走在前沿,希望每个人都要珍惜这样的条件,不要抱着面前的金子去追逐远处的瓦片。
话及于此,先生的表情十分严肃,就连他和蔼的微笑,看起来都已经凝固。
资料:
动物营养所简介
动物营养研究所前身是四川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家畜饲养教研室,1962年建立四川农学院畜牧兽医系饲养营养研究室,1986年成立动物营养研究所,为正处级建制。
本学科点196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9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9年批准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设岗单位,动物营养与饲料工程实验室批准为四川省重点开放实验室。
2000年所在一级学科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2001年再次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
2005年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雷新根领导成立“未来农业与人类健康研究中心”,同年“猪抗病营养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
2007年又一次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并立项建设“动物抗病营养生物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和“动物抗病营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饲料工程中心”和“动物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研究所现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32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6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0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6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5人,后备人选5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1人,国家教学名师1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5人。
此外,有动物营养生理、动物营养代谢疾病、微生态营养、饲料生物技术、动物营养分子生物学等兼职教授9人。
2007年,本教学科研团队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学团队,首批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6)预防兽医:
预防兽医是整个川农兽医学科体系内最强的核心学科。
老实说,川农的兽医一级学科的发展,都建构在预防兽医的发展之上。
兽医一级学科下的三大二级学科,川农的基础兽医学力量微弱,临床兽医学力量几乎空白,只有预防兽医是最有发言权的。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期,川农集中了整个西南地区的畜牧兽医力量。
成为西部地区最优秀的兽医人才队伍。
当时的预防兽医学科有两位大师,一是陈之长,一是夏定友——他们均是预防兽医领域内享有盛誉的学者。
对比川农其他学科的停滞,预防兽医的学科建设还是值得称道的。
预防兽医学在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发展较为缓慢。
在1995年和2005年左右,川农的预防兽医学产生了两个高速发展期。
动物生物技术中心在1995年被批准为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预防兽医学在1996年成为重点学科,随后川农进入211工程,预防兽医学成为发展最为显著的学科之一。
进入211工程之后,川农的预防兽医纳入到了核心的发展规划当中,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2001年预防兽医学在成为硕士点20年后取得突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4年,动物疫病与人类健康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落成,预防兽医学科被列为四川省重中之重学科;
2005年,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落户川农。
实际上步入新世纪一来,川农的兽医学的发展,可能与文心田教授主政川农有着一些微妙的关系。
摒弃这样的背景不提,即便川农的预防兽医在2008年辈增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也依旧掩饰不了学科的脆弱感。
一个曾经西部第一,却苦等了20年才完成从硕士点到博士点转型的学科;
一个投入经费高达3000万,却只在2008年获得了一个重点培育的学科;
一个后继乏人,越来越迷茫的学科——这就是川农的预防兽医学,或者说整个兽医学的现状。
预防兽医的第一代人陈之长教授与夏定友教授均已辞世;
第二代领军者郭万柱已经淡出教学科研舞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乃是第三代人。
崔恒敏、文心田教授两人曾是不错的学者,但受行政工作之累,科研能力业已下滑(崔恒敏教授前不久甚至爆出学术不端的消息);
汪开毓教授在鱼病研究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建树,但鱼病研究并非川农的主流学科,他的能力尚不足以为川农的兽医学开辟空间;
王红宁确实是川农近年来最好的青年学者,很有可能获得国家杰青,但已经跑到川大生命学院任职——余下来的便是程安春和汪铭书这对夫妇。
老实说,川农的预防兽医,不得不感激程安春教授和汪铭书教授的存在。
正是他们的惨淡经营,才使得预防兽医学的旗帜虽摇摇欲坠,却从未倒下。
值得一提的是,程安春教授与汪铭书教授不仅仅是学科中坚,同时还都是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的学科带头人,也都是川农培养出来的继任者——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被报道成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在青年接班人当中,杨光友和邓俊良的水平最高,是川农的兽医学科未来的接班人,也是希望所在。
颜其贵曾经是个具有很高创新能力的青年学者,但近年来囿于体制原因,逐渐陷入沉默。
似乎在中国的国情之下,个人英雄主义远要高于团体主义。
预防兽医学科的发展验证了这一点——在兽医学科中的1项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也是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其他4项科技进步奖上,核心主持者居然都是郭万柱。
无疑,正是曾经候选院士、研究了中国第一个动物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的郭万柱教授撑起了兽医学科的天空。
然而当郭万柱教授离开之后,核心的真空再也找不到人来弥补。
郭万柱教授淡出后的这几年,整个兽医学科一直沉溺于重建原有的秩序当中,内耗不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川农的兽医学科队伍在郭万柱教授离开之后长期处于半停滞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