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docx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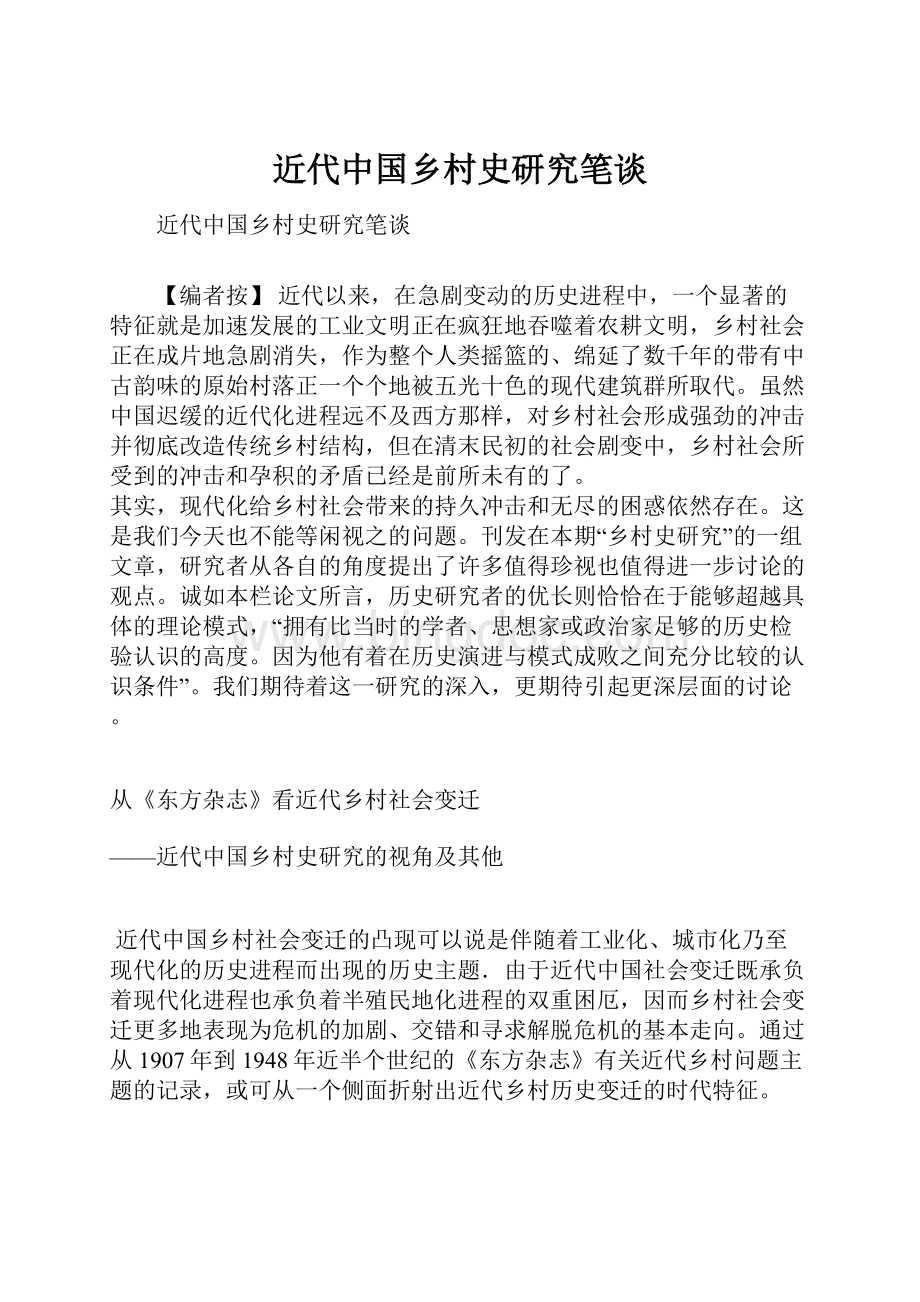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近代以来,在急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加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
虽然中国迟缓的近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
其实,现代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和无尽的困惑依然存在。
这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
刊发在本期“乡村史研究”的一组文章,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
诚如本栏论文所言,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理论模式,“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
因为他有着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之间充分比较的认识条件”。
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更期待引起更深层面的讨论。
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
通过从1907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20年代始,《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研究的篇幅曰渐增多,几乎每期均有专题研究和问题讨论。
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的警告也日见其烈,因而1935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集中刊载着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
而且,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专题化。
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了。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
“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
上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
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①《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
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
主要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教育问题。
对于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认为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高度集中和价格暴长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
在30年代,“我国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
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
”②
这当然不仅仅是历史传承的问题。
虽然历史上的农民也是贫穷的阶层,而且也遭受着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结构性规则引动的升降流动的困扰,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特征。
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
”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③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
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
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
世纪初年。
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
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由工业化浪潮引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
一方面,是原始村落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华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
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最重大转折:
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
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
《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动荡中走向危机四伏的窘况,在这一历史性变动中隐含着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对城市化、工业化路径的探寻.也富含着民族国家的建————————
①朱汉国:
《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
《序》,第2页,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③杨开道:
《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
构、社会结构与和文化结构重构的路向选择等等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成果。
《东方杂志》作为具有学术性、现实性和广泛社会性的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其时代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都不容忽视。
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许多力求解释原由和探寻解救答案的研究,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根本道路的思考。
我们固然不能以简单的成败论英雄,但在各种应对危机方案的成败之间,我们无疑会体察到包含着超越个体、超越时限的普遍性认知理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深刻的研究对象。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
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①。
因此,在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
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等,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
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
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
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
作为历史研究,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模式的时代特征及其意义,不充分揭示和认识这些模式,就无法理解真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与思想,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超越这些模式:
他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
因此,他获得了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的内在比较的深层认识的条件。
这也是我们研究近代乡村史的必要视角。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
[作者简介]王先明(1957—),男,山西屯留人。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
①齐植璐:
《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婚丧嫁娶、风俗人情之类的现象简单梳理,而是要寻求现象背后的意义。
社会史的表达,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达,而更重要是意义的寻求。
从这个视角,社会史跟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往往有着更多的纠缠,唯其如此,社会史的研究才更有价值。
晚清民教冲突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关于演戏和求雨的风俗冲突,在19世纪后半期,因演戏和求雨引起的教案相当多,这也是许多研究教案的论者往往把民教冲突归结为文化冲突的原因,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类的教案理解为教民遵从了西方的文化风习,因而与中国乡村固有风俗习惯产生了冲突。
然而实际上,在那个时代,除了极少数做了牧师的基督教世家之外,绝大多数教民既没有改变习俗的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
西方教会借口不拜偶像,为教民从清朝政府讨来一纸可以免除演戏出份子的特权,其实只是以宗教为借口,为教民争得的一种经济上的优惠。
事实上,中国乡间的演戏,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拜神的仪式,所有的戏剧,名义上都是给神看的,但实际上拜神仪式的偶像崇拜意义早已淡化,人们只是借此娱乐而已,只是在求雨的时候,才具有较强的拜神意
味。
教民中的多数也是中国农民,他们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种娱乐形式,除了少数信仰特别强固之人之外,教民和他们的家人,在村里来了戏班唱戏的时候,大抵也是耐不住的,而教会为他们讨来的特权,实际上使他们变成了占村民便宜的人。
尤其是当求雨唱戏(代价有时比较高),而且真的把雨“求”来了的时候.在村民眼里,教民所占的便宜就太大了,这里,不仅有请戏班子的公份,还有求来的天上的雨。
当然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村庄教民都是绝对的少数,他们不交请戏班的公份,对大局影响并不大,而且每户所应交的戏份,数量一般都很小,只是在人们的感觉里,教民却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白占大家便宜,往往意味着不道德,如果行为不道德还找理由(不拜偶像)辩解,就成了无耻之尤,从而强化了一般村民经济上吃亏的感觉。
所以,起源于似乎很微不足道的”细故”的教案,才会以如此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打、杀、烧、抢)。
这里,所谓文化风俗的冲突,只是一种表象的表达,实际上背后有经济和道德的原因。
"
剪辫部分地成为社会的潮流,要晚于不缠足,由于男人的辫子是汉人服从满清统治的标志,所以,只有在庚子以后,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同时不得不依靠大规模的西式变法来摆脱危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剪辫的潮流。
跟不缠足一样,先进人士之所以对男人留辫子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辫子已经成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的标志,欲脱野蛮而人文明,则非剪辫不可。
但是即便如此,学生和新军中的剪辫风气,也不大可能传染到下层普通民众,老百姓大多听不着也听不懂西方人对于辫子pigtail(猪尾巴)的讥诮,因而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留辫子早已变成了他们的一种强固的日常生活习惯,对保留辫子,不仅有习惯上依恋,还有巫术思维的考虑,其中归顺满清的政治含义早巳淡漠了。
尽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和革命后的一个阶段里,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剪辫的强制运动。
其动机,不仅是为了消除民族耻辱,还有反满和改造国民性(革命党人认为辫子是国人服从满人的奴隶根性的标志)的初衷。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不缠足和剪辫其实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运作的意义,不缠足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民间突破口,而大规模的剪辫运动,则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者为扩大群众基础,“强迫入伙”的一种举措(在人们印象中,辫子一直是否忠于朝廷的一种标志,尽管革命爆发后出于权益之计,清政府已经宣布剪辫自由,但老百姓和造反者却大多不知道)。
正因为如此,辛亥期间先进分子更多在意强迫剪辫,而戊戌期间则着意不缠足。
由于这种政治运作的印记,使得这种风俗变革带有很强的功利和强迫色彩,未免与先进分子所效法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多有扦格(辛亥期间,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曾对强迫剪辫有过抗议)。
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文明”情结,一度显然被政治事件大大地强化了。
从庚子以后到二次革命,是国人狂热地追求“文明”的时期,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庚子义和团运动有关,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中国人背上了野蛮的十字架,为了摆脱这个十字架,所以才事事讲求“文明”,从文明棍、文明帽到文明戏和文明结婚。
如果说文明棍和文明帽不过是外来器物的引进与仿造,那么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则带有文化上的“以夷变夏”的内蕴,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公开彰示中国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或者说中国落后而西方先进。
城市的“文明”热虽然后来逐渐消淡,但这种话语模式却传了下来,中国文化的所有内容,从京剧、中医到宗教和中学,都被打上了落后、迷信的印记。
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在文明热的时候,所谓的文明戏,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点模仿西方的话剧,但又不是话剧,跟写意象征性和程序化很强的中国戏(比如京剧和昆曲)正好南辕北辙,主要是些洋学生用它来演时事(政治宣传)和西洋的故事。
而文明结婚也类似,它不是西方教堂婚礼,只是穿着不中不西的服装,革掉了大部分中式婚礼的程序与仪式,也革掉了所有的中式婚礼中有关巫术和类巫术的成分,诸如撒米、枣、花生,跨火盆等等仪式。
而在此前,繁复的礼仪(包括婚礼)恰是中国人赖以区分文野的标志,讲求礼仪者为文,反之是化外的野人(蛮夷)。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文明”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颠覆意义。
尽管如此,这种风习上的文明追求,依然没有摆脱政治话语的覆盖。
追求文明无非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的仿效,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至少也得摆脱西方强加于我们的野蛮民族的恶谥。
野蛮排外的反教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而追求文明的不缠足与剪辫运动却正好相反。
看社会的进步并不以站在前列的先进人士的意志为转移。
文明戏和文明结婚在乡下从来就没有市场,在都市的支持者也很寥寥。
至于不缠足和剪辫,虽然在城市里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民众的反弹却依然强烈。
辛亥期间,农民为了躲避强制剪辫,甚至不惜不进城卖菜和挑粪,有的地方的城里人甚至制出一种特殊的尖顶帽,以遮掩盘在头顶的辫子。
“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你说邪不邪,娘们穿着男人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样讽刺放足和剪辫的民谣,在到处传诵,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文明追求的社会意义。
其实,不仅先进人士居高临下倡导的社会改造,不能按其表象阐述意义,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苏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时,也有类似的问题。
应该说,苏区在移风易俗是相当深入的,每个乡甚至村,都有列宁小学,编出了适合农民扫盲和启蒙的《工农兵读本》和《劳动读本》,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红星俱乐部和剧社,即使没有这样的组织,宣传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等的文明戏、改良花鼓戏到处都在演,在组织的强制下,原来的僧道和巫婆神汉纷纷改行,包办婚姻也可以在苏维埃法庭解除。
不过,虽然苏区民众的信仰和民俗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将家里神龛里的神佛丢弃了,却换上马克思、列宁的牌位或者画像,在恋爱自由的氛围中,越是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老婆跑得越多,以至于有的地方苏维埃不得不出台决议,禁止“自由找爱”。
实际上,苏区农民信仰结构并没有真的改观,他们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和列宁当成神来崇拜了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是信仰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们给了他们土地和财
物,有用则信,恰是农民信仰的核心精神,只要精神不变,信仰对象的改变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同样,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信条,也不见得一下子就使农民走向现代,在某些方面实际上鼓励了原来在南方农村就存在的性自由,对农村社会有某种瓦解的作用。
其中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肃反扩大化的缘故,苏区的知识分子被殃及过多,以至于预定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完成,也许还有别的。
总之,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回顾我们的社会史的时候,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在研究社会变迁的时候.尤其要慎重,不要被一些热闹的表象所迷惑,轻易做出定性的结论。
[作者简介]张鸣(1957—),男,浙江上虞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中国近代史社会史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
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
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
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
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等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沦为流民无产者。
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
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
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
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
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
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
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
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
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分析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
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
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
“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
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人祸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
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
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
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类:
兵、匪、盗、丐、娼。
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
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
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法律框架之内。
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见刘平:
《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载《文史哲》2004年第2期,第68页)。
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
在中国历史中。
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
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
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
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
狭义而言,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
“平”“团”“调”“柳"八小门:
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
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
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
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
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
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
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
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
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三是土匪强盗。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