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则为一人.docx
《合则为一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合则为一人.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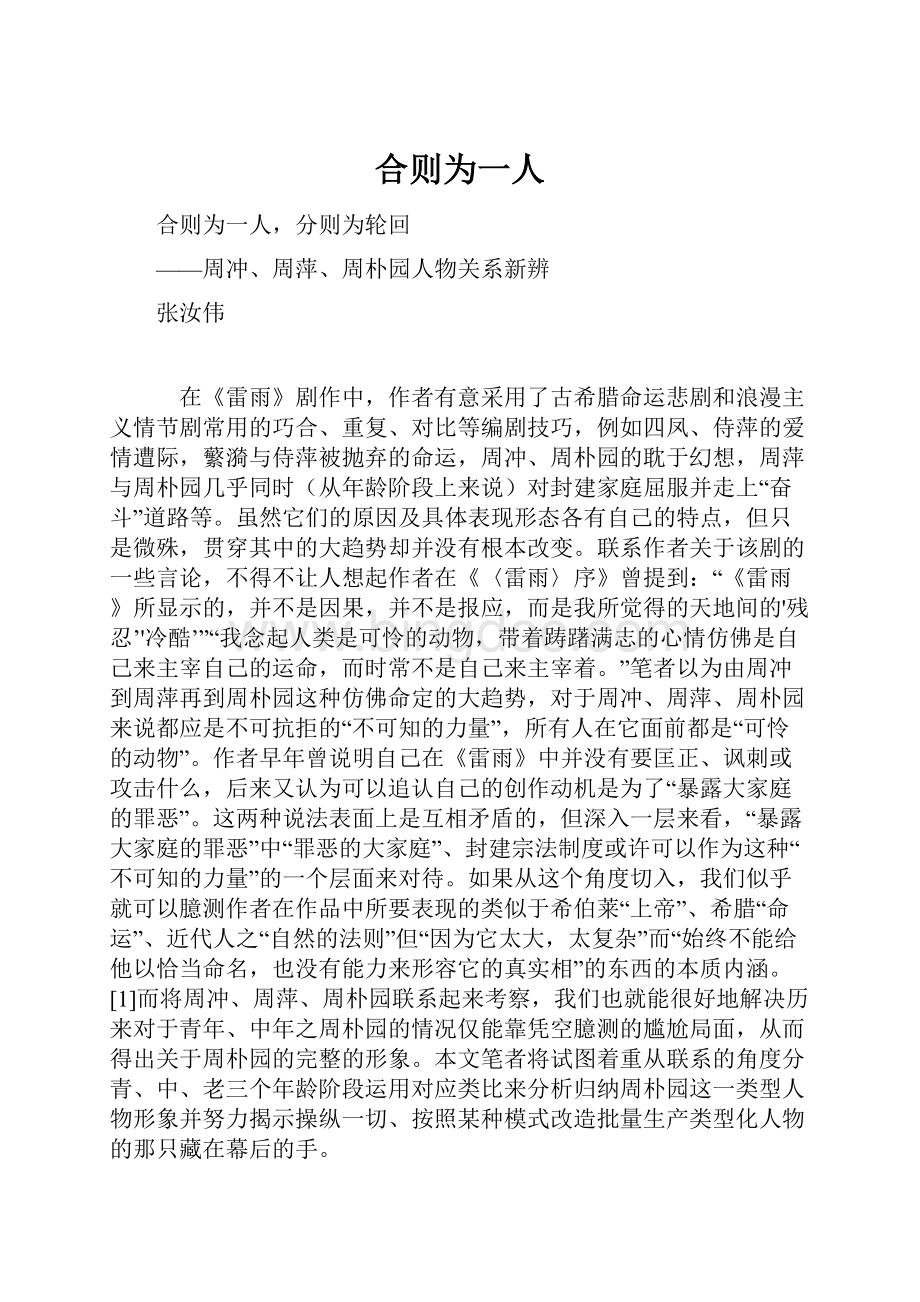
合则为一人
合则为一人,分则为轮回
——周冲、周萍、周朴园人物关系新辨
张汝伟
在《雷雨》剧作中,作者有意采用了古希腊命运悲剧和浪漫主义情节剧常用的巧合、重复、对比等编剧技巧,例如四凤、侍萍的爱情遭际,蘩漪与侍萍被抛弃的命运,周冲、周朴园的耽于幻想,周萍与周朴园几乎同时(从年龄阶段上来说)对封建家庭屈服并走上“奋斗”道路等。
虽然它们的原因及具体表现形态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只是微殊,贯穿其中的大趋势却并没有根本改变。
联系作者关于该剧的一些言论,不得不让人想起作者在《〈雷雨〉序》曾提到: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冷酷’”“我念起人类是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
”笔者以为由周冲到周萍再到周朴园这种仿佛命定的大趋势,对于周冲、周萍、周朴园来说都应是不可抗拒的“不可知的力量”,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可怜的动物”。
作者早年曾说明自己在《雷雨》中并没有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后来又认为可以追认自己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暴露大家庭的罪恶”。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深入一层来看,“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中“罪恶的大家庭”、封建宗法制度或许可以作为这种“不可知的力量”的一个层面来对待。
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似乎就可以臆测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类似于希伯莱“上帝”、希腊“命运”、近代人之“自然的法则”但“因为它太大,太复杂”而“始终不能给他以恰当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的东西的本质内涵。
[1]而将周冲、周萍、周朴园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也就能很好地解决历来对于青年、中年之周朴园的情况仅能靠凭空臆测的尴尬局面,从而得出关于周朴园的完整的形象。
本文笔者将试图着重从联系的角度分青、中、老三个年龄阶段运用对应类比来分析归纳周朴园这一类型人物形象并努力揭示操纵一切、按照某种模式改造批量生产类型化人物的那只藏在幕后的手。
一、周冲——青年周朴园
成功的人物形象,不仅要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且要使其性格处在不断发展和流动之中,如果只是静态的写出人物性格几个不同的侧面,而不能在行动中揭示人物性格变化的轨迹,这个人物同样会使人感到虚假。
人物性格之所以必须发展流动,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本来就是随着年龄、经验、经历、认知能力等的不断增长而有所改变的。
剧本由于受“三一律”的规定制约,不可能有太大的空间来反映人物性格的发展流动过程,因而《雷雨》抓取冲、萍、园三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将其作为系列,进而整合,显得极为巧妙。
1.共通的侍女情结
周冲与早年的周朴园一样,出生在由封建势力统治的富裕大家庭里,虽然所处年代相差了近四十年,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同样压抑的家长专制下,二人的家庭生活环境区别不是很大。
在剧中,周冲年十七,属青春期、学生时代,他有许多憧憬,对社会、对家庭、以至于对爱情。
他天真善良、富有正义感。
在爱情上他有这样几段话:
她是世界上最——(看一看蘩漪)不,妈,您看您又要笑话我。
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
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
最好的,他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不,她是个聪明有感情的人,并且她懂我。
我一定要告诉他的。
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
如果她不愿意我,我仍然尊重她,帮助她的。
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
这里所谓的“她”是四凤,周家仆人鲁贵的女儿,同样也是周家的侍女,其时正与周萍热恋,周冲并不知情。
从以上周冲的那一番发自肺腑的爱情表白,我们虽觉得他单纯幼稚得可笑,犹如做梦,但我们至少应承认周冲对于四凤是“真心的”、真诚的。
可以大胆设想,四凤若不是与周萍恋爱在先,难保不会被周冲的真诚与热情打动,进而产生感情,然后再演绎一场公子与侍女的爱情故事。
与周朴园相较,二人走的都是叫侍女念书的路子,不同之处仅在于“父亲成功了,而儿子只不过做了一个梦”[2]——周朴园与侍女的爱情故事得以演绎,而周冲的爱情则因其兄周萍捷足先登而流产。
如果不是周萍,根据鲁大海对他妹妹的评价以及周萍一系列妒忌性的话语来推敲,笔者乐观地认为周冲与四凤肯定有戏。
抛开周萍、四凤不论,若不是周冲英年早逝,以之真诚热情和身份,要获得某个侍女的倾慕,应当不存在太大问题。
从以上分析看出,周朴园、周萍、周冲有着或即将有着相同的特殊经历,他们在内心本质上有着共同的侍女情结。
2.改造社会的思想抱负
根据时间推算,周冲应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传播开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逐渐进入国人视野。
作为学生,接受新思想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我们看到的剧中的周冲正是一个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热血青年,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改造世界的设想、民主自由的观念,有着“踌躇满志的心情”。
蘩漪担心他与四凤的爱情会遭其父反对时,他表示要进行斗争;周朴园逼蘩漪喝药时,他进行了大胆的争辩,“气得浑身发抖”;鲁大海被打并被开除时,他显示了同情,责问“不公平”;对于整个工人阶级,从他对鲁大海的友好举动中亦可见其是愿意接触与帮助并抱有很高希望的;特别是对四凤,他描绘了一个碧海晴空、白云孤帆的美丽意象,让我们见到了一个健康的积极的有理想的热爱生活的青年形象[3]。
根据作者对他的一些评价,我们知道,作者是用褒扬的笔调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塑造的。
但我们发觉在第二幕中周朴园斥责周冲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知道社会是什么?
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
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
”由此我们应当得出,周朴园当年虽然是晚清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的公子少爷,但他起初并不抱有阶级成见,而是勇敢地接受新思潮,后来又留学德国,并在德国阅读了大量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表现出了可贵的否定自我的反封建精神。
根据时间判断,他还应当是十九世纪末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
这是异常难得的,因为在当时阻碍他行动的复杂力量要显得更为强大。
并且从其能让侍萍念书、与作为侍女的侍萍保持半公开的同居关系长达三年之久等事件上,我们认为周朴园“我自命比你彻底得多”此言不虚。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青年时代的周朴园绝不是一个只知玩弄女性的封建纨绔子弟,而是比周冲更“现代”至少和周冲一样“现代”的“热血青年”,也应属于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喜欢的人”。
周萍也是不安于现状的,所以他对父亲说:
“这二年在这儿做事太舒服了,心里很想在内地乡下走走。
”蘩漪也指出他曾慷慨陈词,“你恨你父亲,你说过,你想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同时,作为一个受过专门教育的堂堂大少爷,能爱上一个婢女,也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壮举”。
我们认为,周萍也有着热烈追求自由,奋勇争取个性解放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蘩漪也是同一系列,同一阵营。
3.挫折之后是退缩
周冲“原是可喜的性格”,是“最无辜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并不允许他那可喜的性格正常发展,并不理会他是否无辜。
在喝药那一幕,现实让他看到了封建家长专制统治家庭父亲的威权;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他看到了慈祥父亲的另一面;在鲁大海身上,他看到了他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母亲,当蘩漪唤他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他透过温情面纱看到了母亲丑恶的嘴脸……现实世界对于藏在理想堡垒里的周冲是残忍的,短短几个小时,他的情感信仰世界被击得粉碎。
在爱情上,即使他退让到同意带着四凤的“他”一起飞向“我们的世界”的地步,仍然没有结果;在实践改造社会的理想时,自己对“工人阶级”善意的同情与帮助换来的却是一顿辱骂——多么可悲的事情!
残酷的现实惊醒了周冲的幻梦,他“失望地立了一会,忽然拿起钱说'好,我走;我走,我错了。
’”到家后,当周朴园和他谈起“你今天早上说要拿你学费帮一个人,你说说看,我也许答应你”的事情时,周冲“怨悔”地答道:
“那是我糊涂,以后我不会再这样说话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灰心失望的周冲形象。
可以想见,周冲“走”后,必将“回”到他原本的“家”、原本的阶级中去,“反省自己”,逐渐“清醒”过来,“认清”社会,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了。
在对第四幕蘩漪对他的责骂“你还是你父亲养的,你父亲的小绵羊”这句话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如果不是早逝,周冲必将更加“清醒”,不会再去找“鲁大海”这类人,不会再替他们喊“不公平”,或许若干年后,他也会对自己的子女说“我自命比你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
联系上段,既然周朴园当年至少和周冲一样“现代”,那么周朴园又是如何变成封建保守的大家长的呢?
根据本段对年轻周冲的分析,再以周萍作为过渡参照,答案跃然纸上。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巧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思想激进的鲁大海不是偶然,他代表的是一类人、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一个认识:
不可知力量是复杂的,内涵相当广泛,虽说鲁大海是“革命力量”、“先进阶级”,有的时候未必不将“复杂力量”中的消极成分内质化,扮演了“复杂力量”的一部分的角色,起着将周朴园、周萍、周冲这类具有反封建意识愿望、同情支持无产阶级、要求革命的封建统治堡垒内部的叛逆推回到其本阶级、不许其革命的消极作用。
二、周萍——中年周朴园
周萍在文中是一个而立之年的人物形象,他有些像《家》里的觉新,在《雷雨》中扮演着牺牲品和卫道士的双重角色。
他是一个不彻底的叛逆,又是一个不完全的投降者。
[4]作品交待“年二十八”,但根据推算应为三十一或三十二。
笔者以之为中年周朴园形象。
1.苍白无助的爱情梦魇
与周朴园、周冲一样,周萍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虽然是私生子,母亲只是一个下女,但因为是周家的血脉,所以仍然是周家大少爷。
其出生应在二十世纪初,但在封建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家庭里,经过类似于十七岁周冲的经历与反思,时代特征在他身上基本已经成为隐性因素了,剧中所出现的只是一个与后母乱伦在前,与下女私好于后的少爷形象。
对于他与蘩漪,很难说是谁勾引谁。
抛开二人不正常关系的性质不论,笔者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有感情的,有例为证:
蘩漪(安慰地)不,你不要这样说话。
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
你什么我都清楚。
……
对此周萍并没有反对,是默认了的。
试想既然二人“闹鬼”长达两年之久,关系到了“只有”的地步,如果还说没有感情,肯定不是实情,是不足信的。
再者能让周萍“每天喝酒胡闹”“恨自己”的,应该是情感问题,至少是为曾经有过的情感问题。
笔者以为,一边是情感,一边是伦理,两相夹攻,才是折磨得他痛不欲生的根本原因。
周萍与四凤,笔者以为也是有感情的。
日久生情属正常情况,况且,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女人的情形也是有的。
不过,周萍对四凤之感情似不及对蘩漪来得深沉。
除去上面提到的“只有”不说,周萍和蘩漪的思想观点也是颇为接近的。
四凤是个纯洁天真的少女,年轻、“健康”、“整个身体都很发育”、“爽快”、“大方”“却很有分寸”,这一切足以打动周萍。
但他可能更多是把她当作远离蘩漪填补空虚心灵的慰安药物来使用的——“她就是我能活着的一点生机”——没有四凤,真想不出灰色的周萍还有什么可以寄托感情。
周萍对于四凤,大约还有一种依赖心理,这是不能混同于爱的。
再者,周萍决定去矿上之初,并没有显示出很想带四凤去的样子,敷衍的成分可能要更多一些。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周萍必须沿用“周朴园模式”,像周朴园抛弃侍萍一样抛弃蘩漪,这是由“复杂力量”(在这里主要体现为伦理道德和血缘关系)决定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因而当蘩漪央请带她一起私奔逃离周公馆时,周萍的回答是:
“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我们承认周萍的性格中或许存在着懦弱自私卑怯冷酷等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决定了他在维护爱情之树的斗争中不至于不顾一切,矢志不移,斗争到底。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懦弱自私”不完全是个人品质问题,更可能是因为作为性格主体的人向现实伦理关系和正统道德的回归,是把“太大,太复杂”力量内质化了;可能既是对现实利益的卑躬,也是对自身思想理念的屈膝。
复杂力量以封建妇道为表征约束、扼杀了个性觉醒、追求人格独立和个人幸福的具有“雷雨”样性格的蘩漪,同时也用伦理道德鞭笞了追求自由、具有民主思想的周萍。
同理,在周萍、四凤的爱情婚姻上,它同样会挥动手中的枷锁。
周冲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即使四凤不是与周萍而是与周冲相爱,最终他也还是要采用“周朴园模式”,像周萍一样抛弃四凤。
2.而立之际的建功立业
面对爱情上的尴尬与混乱,周萍决定要到矿上去了。
去干什么呢?
自然是去当资本家,“学着父亲的英雄榜样”,走“哈尔滨包修江桥”的路,发财致富,然后成为社会名人、慈善家……而“把一个真正明白”自己,爱自己的人“丢开不管”。
我们想中年的周朴园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离家闯荡,最终成为在省府有固定席位的矿业资本家的。
“去矿上”,周萍走的是昔日周朴园走过的道路,是“周朴园模式”;因为情变,或许也正是周朴园早年离家闯荡的原因。
至于周萍出走后的情况,“进步”的趋向也是有可能的。
但比较而言,特别是考察他在周鲁书房谈判一景中的表现之后,笔者倾向于认为其发展轨迹不至过于偏离“周朴园模式”。
3.潜藏在骨子里的家长专制意识
蘩漪是否有病不是本文讨论话题,笔者关注的仅仅只是周萍在不同情境对蘩漪是否有病的看法。
在喝药一幕中,他对蘩漪是否有病未置可否,据其语气与语调应偏重于认为没病;在克大夫诊断之后周朴园询问时,周萍回答说“看完了,没有什么。
”从上面两个证据,笔者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周萍从心底里不认为蘩漪有病。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周萍先后说了这样几句话:
(惊惧地望着她,退后,半晌,颤声)我——我怕你真疯了!
(眼色向周冲)她病了。
(向蘩漪)你跟我上楼去吧!
你大概是该歇一歇。
你先不要管她,她在发疯!
(狼狈地)你叫我说什么?
我看你上楼睡去吧。
(走到蘩漪面前)疯子,你敢再喊!
可见,随着事件的发展,周萍是宁愿把她当作病人来看待的。
在这方面,周萍一如他的父亲,因为蘩漪知道他(周萍)的底细,对他不服从,不放他走;周朴园宁愿让所有人都认为她有病,是希望所有人不相信她说的一切,以免影响了自己“模范丈夫”、“模范家长”、“慈善家”等一系列声誉,损害了自己的权威。
周萍如同他父亲的影子,当蘩漪揭露他的丑行时,他本能地感到了恐惧,妄图用蘩漪是疯子来搪塞,其语调一句比一句重,语气一句比一句强,最后更显得歇斯底里。
虽然纸没有包住火,但其专横冷酷的家长意识已可见一斑。
这种意识、动机伺其成为家长之后,必然导向封建家长专制,搞“一言堂”,要求所有人服从,掩盖自己与蘩漪、四凤的“底细”,正如家庭中的周朴园。
小结一下,上一段,我们推论的是周萍成为资本家的可行性和周朴园变得“热爱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家庭原因。
本段我们所推论的则是周萍、周朴园成为封建家长的必要性。
两段合在一起,得到的则是周朴园具有“中体西用”时代特征的资本家、封建家长双重身份互为表里的两个层次。
三、周朴园——周萍的明天
周朴园受着资产阶级的教养,却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5]他在矿上是董事长,在家里又是老爷,作为一个浸透着封建思想的资本家,他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
在剧中他俨然是高高在上统治一切的封建性质浓厚的家长,但在他身上我们依然见到了周冲般鲜艳的极富人性的色调,更从他身上见到了老年周萍周冲的轮廓。
1.处理罢工事件中“大义灭亲”的周朴园
鲁大海是周朴园二十多年未见的亲儿子,但在处理矿上罢工问题时,周朴园并未因此而丝毫手软,还未见面就已决定——“鲁大海我是一定要开除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自身利益面前,将亲情放在一边、铁碗残酷的周朴园。
然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来考虑问题。
我们知道: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轰轰烈烈;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执行“清党”政策,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汪精卫更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
既然我们承认周朴园是一个资本家,就应该允许他具备资本家的觉悟与“素质”。
生活在特定的环境,经过那个年代,面对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他理应心有余悸,知道心慈手软意味着什么,保持高度警惕、开除鲁大海符合他的身份。
作为资本家,周朴园是精明能干的,谈笑之间就化解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罢工斗争;作为资本家,周朴园是邪恶的,他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扣三百块钱”,叫警察开枪杀了数十多个罢工工人,并且“一分抚恤金不给”。
精明狡黠、有手腕有“魄力”、残忍冷酷是老年周朴园性格的主色调。
不妨打个比方,以周萍在处理与蘩漪情感问题中表现出的绝情、自私与冷漠,如果把他放在第二幕周朴园认鲁妈和开除鲁大海一幕中,他的表现和周朴园不应有太大差别。
2.追念逝去真爱的周朴园
周朴园是真爱侍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没有人能做戏三十年始终如一,并且在没人的情况下还不把伪装脱去。
也有学者指出,根据年龄与时间推算在侍萍与蘩漪之间应当还存在一个“有钱有门第”的“阔小姐”[6]。
但我们发现这个“阔小姐”在剧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说周朴园仅是玩弄侍萍,那么乍得一个“阔小姐”,他应尽极温存才是,但“阔小姐”却抑郁而死。
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与周朴园对其毫不怜悯疼爱有不可割裂的联系。
并且,同为“亡妻”,周朴园缘何厚此薄彼,天南海北都带着笨重陈旧的家具,连侍萍夏天关窗习惯都保持着,却绝口不提“阔小姐”,不见“阔小姐”的半张照片?
通过比较,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但相爱并不一定就能相守,中年的周朴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要爱情还是要“一切”?
选择爱情意味着将被家庭阶级放逐,并为世人所唾弃,成为除了爱情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选择“一切”就必须放逐爱情与良心,“以放弃人格,出卖灵魂为代价”[7]离开心爱的侍萍。
周朴园不幸地选择了后者,——“他这种选择也带有身不由己的因素”[8]——然后便用尽了一生来忏悔。
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力量”决定了的,在它面前个人比蚂蚁还微不足道。
正是它将周朴园与鲁侍萍毫不留情地撕开,逼着侍萍在年三十夜带着方出生三天的孩子离开周家大门去投河。
当然我们承认周朴园的悲剧婚姻也加重了侍萍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但反过来说,或许也正是因为他对侍萍的难以割舍的爱恋才造成了他以后两次婚姻的悲剧。
如果不是结局发生的变故,这一幕或许也将发生在周萍与四凤身上,四凤肚里的孩子强化了我的预感。
顺带指出,这又是一个可怕的轮回,“侍萍道路”。
这一点相对于周冲差异是比较大的,但考虑到复杂力量对人的理念征服的润物细无声的蚕食能力,以及周冲与复杂力量的悬殊对比,周冲最终走“周朴园模式”,成为周朴园第二、第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见面一景表现出更多的仍然是爱。
这一点前辈已多有论述,此处便不再赘言。
那时那刻,周朴园已经成为一家之长,“统治阶级”,表面看来很强大,似乎有了爱情自由,但与“太大,太复杂”的力量相比,周朴园仍然是脆弱不堪的“小蚂蚁”。
爱归爱,他必须服从于自己的地位、阶级、环境、舆论以及时代道德观念,和侍萍“划清界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这是周朴园的悲哀,谁又能说将来周萍、四凤相见不会是同样的情景?
周朴园、周萍个人品质确实存在软弱的一面,但冥冥之中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复杂力量是起了决定主导作用的。
在优胜劣汰、顺昌逆亡的人文“进化”、选择面前,他们只能如此。
所有人都是冥冥之中“残酷”力量的奴隶,它吞噬一切人,包括“由子而为父”的统治阶级周朴园那一类。
“命运借他的手毁杀了蘩漪,侍萍这一群,也毁杀了他自己。
”[9]
3.活在忏悔阴影里的周朴园
剧本借四凤之口告诉读者周朴园念经吃素喝普洱茶,并且“一向讨厌女人家”[10],他“不像一般的有钱人,家有三妻四妾,还要到外面寻花问柳,他在肉欲上对自己近乎残酷”。
他也捐钱给教会,“兴办慈善事业”。
考察剧本的序幕与尾声,我们发现周朴园甚至将自有的房产也捐了出来,诚心皈依了教会。
《雷雨》序幕让周朴园走进教堂,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
长于自省,严于用道德规范拷问自己灵魂是我们民族的基本心理特征,是“所属儒家文化无意识所致”[11]。
周朴园一面行凶,剥削矿工,一面行善,忏悔,这两种行为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有机统一,周朴园正是“妄图”在这矛盾的行为中通过后者作为补偿,求得内心的平衡。
因为前者是“复杂力量”和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的,他只能在凶残冷酷的剥削阶级之外做个“虚伪的慈善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剧本第一幕通过周冲之口指出:
“哥哥现在真有点怪,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不知干什么?
”影视中关于周朴园中年时期“赶”走侍萍后花天酒地但仍很苦闷、“不幸福”的记叙镜头也支持了我关于这对父子命运颇为相似的想法。
四、似无还有的宿命轮回思想
我们不能回避作家的宿命论问题。
曹禺对宇宙的憧憬中,就其思索的内容来说是现实的,其主导倾向是唯物的;但按其形式来说又带有神秘的色彩。
曹禺曾言:
“《雷雨》是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背景。
”《雷雨》不仅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社会背景的特点,而且里面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色彩。
1.反复出现的天命意识
宿命论是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衍生物。
当《雷雨》的悲剧走向结局时,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了宿命的浩叹。
鲁侍萍原就表现了她的宿命思想,她呼喊着“天”,并不奇怪。
蘩漪也惊愕于周朴园这突如其来的宣布,喊出“天哪!
”。
周朴园把侍萍重新找到周家门上说成是“天命”。
一个老仆人也说这场悲剧是“天意”。
四凤向着周萍怪笑着忍不住地喊出了:
“啊,天!
”。
整个结尾笼罩着浓厚的宿命的气氛。
这种叙述上的“重复”,是萦绕在作家心怀的“情结”在起作用。
作家痛恨这种“天地间的'残忍’”,然而由于受世界观和社会阅历局限,他未必深刻认识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实质根源,所以作品中多少有点宿命的思想,这种宿命思想与叙述模式的相互关联,可能正是作家当时处在找不到人生出路困惑迷茫心理当真实写照。
[12]
2.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
周冲、周萍、周朴园三人的经历是极其相似的,这神奇相似的经历不能不令人觉得背后存在着某种操纵了一切的力量,它给周冲周萍周朴园这类人规定了一条发展道路——“周朴园模式”。
本文在前面三部分抓住人物所处年龄阶段的主要事件就此进行了概要的叙述。
周萍的今天就是周朴园的过去,这种互补的人物关系,清楚地说明了令作家感到震颤和恐惧的“命运”、“天地间的残忍”、“自然法则”等等超验的力量,最终显示为代代遗传,延绵不绝的伦理道德。
《雷雨》的结局是反团圆的,也是反出走的。
人人都在挣扎,但谁也逃不脱死亡或灾难的魔掌,惩罚是必然的,又是邪恶的。
因为他们无法彻底战胜创造出自身,又束缚着自身的古老伦理道德体系。
[13]
3.受害者与害人者——“媳妇与婆婆”
周朴园是所有罪恶的总制造者,但又何尝不是凌驾于他头上的罪恶的牺牲品。
他由当年的反封建先锋、周冲式的人物变成如今的封建家长,对周冲更是扮演了当年他(周朴园)父母的角色,这说明他已经被“复杂力量”同化成为其一部分了,成了一定社会原则的化身,实现了由受害者成为害人者的质的“飞跃”。
这种转变相对于他(周朴园)的父辈,不能不说是一个轮回。
剧作借蘩漪之口告诉我们周萍的父亲、叔祖和祖父都一样,把这个轮回指向了遥远的过去;在周萍、周冲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它延绵不绝的未来,这轮回似乎应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不可知力量、“太大太复杂”的力量、命运、“自然法则”的规定性的结果。
而这种轮回残酷的相似性让人悲哀的同时更引人深思,见出作品深意。
4.值得追究的人物命名
从人物命名上看,三人分别为“冲”(c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