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随笔.docx
《知青生活随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知青生活随笔.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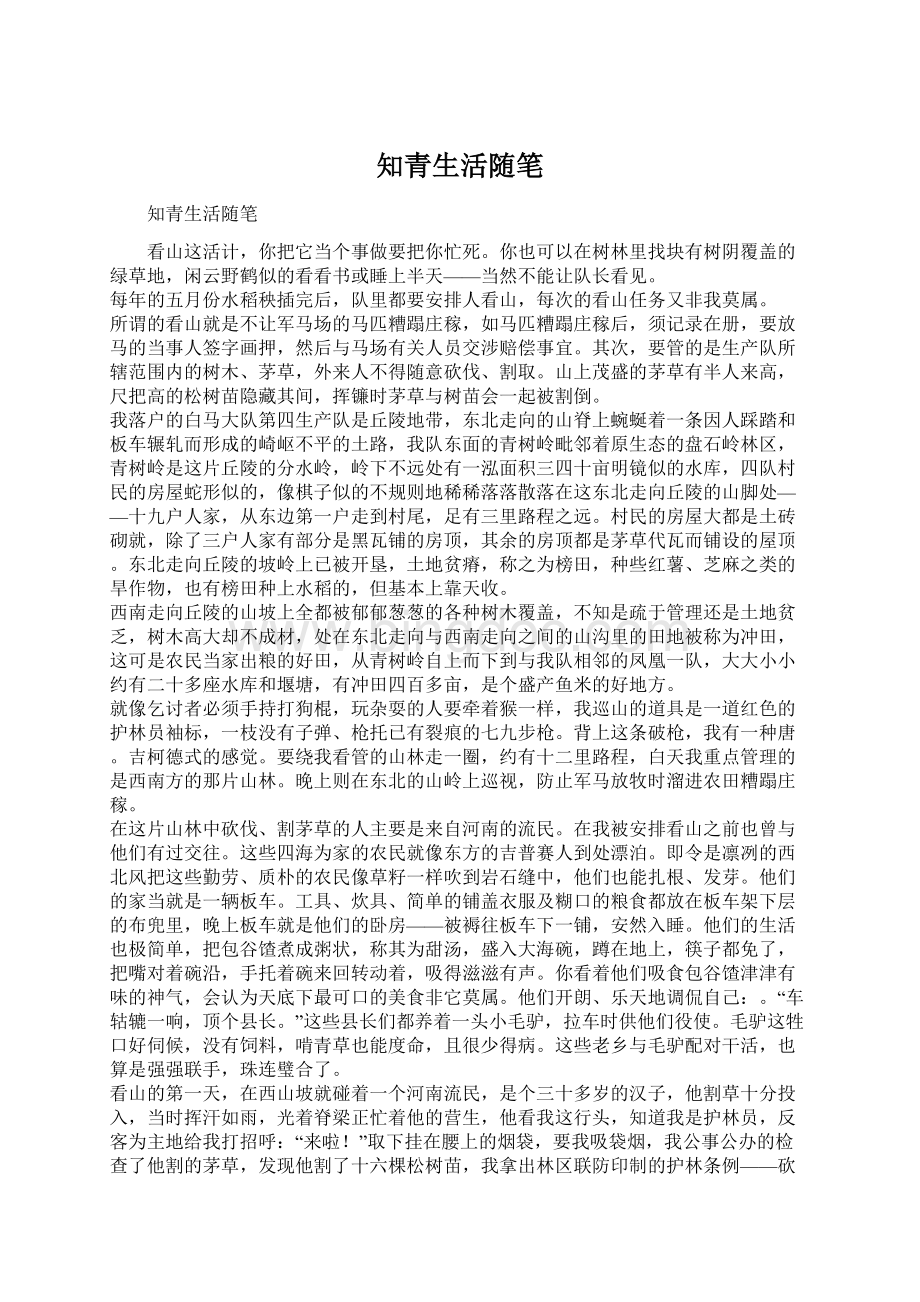
知青生活随笔
知青生活随笔
看山这活计,你把它当个事做要把你忙死。
你也可以在树林里找块有树阴覆盖的绿草地,闲云野鹤似的看看书或睡上半天——当然不能让队长看见。
每年的五月份水稻秧插完后,队里都要安排人看山,每次的看山任务又非我莫属。
所谓的看山就是不让军马场的马匹糟蹋庄稼,如马匹糟蹋庄稼后,须记录在册,要放马的当事人签字画押,然后与马场有关人员交涉赔偿事宜。
其次,要管的是生产队所辖范围内的树木、茅草,外来人不得随意砍伐、割取。
山上茂盛的茅草有半人来高,尺把高的松树苗隐藏其间,挥镰时茅草与树苗会一起被割倒。
我落户的白马大队第四生产队是丘陵地带,东北走向的山脊上蜿蜒着一条因人踩踏和板车辗轧而形成的崎岖不平的土路,我队东面的青树岭毗邻着原生态的盘石岭林区,青树岭是这片丘陵的分水岭,岭下不远处有一泓面积三四十亩明镜似的水库,四队村民的房屋蛇形似的,像棋子似的不规则地稀稀落落散落在这东北走向丘陵的山脚处——十九户人家,从东边第一户走到村尾,足有三里路程之远。
村民的房屋大都是土砖砌就,除了三户人家有部分是黑瓦铺的房顶,其余的房顶都是茅草代瓦而铺设的屋顶。
东北走向丘陵的坡岭上已被开垦,土地贫瘠,称之为榜田,种些红薯、芝麻之类的旱作物,也有榜田种上水稻的,但基本上靠天收。
西南走向丘陵的山坡上全都被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覆盖,不知是疏于管理还是土地贫乏,树木高大却不成材,处在东北走向与西南走向之间的山沟里的田地被称为冲田,这可是农民当家出粮的好田,从青树岭自上而下到与我队相邻的凤凰一队,大大小小约有二十多座水库和堰塘,有冲田四百多亩,是个盛产鱼米的好地方。
就像乞讨者必须手持打狗棍,玩杂耍的人要牵着猴一样,我巡山的道具是一道红色的护林员袖标,一枝没有子弹、枪托已有裂痕的七九步枪。
背上这条破枪,我有一种唐。
吉柯德式的感觉。
要绕我看管的山林走一圈,约有十二里路程,白天我重点管理的是西南方的那片山林。
晚上则在东北的山岭上巡视,防止军马放牧时溜进农田糟蹋庄稼。
在这片山林中砍伐、割茅草的人主要是来自河南的流民。
在我被安排看山之前也曾与他们有过交往。
这些四海为家的农民就像东方的吉普赛人到处漂泊。
即令是凛冽的西北风把这些勤劳、质朴的农民像草籽一样吹到岩石缝中,他们也能扎根、发芽。
他们的家当就是一辆板车。
工具、炊具、简单的铺盖衣服及糊口的粮食都放在板车架下层的布兜里,晚上板车就是他们的卧房——被褥往板车下一铺,安然入睡。
他们的生活也极简单,把包谷馇煮成粥状,称其为甜汤,盛入大海碗,蹲在地上,筷子都免了,把嘴对着碗沿,手托着碗来回转动着,吸得滋滋有声。
你看着他们吸食包谷馇津津有味的神气,会认为天底下最可口的美食非它莫属。
他们开朗、乐天地调侃自己:
。
“车轱辘一响,顶个县长。
”这些县长们都养着一头小毛驴,拉车时供他们役使。
毛驴这牲口好伺候,没有饲料,啃青草也能度命,且很少得病。
这些老乡与毛驴配对干活,也算是强强联手,珠连璧合了。
看山的第一天,在西山坡就碰着一个河南流民,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他割草十分投入,当时挥汗如雨,光着脊梁正忙着他的营生,他看我这行头,知道我是护林员,反客为主地给我打招呼:
“来啦!
”取下挂在腰上的烟袋,要我吸袋烟,我公事公办的检查了他割的茅草,发现他割了十六棵松树苗,我拿出林区联防印制的护林条例——砍一棵树,罚款三圆,种树五棵。
他当时像雷打痴了似的呆住了:
“没钱,就是把俺卖了也换不了四十八块钱。
”我告诉他:
要暂扣他的板车,等他有钱后再赎回。
这汉子蹲在那儿竟然流泪了:
“爷们,你这是把俺往绝路上推呀。
”他自言自语地诉说着他不幸的身世:
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患了眼疾,得了白内障,他想挣点钱把母亲的眼晴治好。
他的诉说使我动了恻隐之心,但又不能这样简单的让他一走了之,必须让他知道林区的管理政策而以后再也不敢到此处割伐草木,我板着脸与他盘桓周旋了一个多小时后,方才让他套上小毛驴驾着板车离去。
转眼就到了七月份。
由于雨水少,堰塘的水因灌溉稻田而浅了许多,也许是水浅缺氧,塘里的胖头、鲢子鱼经常浮头——露着黑色的脊背,张着嘴在水面游弋。
因生活清苦,半年见不着油腥,这些在水面上忽隐忽现浮游着的黑色脊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鱼钩和钓鱼线我是有的,我的住房后面就是一片翠绿的水竹林,钻进竹林,选了根匀称修长的竹子,把线绳和鱼钩连接起来往竹竿上一拴,就是一副不赖的钓鱼竿。
我用书包装了两斤碾面粉后剩下的麸皮做鱼饵,在菜地里挖了几条蚯蚓,于是,钓鱼的全部装备都筹集齐全。
我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塘边,这些鱼听见脚步声和晃动的人影都敏感地闪入了水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为了使鱼儿不注意我的存在,我猫在一棵塘边的柳树下,人影与树影连在一起,人树合一。
往塘中撒了几把麸皮,这麸皮撒在水中并不下沉,蚯蚓也挂在鱼钩上,整装待发。
我息声屏气地等待鱼儿重新露头。
终于,鱼儿逐个的把头露了出来,它们优哉游哉地把嘴一张一合的在水中漫步,颇有几分闲庭信步、温文雅尔的绅士派头。
我把挂着蚯蚓的鱼钩小心翼翼地漂在水面,用极慢的速度把蚯蚓向前拖动,鱼钩上的蚯蚓就像一个慢慢游动的浮游生物,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终于有了收获——一条鱼游到蚯吲前放弃绅士派头,加快了速度冲上前猛咬一口,我认定它已咬钩,猛然向上一拽,一条一斤多重的鱼挂在鱼钩上银鳞闪烁。
亢奋、激动、愉悦的感觉弥漫了我的身心。
我如法炮制,一个多小时后水桶里己装了七八条鱼。
我提着水桶凯旋而归,边走边算计家中还有半瓶白酒,可以惬意的享受一餐美伦美奂的中餐。
去鳞、剖洗后,鱼在锅中煎炸着香味四溢,
刘队长扛着板锹出现在我的灶台边——他的鼻子可真像猫一样灵敏。
刘大贵个子不高,还不到四十岁,是一个干瘦机敏的汉子,浑身黑得放光,就像是用钢筋扎成的人。
他五几年曾在武汉当了几年兵,经常津津乐道的给人们讲述他在武汉当兵时的经历和故事。
他安排我干活时永远是商量的口气,把几种活计摆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我队劳力紧缺,他怕把不如意的活路安排给我做,我一溜了之,跑到别的知青点去串门去了。
当然,他安排别人活路可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回旋余地。
我把酒倒成二份,邀请他共进午餐,吃饭当中我向他反映了青树岭有几亩红薯田被野猪糟蹋的情况,听了我的反映后,他决定向在我队驻队的公社武装部的黄部长要几颗子弹,给予野猪致命的打击。
(我们大队的民兵连是武装基干民兵连,每排(队)都有两杆七九式步枪)
野猪是对农作物破坏极大的家伙,母猪拖家带口,公猪可是独行侠。
它们对根茎农作物独有情钟,田里的红薯,堰塘的藕,经常被它们拱得天翻地覆,为了宣泄它们过剩的精力,有时也跑到水稻田里困泥、打滚。
当然,它们都是夜间行动。
猎野猪小组由三人组成——我、民兵排长赵楚成、打猎有瘾的周明贵。
装备是两颗子弹、两支七九步枪,周明贵用的是他传统的土铳——土铳里加放了铁条。
周明贵是打猎老手,因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他已很长时间没有摸铳了。
他理所当然的成了我们领导人。
他从野猪的脚印中了解了它的重量和来往途径,这是一头两百多斤重的独行公猪,他告诫我们发现野猪后,不能迎着它的头部开枪,头部面积小,中弹率低,而且野猪受到袭击后,非常暴烈,直接往前冲,很容易伤人。
它的獠牙长而锋利,就是豹子、豺狗子(狼),也对它避让三舍,敬而远之。
周明贵把狩猎点选在野猪经常出入的下风处的一个荷塘边的土坎下,我们持着子弹已上镗的枪平卧在土坎下,上弦月从远山朦胧的树冠上冉冉升起,晚风习习,吹走了白日的燥热,萤火虫在林间草丛中忽闪忽明,偶尔也有流星拖着发亮的尾巴划过苍穹的夜空。
不远处的稻田里青蛙在演奏着无休止的大合唱,土丘草丛里的蛐蛐也不甘寂寞断断续续地吟唱着显示着它们的歌唱天赋。
身旁水塘的荷叶沁散着使人超凡脱俗的清淡的荷叶香味。
一直守到深夜两点,夜露润湿了我们的衣裳,仍没看到野猪的踪影,第一天的狩猎无功而返。
第二天晚上,我们三人十点多才到达狩猎点,狩猎的兴奋与新奇感已消逝随之而来的只是枯燥的等待。
到了子夜时分,周明贵用手推了一把我的肩膀,使昏昏欲睡的我警觉起来,在皎洁的月光下看到百米开外处有一黑灰色的动物很悠闲地向我们走来,偶尔还哼哼一声。
这正是我们期盼的客人!
它中规中矩的按着周明贵所预测的路径行走而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在约十五米处,它的左侧面正对着我们的枪口,几乎是不约而同我们扳动了枪机,枪声响后,野猪发了疯似的向它右前方狂奔而冲入一条山沟里。
周明贵很有信心的说野猪起码中了一枪,但没打中头部和腿部——从它跑的动作看得出来。
我坚持着要去找受伤的野猪,周明贵说:
“这黑灯瞎火的,你到那里去找,再说这受伤的野猪,最是凶狠,它的獠牙照你腿咬上一口,你的腿就残了。
”于是我们打道回府,决定天亮后再找。
的确是太兴奋了,我躺在床上,野猪的狂奔的模样总在我脑海里闪现,一直不能入睡。
不到清晨五点,天已放亮,我们三人进入了林区,照着野猪的血迹、脚蹄的印迹、及野猪奔跑时折断的草木,在离狩猎处三里多路的地方找到这头已死去的野猪。
这猪一身灰毛,确实有二百多斤重,獠牙比猪鼻子还长,向上翘起,腿比同重量的家猪要长三分之一。
野猪腹部中了两枪,一枪是土铳打的,另一枪是七九步枪的功劳。
我们用刀砍了一棵小碗口粗细的树做扛子,用绳索捆住猪的四蹄,把杠子往四蹄内侧一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像伙抬到路旁,赵楚成回队拉了辆板车,把这头庞然大物装上板车后拖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前。
这天成了生产队的节日,像杀家猪一样,将烧沸的水倒入腰子盆内杷猪毛退尽,开膛破肚,野猪头、内脏不好分配,放入大锅内煮熟,每家派个代表打平伙。
闻到了肉香,几条狗跑上跑下,窜出窜进很是兴奋。
每户分了六斤肉,我们三名功臣家中比其他人多分四斤肉。
刘队长派人到大队代销店用稻谷换了五斤酒。
到了下午四点钟,太阳还悬在半空,刘队长宣布放工:
“今天让大家伙休息,休息,美美的吃顿肉。
”是啊,还是端午节时,队里架油锅炸了油果子“即油条”。
每个劳动力分了半斤。
平常日子想吃肉无异是想龙肝凤胆一样困难,在打平伙的晚宴上,村民们开怀痛饮,有几个社员酒喝过了头,都不知自已姓甚名谁了。
钻了桌子脚。
看山的工作要在秋收后方才结束。
马无夜草不肥,军马场的马匹夜间也要放牧的,我是固定的看山人,队里的男性劳动力轮换着每天晚上都有两人陪我看山。
我们夜间看山携带着一把生了锈的大刀片子和一只杯口粗细的柞木棒子——这是防豹子、豺狗子的武器。
颇有些草莽英雄的神气。
这天安排的是赵启元和地主周华堂和我共同看山值夜,他们两人已吃了晚饭,换我回家吃饭。
我回家把饭做熟了,还没吃完,赵启元急匆匆地找我,说有三个河南老乡在快干塘的青树岭水库偷鱼。
我要他到村尾喊队长刘大贵,我去找民兵排长赵楚成,一共纠集了七人,带上没有子弹的七九步枪,当过兵的刘大贵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安排了两人组成南路军从南向青树岭包抄,两人组成北路军从北向水库包抄,另三人组成中路军从中路沿着冲田的小路向水库坝底挺进。
以他的手电筒摁亮为总攻信号。
我与总指挥刘队长同编在中路军内,我们三人轻车熟路,衔枚而行,八九分钟后中路军已到达水库坝底,很清楚的听到偷鱼者把水闹得哗哗响,又等了两三分钟后,总指挥认为北路军和西路军已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我们三人爬上了水坝,摁亮了手电。
偷鱼者有一人在岸上,还有一人在浅水中,另一人在深水中布网,我方的西路军和北路军还没到达截击地点,在岸上的偷鱼人听到我们的动静后往南边的树林里跑了,浅水处的人连鞋都来不及穿,半裸着身子向东北方狂奔,在深水布网的倒霉蛋俯首就擒,成了我们的俘虏。
我们勒令他把网拖上岸来,他赤裸着身子上岸后,刘大贵抡起枪托向他腰部捣去,我看他下手太重,足以使偷鱼者致残,便伸手把刘队长拉了一下,于是,枪托打在石块上分了家,断成了两半。
刘大贵恼羞成怒,训斥我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这位俘虏有二十四五岁,个子高挑黑瘦,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有人用竹竿做的细条抽了他几下,他什么都招了——他是修丹江水库时搬到柴湖来的河南移民,是南新集东方红大队某小队的社员。
我队在离与本队十二里外的柴湖围堰造田时也占了四十多亩湖田,湖田是优质的沙质土壤,种什么庄稼都可丰产,庄稼成熟后,因各地民俗的差异,河南移民有闹秋、偷庄稼的习俗,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队湖田庄稼有近一半都被他们闹走了。
本地农民生性孱弱无刚,也曾与河南移民较量过几回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天晚上,捉到了一个病猫,他们的英雄豪气终于迸发,俘虏被带到邓大爷稻场边,稻场边有一棵树阴能遮盖一亩多田的大皂角树,树旁有一副已荒废的大石碾盘,有人用绳绑住这倒霉蛋的双手,把绳从树干上绕过,使劲一拉,被绑人双脚离地,被吊了起来。
赵启元用竹条抽打了这老乡几下,老乡哀告求饶:
“好爷们哪,行行好,别打俺哪!
”这好爷们仍不松手,照抽不误。
他转而向看热闹的妇女们求救:
“奶奶们哪,求求你们,叫他别打俺了。
”这些奶奶们也烦了——原来本地村民所说的奶奶即是老婆之意,河南人所称的奶奶是对上辈的尊称。
于是这些奶奶们拿着竹条也抽打起他来:
“叫你不老实,吊起来了还想占便宜。
”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刘队长怕出人命官司,让人把他从树上放了下来,解绑后他一跛一拐地走了。
三天后这挨了打的黑瘦老乡又来到我队找刘队长——他是来讨要被收缴的鱼网的。
刘队长变成了缩头乌龟,告诉他鱼网在知识青年那儿,那天晚上所做所为都是知青小余安排、指挥的,于是偷鱼的老乡找到了我,这家伙还嫩着点,他把刘队长的原话也告诉了我。
我抽着老乡敬给我的圆球香烟用江湖上的口吻告诉他:
那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我都在场,你认为我是什么角色我就是什么角色,但我决不做打病猫、死老虎的这类不屑于江湖的下三滥角色。
我看你今天精气神都不错,要不,咱俩今天单挑玩玩。
这老乡听明白了我的意思,看我不是一个怕事的主,还要与他动真格的打斗一番,他赔着笑脸,邀请我以后下湖田时到他家做客,那张网是他借的别人的,他要我高抬贵手把网还给他。
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我把鱼网给了他,他再三道谢后,骑着自行车走了。
天旱一直没有下雨。
我队灌溉农田的当家水库群力水库也快干涸了,队长安挑人手把水库里的鱼打捞起来按八分钱一斤分给社员改善生活。
中午我闻讯赶到仓库去分鱼,鱼已分完了;分鱼时他们把我忘了。
刘队长看我不高兴出了个点子,要我到快干塘的柳家堰塘自己去捉鱼,弄多少都不过秤,不记账上。
于是我借了副鱼罩,叫上隔壁十四岁的福香和我同行;他可是个闹鱼的行家里手。
柳家堰塘水已很浅了,只淹及膝盖,我俩先在水中来回跑动着把水搅混,鱼在水中乱窜,鱼罩有了用武之地,不一会就罩了十多条鲢子鱼。
正忙得起劲,我的小腿被什么东西狠狠的撞了一下;肯定是条大鱼,这条大鱼在我们的围追阻截下窜到了浅水处的草丛中被福香一把按住,鱼在水中直扑腾,水花飞溅。
我赶紧上前,轻轻地用鱼罩把它罩定,福香才松开手。
两人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捉了近三十斤鱼。
我留下那条十多斤的大草鱼,其余的鱼都给了福香。
又过了一个多月,夏末秋初,我到移民朋友欧阳连玺所在的东方红二队去还书,并取回我借给他的<红楼梦。
>到湖田去有二十多里路程。
大概中午十一点时分,我才走到湖区里的小河边,河不甚深,约有二十多米宽。
有一座青石做柱,石板做面的青石桥,桥的侧面,河床边长着一排高大挺拔的意杨。
有人在两树当中连接了一根横木,用芦材靠在横木两侧做墙壁,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茶棚。
中午时分,暑气逼人,秋老虎仍在发威。
我口渴难奈,跑进茶棚,落座后泡了杯茶,点燃一支烟,从燠热的烈日下走进阴凉的芦棚内,喝茶就烟的确很惬意。
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
“老余,来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在我队偷鱼并讨要鱼网的那位仁兄赵大发。
我在队里及知识青年中大家都称呼我为小余,今天第一次有人称我为老余,徒然升了一级——我也知道河南老乡对年长者或尊敬的人以老某相称。
果然他十分客气:
“这位朋友的茶钱记在我账上。
”他对卖茶的老板打招呼。
原来他在茶棚的侧面也搭了个小棚专给人理发,赵大发看着我凌乱的长发,建议我把头发理理,我想今天已走进移民老乡的窝子,他要认定哪天晚上是我打了他,要报复我,是祸也躲不脱,于是我坐上理发的木椅,把头交给他处置。
赵大发对工作很是敬业,头发剪毕后,取出剃刀,在我脸额、脖子上刮了三个来回,冷嗖嗖的锋利刀刃在脖子上游走时我心中有些不自在,但我面部表情仍泰然自若,很从容的与他聊着天。
理完发后,他很诚挚的请我到他家去吃中饭,虽然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但在后来的交往中成了朋友。
因为我认为移民老乡豪爽、讲义气、够哥们。
再说我也是一介漂泊无定的移民。
初恋
我到龙山坡排灌站建没工地挖渠挑土已干了二十多天了。
这个排灌站引水渠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靠手挖肩挑,从主干渠到抽水平台有一千四百多米,其中有六百多米地段要挖八九米深,有些地方还是坚硬的石头。
秋收刚完毕,花岭公社各大队都抽派出精壮劳力投入这项工程——排灌站建成后,逢旱年整个公社都可受益。
民工的劳动工作量很大,清晨六点听号声起床,从早到晚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爬坡,最深处要爬两层楼高。
我当时琢磨,如将举重、跑步那些每天锻炼腿部肌肉力量的运动员派到龙山坡挑几个月的土,他们在锦标赛上一定可拿冠军。
生活也艰苦,餐餐啃的是老米,咽的是水煮盐拌的大白菜,农民们吃饭时裆里总摆放着个大沙罐,他们可从家中带菜。
调剂一下生活。
罐里装的无非是腌韭菜、腌大蒜、腌萝卜、腌豆腐、腌萝卜缨子等等,钟祥菜有两大特色,什么菜都能腌,什么菜都可蒸。
这些腌菜淋了些小麻油,的确是香味扑鼻。
知青没有后方,偶尔到关系比较好的村民那儿蹭点菜吃,如爱面子不食周粟,那只得与大白菜为伍了。
三队有个原是旧口区的党委书记叫杨茂山,被打成右派后返乡务农,也被派往工地挖渠,他是在外闯荡见过世面的人,为人豪爽豁达,没把吃食看得很重,一次他从家中带了一罐蒸肉喊我与他共享,说来也惭愧,那顿晚餐消灭了他了小半罐肉。
白天促生产,晚上还要抓革命,学习形形色色的批判孔老二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属于自已的闲暇空间不多。
十月份的某天晚上,公社文艺宣传队到工地演出革命样版戏〔沙家浜〕。
我对演出没有什么热情——经常看,剧情都能背下来了,再说白天干活挖渠的工作的确很累,不如在四面透风的茅草工棚里的马灯下看看书,困了就往床上一歪,比看戏还惬意。
我把《唐诗小札》翻开看了几页,听见有人急匆匆的跑步声并喊着我的名字,说是工地指挥长英主任找我,喊我的是我们四队的排长赵楚成,他边走边告诉我:
今晚演出用的磨电鼓(发电机)坏了,灯泡没法点亮,英主任在演出现场急得抓耳挠腮,领导到底计高一筹,他突发灵感,问哪个连来了知识青年——连电机都不懂怎能称为知识青年?
于是我就成了被抓夫的对象。
我心中有些忐忑,因我对发电机结构不甚了解。
只是文革大串连时到上海花四毛钱买了一台用电池做动力的小电动机玩过。
演出的会场安排在一个很大的稻场内,观众们都已入席,在离演出场地三十米处,发电的动力部分——一部十二匹马力的柴油机已经在正常运行,我拆下发电机的盖壳,发现发电机的电刷没挨在转轴上,只要找到毛病,操作并不复杂——松开电刷的紧固镙丝,把电刷复位后与转轴挨紧,然后拧紧镙丝,把电机传送带与运转的柴油机连接后,十几个灯泡刷的全都亮了,稻场上灯火辉煌,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想不到瞎猫子碰到了个死老鼠,任务完成了,我与英主任打招呼告辞,说是回工棚睡觉。
英主任是个很随和的干部,他连笑带骂的递烟我抽,不让我走,他怕电机还出毛病。
于是我很荣幸地与英主任并肩坐在前排贵宾席观看演出。
饰阿庆嫂的是和我同大队三小队的女知青,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陈远栋。
她的表演是整个戏中最出彩的人物,她的脸型与根据样版戏所拍的电影里的阿庆嫂绝然不同——中等偏高的身材,圆脸,笑时有一对酒窝,大眼睛,小巧的鼻子。
倒与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的脸型相近。
但唱腔道白却也字正腔圆,她是七一届初中毕业后下放的知青,我比她大三届,大队开会、学习、民兵集训也曾与她有些泛泛之交。
这次演出后她的青春靓丽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处在青春期的年青人,谁都有着对异性的向往。
白马连工作挖掘的地段是最艰苦的地段——挖开一米多深的黄土层后,下面是坚硬的页岩。
我当上了炮长,一盘钎共三人,一人掌钎,两人轮锤。
一开始使的是木把锤,震得虎口流血,手掌起泡。
熟练后就模仿打炮眼的高手,把两根竹片镶在铁锤上,做成软把,抡起来成360度,配上哼呀嘿呀的打锤号子,煞是热闹好看。
炮眼一般打1.2米左右深,打好后用小石片盖上,再打新炮眼,在离收工还有半小时的时候,炮手们都忙碌着往炮眼里装填炸药,把长短各异的导火索插在雷管当中,如要震炸下面的石层,把雷管安在炸药上面,想让炮上下发力,把雷管放在炸药中间。
炮装妥当后,收工的号声响起,等民工们回到工棚后,号声又响起——这是点炮前的预备号,炮手们都把香烟点燃,猛抽几口,使香烟火头亮亮的,第三次吹的是急促的冲锋号,炮手们动作敏捷麻利,用香烟先把长些的导火索点燃,后又跑向第二个较长的导火索,然后点最短的第三个导火索,三盘炮点燃后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防炮棚跑去,躲在防炮棚竖着耳朵凝神细听炮的响声——巨大轰响声称之为冲天炮,属失败之作,并没撼动石头的根基。
低沉的轰响是成功之作,起码震松了两方石头——用撬扛一撬石头就剥离开了。
等上十分钟后,再检查排出没响的瞎炮。
这是炮长的责任
转眼已到了十一月份。
这天陈远栋又来到了工地,她不再是阿庆嫂了——巡回演出完毕后,公社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她被小队派往龙山坡工地,也来加入了这挖渠挑土的行列。
她逐渐的成功的转换了角色——她的削肩也挑着沉重的泥土和石块,挖土和搬石块使她在演戏中做玉兰指的手变得粗糙,凛冽的北风把她白晰的脸吹皴了,变成了风吹霜打的红色。
同是知青,彼此也都熟悉,我与陈远栋之间每天都有接触交往——收工后坐在一起吃乏味的水煮大白菜,学习时也并肩而坐。
她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天后,我看她消瘦了许多,身体难以承受这繁重的劳作。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觉得我应尽力帮助她。
我当炮长的权限是可以自由组合副手和掌钢钎的人,打炮眼掌钢钎在工地上是最轻松的活。
一天早上出工前我把钢钎交给了她,于是她顺理成章的成了我的下属。
她的工作就是手掌着钢钎,铁锤在钢钎上打二三下后转动着钢钎(钢钎可不能晃动),当炮眼里的石尘和碎石妨碍钢钎不能往下进展时抽出钢钎,用一根类似掏耳勺的铁勺把炮眼里的石末掏出来后,再把钢钎放进炮眼内,让两个炮手继续轮番锤打,周而复始。
我们休息睡觉的工棚颇有点返朴归原的韵味——工棚搭建在山脚下,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橡树,当然山野之中也少不了茅草,建房者们就地取材,用茅草辅设房顶,用茅草夹成墙壁,这茅草墙在温度下降或起风时形同虚设。
通风条件极佳,的确没有再设置窗户通风的必要。
床是在山上砍伐的原木搭成的统铺。
整个房舍与床铺没用一根铁钉(铁钉当时买不到)。
都是用竹篾、藤条绞紧加固的。
设计这工棚的当家师傅是付木匠,一个矮个子——所以工棚的门只有一米六高,个子稍高点的人都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出。
每天晚七点到九点是学习时间,学习的地点设在男工棚内。
晚上学习时年青的姑娘们手也没闲着,她们总有干不完的活,不是纳鞋底,就是打毛线——的确是革命生产两不误。
当时学习的主流任务是批判孔老二,讨论时每人都要发言。
白马连是先进连队,每晚指挥长英主任都参加我连的学习,这天他逐个点名要那些姑娘们发言,有个口齿比较伶俐的姑娘对孔子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她说完后,英主任又点别的姑娘发言,被点名的姑娘急中生智,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往下点将,都说我也是。
这场面引起了英主任的幽默,他讲了个关于也是的笑话:
有一个道士是个白字先生,有人父亲去世,请他去做道场,超度亡灵,他要孝子把自己和媳妇的姓名写在纸上,孝子姓潘叫金斗,媳妇姓乜,过去妇女无名,纸上写的乜氏。
道士对孝子、孝媳交待,我念下跪你就下跪,我念叩头你就磕头。
我咋念,你就咋做,不可坏了礼数。
于是道士摇头晃脑,抑扬顿错地照着纸念念有词——孝男翻金斗。
孝子一听,说的是我呢,只得一个跟斗翻了过去。
道士接着念孝媳也氏,媳妇一听,要我照着翻呢,硬着头皮也翻了个跟斗。
这个念错字道士的故事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陈远栋在学习时从不做手工活,但这两天她用枣红色的毛线在编识着什么小玩意,我想也许是女伴要她帮忙做点什么。
天还蒙蒙亮,起床号响起,民工们急匆匆地起床穿衣,漱口洗脸,吃饭也是三口并成二口扒。
完成早饭的任务后,我扛着铁锤和钢钎随着人群向工地走去。
走在我后边空着手的陈远栋把我的衣服拉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