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丽人待遇考.docx
《元代高丽人待遇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元代高丽人待遇考.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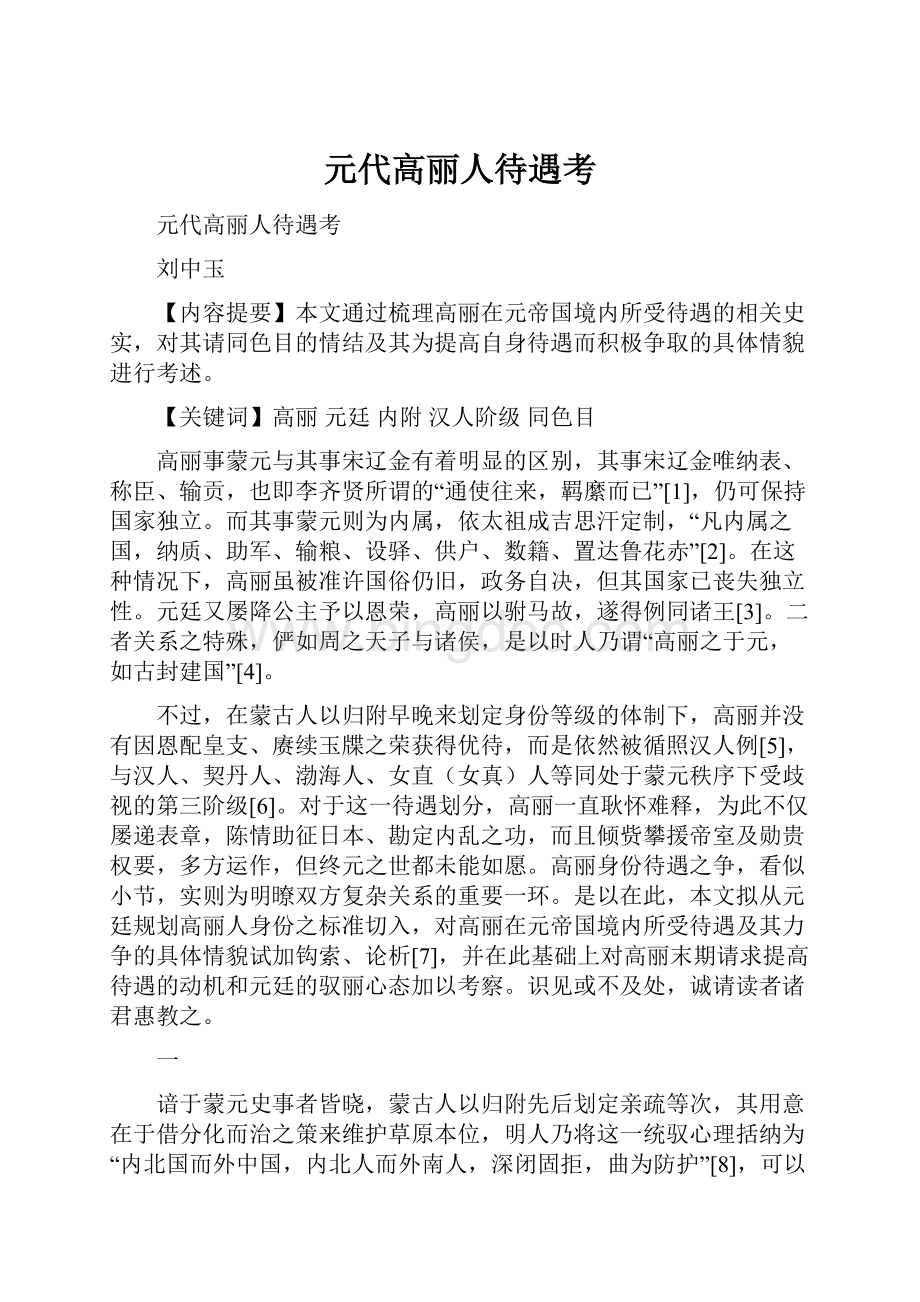
元代高丽人待遇考
元代高丽人待遇考
刘中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梳理高丽在元帝国境内所受待遇的相关史实,对其请同色目的情结及其为提高自身待遇而积极争取的具体情貌进行考述。
【关键词】高丽元廷内附汉人阶级同色目
高丽事蒙元与其事宋辽金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事宋辽金唯纳表、称臣、输贡,也即李齐贤所谓的“通使往来,羁縻而已”[1],仍可保持国家独立。
而其事蒙元则为内属,依太祖成吉思汗定制,“凡内属之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2]。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虽被准许国俗仍旧,政务自决,但其国家已丧失独立性。
元廷又屡降公主予以恩荣,高丽以驸马故,遂得例同诸王[3]。
二者关系之特殊,俨如周之天子与诸侯,是以时人乃谓“高丽之于元,如古封建国”[4]。
不过,在蒙古人以归附早晚来划定身份等级的体制下,高丽并没有因恩配皇支、赓续玉牒之荣获得优待,而是依然被循照汉人例[5],与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女直(女真)人等同处于蒙元秩序下受歧视的第三阶级[6]。
对于这一待遇划分,高丽一直耿怀难释,为此不仅屡递表章,陈情助征日本、勘定内乱之功,而且倾赀攀援帝室及勋贵权要,多方运作,但终元之世都未能如愿。
高丽身份待遇之争,看似小节,实则为明暸双方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
是以在此,本文拟从元廷规划高丽人身份之标准切入,对高丽在元帝国境内所受待遇及其力争的具体情貌试加钩索、论析[7],并在此基础上对高丽末期请求提高待遇的动机和元廷的驭丽心态加以考察。
识见或不及处,诚请读者诸君惠教之。
一
谙于蒙元史事者皆晓,蒙古人以归附先后划定亲疏等次,其用意在于借分化而治之策来维护草原本位,明人乃将这一统驭心理括纳为“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深闭固拒,曲为防护”[8],可以说是抓住了蒙元时期政治的主要特征。
就高丽而言,其虽于高宗王皞六年(1218年)成吉思汗命哈真、札剌追讨契丹叛部时出兵、助粮以示降顺,但这种降顺与蒙古人所要求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置达鲁花赤”还相去甚远。
为了迫其完全归附,从成吉思汗至蒙哥汗的二十余年间,屡加兵戈凌之,但高丽“内恃其险”,一直是表面上“卑辞臣贡”[9],而内心实不乐内附。
忽必烈即位后,乃一改前四汗对高丽的攻伐方略,采用女真人赵良弼和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的怀柔离间之策[10],立高丽世子王倎为新王(即元宗),以束里大为达鲁花赤[11],同时发敕其境,威抚兼施:
……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
大号一出,朕不食言。
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
于戏!
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籓,以扬我休命。
[12]
但元宗归国后仍逡巡迁延,不愿就陆,最后在忽必烈的催逼下,才于中统二年(1261年)正式内附(其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高丽国内对内附仍存在争议,并一度出现废黜元宗的紧张局面)。
忽必烈对高丽的表现非常不满,所以在至元七年(1270年)元宗(此时已更名为王禃)与世子王谌来朝时,乃使其朝会班次在诸王之下,而高昌亦都护则在诸王之上。
元宗当时似对同为相附却境遇悬殊提出疑义,忽必烈乃明确告之分班缘由:
“汝内附在后,故班在诸王之下,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上,阿思兰后附,故班其下,卿宜知之。
”[13]从忽必烈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为了惩戒和警示后归附的国家和种族,蒙古人惯用以等次别之的办法故意体现出亲疏远近。
元宗班次诸王之下,便是一种惩罚性待遇。
至于当时蒙元朝会中高丽班次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从至元十年(1273年)随侍王子顺安侯王悰来贺察必皇后和真金太子册封典礼的李承休所撰《宾王录》中略知一二:
皇帝陛下普会诸侯,以是月(八月)二十有七日落之。
……自诸大王、诸大官人以至百寮,黎明而会,莫不朝衣穿执而云委于中庭。
有阁门使各以其序引进拜位。
其拜位则以黄丹画地面,龙须白席为之方罫,区以别位,而书其官号。
即引立已,令馆伴侯学士、姜宣使引我令殿(王悰)并侯邸及官属,列立于班心之下。
其余诸国来朝之使,从其所服而俾立于最后行尾。
……其赐座位序,则西偏第一行皇太子,隔一位大王六,隔二位我令殿;后行大王七,隔二位我侯邸;后行安童丞相为首十许员,隔二位我行宰臣,次诸官人等;后行之腰,我行尚书、侍郎;后行之腰,我行参上参外;后后行行未得其详。
……[14]
李氏记文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朝会中高丽使团的位序,即拜位“列立于班心之下”,王子座位虽与诸王同列,但在诸王之下。
这种位次与至元七年应无所差异。
而行文中关于“其余诸国来朝之使,从其所服而俾立于最后行尾”的记载,看似随意,实际上则反映了高丽使臣的自我平衡心态。
这种推测并非是空穴来风,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高丽使臣金之淑如元贺圣节时,便因班次问题与交趾使者发生争执,并以“本国率先归附,结为甥舅之亲,非他国比”为辞而请成宗评断,结果被赐坐诸侯王之列[15]。
由此不难想象高丽方面对在蒙元秩序下地位问题的关注程度。
王室朝会班次尚且论归附先后,至于一般高丽人更是为这一标准所绳,被划入第三阶级,与汉人、女真人同列。
而之所以将其归类汉人,则又是蒙古人以文化划分种群观念的体现。
如在对待女真人、契丹人的归属问题上,不通汉语者与通汉语者的待遇便截然不同。
《元史·世祖纪》载: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答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
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汉地,同汉人。
”[16]忽必烈对于汉文化的态度始终为实用主义所主导,其虽重用儒士,却并不喜其文化,而高丽久习汉风,“识会文字,行夫子之道”(忽必烈语)[17]。
他又曾语赵良弼曰:
“高丽,小国也,匠弓羿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史,学孔、孟。
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
”[18]这番话虽是针对赵良弼倡议设经史科以笼络南宋士人而发,但却表达了两层含义:
一是相较于儒学,忽必烈更看重高丽人的“匠弓羿技”;二是高丽人沉浸于儒学甚深,远胜汉人“惟务课赋吟诗”。
在这一背景下,以文化同源将高丽归入汉人之列,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末,高丽人既与汉人、南人处于蒙古人所定秩序的下层,便自然属于被排压的对象。
为了惩戒和防止高丽反复,忽必烈时期曾多次申谕其境,禁止其国人执弓矢和买卖军资:
(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丁丑)蒙古中书省移文,禁国人贸易上国兵器及马。
(至元八年十月甲辰)副达鲁花赤焦天翼曰:
“兵器不可畜于私家,收国人攻珍岛兵仗,悉输于盐州屯所。
”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五月壬辰)达鲁花赤黑的禁人挟弓矢。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丙辰)达鲁花赤张榜国人,军士外禁持弓箭兵器[19]。
《元史·刑法志》也载:
“诸高丽使臣,所带徒从,来则俱来,去则俱去,辄留中路郡邑买卖者,禁之;易马出界者,禁之。
”[20]可以说,位次之别、弓矢之禁,都让高丽对归附后所受到的待遇耿耿于怀。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高丽王室在处理与元廷关系时逐渐采取主动配合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动请婚。
这是最有效的政治投机。
对于元丽联姻之意义,萧启庆先生有肯綮之论,他认为“元丽联姻改变了两国间意理及实质上的关系。
尚主以前,高丽不过是元朝的外藩之一,两国的交往仅限于藩属与宗主间的正式层次。
……尚主之后,宗藩关系逐渐转为姻戚、亲族的关系。
……在实际的层次,此后高丽对元廷的经济负担可能并未减轻,但在意理的层次,礼物的交换已不代表宗藩间的外交行为,而是亲族间的亲睦行为”[21]。
本文在此略而不论。
二、助征日本。
忠烈王(王谌)继位后,一改其父元宗消极推诿的做法,积极配合征日(详参《高丽史·忠烈王世家》,限于篇幅,不一一举论),因此深获忽必烈的好感。
至元三十年(1293年)朝元时,元廷给予隆重接待,“宠赉之厚,诸王驸马无比”。
不久(次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忠烈王被获准亲与丧事,而“元朝丧制,非国人不敢近,唯高丽得与焉”[22](当然这也与其驸马身份有关)。
三、积极与谋元廷选汗和汗位争夺。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忠烈王以驸马身份参与忽里勒台大会,真诚拥立成宗即位,受到成宗嘉许,高丽王室在元廷的地位也因此获得较大提升。
在成宗举行的诸王驸马宴上,忠烈王便被安排坐在第七位,并以功大年高受到乘小车至殿门的礼遇。
成宗又遣翰林学士撒剌蛮询问归附年月,高丽方面已深谙元廷亲疏远近之道,乃以高宗六年助蒙古军攻灭契丹叛部为归附之始奏对(此后但凡其奏表皆以此时为准)。
虽然这与忽必烈所认定的内附时间相差四十余年,但成宗不以为意,仍表示认可。
元贞二年(1296年)忠烈王如元,宴会时仍坐第七。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忠烈王获赐弓矢及剑,其从臣亦得赐弓三十九,矢五百。
赐与弓矢也即意味着弛禁,表明高丽已通过考核,晋升信任之列。
大德四年(1300年)忠烈王再如元朝觐时,只孙宴上的座次又被提升到第四位,可谓宠眷殊甚[23]。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宗时还在量刑上给予高丽人较汉人、南人稍高的待遇。
《元史·成宗纪》载:
大德八年(1304年)十一月壬子,诏:
“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
”[24]
很显然,在这一法律语境下,高丽人的待遇似已比同色目人了。
忠宣王王璋亦积极参与过元廷帝位的争夺。
在其因擅自变更官制被褫夺王爵而不得不再次入侍阙庭“明习于事”后,便与内弟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暗结联盟,《高丽史》记曰:
“武宗、仁宗龙潜,与王(王璋)同卧起,昼夜不相离。
”[25]成宗宾天后,王璋便奉仁宗扫内难,以迎武宗,因此功为第一,被封为沈阳王,同时加功臣号、驸马都尉,勋上柱国,阶开府仪同三司,一时宠眷无出右者[26]。
仁宗即位后又按宗王例,晋封其为一字王“沈王”,进尚书右丞相,并推恩三代,可谓无以尚者[27]。
此外,元廷为示恩宠,还在设置征东行省等问题上予以让步。
《元史·武宗纪》载:
(至大元年,1308年)夏四月,丙辰,高丽国王王章(璋)言:
“陛下令臣还国,复设官行征东行省事。
高丽岁数不登,百姓乏食,又数百人仰食其土,则民不胜其困,且非世祖旧制。
”帝曰:
“先请立者以卿言,今请罢亦以卿言,其准世祖旧制,速遣使往罢之。
”[28]
由此可见,高丽之所以在成宗、武宗、仁宗时期地位获得较大上升,都与拥戴之功分不开。
四、献纳、援交,也即施展进献、贿赂的手段,以讨好帝室、拉拢权要,这是高丽最常用的手段。
如在大德四年的宴会上,忠烈王父子君臣为邀宠不惜亲自奉献歌舞:
(六月)戊辰,王以羊二百头、酒二百榼上寿于帝。
乙巳,又诣阙,设扶头宴。
帝命唱高丽歌。
王令大将军宋邦英、宋英等歌《双燕曲》,前王(王璋)执檀板,王起舞献寿。
帝与后悦。
……(七月)甲戌朔,帝使人勑王,曰:
“凡有所奏言,即闻奏。
”辛巳,王诣阙,献帝童女二人,阉竖三人,又以童女一归丞相完泽。
丁丑,王侍宴,帝以皇太子千秋节赦印侯金忻等。
辛巳,帝命右丞相完泽传旨云:
“高丽王国所奏风俗百事,许令依旧。
”壬午,帝赐王弓矢、海青、鹞子及金鞍二。
癸未,又赐王从臣金段表里各三百三十六匹、弓剑各三十、鞍二十。
乙酉,皇后赐王衣三袭。
[29]
由上来看,高丽王室为使诉求顺利通过,而不惜采取资财、童女、阉竖之献,歌舞之悦,以及贿赂权要等手段,结果不仅再次获得弓矢、马鞍之赐(也即再次被示恩弛禁),而且被准以风俗百事依旧(依世祖故事)。
对于高丽王室上邀宠于帝后,下倾赀结纳朝臣的做法,元朝的清流之士颇轻视之,《元史·姚燧传》载:
时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倾赀结朝臣。
一日,欲求燧诗文,燧靳不与,至奉旨,乃与之。
王赠谢币帛、金玉、名画五十篚,盛陈致燧。
燧即分散诸属官及史胥侍从,止留金银,付翰林院为公用器皿,燧一无所取。
人问之,燧曰:
“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
”[30]
我们从王璋赠送姚燧财物之多便不难想象,高丽王室在援交方面的花费是何等巨大。
而这种浩繁之费最终导致其“国人困苦供馈”,并进而引发内讧[31],元廷则坐收渔人之利(下文详论)。
五、根据元廷政治势力的变化,及时调整外交对象。
参前论可知,武宗是通过政变取得帝位的,即位时国库已虚,但为奖赏功臣,笼络人心,仍旧大肆赏赐,以致仅四个月后,中书省便上奏告困:
“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
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
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
”对此局面,武宗一方面下旨停止赏赐:
“自今赐予宜暂停,诸人毋得奏请。
可给晋王钞千锭,余移陕西省给之。
”另一方面则效仿忽必烈立尚书省,委任脱虎脱、三宝奴等色目人总理财用[32],这就使色目人的势力重新抬头。
对于元中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韩国学者李玠奭先生论议详瞻,他认为武宗政权成立后,元朝支配势力发生重组,蒙古草原贵族、色目军阀抬头,遂使大批草原势力居于朝廷核心地位,他们对汉法的统治体制进行了修正,即“创治改法”[33]。
而这一改造之举触动了以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仁宗)为首的汉法派的利益,所以在其临御后,迅速将尚书省裁撤,并诛杀脱虎脱、三宝奴等人。
但色目人的势力并未因此消退,而是依然在元廷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如泰定帝时的宠臣倒剌沙、文宗时的燕帖木儿等。
这股势力的重新崛起,很快便受到高丽王室的重视,高丽王党为挫败沈王王暠一党的夺位阴谋,乃倾赀攀援贿交,其中忠惠王王祯与燕帖木儿的交往便很典型。
燕帖木儿为句容郡王床兀儿第三子[34],钦察人,武宗龙潜时便入宿卫十余年,深受倚重。
武宗即位后,擢拔其为正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
仁宗时,袭父职为左卫亲军都指挥使。
泰定帝年间,燕帖木儿已为太仆卿,同佥枢密院事,并总环卫事。
泰定帝殂后,以武宗恩宠之故,力主怀王图帖睦尔(武宗子,即文宗)承继大统,遂在文宗朝获无右之宠,官至中书省右丞相,封答剌罕、太平王[35],专揽朝政。
这自然成为高丽王室外交锁定的最佳人选。
天历元年(1328年),王祯以世子身份入侍大都,与燕帖木儿意气投合,二人经常宴饮嬉戏,放鹰游乐,欢若父子。
由于这层关系,王祯在元廷大获恩荣。
天历三年(1330年),经燕帖木儿奏请,王祯被册为高丽国王(时忠肃王为避沈王党而托以疾辞),旋又尚关西王焦八长女德宁公主,也在元廷享有位列属序之荣[36]。
为报燕帖木儿的援引之情,王祯回国后(至顺二年,1331年)便割国中田奉送之[37]。
二
由以上论列我们可以明晰一个基本事实,即在高丽的多重努力下,无论王室、国人在元廷秩序下的待遇都获得了较大提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丽人的地位已经上升到色目人的阶级了,在大德八年、大徳十一年(1307年),元廷都曾明文确定高丽人不在色目人之列。
如《元典章·刑部》“流远出军地面”条(49/5a、1897):
大徳十一年正月行台、申(?
):
强盗持杖伤人、法不所(?
)容。
……照得、近准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箚付、蒙古译核、中书省官人毎根底、宝哥为头、也可札鲁忽赤毎言语,……又“出军的、不知何处出军有?
合出军的合无刺断?
又未审何等为色目人?
”么道,申(?
)明降来。
……为那上头、俺商量了,“旧贼毎再做贼呵、验着经刺来的、前后理算定夺。
……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倶系色目人有。
合出军的贼根底、不刺断、交出军有来。
……”[38]
根据上引文可知,“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倶系色目人有”这一明文实际上再次限定了高丽人的阶级。
由此也说明虽然高丽方面百般努力,但元廷对于阶等的松动是相当有限的,即便是在元丽交好的时期,高丽希望提升待遇的某些要求也被视为过分。
如元贞元年六月,忠烈王上书乞为太师中书令,而元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兼,忠烈王的这一请求虽只是荣衔,但也被视为非分,故遭成宗驳回[39]。
而终元一代,高丽人并未逃脱与汉人、南人同受禁限的命运,尤其是在宿卫这一问题上。
宿卫制度始于成吉思汗,初,宿卫皆从蒙古诸部中遴选,后因黄金家族壮大、机构设置增多,所需宿卫大大增加,遂开始吸收色目人、汉人、高丽人等。
如“至元二年(1264年)十二月,增侍卫亲军一万人,内选女直军三千,高丽军三千,阿海三千,益都路一千。
”[40]然虽同为宿卫,阶级界限依旧存在,特别是在弓矢、服饰方面。
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壬寅,“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41]。
延佑元年(1314年)十二月,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惟不许服龙凤文”,但是,“今后汉人高丽南人等投充怯薛者,并在禁限”。
[42]等等。
尽管如此,由于宿卫在元廷政治中享有诸多特权,且待遇优厚,对处于第三阶级的汉人、南人、高丽人而言仍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故而他们为了避役冒领[43],想方设法混入其中,从而使得宿卫人员大大超限,财政难以支应。
为此元廷不得不经常下旨沙汰。
毫无悬念的是,每次最先被裁汰的便是汉人、南人和高丽人:
(武宗至大二年六月甲戌),以宿卫之士比多冗杂,遵旧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余(其中自然包括高丽人)皆革去[44]。
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仁宗)诏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元籍。
[45]
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元廷又下旨裁汰怯薛[46],此次较以往更为严厉,对于容匿者亦予以惩处。
《至正条格·断例》之卫禁“分拣怯薛歹”条:
文宗至顺元年闰七月初十日,中书省奏,节该:
“各怯薛、各枝儿里,将无体例的汉人、蛮子并(高丽)人的奴婢等夹带着行呵,将各怯薛官、各枝儿头目每,打五十七下。
孛可温、亦里哈温夹带行的人每,打七十七下。
将不应的人,看觑面情,不分拣教出去,却将合行的分拣扰害呵,将各怯薛官、各枝儿头目每,并孛可温、亦里哈温,只依这例,要罪过。
有体例行的怯薛丹、各枝儿每,元支请的钞定、草料,依验分拣来的数目,均减钞定、草料外,分拣出去的人每内,不应行的汉人、蛮子、高丽人每的奴婢,并冒名数目等有呵,怯薛官、各枝儿头目尽数分拣出去。
其有体例合行的每根底,依旧与衣粮,不依体例行的,教监察御史每好生用心体察者。
各怯薛、各枝儿里晓谕呵,怎生?
”奏呵,奉圣旨:
“是有。
与的每根底,依恁商量来的,与者。
”[47]
《元史》对此亦载录甚详,只是时间记为八月: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言:
“臣等比奉旨裁省卫士,今定大内四宿卫之士,每宿卫不过四百人;累朝宿卫之士,各不过二百人。
鹰坊万四千二十四人,当减者四千人。
内饔九百九十人,四怯薛当留者各百人。
累朝旧邸宫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当留者千一百二十人。
媵臣、怯怜口共万人,当留者六千人。
其汰去者,斥归本部着籍应役。
自裁省之后,各宿卫复有容匿汉、南、高丽人及奴隶滥充者,怯薛官与其长杖五十七,犯者与典给散者皆杖七十七,没家赀之半,以籍入之半为告者赏。
仍令监察御史察之。
”制可。
[48]
参上举例证可知,在元廷深闭固拒的统驭心态下,对于具有汉文化背景的高丽人并没有因王室受宠而给予优待,蒙古人的王泽之施,鲜少惠及汉人阶级,即便是在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仁宗、文宗时代,阶级界限也难被打破。
三
而让高丽始料不及的是,顺帝时高丽因忠惠王王祯与燕帖木儿家族关系密切的缘故,受到元廷政治斗争的波及,在以伯颜为首的蒙古守旧势力的严厉排压下,不仅国王在元廷地位下降,而且被重申弓矢之禁。
伯颜与燕帖木儿一样,也是拥戴文宗登极的主要参与者,他对燕帖木儿专横跋扈的做法一直怀有不满,王祯由于依附燕帖木儿,自然遭到他的反感。
迨燕帖木儿死后,伯颜当政,并于后至元元年六月将因怨怼而谋逆的燕帖木儿子侄唐其势等人或诛杀、或放逐[49]。
时王祯正入值宿卫(被废后再度入侍),自然难逃池鱼之殃。
后至元二年(1336年),乃被伯颜寻故遣送回国。
《高丽史》记曰:
大行王(忠肃王)复位,前王(王祯)宿卫于元,时燕帖木儿已死,伯颜待前王益薄。
前王与燕帖木儿子弟及回骨少年辈饮酒为谑,因爱一回骨女,或不上宿卫,伯颜益恶之,目曰“拨皮”。
……伯颜奏帝云:
“王祯素无行,恐累宿卫,宜送乃父所,使教义方。
”制可。
[50]
如前所述,伯颜是蒙古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排斥汉法,对汉人、南人成见颇深。
因而在其主政的元统、至元年间,对汉人裁抑尤甚,不仅重申兵马之禁,甚至提出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荒唐建议。
高丽因与汉人、南人文化同源,再加上王祯的缘故,自然难以幸免。
在伯颜主导下,元廷对高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禁兵马。
后至元三年(1337年),诏谕高丽,重申弓矢之禁,并下令“凡有马者拘入官”,以致高丽百官皆不理事,后在征东行省的斡旋下才允许百官骑马[51]。
后至元五年(1339年)四月,再次宣谕高丽禁弓矢[52]。
二、支持沈王王暠一党,反对王祯袭位。
后至元五年三月,忠肃王卒后,伯颜对王祯的继位百般设阻。
《高丽史》载:
“……由是行省左右司转达中书省,前王(王祯)亦遣前佥议评理李揆等求袭位,而伯颜为太师,寝不奏,且言:
‘王焘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矣。
拨皮虽嫡长,亦不复为王,唯暠可王。
’揆等百计请之不得。
”[53]此后王祯屡遣使前往大都贿求复位,并请耆老权溥等上表陈情,但伯颜固执不允。
与此同时,沈王党曹頔以王祯强暴庆华公主为借口围攻王宫,并密告伯颜。
是年冬十一月,王祯被抓至大都,囚禁刑部[54]。
时伯颜“奏令五府官杂问,而力右頔党”。
伯颜之所以对王祯如此苛刻,究其因乃是“蓄宿憾”,即仍抓住王祯的旧恶不放[55]。
而此时元廷内部也正酝酿一场权力争斗的大戏。
伯颜因过度跋扈擅权,为其侄脱脱所虑,脱脱恐其势败受诛连,乃与顺帝谋划驱逐之。
后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脱脱等乘伯颜出猎之机,以“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的罪名将其贬逐[56],王祯旋即在脱脱的奏请下获释复位[57]。
脱脱当权后,悉更伯颜旧政,尤其是在对汉人、南人、高丽人的态度上大为转变,取消了对汉人阶级的弓矢、军马之禁[58]。
高丽方面乃抓住这一时机,接连上表请同色目:
天必听卑,曲从人欲;事难泥古,断在帝心。
辄露愚衷,敢尘睿鉴云云。
能哲而惠,自诚而明。
遵列祖之宪章,简临宽御;晓多方于品制,迩肃远安。
已推彰信之仁,又笃念功之义。
顾惟弊邑,服我大邦。
敌忾攻辽,助圣武东征之旅;观光过汴,迎世皇北上之师。
遂蒙釐降之荣,获守藩宣之寄。
洎子孙而相继,讲甥舅之至欢。
及际休明,益深缘幸。
元良载诞,允孚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谓三韩之福。
因念曾忝联芳于玉叶,更逢毓庆于璿源。
既然得附于本支,何乃未同于色目。
肆历由中之恳,伫沾无外之恩。
伏望赐以俞音。
(李齐贤所拟《乞比色目表》)[59]
头戴一天,常仰好生之德;身居千里,徒怀恋主之诚。
敢陈忠恳者,上天临下,从物欲以遂生。
大圣执中,顺时宜而定制。
敢陈愚悃,用渎亶聪。
钦惟海纳朝宗,父临族姓。
图成《王会》,示远俗之形容;篇咏《鹿鸣》,得佳宾之燕乐。
伏念小邦,先投圣化,累著殊勋。
方初釐降帝姬,永以庆流于万世;今又诞生圣嗣,必将福及于三韩。
有何不世之功,值此难遭之幸。
亲则是一家甥舅,义则为同体君臣。
兹远别于汉南,得同入于色目。
伏望谅臣匪他之恳,知臣附本之心。
廓阐至仁,俯颁俞旨。
则臣敢不仰日月,披肝露胆,期报恩荣至子孙,竭力输忠,勉修臣贡。
(安轴所拟《请同色目表》)[60]
表中提到的“圣嗣”、“元良”即指爱猷识理达腊[61],“更逢毓庆于璇源”,乃指是年三月高丽奇氏被封为第二皇后。
同时,表中又重提高丽归附、助征之功,希望元廷能施“无外之恩”、“廓阐至仁,俯颁俞旨”。
但其请同色目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元廷对其在某些方面的禁限仍较严格。
如至正元年(1341年)六月戊午,“禁高丽及诸处民以亲子为宦者,因避赋役。
”[62]后因王祯归国后继续“昵比恶小,荒淫纵恣”,致使国内民怨沸腾,奇后兄奇辙等亦上书告诉,顺帝乃于至正三年(1343年)十一月派使臣朵赤等将之索拿大都[63]。
为此李兆年、李齐贤等高丽重臣纷纷上书请宥,其中李齐贤在《上征东省书》中又提及高丽待遇问题:
……宝塔实里王(王祯蒙古名)虽疏且远,其于世祖,实有肺腑之亲焉。
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诞毓元良,为天下所庆赖。
朝廷之视小邦,不应与诸蕃同焉。
……[64]
在高丽方面看来,之所以会屡屡发生国王被废、被抓、被流放这样的事件,主要还是因为高丽在元廷秩序下地位不高的缘故。
高丽虽有甥舅之亲,有“上配至尊,诞毓元良”之荣,但却无助于提升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