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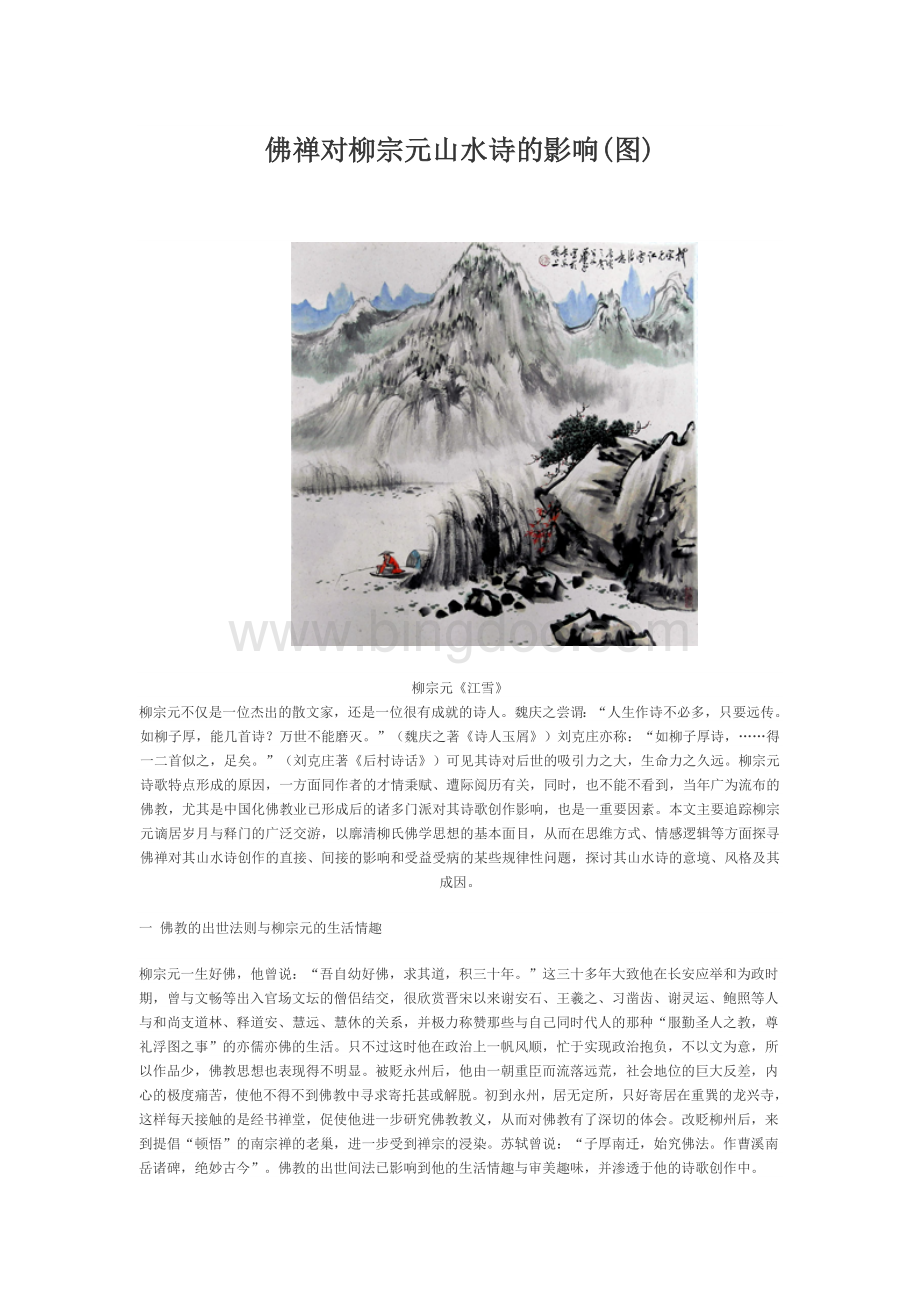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
”(《构法华寺西亭》)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蹇衣。
”(《夏夜苦热登西楼》)
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
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
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
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
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
柳宗元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
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
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佛与儒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
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
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
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
1.清冷幽寒的画面
常言道:
“天下名山僧多占。
”古刹名寺一般都座落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乡,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又远离人事的格斗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同高僧们潜心研读经典必需的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们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从而潜心于体悟禅理经义。
所以,尽管禅宗也主张“平常心是道”、“担水劈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无非妙道”,主张在正常的与世俗无异的生活中体悟自性,证得无上菩提,但他们仍然偏爱这幽静的所在,与自然山水有着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
佛门以“空”为本,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常住不变的本相。
“空”为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义。
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虚无,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
佛家这种讲出世、重自然、追求平静、清幽的境界,对柳宗元的审美趣味影响很大。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却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
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
这种审美趣味决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的,他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曾把美的形态概括为两种:
“游之适,大率有二:
奥如也,旷如也。
如斯而已。
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
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
”这种美学观自然体现在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上,于是,反映幽深静寂的图景,便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幽”、“寒”等充满凄冷意味的字句。
例如:
“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
”(《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
”(《新植海石榴》)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
”(《巽公院五咏.苦竹桥》)
“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
”(《赠江华长老》)
“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江高。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
”(《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这些诗句,勿需外在的刻意渲染,就已弥漫着清寒幽冷的气氛,表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记》)的境界。
据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审美情趣》一文统计,在柳宗元一百六十多首诗中,竟有七十三首使用了“幽独”、“清寒”的意象。
足见其审美情趣的独特性。
2.宁静淡远的意境
贬谪中的柳宗元,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
他同他们参禅论道,谈玄说佛,并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序碑铭。
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
在青灯梵呗、晨钟暮鼓的氛围中,他暂时忘却了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得到了“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的愉悦与满足,因而,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宁静、淡远的意境。
古人早就注意到柳诗情绪冲淡这一重要特征。
“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东坡题跋》上卷《评韩诗》)杨万里说:
“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
”(《诚斋诗话》)柳宗元确实擅长从普通的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构思淡雅秀美的意境。
试看《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永州后定居愚溪时所作。
诗中写自己已厌倦了长期官场的拘束,认为这次被贬南荒反是幸事。
作者透过对晨出夜归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悠雅清淡的图画,表现了作者悠闲惬意的心境。
诗中船桨碰撞溪水中的石块发出清亮的音响及作者的引吭长歌,衬得山中更加幽寂。
因为这些声响正是以“来往不逢人”的夜的宁静作背景,诗中虽描写了声响,但最终还是导向静谧的,在意境的创作上,着意追求一种无人之境的宁静之美。
再看《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未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
全诗清空恬淡,没有世俗的喧嚣扰攘。
诗人以“无事”之心,造宁静之境,描写了雨后愚溪北池早晨的景色:
云散日出,溪景明丽,高树临池。
诗人置身其间,闲适的心境与清幽的景物如宾主相得,浑然融契。
全诗的景物平凡、自然,丝毫看不出诗人主观情绪的涉入。
这些景物以本来形态直接与心灵契合,似乎已经消除了语言的中介。
“就文学范围而言,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启示,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悟道的深度,而是在于禅学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构思的渗透与影响。
”(注:
许总《论柳宗元谪居心理空间与诗境构造方式》,《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泥束缚,雕琢藻饰,一切都在本然之中,都是自然本心的流露,一切都是淡而无为,而不应是用心著力的。
禅宗许多公案表现了这种淡然忘机、无系于心、无所挂碍的精神。
“僧问:
‘如何是僧人用心处?
’师曰:
‘用心即错!
’”“问:
‘如何是学人著力处?
‘春来草自青,月上已天明’”(《五灯会元》卷11)。
禅在自然而然中,如春日草青,月上天明一样自然,不可以用心著力。
读柳宗元的山水诗,常常会感到禅宗非理性的直觉体验与不于境上生心的思维方式对其艺术构思的渗透与影响。
如《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
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
诗人写在江雨初晴的傍晚,独自向溪边漫步所看到的景象:
渡头大水泻过,通向村中的小径显露出来,由上游冲下来的浮木高高地挂在树梢之上。
诗人写雨后景象,仅以渡头水落后初显及遗存的物象为着眼点,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既生动又逼真,透过清淡的景象,可见诗人直观摄照的特点。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平淡的风格,来源于诗人无所缚系、任运自在,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不执着于物的主体心态。
再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作者以素描的手法,用浅淡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幽雅秀美的江南水乡风光图,生动地描绘了湘江渔夫日常的水上生活和湘江周围的自然景色。
漂泊的渔翁,清澈的江水,袅袅的炊烟,初升的红日,构成了一幅闲适恬静的画面,使人产生一种柔和秀美之感,而依稀的橹声更反衬出画面的寂静。
诗的最后两句不正是禅宗“不于境上生心”的形象表现吗?
再如下面这些诗句:
“远山攒众顶,澄江抱清湾。
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
“平野春草绿,晚莺啼远林。
”(《零陵春望》)
“霰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
”(《旦携谢山人至愚溪》)
“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
”(《首春逢耕者》)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夏昼偶作》)
“旷野行人少,时闻田鹤鸣。
”(《游石角小岭至长乌村》)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
”(《与崔策登西山》)
这些诗句,都是使诗人在一瞬间直觉地发现大自然澄江如练、夕照临轩的画面,感受到雁鸣高天、莺啼远林、童敲茶臼、旷野鸣禽的清音。
诗中静中有动,寂中有喧。
这种寂静气氛的捕捉与传达,正是诗人心中那“无念”、“无住”之禅境的外化。
“禅学给唐诗带来了禅境,因而也带来了诗境。
这对于唐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是禅境,才使唐诗获得了美好的意象与清醇的意境。
这是唐诗艺术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关捩或秘密,是唐诗空前繁荣的最重要的遗传基因。
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44页。
)我们不防套用一句说:
是禅境成就了柳诗的意境。
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提,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
因而,他能够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恶,一死生。
他“夙志随忧尽”(《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二十韵》),“处心齐宠辱”(《献弘农公五十韵》),认识到“荣贱俱为累”(《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居宠真虚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他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
“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与崔策登西山》)从而萌发了“乐居夷而忘故土”(《钴鉧潭记》)的念头,恬淡的心情于是凝结为诗歌中的冲淡美。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柳宗元的山水诗,虽有许多写无我之境,但更多是写有我之境。
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的。
读这些山水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这些具有人的品格的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
古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茅坤在《唐大家柳柳州文钞》中指出:
“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
他所吟咏的对象,无论是“窈窕凌清霜”的红蕉,还是“劲色不改旧”的青松,无论是“晚岁有余芳”的桔柚,还是“蓊郁有华枝”的新竹,都有着同诗人同样美好的品质和不幸的遭遇。
这种感情在《愚溪诗序》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
愚溪“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
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空寂的佛门,宁静的大自然净化着他来自世俗尘网的怀抱,但儒家强烈的入世意志又使他难以忘怀世事,于是在他的笔下,那些原本是自然存在的山水都被解读为因遭贬而屈居是州。
面对钴鉧潭西的小丘,他叹息到:
“噫!
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户、杜,则贵游之士争买之。
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鉧潭西小丘记》)。
来到小石城山,他又说道: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
及是,愈以为诚有。
又怪其不为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
无疑,他是在通过这些秀美山水的无人赏识来证明他的自身价值和不公命运。
“永州那远离京华的自然环境,山水之奇崛几乎就是他自己被弃绝不用的美才的写照”(注:
陈幼石著《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56页。
)。
读柳宗元的山水诗文,我们很难分清作者是写山水,还是在写自己。
可以说,它们句句是景语,字字是情语。
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无不带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
这种物我一体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正是受佛门物我同根的思想影响所致。
佛性说到天台宗荆溪湛然时,在原来“众生有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说。
意思是不仅一切有情众生具有佛性,就连砖瓦石块这些无情之物也具有佛性,因为佛是无处不在的。
禅宗主张法遍一切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
而作为重巽的俗家弟子及被苏轼誉为“妙绝古今”的曹溪南岳诸碑的作者柳宗元不可能不受到这一学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原本无情的山水景物,都具有了人的感情。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首诗:
《商山临路有孤松》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
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
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这是诗人在元和十年诏回长安,再出柳州,途经商山而作。
诗题中这样写道:
“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
正如详注中指出的:
“盖有自况之意”。
诗中处处写孤松,又笔笔写诗人自己。
作者写松,取其冬夏常青,岁寒不凋的本色,正是写自己怀抱理想,坚定不移的品格;
而一“孤”字,更托出自己去国离乡,茕茕孑立的特定心情。
前四句写自己在仕途上的遭遇:
秉正而行,光明磊落,却遭到奸党小人的迫害。
诗人在同期写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中也作过同样的反思: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把政治失败归之为自己行为的直道而行,不拘小节和才华、名气太大而遭到奸小嫉妒。
两诗对照着读,更能领会诗人曲折而深刻地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
后四句写出诗人对同情者的感激和对统治者抱有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作者不甘沉沦,实现抱负,建功立业的渴望。
再如《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
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湘江流水的命运联系起来,流水的一去不复返,不正是诗人终身贬黜,难返故乡的写照吗?
再看《南中荣桔柚》:
桔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
密林耀朱绿,晚岁有余芳。
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
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桔柚的贞质和命运,实际上仍是写诗人自己的品格和遭遇。
诗的前四句就桔柚的“贞质”、“余芳”,赞美了自己的才华和品格,肯定了自己的理想抱负;
后四句以“殊风”、“飞雪”暗喻奸党小人的打击和阻挠,使自己北归无望,只能北望故乡,攀条叹息。
诗人把自己的生平遭遇与桔柚的品质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以佛门的物我同根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抒发了其儒家的怀才不遇的愤懑抑郁之情。
4.欲求解脱而不能的寂寞情怀
在长期的贬黜生涯中,柳宗元由于对世事的系念难忘,致使佛教的精神药方难以彻底医治他心灵的痛苦,山水的宁静反而引发他寂寞的情怀。
他在佛教与山水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与沉迷,却很快被现实的剧痛唤醒。
于是他的山水诗形成苏轼所说的:
“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南涧中题》详注)的模式。
用柳宗元自己的诗句来概括,就是:
“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
《构法华寺西亭》一诗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诗人寻求解脱而不能的心理历程。
诗的开头两句点明了诗人不幸的身世及恶劣的环境,贬谪南荒的确使他心情郁闷。
为了消解这种郁闷的痛苦,他“步登最高寺”,俯视人间万物,开阔的大自然真的具有神奇的疗效,此刻,他似有飘若升仙之感。
他与现实社会的距离逐渐拉开,贬谪之苦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心理渐趋平衡,心境渐趋宁静。
然而,在短暂的沉醉之后,各种“离念”却纷至沓来,久已难得的“开颜”和转瞬即逝的“赏心”,很快就被远离亲人和京城的痛苦和蛰处蛮荒的寂寞所代替。
诗人排解郁闷的目的并未达到。
再如《南涧中题》,诗中既有气氛的清冷凄迷,又有境界的幽静深邃。
大自然的风声林影,使他“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其实,诗人这里忘却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更是灵魂的疲惫。
他的若有所得,不正是从这静谧的大自然中悟到的禅意吗?
那空谷中鸣响的禽语,那涧水中回旋的寒藻,多么合乎自然的本性。
可是,他的心灵在这短暂的歇息之后,又回到令他痛苦不堪的现实社会中来,眼前的景物勾起诗人孤单寂寞的身世之感。
于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全诗意境宁静、淡远,但在这宁静淡远中却蕴聚着诗人深重的忧伤,折射着诗人贬谪后孤独寂寞的情怀。
再看《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诗人写月夜的静谧,却是通过繁露坠地,石泉鸣响,山鸟啼叫这些声音反衬出来的。
诗人若不受过禅学的熏染,是很难捕捉到这大自然的清音的。
但诗人身处静境却难以入静,恬淡中又总感寂寞。
这不能不说是其“机心”太浓所致。
再如《首春逢耕者》,诗中写出了南国早春的景色:
”二句描绘出一幅多么宁静,恬淡的画面,可是诗人却一笔荡开,由眼前景物想到久别的故园,那里是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地方,可是已经荒芜了,并且长满榛荆。
其实荒芜的不仅仅是故池田园,也是诗人建功立业的“经世”之心啊。
而这正是诗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所在。
“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
”二句写出了他对这种佛与儒之间的矛盾的清醒认识。
全诗在一片空旷,寂静中透出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沈德潜说:
“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说诗晬语》)。
其实,哪里仅是愚溪诸咏,柳宗元的山水诗大都是在闲静中深蕴着忧愤,旷淡中凝聚着寂寞。
元好问《论诗绝句》早已认清这点: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形象地指出了柳诗以“风容”之美写寂寞之心的忧乐杂糅的风格。
结论
柳宗元一生好佛,佛禅为柳宗元的山水诗提供了宁静、淡远的意境,而“统合儒释”的思想又使他对社会表现出比对自然更多的关切,因而其山水诗又表现出难耐的寂寞。
他既寻觅幽静的所在以歇息灵魂,又总觉得“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他始终徘徊于自然与社会之间。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
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柳宗元可以说是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
入世与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
这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如身投汨罗的屈原,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灯古佛为伴。
他的山水诗留下了“统合儒释”的鲜明印迹,是其“统合儒释”思想鲜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