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评析围绕新《行政诉讼法》第Word格式.docx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评析围绕新《行政诉讼法》第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律适用评析围绕新《行政诉讼法》第Word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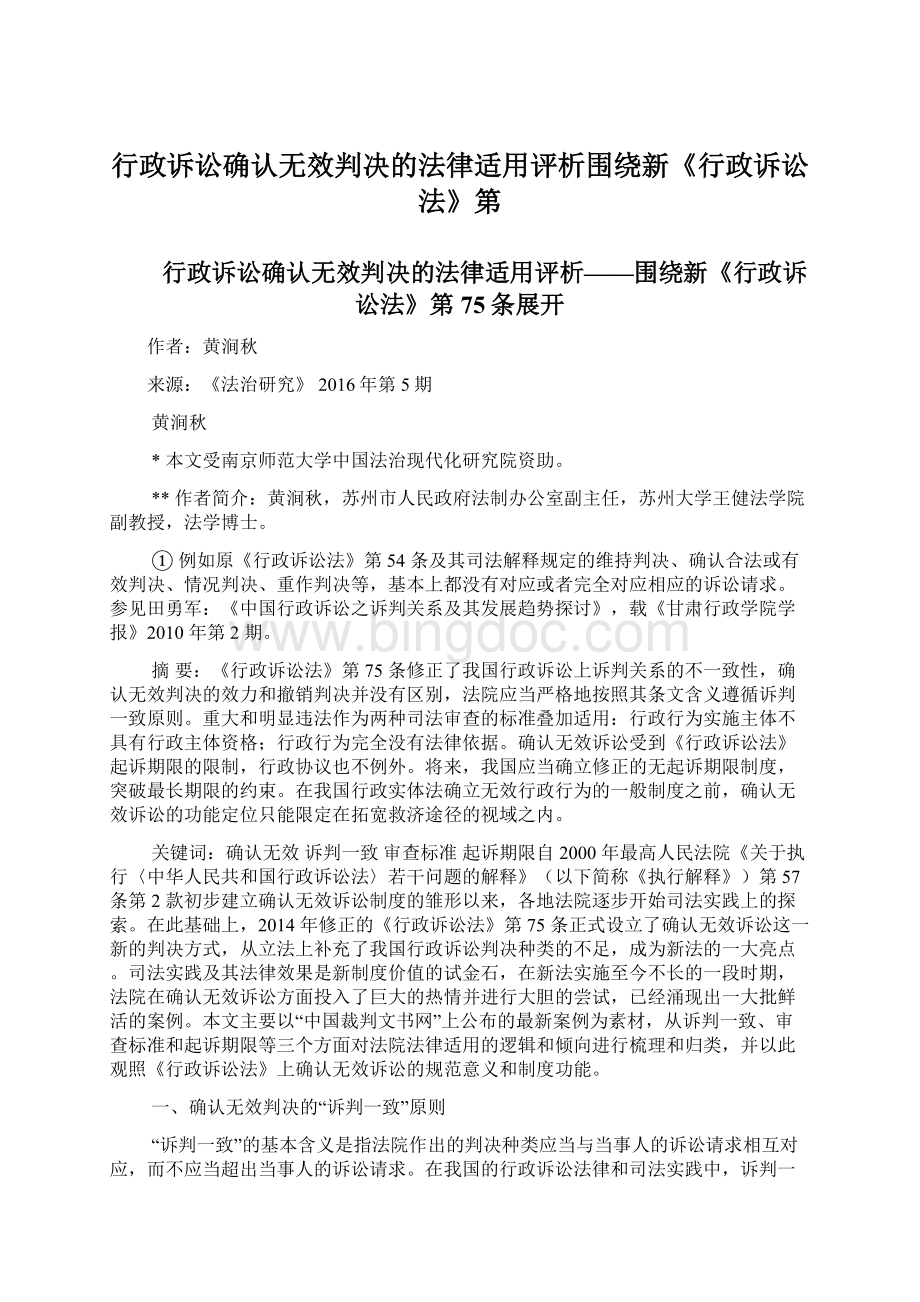
关键词:
确认无效诉判一致审查标准起诉期限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57条第2款初步建立确认无效诉讼制度的雏形以来,各地法院逐步开始司法实践上的探索。
在此基础上,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第75条正式设立了确认无效诉讼这一新的判决方式,从立法上补充了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种类的不足,成为新法的一大亮点。
司法实践及其法律效果是新制度价值的试金石,在新法实施至今不长的一段时期,法院在确认无效诉讼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进行大胆的尝试,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鲜活的案例。
本文主要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最新案例为素材,从诉判一致、审查标准和起诉期限等三个方面对法院法律适用的逻辑和倾向进行梳理和归类,并以此观照《行政诉讼法》上确认无效诉讼的规范意义和制度功能。
一、确认无效判决的“诉判一致”原则
“诉判一致”的基本含义是指法院作出的判决种类应当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互对应,而不应当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和司法实践中,诉判一致原则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
①但是,《行政诉讼法》第75条(以下简称第75条)首次对确认无效判决确立了严格的诉判一致原则:
法院判决确认无效的前提之一是“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
既然《行政诉讼法》仅在此条规定诉判一致原则,依反面解释进行推论,其他判决种类不一定要遵循诉判一致原则。
最典型的例子是确认违法判决,当事人如果提出撤销行政行为的诉请,那么法院有权根据情况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
第75条将判决类型与诉讼类型相互对应,架起沟通诉讼请求与判决方式的桥梁,在确认无效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已经开启了将判决类型模式转变为诉讼类型模式的路径。
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体系内,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受到最为严格的制度约束。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确认无效诉判一致原则的适用还有一种反向情形:
即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无效,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判决确认无效的情形,那么只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不是作出其他判决。
因此,原告在确定提起诉讼的类型时,就必须慎重地考虑和预测判决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诉判一致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上没有特别规定,从第70条关于撤销判决的规定考察,撤销判决的作出并不受到诉判一致原则的约束。
在新法实施以后,各地法院有关确认无效的判决并没有完全遵守诉判一致原则。
(一)原告请求确认违法,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在李欢与迁西县国土局注销宅基地使用证案中,②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注销其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
法院认为:
被告不具备注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主体资格,被告以本机关名义用通知形式注销原告土地使用证,因此该注销行为应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法院遂依据第75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注销行为无效。
综观该案案情,如果法院根据原告诉讼请求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由于此种判决并不涉及被诉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告被注销土地使用证的现状没有发生变化,确实不利于其权利保护。
这可能正是法院变更判决方式的原因。
但是,该判决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第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法院在判决主文径行变更为确认无效,明显有违第75条关于诉判一致的规定,而且对于这一变更,法院没有说明理由。
第二,无效行政行为是需要由行政程序法予以确立的重要制度,我国并没有在立法上建立起统一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③第75条只是确立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方式,我们并不能以此反推其创设了行政程序法上的无效行政行为这一类别。
法院将被诉行政行为定性为“无效行政行为”,但没有指明这一定性在行政实体法或者程序法上的依据。
第三,法院如果为了充分保护原告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应当作出撤销被诉注销行为的判决,原告土地使用证的效力因此恢复,即为已足。
(二)原告请求撤销,法院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在刘晓龙与武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罚决定案中,④原告请求撤销处罚决定书。
该处罚决定书由被告的巡警大队作出,法院认为:
巡警大队以自己名义对外公开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执法主体资格欠缺,该行为无效。
据此作出确认该处罚决定书无效的判决。
该案的判决思路主要是基于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第75条“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但是法院没有对为什么不按照原告诉讼请求而作出撤销判决进行说理。
⑤
法院径行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况在婚姻登记行政案件中尤为突出。
这一类案件的事实较为特殊:
一方面,行政机关在婚姻登记中已经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另一方面,当事人在申请婚姻登记过程中隐瞒相关事实。
易言之,行政机关没有过错和违法性,而过错和违法性往往就在于现在诉请撤销的原告,那么,这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登记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法院感到非常为难,其说理过程也显得捉襟见肘。
例如在周连满与承德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⑥法院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作出的婚姻登记发证行为,“该行政行为形式上虽属合法,但因其有重大、明显的瑕疵”,显然不符合《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有关结婚登记的条件,该行政行为应当被确认无效。
在袁辉、曹俊华与泰州市海陵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⑦法院采用了相同的审理逻辑,强调被告“在行政程序中已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但由于两原告采用了欺骗的手段,提供了虚假的材料,导致被告为两原告作出了第二次结婚登记(即被诉登记行为)。
有意思的是,虽然该案最终确认被告作出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但同时确认“两原告采用欺骗手段造成登记行为的无效,应当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文以为,该两个婚姻登记案件适用确认无效判决与第75条存在抵触:
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条件是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被诉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是确认无效判决的基础。
该两个判决均从客观角度强调涉案婚姻登记行为没有效力,虽然都引用第75条作为判决的基本依据,但都没有将案件事实与第75条的适用条件进行对应,难以自圆其说。
(三)原告请求确认无效,法院作出撤销的判决
在杜贤峰与萧县人民政府行政登记案中,⑧原告请求确认萧县政府为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无效。
一方面,被告具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确认无效的理由不符合第75条的情形;
另一方面,被告的颁证行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遂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
类似地,在六间楼八组与商水县人民政府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案中,⑨法院认为:
被诉颁证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
原告在诉请中要求确认被诉颁证行为无效,经审查被诉颁证行为不符合第75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不予支持。
这两个判决的共同思路是:
被诉行政行为符合撤销判决的情形,但不符合确认无效判决的情形,因此法院直接改判为撤销。
法院有意在撤销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之间进行明确的界分,并且隐含着确认无效判决涵摄的违法性程度高于撤销判决,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确认无效判决的立法目的。
如前所述,这种改判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第70条关于撤销判决适用情形的规定,具有合法性的基础。
(四)小结
第75条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国行政诉讼上诉判关系的不一致性,对于确认无效判决来说,其不仅涉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还进一步触及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在适用时应当保持应有的克制和谦抑。
⑩但是在新法实施以后,各地法院对于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采取了较为积极甚至激进的态度。
在当事人没有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的时候,法院为了彻底地解决纠纷,罔顾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动适用第75条而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这类案件中法院进行改判的思路不尽一致,但都明显违反第75条关于“诉判一致”的规定。
本文以为,新法生效不久,对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法院更应当严格地按照其条文含义予以把握,否则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
如果法院认为由于当事人的知识局限未能适时地根据案情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请,从而不利于其权利救济,法院也应当做好法律释明,引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法院将撤销之诉直接改判为确认无效,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法院认为有的被诉行政行为不能适用撤销判决,因此只能适用确认无效判决。
例如在姬晓明与金鸡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行政撤销一案中,?
法院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及行政原理,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对该无效行为无撤销必要,依法应作确认无效处理。
故对原告的请求,本院直接予以纠正。
”据此,无效行为既然自始无效,自然就不存在被撤销的问题,没有适用撤销判决的余地。
对此,本文以为:
该法院过分强调撤销判决与确认无效判决在适用效果上的区别,这仅仅是学理上的一种论断,而缺乏实定法上的支撑。
虽然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即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而可撤销行为嗣后无效,并以此界分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的效力,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两种判决都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全面否定,都力求恢复到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状态,行政行为的无效与可撤销之区分没有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
事实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判决的效力,如果某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撤销,其效力自然要追溯至其作出之时,否则就不会产生附带的国家赔偿问题。
即使是在确立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制度的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其第118条明确规定:
“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我国有学者提出严厉批评:
有限公定力理论将立法上都难以客观确定的判断权交给当事人,同时也将错误判断的责任风险给予了当事人,反而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相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来说,我国目前缺乏当事人抵抗权制度,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权还是掌握在法院手中。
“尽管命令无效,但除非要求法院作出判决,否则没有办法证实其无效性。
”?
行政行为在被法院确认无效之前,其持续具有公定力,当然可以成为法院撤销判决的对象。
质言之,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体系内,确认无效和撤销判决的效力难分伯仲。
当事人即使在撤销之诉中主张了属于构成被诉行政行为无效原因的违法情形,法院只要将其作为撤销诉讼进行审理也就足够了,?
并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确认无效之诉。
行政诉讼的诉判一致建立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致的基础上,如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一致,就会导致诉判关系的不一致。
行政行为不合法不一定导致其丧失有效性,例如在情况判决的情形。
上述两个婚姻登记案件中法院进行直接改判,则体现了另一种不一致,即行政行为合法,但又无效。
法院在说理部分一方面强调行政行为合法,另一方面又将行政行为归结为无效,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出现了乖离,但是这不能成为法院适用第75条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法定事由。
第75条的核心适用条件是“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其判断标准按照通说,是该违法情形已重大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
而这两个案件中,正是由于当事人在申请婚姻登记隐瞒了事实,而行政机关又难以发现客观事实,导致了错误的登记,此种情形,行政机关的明显违法从何而来?
反之,结合该两个案件的事实,法院完全可以适用撤销判决中“主要证据不足”的法定事由,遵循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撤销登记行为的判决,而不是越殂代疱。
二、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
行政行为无效不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后果,而是它的一种极端情形。
从逻辑上看,确认无效判决与无效行政行为相互对应,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实体法上的概念,而确认无效判决属于行政救济法的范畴。
我国仅在《行政处罚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零星地提到“无效”的行政行为,但是并未在行政实体法中构建出普适性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上,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事实上取代了无效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第75条将审查标准确定为“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按照文义解释,“重大且明显违法”属于审查标准的内涵,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两者系对其外延的例示性列举。
易言之,如果行政行为构成该两种情形,原则上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无效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其法律特征同时也是区分其与可撤销行政行为的分水岭。
日本在“二战”后就无效行政行为的特征提出“重大明白说”和“明白性补偿说”两种判断标准,前者成为通说。
“重大明白说”不仅要求瑕疵的重大性,而且要求存在瑕疵外观上的形式明白。
而“明白性补偿说”则认为明白性相对于瑕疵的重大性,仅仅是具有补充性的加重要件之一。
21明显性要件的基础在于信赖保护原则,即:
既然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在外观上已经一目了然,法院判决确认其无效也不至于损害相对人和公众对它的信赖。
22类似地,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采纳“明显且重大瑕疵”标准,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规定:
行政处分具有“重大明显之瑕疵者”为无效,并就具体情形作出列举。
总体来看,重大且明显违法已经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审查标准。
可以说,我国第75条正是沿袭了上述立法例。
据此,对于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而言,“重大”和“明显”违法两者叠加适用。
其中,前者侧重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构成要件,例如主体、程序、职权等方面;
后者侧重于行政行为的外在判断主体,即任何人在具有一般知识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其违法性,以此质疑其公定力。
第75条有意从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确立确认无效判决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以期与撤销、确认违法等判决各司其职。
(一)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我国法律上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行政诉讼法》第2条虽然新增规章授权组织,但只是用于解决行政诉讼被告问题,而不是承认其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行政主体问题被判决确认无效的,包括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1.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本身不是行政主体。
在新法实施前的封氏农业生态科技公司与苏州市相城区农业局注销《动物防疫合格证》案中,23法院以被诉行政行为实施主体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系未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机构为由作出确认无效判决。
在前述刘晓龙案中,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由武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警大队作出,而武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三定方案”中并没有巡警大队这一机构,被告也未能提供巡警大队的行政主体执法资格证,因此法院认定巡警大队“以自己名义对外公开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执法主体资格欠缺”,确认其作出处罚决定无效。
从各地实践看,巡警大队普遍可以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而行使行政处罚权,但该案中的巡警大队和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相同,连机构编制上都不存在其合法“名分”,更遑论其行政主体资格。
2.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职权。
在查得保与南漳县城乡建设局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案中,24法院认定“南漳县城乡建设局没有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不具有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判决确认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在张明希等与田氏镇人民政府确认集体土地使用证无效一案中,25法院认定被告不具有颁发土地证书的相应职权,其“依法不具有相应的行政主体资格,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属重大且明显违法”。
该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是行政机关,但是作出的行政行为都超出其法定职权,因此被确认无效。
(二)没有依据
第75条中“没有依据”究竟是指没有事实依据还是没有法律依据,表意不明确。
各地法院在适用这种情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对“没有依据”的理解出现五花八门、含糊不清的情况。
在康某某与皋兰县西岔镇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中,26法院认定:
“综上,被告西岔镇政府在征收房屋权属不清的情形下,即与第三人赵某某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
”在河南隆源食品有限公司与确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确认案中,27法院认定:
“被告确山县工商局依据虚假材料核准公司变更登记是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系该变更登记行为没有依据,属重大明显违法。
”在这两个判决中,法院将“没有依据”理解为没有事实依据(根据)。
在李桂林与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案中,28法院认定:
“被告在没有确认原告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是否存续的情况下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
在李家祥与新津县花桥镇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协议案中,29法院认定:
“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没有提供能与原告签订协议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故视被告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没有相应依据。
法院最终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确定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依据,属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
由于行政诉讼举证规则的作用,这种情形属于被诉行政行为全然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比较容易认定。
(三)小结
“重大且明显违法”审查标准说明:
《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违法行为的框架内确定无效行政行为判断标准,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不能超出这一红线的范围。
在这一点上,第75条与《执行解释》第57条存在显著区别:
后者将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确定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实际上没有确立判断标准。
这一多少带有“同语反复”之嫌的标准隐含着转致的功能,即诉讼法上的确认无效以行政实体法(特别法)的规定为依托,《行政处罚法》第3条“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即为其典型适例。
在第75条在行政诉讼制度上确立了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以后,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不应当转致适用行政实体法(特别法)上的标准,而应当以“重大且明显违法”为最终判断依据。
各地法院在第75条“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审查标准的适用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口径,反映了法院在区分确认无效判决和撤销判决适用上的困惑。
从《行政诉讼法》各判决方式适用条件的体系解释来看,第75条指的是完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情形,而区别于实施主体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无相应职权的情形。
31对于实施主体系行政主体,但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其法定职权的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4项“超越职权”的规定,法院应当判决撤销。
如果此种情形也属于确认无效的审查范围的话,那么,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范围将与撤销判决无法界分,前者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独立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将“缺乏事务管理权限”列为行政行为无效的事由之一,对此,台湾学者吴庚认为:
该项事由的适用应当限缩于重大明显的情事,例如违背权力分立等宪法层次上的权限划分,或者教育部门核发建筑执照等明显超越权限的事例。
32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其基本顺序是首先确定行政行为实施主体有没有行政主体资格。
按照常理推断,如果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连最基本的行政主体资格都不具备,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足以构成重大而明显违法情形,因此应当被确认无效。
上述刘晓龙和封氏公司两案的情形类似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所列举的无效行政行为情形之
(一):
“不能由书面处分得知处分机关者”,在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92年判字第1259号判决中,工务局作出的行政处分通知仅仅盖有其内部单位建筑管理处的印信,被认定为“已欠缺形式合法要件,为违法之行政处分应属无效”。
33我国的行政机构和其他公共事务组织体系较为复杂,有的纯属于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例如政府部门的科室,相对人比较容易判断其法律地位;
而有的事业单位是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对人从其名称上较难确定。
34在封氏公司案中,原告起诉其《动物防疫合格证》被相城区兽医卫生监督所注销,而先前的《合格证》上就是加盖了该所的印章,但被告相城区农业局在答辩中根本就不认可该机构的存在,这种主体资格问题对于原告来说几乎成了“无头公案”。
因此,就行政主体资格而言,如果一概以“任何有理智的人均能够判断的程度”来判断是否构成明显违法,对于相对人来说确有勉为其难之虞。
即使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较为成熟的德国,瑕疵明显与否,以一般理性、谨慎市民的合理观察视角来观察,仍有主观、抽象和不确定之嫌。
35由此看来,第75条中“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审查标准应当属于对“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一种推定,而仅仅是实施主体超越职权,在一般情况下难以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关于第75条中“没有依据”的适用,有的法院理解为没有事实依据,有的认定为没有法律依据。
本文以为,参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61条“没有法定依据”的表述,并结合确认无效判决的独立性,“没有依据”应当理解为行政行为没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依据。
“依据”一词通常对应于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关于事实问题,我们通常表述为“根据”。
36没有事实根据是指没有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此种情形,应当归结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撤销判决中“主要证据不足”的事由。
另外,上述李桂林案中法院所称“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审查标准,在文字表述上明显属于第70条撤销判决的法定情形。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适用了不应当适用的法律,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与“没有法律依据”不能等量齐观。
被告如果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对法律理解的偏差;
而如果没有法律依据,那说明被告根本就无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其违法的重大和明显程度高于前者,因此应当受到判决确认无效的否定性评价。
因此,第75条“没有依据”应当指全然没有依据,法院在审查中主要根据两种情形确定:
一是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上没有引用任何法律依据;
二是被告在应诉答辩过程中没有提供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
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中确定了原告在确认无效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原告的举证责任限于证明确认无效之诉不同于撤销之诉的例外情形(即重大且明显的程度),而行政行为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仍然在被告,包括被告已尽了调查义务。
37这样,在庭审过程中,原告需要出示没有载明任何法律依据的行政行为文书,而被告应当举证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并对为什么事先没有载明法律依据进行说明,以避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如果被告像上述案例一样没有作出任何举证,法院即可认定其“没有依据”。
三、确认无效之诉的起诉期限
起诉期限也是确认无效诉讼的一个特殊问题。
自从《执行解释》第57条初步构建确认无效诉讼制度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确认无效诉讼是否适用起诉期限的限制一直争论不休。
比较而言,认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
“不受限制论”以无效行政行为的自始、当然无效性为依托,进而推断无效行政行为从作出时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得随时宣告其无效,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随时请求行政机关和法院确认其无效。
38在立法上,《行政诉讼法》虽然正式确立了确认无效之诉,但并没有在起诉期限上为其作出特殊的制度性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主编的新法释义书籍中秉持“针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起诉,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而且也不受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