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docx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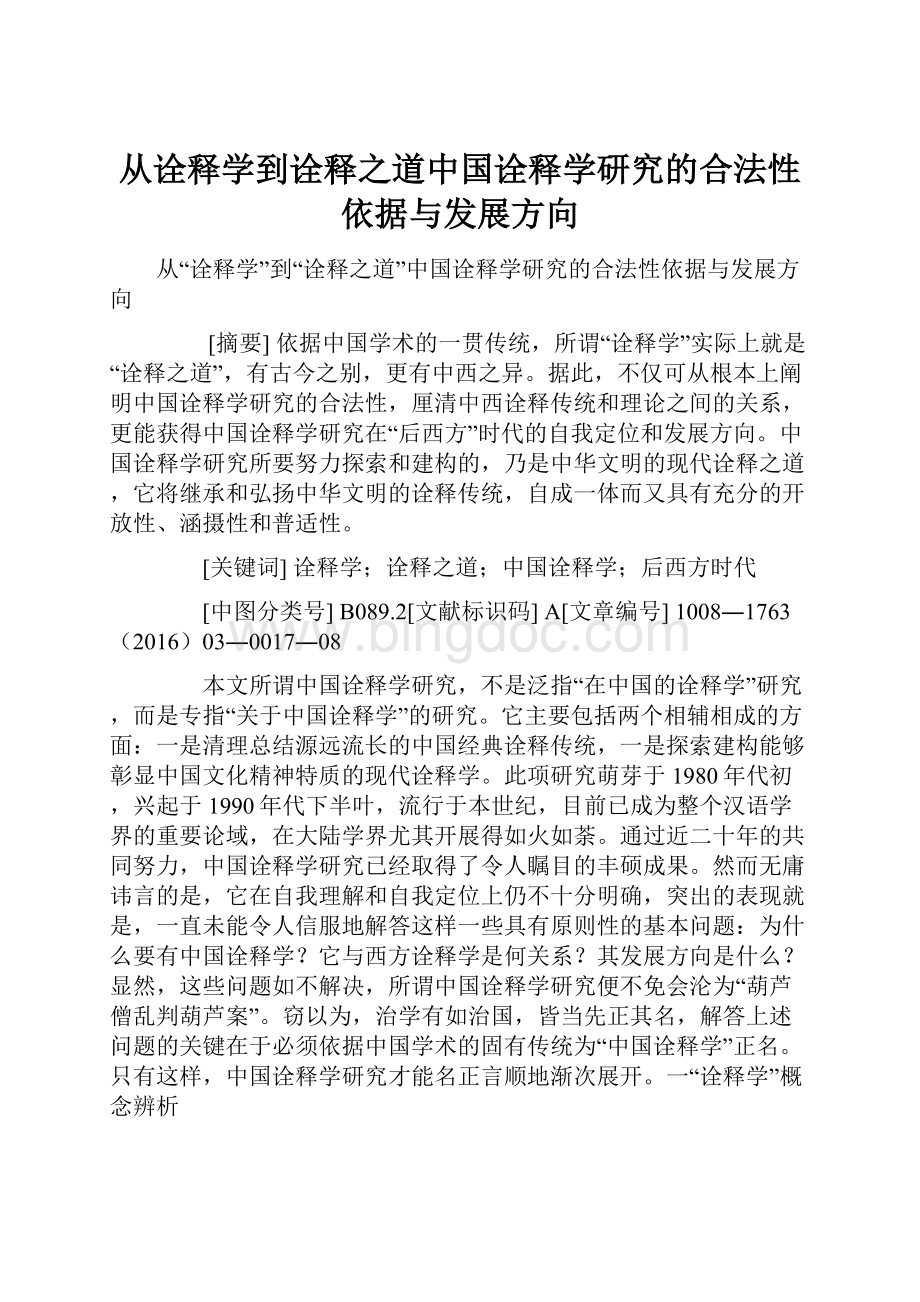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摘要]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
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
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关键词]诠释学;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后西方时代
[中图分类号]B0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6)03―0017―08
本文所谓中国诠释学研究,不是泛指“在中国的诠释学”研究,而是专指“关于中国诠释学”的研究。
它主要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一是清理总结源远流长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是探索建构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现代诠释学。
此项研究萌芽于1980年代初,兴起于1990年代下半叶,流行于本世纪,目前已成为整个汉语学界的重要论域,在大陆学界尤其开展得如火如荼。
通过近二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诠释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它在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上仍不十分明确,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直未能令人信服地解答这样一些具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为什么要有中国诠释学?
它与西方诠释学是何关系?
其发展方向是什么?
显然,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所谓中国诠释学研究便不免会沦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窃以为,治学有如治国,皆当先正其名,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依据中国学术的固有传统为“中国诠释学”正名。
只有这样,中国诠释学研究才能名正言顺地渐次展开。
一“诠释学”概念辨析
今日所谓“诠释学”,是德语Hermeneutik或英语hermeneutics等词的汉译。
诚然,我国学者杭世骏(1695-1773)于18世纪即已提出“诠释之学”的说法,其《道古堂文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谓:
“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
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三也。
”[1](P280)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诠释之学”并未成为专门概念,更未发展为独立学科。
故当西方诠释学传入中国之初,我们一时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现成名词来对译,所以除了“诠释学”外,还有“阐释学”、“解释学”、“释义学”、“传释学”等不同译名。
由于“诠释学”是源自西方的外来概念,所谓“中国诠释学”便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说法。
事实上,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能否成立一直是个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赞成派的现有理由主要有三:
1)诠释现象与诠释问题(如语言与解释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性,故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诠释学也具有普遍性,并非西方所得而专;2)中国古代的诠释传统不仅源远流长、经验丰富,而且自具特点;3)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学术研究。
据此,便有理由提出“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以之指称古代中国的诠释传统,以及有待建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理论。
换言之,古代中国已有自成一体、自具特色的“诠释学”,现在则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
反对派的意见也可综合为三点:
1)根本不存在古代的“中国诠释学”,它不过是“一只想象中的怪兽”,因为所谓“诠释学”乃是一门有着系统理论与方法的现代学科,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正式形成,中国古代诠释传统不可与之同日而语;2)也根本不存在现代的“中国诠释学”,因为作为一种普遍的学科理论,诠释学就是诠释学,无所谓西方诠释学和中国诠释学,只有“诠释学在西方”、“诠释学在中国”,即只有“表现形态与表现方式的差别”而已。
3)完全没有必要建立现代的“中国诠释学”,因为要真正理解一个文本尤其是经典,恰恰不能像现代西方那样采取诠释学这种“现代学问的样式”,而应像西方当代“解经大家”列奥?
施特劳斯(LeoStrauss,1899-1973)那样,自觉地“反对任何诠释学理论”,回归到“古典学问的样式”。
[2]
反对派的上述观点,实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
对此作出有力响应,乃是赞成派无法回避的任务,但仅据上述理由显然并不足以完成此一任务。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李清良,夏亚平: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此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诠释学”。
由上可知,现有的赞成意见主要围绕“诠释学”中的“诠释”讲理由,反对意见则主要抓住“诠释学”的“学”字做文章。
其实,对于“诠释学”,必须同时从“诠释”与“学”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并且对每一方面的理解都不能仅执一端,不计其余。
“诠释学”是以“诠释”即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诠释活动是借助语言对意义进行理解、解释和传达的活动,不仅具有普遍性,更具有根源性与多样性。
所谓根源性是指,诠释活动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且如不可或缺的语言活动一样遍存于一切生存活动尤其是交往活动中,故伽达默尔称之为“无所不包和无所不在”(umfassendeunduniversale)。
[3](P554)诠释活动之所以具有普遍性,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根源性,因为它作为意义交流活动与语言世界同其范围。
诠释活动的多样性则指,它不像客观的科学认识活动那样可以也应该千篇一律,而是恰如艺术活动一般不可避免地随人、随时、随文化传统而各具风采。
对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加以反思和研究的学问即是“诠释学”。
据当代最著名的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此词(Hermeneutik)源于古希腊,以诸神信使赫尔默斯(Hermes)之名为词根。
[3](PP114-115,365-377)不过其本意并不指作为系统理论即“科学知识”(epistēmē)的“学”,而是指理解、解释和翻译的实践技艺(technē)。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实践技艺(technē)介于实践经验(empeiria)与“科学知识”之间,虽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理论性却并不是纯理论。
[4](PP234-245),[5](PP24-26,35,38-39)故如洪汉鼎先生所说,Hermeneutik的词尾是-ik而不是-ologie,-ik多指着重操作的实践技艺,-ologie才指普遍系统的理论知识,所以Hermeneutik一词本身就表明它原非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理论之“学”,将其译为“诠释学”并不恰当。
[6](PP438-439),[7](PP394-395)事实上,直到19世纪之前,西方诠释学一直只是诠释经验、方法和规则的汇集,既没有系统理论,也不是独立学科,因此常被称作古典诠释学。
只有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诠释学才逐渐演变为现代诠释学,并于19世纪初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而系统的“学”。
由此可见,诠释学实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并非只有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诠释学这一种形态。
换言之,所谓“诠释学”,只能宽泛地规定为对于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的自觉反思、探讨与总结,而不能狭隘地将成不成系统作为界定“诠释学”的唯一标准。
伽达默尔便反复讲到,他所理解的“诠释学”就是诠释活动或诠释实践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ndnis),是包含理论自觉的实践经验而不是脱离经验的纯粹抽象的理论系统。
[3](PP560-566),[8](P377) 既然对于人类而言诠释活动是如此根源与普遍,那么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自成一体的文明与文化就不可能不有这种自觉,不可能不各有其“诠释学”。
只有基于现代人的傲慢,才会否定古人早有自觉的“诠释学”;只有认同现代西方文明的傲慢,才会否定其他文明也有自觉的“诠释学”。
由于诠释活动具有多样性或分殊性,作为对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之自觉的“诠释学”又不可避免地有古今之别尤其是文明与文化之别。
诠释学作为一种意义交流与沟通理论,本质上是对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反思、解释与规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言说,因此必会由于文化传统和生存实践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
简言之,有多少种文明与文化传统,就有多少种诠释学。
[2]
因此,将中国古代诠释传统称作中国古典诠释学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只是就形态而言,若就思考水平而言,中国古典诠释学要超过西方古典诠释学。
[9]不少汉学家也明确指出,中国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中国诠释学”。
[10](P195,P254),[11](P18),[12]诚然,笼统地说有“中国诠释学”,确易让人误会为古代中国已有一种现代诠释学,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不过,倘若本就注意到诠释学有古今之别与中西之别,而不固执于西方现代诠释学这一种形态,这种误解并非不可避免。
古代中国已有古典诠释学,现代中国则应有现代诠释学。
反对派之所以认为诠释学就是诠释学,无所谓西方诠释学和中国诠释学,就是因其对于诠释学的理解,不仅无视“诠释”之特性,而且昧于“学”有多般,亦即既未注意到诠释活动的多样性与分殊性,也没有意识到诠释之“学”并不是脱离诠释实践的抽象理论,因而不能不随规定诠释实践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之别而各异。
若无这种偏见,“中国诠释学”和“西方诠释学”之别,实如中西艺术之别、中西文学之别一样毋庸置疑。
然而,上述辨析虽能说明我们为何可有“中国诠释学”,却终究不足以解释我们为何要有“中国诠释学”,毕竟对于中国学术而言“诠释学”是一外来概念。
反对派仍可以像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那样说,现代中国学人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习惯,西方有什么,就一定要说在中国也已有。
[13]二“诠释之道”的提出
要从根本上讲清我们为何需要“中国诠释学”以及中西诠释学的关系,就不能仅就西方的“诠释学”概念来讲,还必须从中国学术传统出发阐明其实质与地位。
我国学术传统中有一最基本的观念:
天地宇宙之间无往而不有道,人类的一切活动与行为只有合于道才会既有成效又有价值。
正如金岳霖先生所指出的:
“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14](PP16-17)道既可“合起来说”也可“分开来说”,若“合起来说”,天地间便只是一个整全之道;若“分开来说”,则可以细分为天道、地道和人道等等。
人道即人类生存之道,又可随角色、事务、时势等等之异,细分为“父道”、“子道”、“夫道”、“妻道”、“友道”、“师道”、“君道”、“臣道”、“政道”、“商道”、“兵道”乃至“茶道”、“棋道”等等分殊之道,甚至“盗亦有道”。
总之,事事物物之间莫不各有其道,虽一饮食、一起居之间亦莫不有其道,时异、地异、事异则道亦异;只有事事皆循道、由道,一个人的立身处世才会合理、有效、有价值。
故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论语?
雍也》)《中庸》也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
无论是“合起来说”的全体之道,还是“分开来说”的分殊之道,都不是摆在面前的现成之物,要知道、修道从而合道就必须不断原道即探索道、讲求道。
因此,在我国学术传统中,对于各种基本的生存活动不断进行反思、探索以建立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各种分殊之道,始终是一项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任务。
诠释活动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一项生存活动。
依据中国学术的重道传统,必须对之加以自觉反思、探索与研究,以建立起可合理解释与有效规范各种具体诠释活动的诠释之道。
若无诠释之道,一切诠释活动便如暗夜冥行,莫知所由,莫知所止,而无时不含诠释的各项生存活动也不可能做到无往而不合道,整个生存之道必定因此残缺不全。
更进一步说,若无诠释之道,一切原道活动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因为无论对各种生存之道的讲求,还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所有这些原道活动本身都是诠释活动,都需要诠释之道的引导和规范。
总之,正是诠释活动的根源性决定了诠释之道的重要性。
诠释之道不仅是诠释活动得以自觉进行的根据,也是整个生存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并且还是各种生存之道得以建立的基础。
正因如此,我国学术传统不仅向来重视诠释活动尤其是经典诠释活动,也特别注重讲求诠释之道,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比如早在先秦时代,便有古圣先贤分别基于其诠释经验和思想宗旨,从不同角度对诠释之道作了探索。
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各得其所”和“知言”“知人”,老子提出的“致虚极,守静笃”,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和“道通为一”等等,都成为了后世诠释活动之圭臬。
秦汉以后随着经典诠释传统的形成与兴盛,对诠释之道的讲求亦精益求精。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学术思潮的更迭,无不以诠释之道的拓展与通变为其转型之枢机。
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
“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
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
”[15](P23)此所谓“新眼光新方法”即指新的诠释之道。
一旦在时势推动之下发现或者说建立了新的诠释之道,各种具体的诠释活动便将呈现出新面貌,从而开启一个学术新时代。
近年学界对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相关研究尤可表明,我国古代学者不仅长于通过精湛的诠释活动来实现思想观念的继承、弘扬和创新,也高度重视诠释之道的自觉反思与不懈探索,并且构成了一种传统。
因此,我国源远流长、深厚丰富的诠释传统其实包含了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一是对各种典籍不断进行实际诠释的传统,一是对诠释之道不断加以探索的传统。
当然,由于学派取向之异(如有儒、道、释诸派之异)和典籍性质之别(如有经、史、子、集之别),这两个层面的传统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相互竞争也相互影响的多个面向。
对于整个诠释传统而言,不断反思和探索诠释之道的传统不仅是灵魂,也是动力,我国学术传统由此乃有其一以贯之而又不断通变的诠释之道,从而有各种学术思潮的适时嬗变和整个学术传统的生生不息。
依据《易传》所谓道“兼三才而两之”以及宋明儒者所谓道是“理一分殊”,诠释之道可以也应当既“分开来说”又“合起来说”。
“分开来说”的诠释之道不仅随诠释目的、诠释层面等等之别而各异(或偏重方法与规则,或注重智慧和修养,或强调理论与玄思等等),而且必随学派及时代之别而各异,也必随文化传统之不同而不同,因此必须“唯变所适”而不可混同执一。
但“合起来说”,则一切“分开来说”的诠释之道,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无论是专注技艺与规则的,还是关心智慧、修养或玄思的,都可以统称为“诠释之道”,不过所关注的层面或方面各有不同而已。
根据中国学术的上述传统与观念,我们可以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其一,今日所谓“诠释学”首先应作为“诠释之道”来理解。
诠释学研究的实质,是通过对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进行自觉反思、探讨与总结,以建立人们应当遵循的“诠释之道”。
西方诠释学即是西方文明的“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则是中华文明的“诠释之道”。
我们讲中国已有一种古典诠释学,无非是说它固有自成一体的诠释之道,或者说对诠释之道的不断反思与探索也是我国诠释传统的一个重要层面。
从西语“诠释学”即Hermeneutik或hermeneutics一词来看,将其译为“诠释之道”也更贴切。
学界公认中国所谓“道”与西方所谓logos大体对应,而在古希腊人看来,logos并非专指纯粹理论之“学”,也包括实践技艺(technē),毕竟只有经过logos的条贯和提炼,经验才能上升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技艺;因此实践技艺虽非最高的、纯粹的logos,但已属于logos,是可以授受、具有实践性质的logos。
[4](PP200-201,239),[5](P24)作为实践技艺的“诠释学”,显然也属于logos。
可见,即使依照古希腊传统,将“诠释学”理解为“诠释之道”,一种技艺层面的“诠释之道”,也是相当恰切的。
到20世纪,海德格尔将诠释学讲成比任何一门科学都更源初的基础存在论,伽达默尔晚年又将诠释学讲成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实践哲学,这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诠释学就更可以理解为“诠释之道”,一种包含形上之思的“诠释之道”。
其二,不存在唯一普遍的诠释之道,不同文明与文化传统的诠释之道各成一体而不尽相同。
诠释之道乃是生存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维度,是从意义交流层面对人们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加以解释与规定,因而与生存之道一样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
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的人们,有着不尽相同的生存之道和生存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尽相同的诠释之道和诠释方式,彼此之间不管有着多少相通之处,都是各成一体、相对独立,不可能相互替代或覆盖。
中西诠释学作为两种不同文明与文化传统的诠释之道各有系统,可以也应该对话沟通,却不容混同为一,更不容以彼代此。
其三,由于诠释之道必因古今时势之别而有时代性,中国文化传统虽固有其诠释之道,但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却必须适时通变(即人们常说的创造性转化),建立其现代诠释之道。
然而近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大侵逼和影响下,中国传统的诠释之道未能获得顺利转化,反倒逐渐被肢解与遗忘,现代中国学者用以解释和规范诠释活动的,主要是各种流行的西方现代性观念和科学主义理论与方法,不足以成为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可以说,迄今为止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仍未能真正建立。
近年来,我国学者深感现代中国学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失语症”和极其普遍的“反向格义”、“汉话胡说”现象,由于缺乏自成一体的诠释系统和标准,既不能独立自主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也不能提出创造性的诠释与主张。
为此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以中解中”的诠释学诉求,这实际上是主张,现代中国的诠释之道必须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始能真正建立。
[16]
由此观之,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中国诠释学”,实是因为现代中华文明必须建立其属己的现代诠释之道。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展开中国诠释学研究,并不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并不是本无其实,徒慕西方诠释学之名,而是出于对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与现代需求的自觉。
中华文明要建立自觉自明的诠释之道和完整无缺的生存之道,就必须要有中国诠释学研究。
中国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之间不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尽相同的普遍之道的关系;形象地说,它们不是父子关系,而是朋友关系,是两种不同文明的诠释之道。
中西诠释之道各成一体、各具系统,有着不尽相同的问题意识、理论立场和价值追求,彼此之间虽然可以也应当相互对话和学习,互资启发与借鉴,但主要是为了提升和拓展自身,而不是旨在解决对方的问题,更不是为了相互取消和替代,以便成为唯一普遍的诠释之道或作为其过渡环节。
事实上,正如《中庸》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任何一种文明的诠释之道乃至整个生存之道虽然都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绝不是那种唯一而绝对的普遍性。
应当指出,我们虽然主张应将中国诠释学理解为中华文明的诠释之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诠释之道”完全替代“诠释学”。
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先行发展和广泛影响,已使“诠释学”(Hermeneutik/hermeneutics)成为了现代学术中的通用概念和独立学科,我们尽可批评和超越它,却无法回避或无视它。
有些学者主张“反对任何诠释学理论”,只要基本的解经原则。
[17]但任何解经原则要被广泛接受就必须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因而仍可以称作“诠释学”。
换言之,我们在今日必须借助“诠释学”来讲“诠释之道”。
即使将来“诠释之道”一词为举世周知并接受,也不必尽弃西方“诠释学”一名而不用,而可像杭世骏那样用“诠释之学”意指“诠释之道”。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讲“中国诠释学”是要将其建成一独立学科,若将其理解为“中国诠释之道”,岂非又使其退回到传统知识形态?
其实,“道”包括“学”而不止于“学”。
惟其包括“学”,故在今日虽讲“诠释之道”,仍可建立相对独立的“诠释学”;惟其不止于“学”,故虽讲“诠释学”却不限于一般科学意义之“学”,而是自觉地以更为闳深的视野和更为切己的关怀向“道”上达。
以“道”来涵摄和转化“学”,这正是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和根本精神,我们在建构现代中国诠释学时理当对此加以自觉的继承和发扬。
总之,只有从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出发,将“中国诠释学”作为中华文明的“诠释之道”来理解和探索,才能从根本上阐明我们今天为何需要“中国诠释学”,也才能真正讲清中西诠释学之关系。
上述分析还表明,从西方诠释学的原初涵意及其当代发展趋势看,将“诠释学”理解为“诠释之道”也是可以成立的。
三诠释学的“后西方”转向
我们之所以主张中国诠释学研究应将“诠释学”作为“诠释之道”来理解和探索,还有更深一层考虑。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实际上是整个现代诠释学在“后西方”时代发生重大转向的重要标志,它只有自觉地将“诠释学”讲成“诠释之道”,才能在诠释学的“后西方”转向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作出其应有贡献。
现代诠释学已经有过几次重要转向。
第一次转向发生于19世纪初叶,是从特殊诠释学转向到普遍诠释学,由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1768-1834)完成。
此前在现代性观念尤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西方学者已试图将古典诠释学发展为现代诠释学,因而形成了神学诠释学、法律诠释学、语文学诠释学等各种特殊诠释学。
但只有到施莱尔马赫,由于建构了一个以追求精确理解为目的、适用于各种语言性文本的方法论体系,才成功建立起可以称作“科学”的“普遍诠释学”,“第一次使诠释学成为一种在大哲学体系结构中的独立学科”。
[18](P266)这次转向标志着西方现代性观念成为了普遍的意识形态,包括神学在内的所有传统观念的堡垒几乎都已被攻克。
第二次转向发生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诠释学从一般的诠释方法论转向为整个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由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完成,其目的是为了在自然科学模式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捍卫人文传统和人文研究的存在价值与合理性。
狄尔泰强调,精神科学不仅在对象上而且在方法上具有独立性,诠释学之所以应该成为整个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就是因为它能证明精神科学的“理解”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具有同等的客观性与严密性。
这次转向标志着西方现代性观念出现了分化,逐渐意识到科学理性的局限,而注意到人文理性或历史理性的独立价值。
第三次转向发生于20世纪,是诠释学从精神科学方法论转向为一种新型的存在论与实践哲学,主要由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和伽达默尔师徒完成。
海氏认为,现代社会摆脱日益明显而深重的现代性困境,就必须从根源上克服自柏拉图以来的“遗忘存在”的存在论,建立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存在论――“事实性诠释学”或者说是“此在诠释学”。
[19](PP94-122)在此基础之上,伽达默尔遂建立“哲学诠释学”,进一步阐发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并在晚年将其发展为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实践哲学。
总之,在他们看来,要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性困境与危机,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讲诠释学。
这次转向标志着现代性运动发展到今天必须加以全面反思和纠偏,走出其原有模式而进入新阶段。
有些学者认为第三次转向当分两次,也有些学者认为此后还有新转向,不管怎样,现代诠释学的已有转向都发生在西方。
这是因为现代诠释学从兴起到发展始终都是现代性运动的结果,是因现代性运动的逐渐深化而不断转向和发展;现代性运动虽是一场席卷各大文明的世界历史运动,但它不仅发轫于西方,也一直由西方来推动,因此数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实可称之为“西方”时代,即由西方文明主宰与控制整个世界的时代;在这种形势之下,现代诠释学的建立与转向自然只会由西方文明来承担。
然而,随着现代性运动的日益普遍与深化,当今世界历史已逐渐走出“西方”时代,而开始进入“后西方”时代。
对此中外学者已有不少分析和描述,但在定性上并不一致,或称作“文明冲突”时代,或称作“文明对话”时代,或称作“文化自觉”时代,近年又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后西方”时代。
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2月1日发表了杜平的《国际秩序进入“后西方时代”》,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春季号发表了西蒙?
瑟法蒂(SimonSe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