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翻译解析.docx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翻译解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翻译解析.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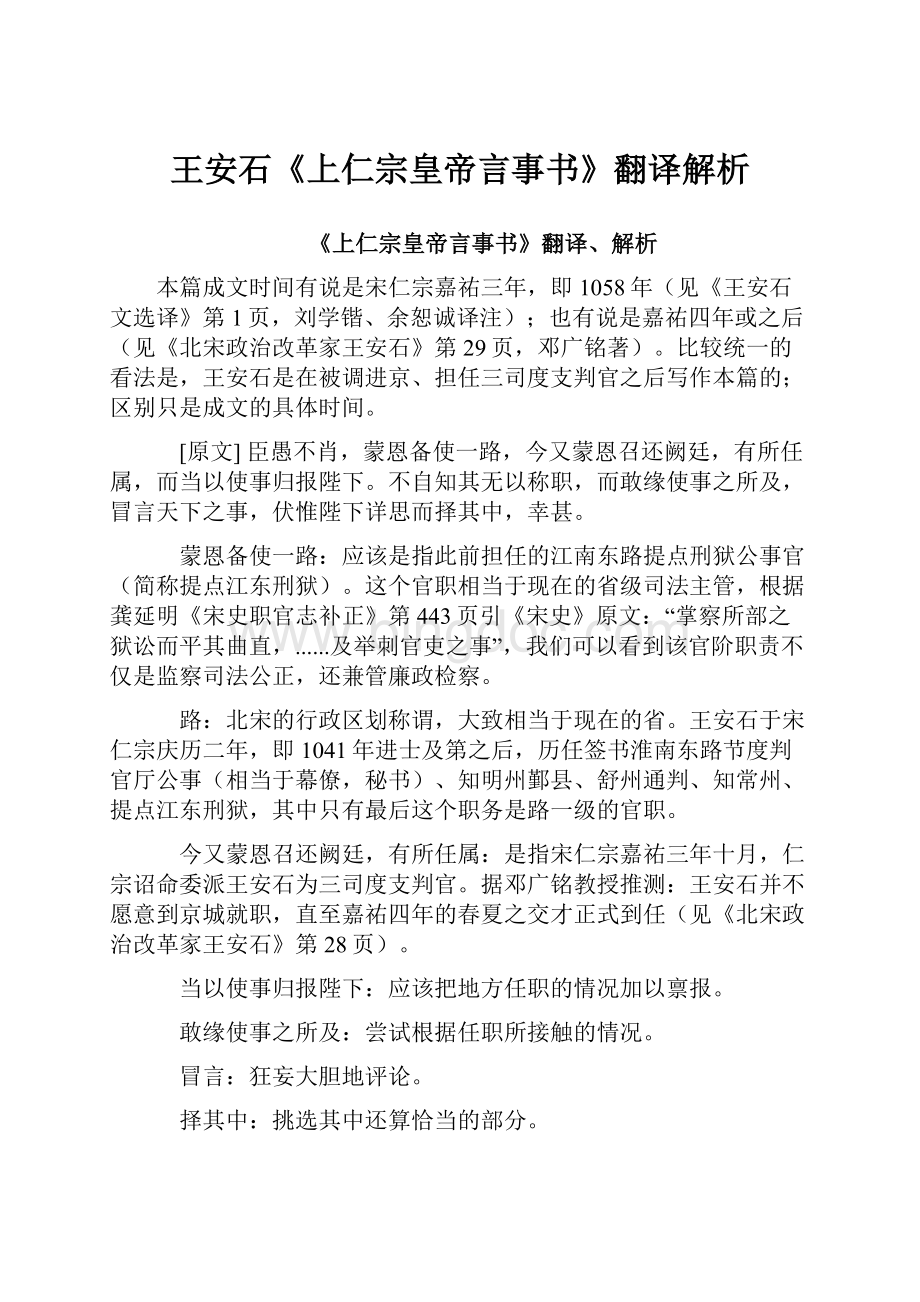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翻译解析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翻译、解析
本篇成文时间有说是宋仁宗嘉祐三年,即1058年(见《王安石文选译》第1页,刘学锴、余恕诚译注);也有说是嘉祐四年或之后(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29页,邓广铭著)。
比较统一的看法是,王安石是在被调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之后写作本篇的;区别只是成文的具体时间。
[原文]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
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蒙恩备使一路:
应该是指此前担任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官(简称提点江东刑狱)。
这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司法主管,根据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443页引《宋史》原文:
“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及举刺官吏之事”,我们可以看到该官阶职责不仅是监察司法公正,还兼管廉政检察。
路:
北宋的行政区划称谓,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
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即1041年进士及第之后,历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幕僚,秘书)、知明州鄞县、舒州通判、知常州、提点江东刑狱,其中只有最后这个职务是路一级的官职。
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
是指宋仁宗嘉祐三年十月,仁宗诏命委派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
据邓广铭教授推测:
王安石并不愿意到京城就职,直至嘉祐四年的春夏之交才正式到任(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28页)。
当以使事归报陛下:
应该把地方任职的情况加以禀报。
敢缘使事之所及:
尝试根据任职所接触的情况。
冒言:
狂妄大胆地评论。
择其中:
挑选其中还算恰当的部分。
[原文]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
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
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此其故何也?
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王安石先对当今皇上进行了非常必要的恭维,包括:
1、德才皆备; 2、努力不懈; 3、不好声色冶游;
4、节俭、爱民; 5、任贤、避佞。
我们把这种恭维称之为非常必要,是因为在专制的前提下,进言者确有保护自己生命的首要义务。
这让我想起了伊拉斯谟在《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对查理五世的恭维:
“英明冠盖众君主的查理”、“您的善好本性,您的诚实心智,您的天纵英才,还有您在那些极为高尚的教师手下所受的教养”。
这样的恭维为被恭维者接受恭维者的建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用一句“而效不至于此”来完成了论述的转折,务虚的恭维立即变成了现实的批评,而且非常尖锐。
包括:
1、从内部来看,国家的治理形势难以乐观;
2、从外交来看,军事前景堪忧。
当时,北方边境有辽的威胁;西北有西夏的挑战;西南有交趾的蚕食(见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
北宋朝廷一时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只能在外交、军事中采取守势;
3、经济状况困窘。
据说宋仁宗时期,每年财政收入的5/6用于军备和养兵(见杨硕《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前言),只有1/6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政府开支;
4、社会风气败坏;
5、有志之士对国家前景深感忧虑。
从王安石的这些文字,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北宋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如此尖锐的批评,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恶毒攻击”、“蓄意贬低”。
彭德怀上万言书的结局大家不应忘记,相比之下,王安石的处境竟然宽裕很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王朝的“积弱”、“积贫”呢?
王安石认为:
根本问题在于不重视法治、不重视制度建设--声明一下:
这个解释是暂时的,读下去才能知道是否恰当。
如果王安石说的“不知法度”确实是不重视法治、不重视制度建设的意思,那么王安石真的非常勇敢。
因为不重视法治、不重视制度建设是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通病,王安石之前是如此,王安石之后也是如此。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种通病,其实是由专制政治体制本身所决定的。
王安石指出了这个体制的弊病,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体制的基础。
当然,王安石本身并不知道自己的见解具有极大的“革命性”,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在千年之后得以实现。
[原文]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
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孟子曰:
“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
”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王安石继续写道:
现在朝廷法令严密、无所不备,而我王安石却说没有法度(不重视法治、制度),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再次转折,应该是想到了反对者最容易作出的指责。
王安石这一段文字的意图是,通过反击这种指责来树立自己行政变法的旗帜:
法先王之道。
他说:
我之所以说没有法度,是因为这些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注:
先王是指三皇五帝)的执政理念。
王安石所引孟子言论,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
原文应为: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榘,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虽然字句有出入,但在语义理解、佐证为据上,王安石并未失误。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意思是:
现在有些诸侯,有仁爱的愿望、或有仁义的名望,可是他们的百姓却没有实惠,他们的行为也无法成为后世的榜样,这是因为没有施行先王的执政原则。
用孟子的这个观点来分析后世的政治,那当然是“不行先王之道”,从而也就被王安石定义为“不知法度”。
那么,孟子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我认为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离娄眼力好、公输般技术高,但如果不用圆规、曲尺,他们也画不出方圆;师旷的听力好,但如果不用校音的六律,他也无法调校音准。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
你有愿望、有能力,还得需要使用工具、需要尊重客观规律,然后才能兑现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是接下去孟子的推理却发生了偏差,因为尧舜之道、行仁政和平治天下,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这些都是愿望,问题是工具在哪里?
仁政是工具吗?
当然不是工具,因为这个“仁”是无法度量、无法标准化,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实际操作。
所以,我们需要为仁政寻找工具,比如法制建设。
那么,孟子的话可以改为:
“尧、舜之道,不以法制,不能平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无法制故也。
故曰: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政不足以施仁。
”也就是说:
行政和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孟子的推理结论却正相反:
徒法不能以自行。
虽说是仅仅有法是不够的,但是这样的观念导致的实际效果却是:
我们历来不重视法的作用、法的建设。
其实,“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理由非常简单:
只说不做。
仁心、仁闻都只是诸侯装扮自己的工具,那老百姓还哪来的实惠呢?
那么孟子难道不知道如此简单的理由吗?
我认为孟子知道,但是他不能说。
孟子的做法就像大人哄孩子:
快吃饭,你看那边的妹妹快吃完了,你要超过她,超过她、你就是冠军!
儒家的如意算盘是抬高三皇五帝,然后哄哄那些诸侯:
看,这些古代的圣人至今为人赞颂,你们想不想成为那样的圣人?
想,就快推行仁政吧。
那么,王安石知道孟子的难言之隐吗?
我认为王安石也知道。
只是王安石和孟子相比,政治环境并没有什么根本变化--或者说更糟了:
孟子还可以周游列国,王安石却铁定只能效力于一个皇上--所以,王安石也只能采用孟子的老办法:
哄孩子。
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悲哀,而更为悲哀的是我们这些后人还不能理解孟、王的悲哀。
[原文]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
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
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
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
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
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王安石继续写,同时也继续转折,如下:
现在距离先王太遥远了,碰到的变化、发展都有很大差异,如果还想重新恢复先王的政治,再笨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而我所说的现在的缺陷在于没有取法先王的政治,是指应该取法先王的用意、原则。
谢谢王安石的坦率!
他好像急于为我上面的推测提供证据,很快就说明:
所谓法先王之政,只是法其意。
而我这里再次推测:
所谓法先王之意,其实是借先王之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什么是先王之意,谁都说不清楚,也无从核实、证明,那么“法先王之意”其实就是一个口号、一面旗帜而已。
王安石说:
从尧舜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历时一千多年,治、乱交替,盛、衰轮转。
国情非常复杂,执政措施也因时而异。
但是他们治理国家的原则,措施的主次、先后,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说要取法他们的原则、用意。
只要依据他们的原则、用意,则现在要进行的改革、变易,就不至于让国家动荡、让臣民恐慌,因为这些改革已经遵循了先王的原则、用意。
王安石又证明了我的推测是对的。
在“法先王之意”的旗帜保护下,改革将比较顺利、遭遇的反对和批评将减少到最小。
王安石对于自己想要推行的改革、及其将引发的社会反应、将遭遇的阻力和斗争,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估计。
所以,王安石这里的文字可谓一箭双雕:
一、树立“法先王之意”的旗帜,为自己的改革大业保驾护航;二、争取最高决策者的支持,这样一来“法先王之意”就变成了“遵今上之义”,改革大业将顺风顺水、畅通无阻。
[原文]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
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
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
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王安石为变法找到了一面大旗:
法先王之意。
但是,他认为即使如此,改革还是很难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当时人才不足。
王安石再次恭维了宋仁宗的盛德,借以说明改革不成功不是最高决策者的责任;而政治体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王安石则提也没提;那么改革不成功怪谁呢?
怪人才不够。
这里所谓的人才,是指德、才兼备之士。
一句话,就是君子不够多、圣人不够多。
王安石把改革难以成功归责于人才不足,我认为有二方面的原因:
一、要寻找一个现实的理由来为改革失败负责,否则没法向历史交代。
二、王安石的思维逻辑并没有超越儒家的仁义道德范畴,仍然认为君子是社会进步的保证、小人是阻碍改革的羁绊。
王安石的这个说法--“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对不对呢?
我认为有对,有不对。
对的地方是:
1、懂经济、会经营、能为国理财的专业人才异常稀缺;2、虽然不懂经济,但是有能力、有才气、支持改革的人才非常稀缺。
不对的地方是王安石不能理解:
1、和实际需求相比,人才的供应永远是稀缺的;2、不为国谋利、只为自己牟利的人,也是人才;3、完善司法,建立市场体系,靠市场来培养人才。
[原文]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
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
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
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
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
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
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
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
臣故曰:
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
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
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
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
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
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
故曰:
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王安石说:
我尝试着考察担任官职的人才,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过。
既然已担任官职的人才少,那么在野的人才应该不少吧。
可是我在民间考察过,在野的人才也是非常稀少。
或许是教育不得法,所以人才如此稀少吗?
我上面已经分析了王安石的论述隐含了对人才的定义,即:
1、德才兼备;2、懂经济或法规;3、支持变法。
具备这三条的才叫人才,不具备这三条的就不是人才。
否则的话,我也可以说:
现在人才的稀少,比王安石时代还严重--我们有王安石吗?
有司马光吗?
有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吗?
所以,王安石讲得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年代。
而这个星光灿烂,和北宋的政治开明是息息相关的。
王安石接着用自己的任职体验来作为例证:
以“路”为辖区的方圆数千里地域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明晰政策的轻重缓急,从而促进百姓安居乐业的官员非常少;相反,没有才能、马虎草率、贪婪失德的官员却很多,不可胜数。
能够坚持先王的执政理念,与当今实际相结合的官员,几乎绝迹了。
朝廷颁布的法令,其用意虽好,但官员们推行不力,百姓们得不到应得的利益;而基层官吏则利用这些法令动歪脑筋,敲剥百姓。
读了王安石的话,我们怎能不感慨系之呢?
我们现在距离宋仁宗年代差不多有一千年了,可是政治状况却变化不大。
我们也经常说: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地方执行却变味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
最高层是好的,最低层也是好的,问题就出在中层。
这些说法对不对呢?
王安石论述了一个事实:
大部分官员是不合格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当然就在那个任命、考察官员的制度了。
所以,要改变这个状况,就要先改变那个任命、考察官员的制度。
我们历来是皇帝考察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考察地方政府,老百姓则只有被管、受压的份儿;谁都没有想过老百姓可以考察地方政府吗?
我们的政治思路到韩非的法学其实就终止了。
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见《韩非子》扬榷第八),这个中央集权的基本理念千年未变,从来没有过“分权”的设想,更没有过向底层民众分权的打算。
殊不知在这个体制里,权力和责任是如此的不平等。
任命和考察官员的权力在上,而官员失职、失误的直接结果却由下面的民众承受。
可是,谁又会为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呼吁呢?
王安石继续说道:
就算中央政府称职,能够帮助陛下推行改革,但是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岂能做到百姓人人受益?
所以,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说法令的推行还需要人才多多,否则法令就是空的。
王安石的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想法。
他们认为:
法制虽然好,但是法律需要有德之士的推动,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去执行,否则法制只能失败。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认为这是大家不明白法律的渊源。
按照我国传统的观念,法律的渊源是成文法(宪法、其它法律)、行政法规(政策、文件)、地方法规、部门或行业法规、国际条约和惯例。
也就是说,一个行政部门出台的某一个文件也是具备强制意义的法律文本,那么立法的权力其实是零散的、执法的权力也是零散的,所以,如此之多的掌握立法和执法权力的人当然应该是德才兼备之士才好。
然而我们的悲哀在于:
事实是正相反。
那么怎么办呢?
是等待德才兼备的君子大批量出现吗?
还是推动立法、执法机制的改良?
从王安石的文章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了:
千年等一回,也等不到那个“君子”、“圣人”批量生产的时候啊!
所以,没有人才怎么办?
我们需要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人才(请注意:
不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人才!
)立法、执法机制不完善怎么办?
我们通过学习、遵守、讨论来推进它们的完善。
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有法是不会自己得到执行的,很对。
那么怎么解决呢?
应该从立法上就加以解决。
如果是由最高决策层来立法、或者是中央政府来立法,那么,这个法当然是“不能以自行”的,因为这种法令只是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图,而不能体现守法者的利益。
立法需要体现守法者全体的利益,这样的立法才能不令而行。
当然,立法和执法的力量需要隔离,这样才能保证立法和执法的公正。
王安石总结道:
现在最紧急的事情是人才不足。
如果人才足够多,那么任命官员就有挑选的余地。
等到官员们都能尽心尽职,改革的时机比较成熟了,再按民众反映的情况来改革存在弊端的旧法,逐步接近先王的执政理念,就比较容易了。
现在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是一样的。
先王时代的人才多,而现在又为何这么少呢?
所以我说:
这是教育不得法。
王安石的这个看法的确是超越了时代。
王安石认为按照当时的科举考试、诗赋取士办法,无法招揽懂经济、有经验的实干人才。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到了晚清末期才正式取消的,由此可见皇权专制和科举取士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
但王安石看到了诗赋取士的科举实际上阻碍了最高当局吸收真正的人才来为自己服务,这不能不说明王安石具备超越时代的冷静和勇敢。
虽然改革教育方法、改革科举制度,不能改变皇权专制的本质,但是,摒弃传统学说的教条、崇尚经世济民的实务,这本身就会改变知识分子对经济事务的态度,从而改变对信用、契约、规则、权利、利益的狭隘理解。
这将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同时这又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前进。
换言之:
社会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道德和学说,而是来自市场和契约。
[原文]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
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
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
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
《诗》曰:
“恺悌君子,遐不作人?
”此之谓也。
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
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
《诗》曰: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又曰:
“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
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
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
故诗人叹之曰:
“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
”盖悯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
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
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
故诗人美之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
”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
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这段文字,王安石通过几篇《诗经》来推证自己的观点:
人才,需要最高统治者来培养和造就。
王安石说:
商朝末年,天下大乱,人才凋零。
这时,周文王善于培养、造就人才,使治下的子民都有士、君子的才德,而后根据其才能特长来担任官职。
《诗经·大雅·旱麓》篇有诗句道:
“恺悌君子,遐不作人?
”意思是开明的君主,难道还不会造就人才吗?
(参见魏晓虹解评《王安石集》)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古人作文、辩论都喜爱引用《诗经》?
偶尔翻阅夏传才先生的《诗经研究史概要》,读到“《诗经》和孔子的关系”一章,夏先生提到了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认为没有学过《诗经》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是说不好话的。
怪不得孔子之后的著作会经常引用《诗经》,比如《大学》、《中庸》、《孟子》,都是如此。
胡适认为:
“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是,这个史料掺杂了很多讴歌文字。
“恺悌君子,遐不作人?
”我们今天可以参想一下:
人才,是君主培养的,还是君主发现和使用的?
如果君主善于陶冶人才,而不是善于发现人才,那么最好的君主岂非都是最好的教育家?
而这是不可能的。
有句老话说:
“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可见多用自己“陶冶”的人才是不会成功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校长”的败逃台湾。
王安石说:
周文王成功以后,地位卑微之人如猎户,都尊崇道德。
《诗经·国风·周南·兔罝》就是称赞这个情形的。
(参见魏晓虹解评《王安石集》)罝,据《辞海》注音jie,又念ju。
而在电脑拼音里,则只有ju音。
且不论《兔罝》诗是否这样理解,就算如诗中所写的“肃肃兔罝”,那又岂能归功于周文王的教化之功呢?
由此可见,一切功劳归于最上的恶习,从《诗经》就已经开始了。
王安石继续说:
猎户都能这样,何况于担任官职的人?
正因为文王有这样的成就,他才能攻的时候就取胜、守的时候就治安。
《诗经·大雅·棫朴》篇有诗句: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意思是周文王的文臣很多;还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意思是周文王的武将很多。
(参见魏晓虹解评《王安石集》)
到了周夷王、周厉王的时候,天下又乱,人才也变少了。
周宣王中兴,能够和宣王一起谋划大事的,只有一个仲山甫。
《诗经·大雅·蒸民》篇说道:
“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说像羽毛一样轻飘的德行,只有仲山甫去担当,其他人爱莫能助。
王安石认为这是叹息人才太少了,仲山甫太无助了。
宣王归纳了仲山甫的特点,以此模式来对天下的士子进行培训和拓展,然后人才渐渐地多了起来。
这样就有能力内修政务、外讨叛逆,周朝再次拥有了文王和武王的治国规模。
《诗经·小雅·采芑》篇说: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意思是大家正在采摘芑菜,刚摘完开垦了二年的田地(称新田),又来到开垦了一年的田地(称菑亩)。
王安石认为这是称颂周宣王能培养和改进人才,就像农夫善于耕种和改进农田,使之可以持续产出一样。
从《采芑》本身来看,王安石的理解有点牵强。
《采芑》的主题是描写方叔出征,采芑的场景好比是观众的立场,从农田里抬起头来,远远地看到大军开来。
所以,一定要把开头的几句说成是对周宣王人才战略的颂扬,我认为比较牵强。
通过五篇诗经的推论,王安石得出了结论:
“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意即:
人之所以成才,完全可以由人主(帝王)的精心培养和造就来加以实施。
王安石的这个人才观、育才观,当然是错误的。
和儒家传统思维一致的是,王安石完全赞同人才要为国尽其用,其实也就是为帝王尽其用。
这样的人才观,是由帝王专制制度所决定的,从而也是我们今天要加以反对的。
人才,首先不是为国家发挥作用,而是为自己发挥作用。
[原文]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
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那么什么是对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呢?
王安石认为:
就是对人才的教育、福利、选拔和任命,都要讲求原则。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
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
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法在于学。
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
何谓饶之以财?
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
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
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
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
何谓约之以礼?
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
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
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