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docx
《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docx(2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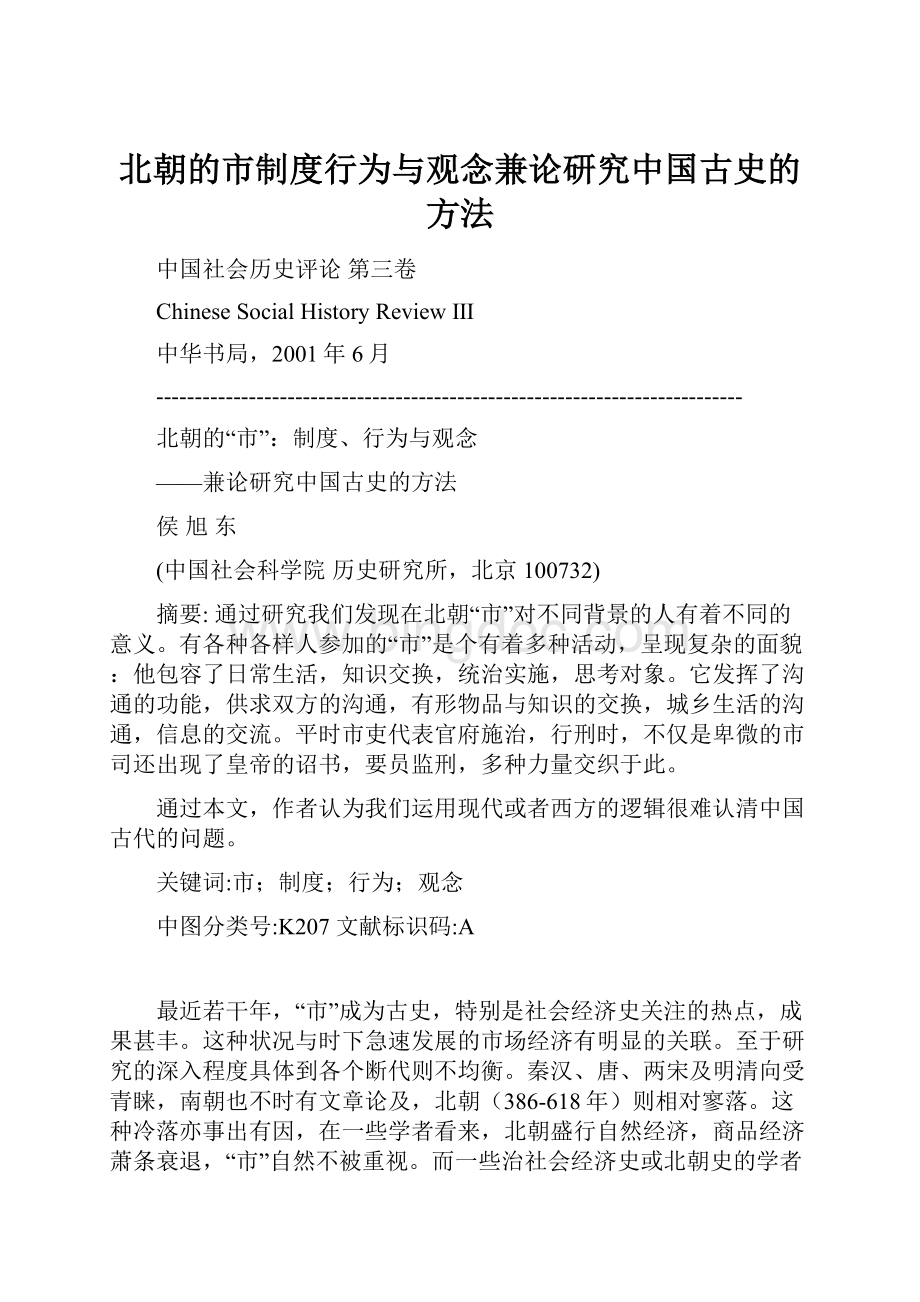
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
ChineseSocialHistoryReviewⅢ
中华书局,2001年6月
----------------------------------------------------------------------------
北朝的“市”:
制度、行为与观念
——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
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北朝“市”对不同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
有各种各样人参加的“市”是个有着多种活动,呈现复杂的面貌:
他包容了日常生活,知识交换,统治实施,思考对象。
它发挥了沟通的功能,供求双方的沟通,有形物品与知识的交换,城乡生活的沟通,信息的交流。
平时市吏代表官府施治,行刑时,不仅是卑微的市司还出现了皇帝的诏书,要员监刑,多种力量交织于此。
通过本文,作者认为我们运用现代或者西方的逻辑很难认清中国古代的问题。
关键词:
市;制度;行为;观念
中图分类号:
K207文献标识码:
A
最近若干年,“市”成为古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成果甚丰。
这种状况与时下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关联。
至于研究的深入程度具体到各个断代则不均衡。
秦汉、唐、两宋及明清向受青睐,南朝也不时有文章论及,北朝(386-618年)则相对寥落。
这种冷落亦事出有因,在一些学者看来,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市”自然不被重视。
而一些治社会经济史或北朝史的学者则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商业日见活跃,若干都市亦颇繁荣,尽管各人对商业发展水平估价尚不一致。
出现两种不同见解应与学者所持的立场、论题密切相关,这里不能深论。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Skinner)曾指出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
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界隔离。
许倬云对汉代农业的分析证实了施氏的见解。
上述关于北朝“市”的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也许是截取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所致。
许倬云的研究着力考察了汉代农民生计与市场的关系。
截至目前,北朝的相关研究远未深入到百姓生活中,揭示出其与“市”的关系。
即便关注“市”也只限于列举若干都市如洛阳、长安、邺城等,泛论商业发展,未旁及一般城镇的“市”;而且大多从经济史角度立论,极少注意“市”的非经济侧面。
殊不知,古代的市,特别是集中市制时期,在买卖物品之外尚承担其他职能。
这一点倒是若干日本学者有所分析,虽然他们也很少留心北朝的市。
此外,市制与市内的买卖活动向为学人讨论的重点,当时人们对市的思考却被划为思想史的领地,不幸的是思想史家对此极少措意,使得我们笔下的“市”成了徒具制度、行为的躯壳,割裂了与市有关的思想与行为、制度间的内在联系。
这些不足都有待解决。
研究“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本文意旨不在揭示北朝“市”较之其它朝代所显现的特点,也不在论证当时社会经济的性质,而是侧重考察北朝朝廷及城乡居民生活与“市”的关系、“市”在朝廷及百姓生活中的意义,因此采用“内部观察(emics)”为主的方法。
所谓“市”指附设在都城、州、郡、县城以及军镇——以下简称“城镇”——中的“市”。
边境上的互市、交市不在讨论之列,隋代统一全国后淮河以南的“市”亦不在讨论之列。
涉及的问题,大体说来,包括与市有关的制度、行为与观念三方面,如朝廷对“市”的制度安排、人们日常生活与市的关系,时人对市的理解及理解与活动的关系,市制的背景、“市”对百姓的意义,等。
希望以“市”为切入点展示当时的生活,丰富今人的认识,并基于此,反思一些研讨中国古史的方法。
迄今研究北朝市尚不充分,似仅日本学者佐藤佑治做过专门考察,仍留下不少基本问题需澄清。
本文不得不从“市”的分布、形制等一般情况着手讨论。
一、市的分布、形制与管理
南北朝间南方出现的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方未见。
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但尚不普遍,且几被列为铲除对象。
这一时期商业活动仍主要在城镇所设的“市”内进行。
市的情形,仅洛阳、邺城、长安等都城常被论及,其他城镇情况不明,这里就资料所及,做些补充。
先论分布。
《魏书·食货志》载,武定六年(548年)朝廷规定“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来核查规范百姓用称。
东魏所辖州镇郡县不少立市,自不待言。
时至北齐,情形依旧。
河清中所定《齐律》论死刑时说:
“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
”高齐境内少数城镇没有设市,但立市属常态,不然律文不会如此规定、如此表述。
普遍设市,官制上也有所反映。
北朝承汉晋旧制,设吏治市。
《魏书·李顺附李裔传》述北魏末年杜洛周起兵定州“特无纲纪,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可证北魏地方州镇郡县亦置市令。
北齐与隋开皇时官制见《隋书·百官志》,据该志,北齐的上上州、上上郡、上上县与镇的属吏有市令或市长;隋初规定上上州、郡及县置市令、市丞。
隋开皇六年(586年)龙藏寺碑题名有“州前市令、前恒山郡录事、维那刘雅”。
西魏北周之制,史书不载,据王仲荦先生考证,北周设司市下大夫、小司市上士。
州亦设市令,天和元年(566年)十一月廿日宋金保等17人造像记题名有“旷野将军、员外司马、斌州市令礼平国”,县亦设市司,隋开皇元年(581年)四月八日豆卢通造像记题名有“前石艾县市令、平州临虑关录事韩开”,立像时间距杨坚登基仅三个月,韩开任市令殆值北周,宇文氏一朝县亦尝置市令,应无疑意。
设市吏之城镇自然有市。
由以上两方面情况看,北朝时境内不少城镇设置市廛是可以肯定的。
各个城镇设市数量不一。
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
都城往往置数市:
北魏迁都洛阳后设三市,东魏北齐都城邺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二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
市之形制,当一如汉唐,为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
市在城镇布局中的位置,仅北魏洛阳、隋代长安、洛阳可考。
东魏北齐都城邺与隋代两都规划均仿自北魏洛阳,试以北魏洛阳为例作些分析。
据《洛阳伽蓝记》及多年的考古发掘,知北魏洛阳城为三重,核心为皇帝所居的宫城,其外为内郭城,其中分布众多官署、朝廷的祭祠场所与朝廷兴建的佛寺(如永宁寺),最外层为外廓城,内中以居民里坊为主,市廛亦座落其中。
洛阳城规划建设具体由李冲、董爵、穆亮负责,这种布局体现了他们的设计思想,也包含孝文帝本人的意见。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改变了“面朝背市“的传统都城格局,而是市廛的方位与权力中心的远近关系及其思想背景。
从整个城市布局看,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
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迁洛后虽不断有人呼吁修建,但工程进展缓慢,至北魏亡亦未竣工,故可不计。
整个洛阳权力、礼仪中心处于中心的内郭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
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
市肆隔绝于权力、礼仪中心之外,相对居于边缘,若较之其他国家城市的布局会看得更清楚。
公元前4——前1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的中心广场居显著位置,是商业、政治活动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为店铺和庙宇。
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是鱼肉市场。
市场在该城居中心地位。
公元476年以前一直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的中心是罗马广场(Forum),它亦是集政治、宗庙与贸易中心于一身。
公元79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罗马城市庞培(Pompeii)中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theForum)是全城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
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Macellum)、城市守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
建于9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平面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
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600年达至鼎盛,8世纪后半叶被毁,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是主要的神祠、宫殿群(the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GreatCompound)。
上述城市中市场多位于城中心,往往与政治、宗教中心毗邻或重合,与中国洛阳城布局显然有别。
后者“市”与权力、礼仪中心相距较远,且隔以城墙,居于边缘。
北朝其他城镇“市”的位置不明,参照洛阳布局,若是新建城镇,置市处当亦远离代表权力中心的官衙,应无疑意。
对于“市”内活动,北朝亦禀承前代,实施管理。
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
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传》,知隋初有是制。
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
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确定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
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却说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
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
《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包含有关规定。
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
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关市”篇,似可信从。
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
北魏末期以降,亦曾数度征税于市人及市内店肆,不过,正如李剑农、唐长孺先生所云,市税常在存废不定之中。
朝廷、官府治市,主要依靠市令、市长等市司。
各代司市倾注心力不少,但这并不意谓市在朝廷地位有多重要,前述“市”之方位是一表现,司市官吏在官员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亦揭示了这一点。
《魏书·官氏志》载前职令中“京邑市令”为从五品中,当时司州司事、从事,代郡功曹主簿仅为“第六品上”,此时京邑市令地位并不算低。
后职令不知何故未列诸市令,而河南偃师出土的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翟兴祖等人造像碑碑阴题名有“扫虏将军、京邑东市司马王安兴”,按后职令,扫虏将军“从八品上阶”,依常例,将军号高于执事官品级,东市司马品级更低。
京邑市令品级较前应降低不少。
其他城镇市司之品级当更低,或为流外。
《魏书·李裔传》讽刺杜洛周特无纲纪,称“至于市令、驿帅,咸以为王”,时人眼中,市长之属不过是些卑官末职。
京邑市令在北齐为从七品,北周司市下大夫为正四命,相当于正六品,隋开皇制为正八品。
地方州郡市令品级不载,好在北齐,隋州郡县属吏品秩高下与其在《隋书·百官志》中排列的先后顺序大体相同,可据市令的位序大体确定其品级。
据《隋书·百官志中》,北齐上上州市令列于州吏西曹书佐与祭酒从事史之间,诸州西曹书佐为视从八品,祭酒从事史视正九品,州市令品级当近乎二者。
镇郡县市令之品级则在流外。
隋代上上州市令居部郡从事、仓督之后,部郡从事已为视从九品,市令应属流外。
炀帝废州后郡市令不会高于此,县市令品级则更卑微。
时制“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市令跻身君子者少,属小人官者多。
具体到各级官府内部,除京邑市令或直属司农、太仆,在司州诸职中地位稍高外,在州镇郡县属吏排序中,市令、市长均靠后,甚至为末席。
北齐上上州中位置稍前;上上郡中仅列仓督前,为次末席,尚在太学生之下;上上县中则殿后;镇中亦居次末位。
隋开皇制中州郡县之市令均为末位。
北朝时郡守县令长期为士流所耻居,属吏地位更可想而知。
官员品秩高下体现了朝廷的重视程度。
《魏书·甄琛传》载,宣武帝时琛任河南尹,欲整顿洛阳治安,上表称太武帝时平城盗窃为患,帝“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设吏士,“崇而重之,始得禁止。
”认为洛阳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致生奸弊,要求或任八品以上将军领里尉,或提高里尉品级,以求救弊,正反映了这种思维逻辑。
朝廷基本采纳了甄琛的建议,说明这一逻辑亦为朝廷所接受。
据此,北朝间不少州镇郡县立市设官施治,但市司品秩大多较低,不少甚至不入九品,连比视官也未曾列入,属于卑微末职;在同级官府僚属中也无足轻重,可以说处于官员等级体系的末端,表明当时官府对市并不重视。
考虑到“市”在城镇中的边缘位置,可以说北朝城内立市虽不少,但它在朝廷与官府心目中仍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
上述现象体现了官方的设计与观念,这是否意味着市在时人生活中同样无足轻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二、市:
买卖所之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市”的重要职能。
北朝时亦是如此。
关于北朝人日常生活,文献记载迥异。
《颜氏家训·治家》云: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
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
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
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颜之推描划了一幅近乎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生活画面,认为北方近之。
断定北朝自然经济发达,这是一条重要依据。
而同为北朝人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则勾勒出另一番景象。
他在许多作物种植法中提到选择何种时节,出售作物,还开列了单价与收入。
仅举一例。
该书卷3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
一升葵,还得一升米。
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
”“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
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
”类似内容书中尚有不少。
要知道贾氏本人反对舍本逐末,书中对“商贾之事,阙而不录”。
大量的类似记载值得玩味。
两人笔下的生活相去悬远,哪个更贴近实际?
只有深入到城乡居民生活中加以辨析,才能找到答案。
北朝城镇居民包括官吏(都城还包括皇室)、士兵、工匠商贾及少量农民、术士。
首先,试析官吏家庭生活,比较其收入与生活所需,了解他们与“市”的关系。
据学者对北朝官俸研究,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颁禄前,官员收入主要靠赏赐、掠夺民户,亦与商人勾结,“要射时利”。
颁禄后,俸禄标准是每季若干匹帛,粟米并非俸禄内容,另外,京官还有酒、肉及廪食供应,宰民的地方长官、上佐则另有公田。
太和末年曾规定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看来也确实实行过。
北齐亦是以帛计俸,按季发放,标准依品级高下、职务繁简而定。
支付时一般1/3给帛、1/3给粟、1/3给钱;州郡县官还有以绢充“干物”的收入,僚佐多以帛为秩。
北周则将俸禄颁发与收成好坏相联。
北魏有封土者可获封户交纳的部分租税,亦是粟、帛之属;北齐北周食租税者甚少或纯为虚封。
隋代百官给禄并以石(斛)计,似以实物为主。
食封、散官、地方僚佐、胥吏不给禄。
官员另有职田、公廨田、公廨钱。
均田制下官员给田的规定只是限额,并非实有。
显然,官俸所得并不能满足官员日常生活全部需要,甚至可以说,多数种类物品朝廷未尝提供,除少数可通过征发徭役等途径获取外,余者主要应通过“市肆”交易而得。
文献所见购于市的物品约有如下几种:
米。
官俸中往往有米,但未必敷用,不免要买于市。
《颜氏家训·治家》载,北齐吏部侍郎房文烈“经霖雨绝粮,遣婢籴米”,吏部侍郎(应作吏部郎中)为正四品,岁禄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其中1/3二十匹折为粟,数目应不少,尚有断粮之时,其他官宦之家光顾市廛购买米麦可能更频繁。
西魏时赵平太守孟信去官后居贫无食,只好卖牛“拟供薪米”。
按北齐制,“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隋制“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去职者更应无禄。
除非买田置业,否则口粮都需仰仗市易。
盐菜。
官俸中基本不含,又为生活所必需,获得途径主要是市买。
《隋书》卷74《厍狄士文传》称开皇初士文任贝州刺史,“所买盐菜,必于外境”,有些特殊。
士文性孤直,不与邻里至亲往来,僮隶亦不敢出门,故购盐菜于外境,通常则买于当地。
关于蔬菜,《齐民要术》中多处谈到如何为城镇供应蔬菜,《北齐书》卷10《彭城景思王浟传》记高浟如何明谋善断时也涉及市上售菜事。
购买者主要应是城镇居民,官吏当为最大的买主。
《北史》卷54《斛律光传》载北齐后主时,帝以“邺清风园赐(穆)提婆租赁之。
于是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此属特例,亦可见官员所需蔬菜量之大。
书。
官员、儒士所读的典籍多从市购得。
据说常景“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
”市上流通的著作罕见者不少,故崔亮显达前曾“观书于市”,北魏延昌初在朝廷典司经籍的秘书省担任著作佐郎的王遵业也要“买书于市”,足见洛阳市肆售书品种之丰富。
市廛所卖不尽是圣贤之书,东魏末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
”后“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
卖书者曰:
‘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这则逸事说明市肆售书包罗甚广,良莠杂陈,轻薄浅陋之作同样颇有市场。
当时出现的佣书、抄书者,部分应与市肆售书有关。
以上是文献足征者,若参考地下出土资料,购于市的物品清单还可列出许多。
各地北朝墓葬中出土大量日用陶瓷器,种类繁多,多是实用器,有些尚保留着使用过的痕迹。
这些器物由专门陶瓷窑烧制,通过“市”购买获得。
198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发现不少瓷器与釉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器,便是明证。
北朝大中型墓葬的墓主为贵族、官吏,这类墓中主要的随葬品是陶模型明器。
考古发掘证明北朝存在生产陶明器的作坊。
模制明器应为批量生产所得,走的是市场化的道路。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菩提寺》说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
”陶俑盖属送死人之具。
以陶明器随葬之俗遍及北方,各地市肆都少不了此类物品。
墓中随葬的铜镜、铁镜之类亦是起居所用,非家庭所能制作。
其来源也应是市肆。
时至北齐,不但官吏平日生活离不了市易,连朝廷祭祀用牲也开始购于市。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载天保八年(557年)八月诏:
丘、郊、禘、袷、时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监视,必令丰备。
据《隋书·礼仪志》,北齐初每三年一祭昊天上帝于圆丘,连配祀、从祀,合用苍牲九;后改为冬至祀之。
又每岁一祀南郊,“其上帝,配帝各用牲一”;春夏秋冬时祀一年共四次,“每祭,室一太牢”,高洋践祚置六庙,并同庙而别室。
时祀每年需牛、羊、猪各24头,连同丘、郊等,每年祭祀所需祭牲并不太多,即便如此,都需仰仗市取,朝廷需要的其他大宗的、非赋税征收可得的物品更应购于“市”。
朝廷活动所需开始采购于市,表明市地位日重、影响日广。
限于作者的立场与视角,文献对官吏日常生活只有蜻蜓点水的触及,有时不得不加以推测。
仅凭文献尚不能完全揭示其生活与市的联系。
辅之以考古资料,或可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综合二方面的资料,可以断定当时官吏日常所需物品除少数由朝廷官府供应外,更多的是采买于市。
至于城镇驻扎的士兵的供应,目前仅知北魏中期以后军队出征,政府供应军粮,地方镇戍兵亦由政府提供军粮,屯田亦解决部分供应。
详情不明。
据居延汉简所见两汉制度,西北边塞屯戍将士虽由官府供官俸、廪食、装备,平日赴市买卖仍很常见,购售物品种类亦涉及甚广。
北朝情形应相去不远。
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至于他们的生计,尚不清楚。
孝文帝以后官方的束缚渐松,他们开始通过“市”与普通百姓打交道。
《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述大市部分论之颇详,地方上亦如是,据《魏书》卷37《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便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
工匠生活所需也少不了依靠市肆。
城镇中的农民除农产品可自产外,余下的物品也要求之市廛。
术士的情况详下。
城镇居民情况如上。
农村居民不但近都邑有市处者要在市上向城镇出售多种物品,而且所有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的不少物品不同程度地由“市”供应。
铁农具多购于市。
班固指出铁器“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北朝时并无变化。
《魏书·孝感传》记赵琰“遣人买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还刃主”。
所谓“耜刃”,应是木制挖土工具“耜”刃端套上的凹字或一字形铁刃,这种农具通称为“”,各地出土甚多。
此事发生在迁都洛阳之前,史书载此意在褒扬赵琰高义,具体背景不详,却揭示铁农具交易情况。
赵琰身为官吏,所需农具尚需购买,农民更应如此。
同书卷52《赵柔传》云曾有人给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
”铧装在犁上用来破土,一云为锸,即今之铁锹。
赵柔一次售出铧达数百枚,可知市上铁农具销量之大及农民需求之多。
其时除计口授田者由朝廷供给农具外,余者均需自行购买。
二事涉及农具不同,一买一卖却证明农民使用的铁农具主要购自市肆。
当时农民使用的农具不止这两种。
早在《管子·轻重乙篇》中便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銍,然后成为农”,两汉时铁农具已臻完备,至北朝种类则更丰富。
见于《齐民要术》的尚有铁齿(牲畜拉的铁齿耙)、劳(无齿耙)、锋(有尖犁鑱而无犁壁的农具)、辗(磙压农具)等,其中不少为铁制,来源也应是市廛购买。
当然,铁农具使用周期长,因此而赴市的机会不会太多。
耕牛,特定情况下也需购买。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李彪上表建议取州郡民屯田,说“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获准施行。
隋文帝时,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这两例均是朝廷或官员出资为百姓购买,通常农民需要耕牛,恐怕也只有市买一途。
北魏初屯田民尚可由朝廷配给耕牛,太和中已改为购买,至北齐时朝廷祭祀用牲亦仰市取,普通百姓恐也别无他途。
一些作物的种子也需购自市肆。
《齐民要术》卷3《种韭》“收韭子,如葱子法”下注称“若市上买韭子,宜试之”,并讲述了具体方法。
贾氏所著乃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成,此说当有实据,非空穴来风。
韭子可市买,其他作物种子也未尝不可,虽然书中不载。
这种情况揭示了农民生产与市的密切联系。
此外,村民每日离不了的盐也要购买而得,尽管史书缺乏有关直接材料。
村民起居使用的各种陶制品(少数人或许开始使用瓷器)大部分也来自市廛。
《齐民要术》卷7《涂瓮》讲到瓮“若市买者,先宜涂治,勿便盛水。
”据此,其他日用器皿恐怕相当部分也非自行烧制,而采买于市。
综观文献与考古资料,北朝城乡居民物质生活上与“市”联系的广泛、密切程度要超出以往的想象。
视之为自给自足,显然不准确。
同时“市”不仅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场所,也是卜师、相士活跃的舞台,他们聚集于此为各色人等有偿提供知识,决疑解惑。
这一点学者多未措意,实不可不察。
关于隋初杨伯丑的记载稍详,可见市内术士活动之一斑。
伯丑《隋书》及《北史》《艺术传》分别有传,文字几乎一致。
现据《隋书》节录如下:
(开皇初,伯丑入朝,后游行市里)尝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乐每从之游。
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伯丑亦开肆卖卜。
张、杨卖卜之处不出长安二市,据后文,伯丑卜肆似在东市。
《隋书·百官志下》记隋都长安设京市令,下辖尚有“肆长四十人”,卜肆应居其一。
操此业者绝非仅张、杨二人。
由“卖卜”一语看,他们的服务是有偿的。
传又云:
有人尝失子,就伯丑筮者。
卦成,伯丑曰:
“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
”如言果得。
或者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伯丑,为筮之曰:
“金在矣。
”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
“可取金来?
”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
《礼记·曲礼上》指出“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
”穆亮对孝文帝说“占以决疑”杨伯丑为人卜筮起的正是这种作用。
上述事情,在今天均应由警察、法官处理,当时往往要求助于术士。
他们的服务对象并不限于普通百姓,有时甚至被召入宫廷,替皇帝解疑。
史书又云:
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
……(伯丑)具言隐者姓名容状。
上如言簿责之,果得本珠。
伯丑效力皇室并不仅此一遭,之前还曾为太子所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