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清代学术史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学术史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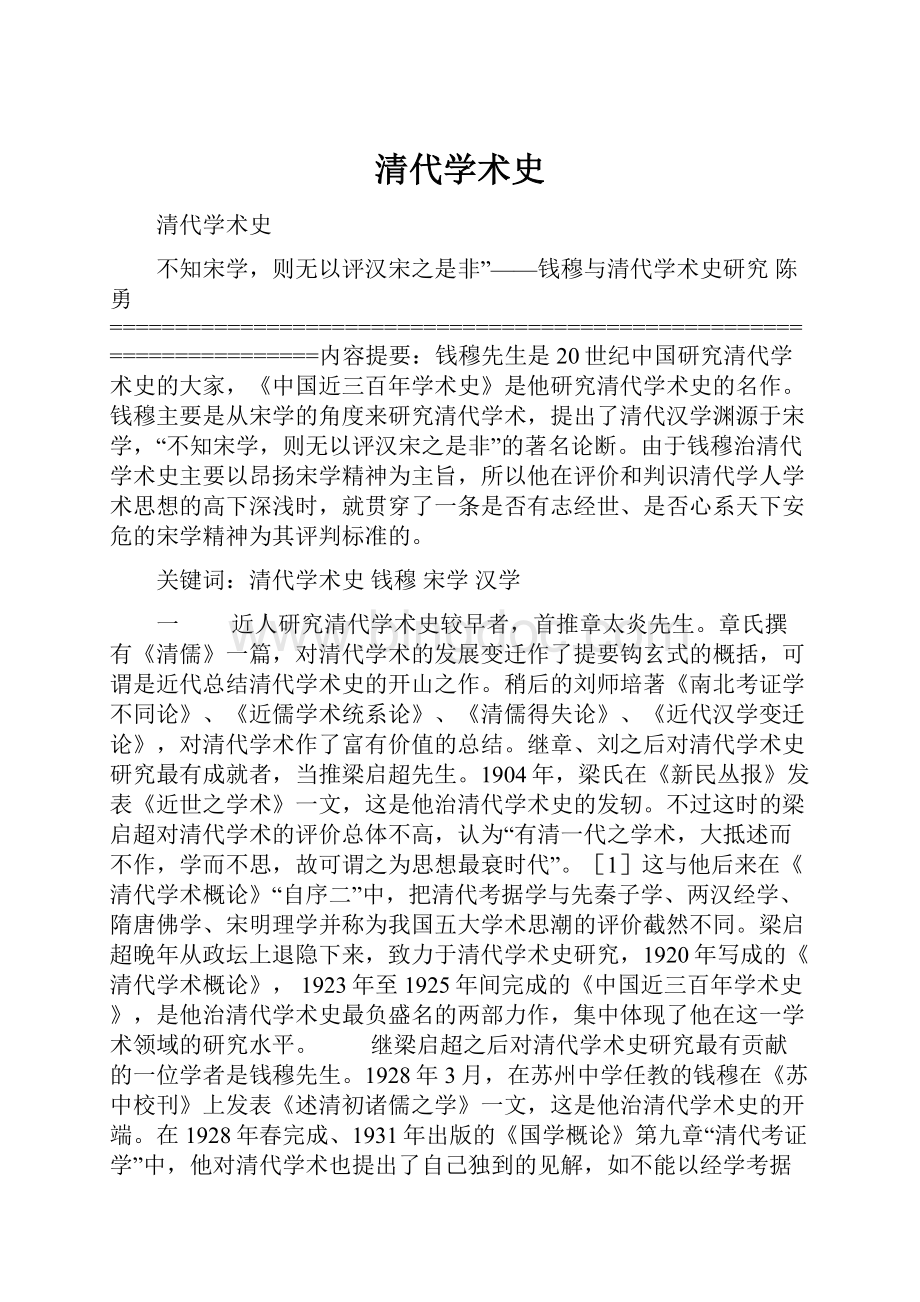
根据钱穆晚年的回忆,他最早接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在1924年的《东方杂志》上。
梁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1924年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过,钱穆首先在该杂志上拜读了梁著的这一部分内容。
梁著全书出版后,他曾在北平东安市场某一书肆购得了这部治清代学术史的名著。
梁氏此书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疏理清代学术史,多著眼于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处。
钱穆不赞同这一观点,所以他在北大史学系特开此课程,以阐发自己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
由于此课程是在梁启超卒后不久续开,所以备受学术界的注目。
当时钱穆一面授课,一面编写讲义,前后五载,终于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不朽的名著。
钱著共分14章,上起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晚明诸遗老,下至晚清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共叙述了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抗战军兴,钱穆流转西南。
1941年,在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担任教职的钱穆接受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之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一书。
在此之前,虽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但江书仅迄乾嘉,又固守汉学壁垒,详汉略宋,殊嫌不备。
继起者唐鉴的《清学案小识》,专重宋学义理,排斥汉学,分类牵强,其书止于道光季年,亦未穷尽有清一代学术原委。
近人徐世昌所辑《清儒学案》208卷,1169人,止于清末,最为详备。
然该书旨在搜罗,未见别择,被后世讥为“庞杂无类”。
钱穆承担《清儒学案》的编写后,先读清人诸家文集,每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
他托友人代为收购清代关学遗书二十种左右,有清一代关学材料,“网罗略尽”。
勤读李二曲集,采其言行撰一新年谱,所花精力尤多。
又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之书,“于程山独多会悟”。
对于苏州汪大绅以下,彭尺木、罗台山各家集,也提要钩玄,“颇费苦思”。
钱穆称《学案》一书的编写,以这几篇最有价值。
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共编孙夏峰、黄黎洲等64个学案,一代学林中人,大多网罗其中。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审察<
清儒学案>
报告书》中称赞钱著“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
”[2]该书字字皆亲手抄写。
由于当时处抗战中,生活清苦,没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
抗战胜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
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葬身鱼腹。
全书仅存序目一篇,在寄稿前录存,刊于四川省立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集刊》第三期上。
陈祖武先生对近人治清代学术史作了这样一个简明而中肯的总结:
“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
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
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
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
……今日治清代学术史者,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
”[3]确为不易之论。
二
对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近代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清代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
此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出了“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的主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详加阐述。
在梁启超看来,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路径。
这条路径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反理学思潮(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
所以,他认为从明末到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据此,梁著把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并把汉、宋对立这一思想贯穿全书[4]。
钱穆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
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
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甚深的影响。
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
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绂、全祖望等人也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
即便是到了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
所以,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见解。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
曰:
必始于宋。
何以为始于宋?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
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
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
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而于时已及乾嘉。
汉学之名,始稍稍起。
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
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
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梁启超把宋学、汉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的,旨在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
从清代学术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动说”无疑有他的合理性。
因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经学考据,重实证,以求是为宗,与晚明空疏的学风确有不同。
从清初开始,学风由虚转实,由主观的推想变为客观的考察,这的确是对宋明之学的一种反拔[5]。
钱穆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6]。
就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言,钱穆的“继承说”较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争更为合理一些[7]。
因为:
首先,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史仅仅归结为一经学考证史,并非全面。
清代学术的主流毫无疑问是经学考证,但这却不足以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史。
有清一代,不仅有盛极一时的汉学,与汉学相伴的还一直存在着追寻义理的宋学。
即使是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这种学风依然存在并始终与考据学相颉顽。
与考据学大师戴震同时的章学诚揭橥史学经世的旗帜,发出了搜罗遗逸,擘绩补苴、不足以言学的呼声,便是对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风的抗议。
而此时讲求经世致用,追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已在其内部酝酿发皇。
到了晚清,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有常州公羊学派的崛起。
到近代,康有为等人把该派的观点发挥到极致,借经学谈政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这些学术思潮,的确是无法用考据学来取代的。
钱穆早年就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
他在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据学”中开篇就说:
“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据,固也。
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
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
”到道咸之时,乾嘉汉学流弊重重,乾嘉诸儒的古训、古礼之研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
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
到了清季,康有为“以今文《公羊》之说,倡导维新变法,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自此绝矣。
”[8] 其次,大凡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在前一个时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迹象,同时也不可能在后一个时代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钱穆在《清儒学案·
序》中指出:
“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
”所谓“每转而益进”,指的是学术思想的继承。
前后时代的学术思想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别,但其中必然有内在的联系,必然有前后延续的成份。
而“途穷必变”,则是指学术思想、方法的变革和创新。
研究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只看到前后时代的学术差别而看不到继承,或仅着眼于前后的继承而看不到前后时代学术的区别,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确的方法应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
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整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都隐含了这样一种方法。
他说两汉经学,并不是蔑弃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而别创所谓经学,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为经学之新生。
宋明理学,并不是蔑弃汉唐而另创一种新说,而是包孕两汉隋唐之经学和魏晋以来流布中土之佛学而再生。
清代学术也不例外。
对清初诸儒而言,宋明理学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知识资源,宋学对他们的影响自不待言。
乾嘉诸老以考据为宗,但是他们从事考据的终极目的仍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的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不可掩。
而道咸以来,随着训诂考据一途走向绝境,学者把眼光再次投注宋明理学,汉宋调和、尊宋抑汉风靡学界,经世意识和宋学精神得到高扬,理学重新得以复兴。
所以钱穆认为,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而来。
诚如所言:
“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
[9]钱穆治学术史,善于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运动中加以分析,善于从中国自身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去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
他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在近现代学术界并不是没有赞同者、响应者。
比如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前半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专辟“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来讨论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认为清代汉学家表面上虽然表现为反道学,但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仍是宋明道学的继续,与钱穆持有相同的见解[10]。
三 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分期,钱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着眼,把清代学术史分为前后二个时期。
从顺治入关到乾嘉时代为前期,清初诸儒承袭了宋明儒思想的积极治学传统,在清初学术史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但到了乾嘉时期,学者在清廷刀锯鼎镬的淫威下走上了训诂考据之路,毕生在丛碎故纸堆里,追求安身立命之所。
从道咸起至清廷覆灭为后期,在后期八十年中,一方面是清朝政治腐败,另一方面则是西学东渐,二者给晚清学术思想以极大的影响。
在《清儒学案序》中,钱穆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把清代学术史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个阶段,并对四个阶段不同的学术特征作了归纳概括。
钱穆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第一章“引论”论述清代学术的源起及其与宋明学术的关系外,其余十三章皆以各个时期学术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为题。
各章所选择的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乾嘉、晚清三个时期,涵盖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上的经世思潮、经学考据和今文经学等各个层面。
这里我们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考察中心,对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作一些论述和分析。
1.清初诸儒之学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清初诸儒之学。
他在1928年发表的《述清初诸儒之学》一文中称清初诸儒,“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
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
有朴学家之博文广览,而无其琐碎。
宋明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
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
”与此文大约刊出的同时,钱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第九章中,也扼要地勾画出了明末清初群儒的思想。
他说“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者,有黄梨洲”;
“辨体用,辨理气,而求致之于实功实事者,有陈乾初”;
“不偏立宗主,左右采获以为调和者,有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
“绝口不言心性,而标‘知耻博文’为学的者,有顾亭林”;
“黜阳明而复之横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实,以纠心知觉念之虚妄者,有王船山”;
“并宋明六百年理学而彻底反对之者,有颜习斋”。
[11]在钱穆看来,在清初诸儒中最有建树的,当推黄梨洲(宗羲)、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颜习斋(元)四家,所以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章著重对这四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清学史中的影响作了专门的研究和阐发。
黄梨洲从学于刘蕺山(宗周),以发挥其师慎独遗教为主。
他把读书与求心,博学与良知统一起来,对于矫正晚明王学未流空疏偏狭之弊,极有意义。
顾亭林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相标榜,治学明流变,求佐证,不言心性,为乾嘉考据学开一新途辙。
但亭林治学以考据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学宗旨在于明道救世。
王船山学宗横渠(张载),“能辟佛老以返诸儒”,论学始终不脱人文演化之观点,其学博大精深,三百年来思想之深刻无出其右。
颜习斋论学深斥纸墨诵读之业,对宋明六百年来之理学,高言排出,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开二千年不敢不之笔”,在清初学术史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在清初四大家中,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主张对乾嘉考据学风影响至大,乾嘉时期的经学考据实由此而衍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顾炎武推崇有加,尊之为清代“汉学开山”。
他说顾氏在清代学术界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于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
其二在于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力戒雷同剿说,虚心改订不护前失等。
其三在于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讲求音韵,说述地理,研究金石等。
故亭林之学,气象规模宏大,乾嘉诸老,无人能出其右。
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他发其端,后人衍其绪,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的去向[12]。
所以梁启超指出,亭林之学“对于晚明学风,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
所以论清代汉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13] 钱穆并不否认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不否认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他说亭林“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
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
……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
”[14]但与梁启超所不同的是,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思想渊源作了一番穷源竟委的考证和解释,认为此说并非顾氏自创,清初钱谦益已开其先,而钱氏之说又源自明代的归有光。
他说:
“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佐证,以开后世之途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
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
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绝之姿,为斩截之论,即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15],故其说遂为后世瞩目。
在钱穆看来,对乾嘉考据学风影响很大的并非顾炎武一人,在晚明诸遗老中,黄宗羲的影响就不小。
此说在他早年著作《国学概论》中已有阐发,在《近三百年学术史》“梨洲经史之说”中亦详加讨论。
黄氏考证《易经》,著《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
胡渭著《易图明辨》,卷末备引其说。
著《授书随笔》一卷,实开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之先导。
又究天文历算之学,亦开风气之先,著《授时历故》等书,俱在梅文鼎前。
于史学,贡献特大,为浙东史学的开创者。
浙东史学自梨洲开其端,一传为万季野(斯同),再传为全谢山(祖望),止于章实斋(学诚),遂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双峰并峙,交相辉映。
钱穆认为,黄宗羲为矫晚明王学空疏之弊,力主穷经以为根底,已为新时代学风开一新局,其影响后学,实不在顾亭林之下。
后人言清代汉学,不提黄氏的影响,全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为截断众流,是因为顾氏之说符合汉学家的口味,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重。
钱穆认为,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走入顾氏“经学即理学”一途,浙东精神未能彰显于世,这实在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件值得令人惋惜的事[16]。
所以他批评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氏一人之力,为“失真之论”[17]。
2.乾嘉经学考据 清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弃了顾炎武、黄宗羲等晚明诸儒通经致用的思想,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
所以,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至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而大变,其学术精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
乾嘉考据之学至吴人惠栋、皖人戴震已臻全盛,尊汉排宋,风靡学界。
所以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0章专论乾嘉考据之学。
将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已露端倪,而将两派学术异同作区分并加以论述的则首起于章太炎。
他称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
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
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
此其所异也。
”[18]梁启超继承章氏之说而发以发挥,认为吴派为学淹博,拘守家法,专宗汉说;
皖派治学不仅淹博,且重“识断”、“精审”。
于是惠、戴之学中分乾嘉学派,遂成定论。
吴、皖两派分帜对立之说创立以来,学术界多遵章、梁之说,不免忽略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
钱穆在研究乾嘉学术时,不仅看到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区别,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及其相互影响,这体现了他治学的敏锐和识见精深之处。
钱穆认为,苏州惠学尊古宗汉,意在反宋,惠栋即有“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之说。
而皖南戴学却“从尊宋述宋起脚”,初期志在阐朱述朱,与反宋复古的吴学宗旨不同。
但自乾隆22年(1757年),戴东原(震)北游后南归,在扬州见到惠定宇(栋)以后,其学大变,一反过去尊宋述朱转而诋朱排宋,而戴门后学,排诋宋儒,蔚为风尚,乾嘉汉学由是大盛。
钱穆认为,“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
[19]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出了多条理由以证其说[20],得出了“东原极推惠,而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的结论。
所以,钱著以惠、戴论学有舍,交相推重为由,将二人同列一章,即体现了这种布局安排。
由于钱穆力主清学导源于宋学,重视宋明理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所以其著作在内容的安排上,特别注重发掘清儒对宋明理学问题的探讨,即便是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代,书中的编纂布局亦是如此。
钱著笫八章以戴东原为题,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栋)、程瑶田(易畴)附之。
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于厘清戴学的学术渊源。
钱穆指出,徽、歙之间,乃朱子故里,学者讲学,多尊朱子,故尚朱述朱之风,数世不辍。
对于皖学的渊源,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
江(永)治学自礼入。
其先徽、歙之间,多讲紫阳(朱子)之学,远与梁溪、东林相通,(江)永盖承其绪风,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
”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氏作了更详尽的考证:
“考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
有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汪佑、吴慎、朱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以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汲其余波。
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
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
”[21]江氏之学传至东原,形成皖学。
钱穆述东原之学源于徽歙,戴学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学对戴氏的影响上。
这说明皖学自绍宋入手,与吴学自攻宋起脚异趣。
戴氏晚年排诋宋儒,刻深有过颜李,所以章学诚力斥东原攻朱子之非,讥其“饮水忘源”。
钱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云苔(元)、凌次仲(廷堪)为题而附之以许周生(宗彦)、方植之(东树),也体现了这种安排。
焦循、阮元、凌廷堪学尊东原,为考据名家,但钱穆看重的并不是他们在考据学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们对汉学流弊的反思和批评上。
钱穆指出,焦氏之学“主用思以求通”,与当时名物训诂逐字逐句的零碎考释学风已有不同。
阮元“颇主求义理,故渐成汉宋兼采之风。
”而凌廷堪对当时汉学流弊多有不满,有“不通世务,不切时用”,“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意气日盛”等批评之语[22],实开近代抨击乾嘉学风之先声。
焦、阮、凌三人皆为汉学考据大家,却群起批评自己学派的短弊,从中亦可透显出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即将来临。
故此章以考据学风的批评者许宗彦附于三人之后,又以攻击乾嘉汉学最烈的方东树殿尾,无非是要向人们表露这样一个信息:
乾嘉汉学此时流弊重重,逐渐失去了学术界的支持,“路穷而思变”,此后的学术路向必然要向汉宋兼采的方向发展。
此章的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23]。
3.常州今文学派 在考据学风弥漫的乾嘉之际,公开站出来批评这种学风、树反汉学旗帜的有史学家章学诚。
章氏祭起“学术当以经世”的旗帜,高唱“六经皆史”之说,对乾嘉汉学埋首考据的琐碎学风大加抨击。
到道、咸之际,随着训诂考证一途走向绝境,有追求微言大义的常州今文学派的异军突起,湮灭了一千多年的西汉今文经学重新得以复兴。
钱穆指出,常州今文学派“起于庄氏(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而变于龚(自珍)、魏(源)。
”所以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章以龚定庵(自珍)为题,附之以庄方耕(存与)、庄葆琛(述祖)、刘申受(逢禄)、宋于庭(翔凤)、魏默深(源)、戴子高(望)、沈子敦(垚)、潘四农(德舆),对晚清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常洲今文经学作了专门论述。
常州之学由庄存与开其端,庄氏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著《春秋正辞》,旨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
常州公羊学至庄存与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时张大旗帜。
常州言学,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最终必归趋于论政,开此风气之先者首推龚自珍。
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