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docx
《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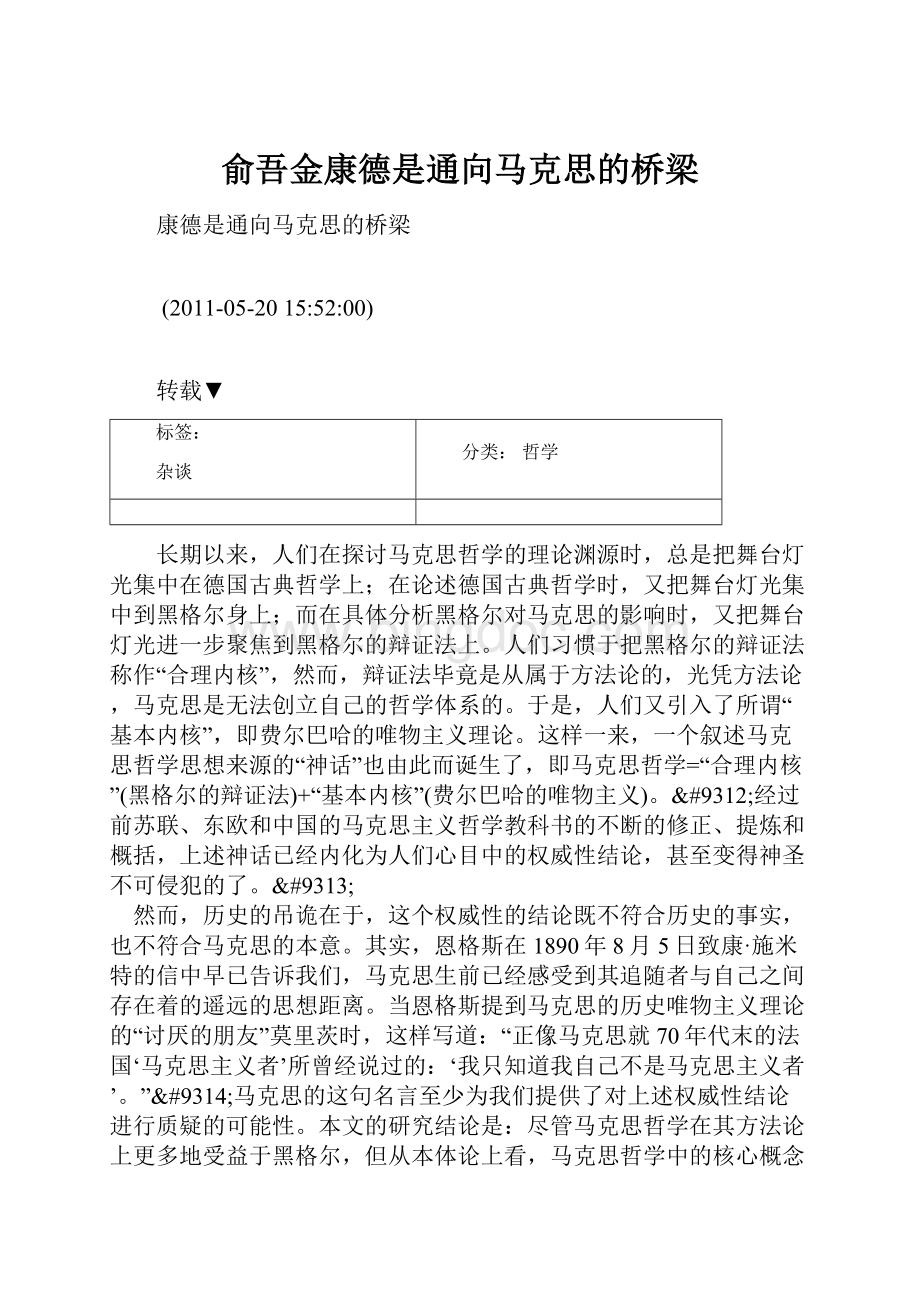
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2011-05-2015:
52:
00)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哲学
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舞台灯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在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又把舞台灯光集中到黑格尔身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时,又把舞台灯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
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然而,辩证法毕竟是从属于方法论的,光凭方法论,马克思是无法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
于是,人们又引入了所谓“基本内核”,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
这样一来,一个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神话”也由此而诞生了,即马克思哲学=“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①经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断的修正、提炼和概括,上述神话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②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其实,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早已告诉我们,马克思生前已经感受到其追随者与自己之间存在着的遥远的思想距离。
当恩格斯提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讨厌的朋友”莫里茨时,这样写道:
“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③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权威性结论进行质疑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尽管马克思哲学在其方法论上更多地受益于黑格尔,但从本体论上看,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实践、自由、社会生产关系等,却更多地受惠于康德。
康德才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一、唯心史观和市民社会
众所周知,尽管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止于其辩证法,但其辩证法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告诉我们: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④在这段常被研究者们引证的、极为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概念,即“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
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人们通常把“神秘外壳”解读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是这种唯心主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倒立着的”,所以,要引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再“把它倒过来”。
其实,这种滥觞于斯大林的、流俗的阐释方式,既没有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性,也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殊性及它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差异。
我们还是让马克思本人来替我们解开谜团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一书时,曾经写道: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⑤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人”、“劳动”、“异化”、“对象化”和“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表明,他不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后来恩格斯谈到的一般的唯心主义,⑥而是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方向也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段重要的论述中得到印证:
“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地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
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
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
……这一运动的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
”⑦在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但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论述中,马克思不正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吗?
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着重讨论的并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这就表明,马克思试图加以颠倒的不是黑格尔的一般唯心主义理论,而是其历史唯心主义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还未使用“神秘外壳”这一提法,但当马克思强调“《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时,他注意到的正是黑格尔哲学(包括其辩证法)的神秘化的外观。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其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
”⑧这里说的“将近30年前”也就是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
这就表明,《手稿》批判的重点之一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方面”。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谈到的“被神秘化的批判”或“神秘的方面”也好,“神秘外壳”也好,其指涉的对象都是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
一言以蔽之,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才是马克思首先要加以颠倒的对象。
事实上,也只有在思想基础得到正确的安顿之后,马克思对“倒立着的”的辩证法的再度颠倒才成为可能。
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是重大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
正统的阐释者们倾向于前一种立场,为此,他们认为,马克思认同并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他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
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论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而这种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被用来摈弃或克服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他这样写道: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⑨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启示我们:
第一,既然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运用其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改造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人类社会的意识发展史(颠倒过来就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发展史)作为载体的,而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是以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作为载体的,因而它根本无力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性的改造;第三,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实际上已经预先设定了对以后出现的“推广论”的批判。
何谓“推广论”?
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经典性的表述: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⑩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
由此可见,在“推广论”的叙述模式中,完全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唯物主义(自然界是本原的)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其原因很简单,“推广论”把辩证唯物主义置于逻辑在先的位置上,而当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时,这个自然界与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才得到研究的人类社会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由此可以推断,“推广论”的叙述模式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马克思在上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也已告诉我们,从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出发,无论如何引申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来。
显而易见,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般唯心主义的时候,把这种唯心主义倒过来,就是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而这种唯物主义关注的就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
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抽象的说教正是在这种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的。
可是,他们居然把这种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其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只有当人们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解为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实质的道路。
在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视野中,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而是“人”、“国家”、“宗教”、“对象化”、“市民生活”、“历史的结果”等概念,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批判则始终聚焦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理论上。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其法哲学理论中,而其法哲学理论的要害正在于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
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正是从这一点切入的。
他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时这样写道:
“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
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
”(11)马克思摈弃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神秘外壳”是从恢复市民社会的现实地位着手的。
马克思一旦把“市民社会”概念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拯救出来,立即赋予它以真实的含义和重要的地位: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12)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概念的崭新的认识,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初步的叙述: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13)由此可见,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的,只能是以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确信,上述断言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回顾自己思想发展的道路时,就已告诉我们: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14)在这段论述之后,马克思表示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在研究过程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接下去的一大段话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性表述。
所有这些都表明,正统的阐释者们所创造的神话——即马克思先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再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里,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如下:
先批判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代表作《法哲学原理》,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真正舞台是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只能诉诸政治经济学。
于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实践理性和主体意识
在大致弄清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形成过程后,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才刚刚开始。
因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时获得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载体。
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所赖以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的,从而无论是“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时拯救出来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是无法充当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载体的,因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提示我们: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15)显而易见,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的解读中,市民社会是一个拥有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的、基础性的概念,但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中,这个概念却缺乏积极性。
此外,这个概念的哲学含义要远远地弱于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含义。
所以,马克思并不打算把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辩证法的载体。
那么,马克思为其辩证法寻找的真正载体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条实际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马克思这样写道: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6)在马克思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上,而要深入下去探寻市民社会得以可能的原因。
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从哲学上看,“实践”才是真正的始源性的概念,因为市民社会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
“实践”概念会不会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过来的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17)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抽象思维时滑向另一个极端,即沉湎于感性直观,但他所理解的“感性”并不是实践活动意义上的感性。
马克思还进一步阐发了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8)这就又一次启示我们,所谓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直观的唯物主义绝对不可能成为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桥梁。
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追问的是,究竟马克思是从哪个传统、哪些哲学家那里接受了“实践”概念,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呢?
我们知道,正统的阐释者们在提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来源时,常常追溯到青年黑格尔派,并由此而上溯到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据奥古斯特·科尔纽的考证,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阵营中,是奥古斯特·冯·契希考斯基在《历史哲学引论》中最先提出了“实践”概念。
在该书中,契希考斯基曾经写道:
“实践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实践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的发展,——一般说来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本份。
”(19)在科尔纽看来,尽管契希考斯基比马克思更早地意识到了“实践”概念的重要性,并率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还把它与费希特的“行动哲学”贯通起来,但“像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契希考斯基不是把实践看做目的在于直接地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看做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应该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否定来改变现存制度。
”(20)事实上,当时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实践”概念的。
布·鲍威尔在1841年3月3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曾经表示:
“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智的。
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完全不能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
”(21)总之,这种马克思后来称之为“理论范围以内的实践”(22)并不是马克思所使用的“实践”概念的来源。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伟大的思想传统。
青年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全面地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实践的智慧”(phronesis/practicalwisdom)的概念,主要指涉人们在政治、道德方面的行为。
在亚氏之后,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理论理性”(dietheoretischeVernunft),它以现象界的感觉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然必然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diepraktischevernunft),它以本体界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由。
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直接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
我们前面提到的契希考斯基的“实践的哲学”、布·鲍威尔的“理论实践”和费希特的“行动哲学”也都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余绪。
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理解并阐释康德的这一重要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做出了透彻的批判:
“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
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
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
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
”(23)那么,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究竟是什么意思?
黑格尔告诉我们:
“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一种能思维的意志,亦即指依据普遍原则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
实践理性的任务在于建立命令性的、客观的自由规律,这就是说,指示行为应该如此的规律。
”(24)意志本身作为生命的冲动,乃是非理性的力量,康德的实践理性把意志理性化,即使意志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服从理性的绝对命令,按照善良意志来行事。
康德把任何不按照善良意志来行事的行为都斥之为不道德的。
从一方面看,康德的实践理性把人的尊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的:
“实践理性呈现给我们一条纯粹的、脱尽一切利益的道德法则,以供我们遵守,而实践理性的声音甚至使胆大绝伦的罪人战栗恐惧,不得不闻而逃匿。
”(25)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在现实生活中,康德的实践理性和善良意志又是难以得到贯彻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批评道:
“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
”(26)上面我们引证的马克思这段话中的批评,即指责康德的善良意志是软弱无力的,也正是沿着与黑格尔相同的方向来展开的。
可是,马克思的批评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康德实践理性的阶级根源:
“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
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
”(27)所以,理论思想,当然也包括道德理想在内,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人的意志则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由于德国的小资产者,包括其代表人物康德在内,害怕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方式,因而他们竭力把法国资产阶级的血淋淋的革命“实践”转化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实践理性”。
通过深入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但从中剥离出“实践”概念,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实践概念是指人的一切感性活动(除去单纯的直观和思维),狭义的实践概念或指涉生产劳动,或指涉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其他一切哲学思想的差异正在于是否诉诸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
他写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8)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含义的改写与提升是与他对“主体”(Subjekt)概念的提升同时进行的,而“主体”概念同样源自康德,尤其是源自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1787)中表示:
“迄今为止,人们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遵照对象;但是,关于对象先天地通过概念来澄清某种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在这一预设下都归于失败了。
因此,人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们假定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认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
……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的思想是相同的。
”(29)在以往形成知识的过程中,认识主体始终是围绕认识对象而旋转的,引入哥白尼式的革命原则后,这个过程完全被颠倒过来了。
康德提出的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由立法”等一系列见解表明,哥白尼式的革命不仅发生在认识论领域里,也发生在哲学的其他一切领域里。
正是通过这一革命,康德极大地高扬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而思想敏锐的马克思,正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直接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马克思写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0)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从实践出发、从主体出发去理解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的重要观点。
如果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凝炼起来,就是从主体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
那么,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主体”究竟指涉什么呢?
在通常的情况下,“主体”指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则指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人。
比如,马克思曾经表示: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31)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提出以及这一概念与“主体”概念的融合,到“实践唯物主义”思路的形成,处处都可见到康德传统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三、自在之物和意志自由
其实,说“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蕴。
它还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侧面深入地加以解读:
一方面,正是马克思破解了康德“自在之物”的秘密。
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的概念。
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个架构就无法支撑起来。
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通常有三层含义:
一是感性刺激的来源,二是知性认识的界限,三是实践理性的范导性原则。
康德以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批判甚至否定自在之物的概念。
然而,大部分哲学家在这样做时,触及的只是自在之物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含义,很少有人触及第三层含义。
但叔本华在这一点上却独辟蹊径,声称自己的哲学是直接接着康德的。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向我们揭示了自在之物的谜底:
“自在之物是什么呢?
就是——意志。
”(32)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世界的本质,换言之,世界就是意志的逐级客体化。
在人诞生以前,意志表现为盲目的冲动;而在人诞生以后,“认识之光侵入了盲目地起作用的意志的工地里去了,把人类有机体的纯生理机能照明了:
在磁性催眠术中就是这样。
”(33)于是,人们试图运用认识之光显示的真理来遏制意志,但意志是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