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docx
《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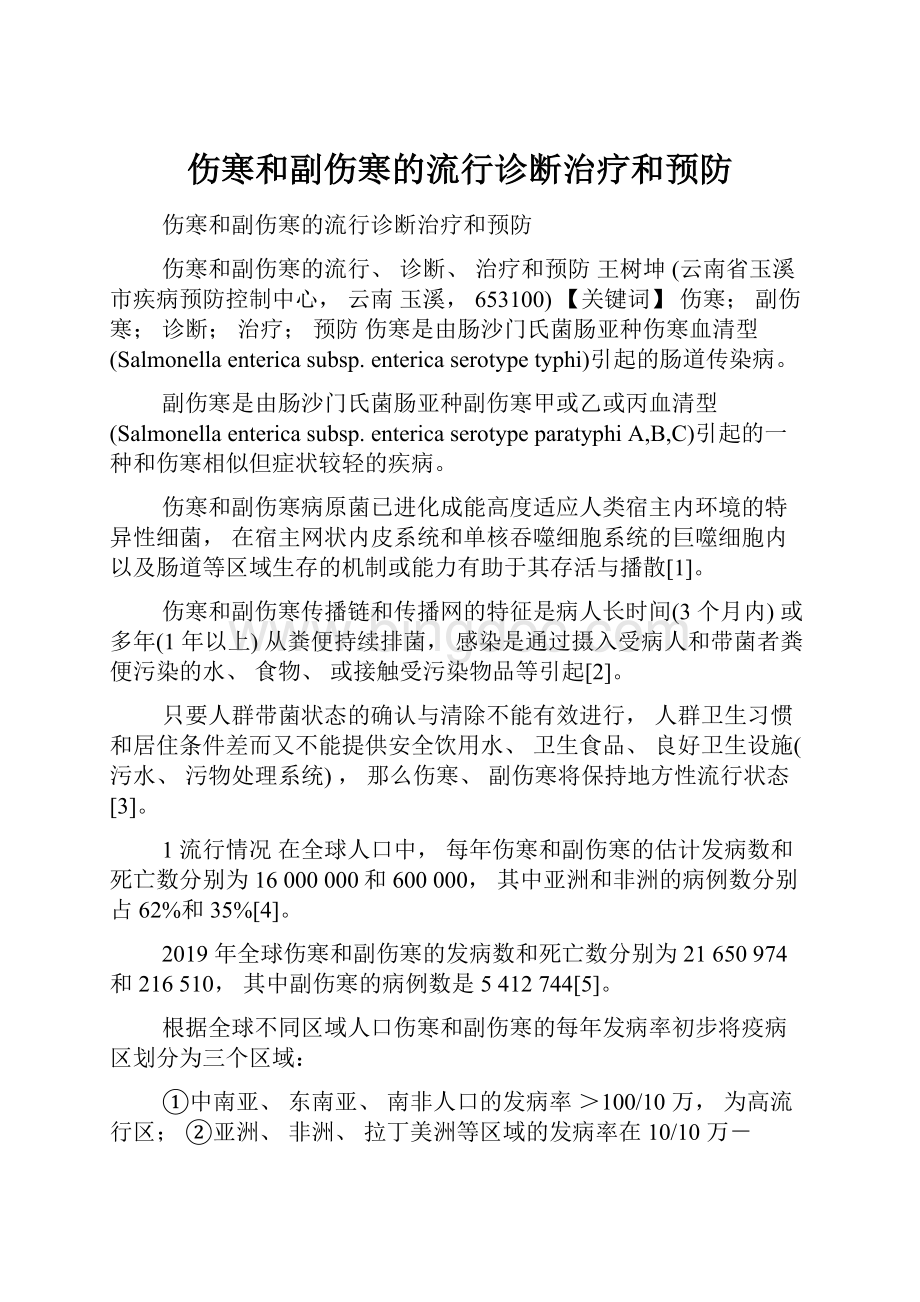
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
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
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诊断、治疗和预防王树坤(云南省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玉溪,653100)【关键词】伤寒;副伤寒;诊断;治疗;预防伤寒是由肠沙门氏菌肠亚种伤寒血清型(Salmonellaentericasubsp.entericaserotypetyphi)引起的肠道传染病。
副伤寒是由肠沙门氏菌肠亚种副伤寒甲或乙或丙血清型(Salmonellaentericasubsp.entericaserotypeparatyphiA,B,C)引起的一种和伤寒相似但症状较轻的疾病。
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已进化成能高度适应人类宿主内环境的特异性细菌,在宿主网状内皮系统和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巨噬细胞内以及肠道等区域生存的机制或能力有助于其存活与播散[1]。
伤寒和副伤寒传播链和传播网的特征是病人长时间(3个月内)或多年(1年以上)从粪便持续排菌,感染是通过摄入受病人和带菌者粪便污染的水、食物、或接触受污染物品等引起[2]。
只要人群带菌状态的确认与清除不能有效进行,人群卫生习惯和居住条件差而又不能提供安全饮用水、卫生食品、良好卫生设施(污水、污物处理系统),那么伤寒、副伤寒将保持地方性流行状态[3]。
1流行情况在全球人口中,每年伤寒和副伤寒的估计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16000000和600000,其中亚洲和非洲的病例数分别占62%和35%[4]。
2019年全球伤寒和副伤寒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为21650974和216510,其中副伤寒的病例数是5412744[5]。
根据全球不同区域人口伤寒和副伤寒的每年发病率初步将疫病区划分为三个区域:
①中南亚、东南亚、南非人口的发病率>100/10万,为高流行区;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的发病率在10/10万-100/10万之间,属中流行区;③世界其它区域的发病率<10/10万,为低流行区[6]。
自从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欧洲和美国伤寒和副伤寒发病率随着清洁水和良好污水处理系统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了,但该疾病仍然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严重公共卫生问题[4]。
在发达国家,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散发于归国旅游者和外来移民,偶尔发生点源爆发,在过去50年内疾病模式的两个主要变化是发病率明显下降和旅游相关疾病特征性表现[4]。
美国在1975-1994年期间每年报告病例数范围是375~441,在1994-1999年间报告病例总数是1393例;发病率自1940年的7.5/10万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0.2/10万,而旅游相关病例数的构成比自1967-1972年期间的33%上升到1996-1997年间的81%[7,8,9]。
大约10%未经治疗的伤寒和副伤寒病人粪内排除病原菌的时间大于3个月;1-5%病人成为粪或尿内排除病原菌时间大于1年的慢性带菌者,几乎25%慢性带菌者没有伤寒和副伤寒病史;妇女、50岁以上人员和患有血吸虫病、胆石病、胆囊肿瘤以及其它胃肠道癌症病人的带菌率较高[10]。
虽然慢性带菌者对病原菌存活或作为传染源的意义很重要,但其在疫病区作为直接感染源的意义没有受污染水或食品重要[6,10,11]。
【作者简介】王树坤(1964-),男,博士,主任检验技师,从事微生物与流行病学和传染病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工作,Email:
yxwsk@hotmail.com伤寒病人的病死率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变化相当大,平均病死率<1%;副伤寒病人很少出现并发症,病死率更低。
在住院病人中,巴基斯坦和越南的病死率<2%,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区域因难以获得有效的诊断和治疗,病死率达到30%-50%[12,13,14]。
一岁以下儿童和老年人的病死率最高,不过,不良结局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接受治疗或延迟有效抗菌素治疗,抗菌素的作用是缩短病程、降低并发症出现率、降低病死率[12,13,14]。
2危险因素人是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的唯一天然宿主,该病原菌在地下水、池塘水、或海水中能存活几天,在鸡蛋和冷藏鸡肉内可存活数月[6]。
传播媒介通常为病人和带菌者粪尿污染的水、食品、其它物品,口服感染剂量在1000-1000000个菌体之间[6,11,12]。
在发展中国家卫生条件较差的伤寒和副伤寒地方性流行区,一些流行病学研究确认该病的危险因素是吃家庭外制作街道食品(冷饮、生菜、水果等)、饮用受污染水、接触患者或带菌者、不认真洗手、不良居住地卫生设施、近期使用抗生素、受幽门螺杆菌感染[6,11]。
有研究证明,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数的比例会因城市化、更多依靠街道食品和免疫预防而发生改变,伤寒和甲型副伤寒的感染剂量和传播途径有一定差异,个人卫生、居住条件等家庭因素可能是伤寒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街道食品、饮水污染等家庭外因素对副伤寒传播更为重要[11]。
预防控制伤寒和副伤寒资源投入的重点是饮用水管网、污水处理系统、食品安全、卫生教育、带菌者确认与清除。
3病原菌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属于肠杆菌科沙门氏菌属肠沙门氏菌肠亚种中的成员。
沙门氏菌能发酵葡萄糖但不发酵乳糖,仅有肠沙门氏菌(Salmonellaenterica)一个种,分为enterica、salamae、arizonae、diarizonea、houtenae、bongori和indica七个亚种,根据血清型能将这些亚种进一步分成2463个血清型,其中enterica亚种有1454个血清型,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为enterica亚种中的4个血清型[1,6]。
采用分子分型技术的研究结果证明疫病区存在不同的遗传变异株,但爆发或流行常由少数变异株引起[15,16]。
变异株还与临床表现有联系,多种药物抗性分离株的毒力比敏感株的强,死亡病例分离株也可能和常见株不同[17]。
一个多种药物抗性伤寒病原菌株的完整DNA系列测定显示有4809037个碱基对,估计有4599个基因。
在菌株间保留的核心区域(染色体的70%-80%)代表着和肠杆菌科细菌相关肠道定值、环境存活和传播等基本功能的基因指令;已经确认了10个沙门氏菌的毒力岛,所有沙门氏菌株都有称作沙门氏菌毒力岛1(SPI-1)和2(SPI-2)的两个大基因族,使得沙门氏菌菌株容易侵入宿主细胞并在宿主细胞内存活;伤寒病原菌基因组还包含SPI-7,拥有编码Vi多糖产物的基因以及许多未知功能的其它基因[18]。
4抗菌素抗性1948氯霉素疗法的问世改变了伤寒观,将一度认为是重症、致死性疾病转变为普通、容易治疗的感染病,氯霉素、氨苄西林、TMP-SMZ成为治疗伤寒和副伤寒的规范抗菌素(三个一线药物)。
1972年报道多起氯霉素抗性伤寒的爆发,当时分离菌株还对TMP-SMZ、氨苄西林、阿莫西林敏感[19]。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报道了氯霉素、安苄西林、阿莫西林、TMP-SMZ、四环素多种药物抗性伤寒的爆发[6,12,15,16,19]。
氯霉素抗性与高分子量、可转导的IncHI质粒有关,多种抗菌素抗性是通过Phcm1质粒介导的,也携带编码抗性基因的100000-120000-kDIncHI质粒[2]。
在质粒介导多种药物抗性株出现后,氟喹诺酮类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素成为伤寒和副伤寒治疗的首选药[19,20,21]。
有资料报道将2g/d头孢曲松作为首选疗法[21]。
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出现是一个重大进展,该药高效、耐受性好,并可口服使用。
对环丙沙星敏感而且最小抑菌浓度小于0.03mg/L的分离株也必然对第一代喹诺酮药物敏感;一些分离株的体外药敏实验结果显示对环丙沙星敏感,最小抑菌浓度为0.125-1.0mg/L,但通常临床治疗失败[2,6,22]。
1997年发生的一次伤寒爆发在6个月导致8000人患病和150人死亡,尽管药敏实验报告这些病原菌株对氟喹诺酮类药物敏感,但所有NAR菌株氟喹诺酮类药物MIC为完全敏感株的10倍[2]。
越南一项研究报道NAR株和敏感株的构成比自1993年的4%上升到1998年的76%,这些NAR株的体外药敏实验结果显示对头孢曲松、头孢克肟和阿奇霉素敏感,但临床应答缓慢,热退时间大于7d,失败率高于20%[2,6]。
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喹诺酮药物抗性通常由喹诺酮药物抗性的染色体决定区gyrA基因的单点突变(Ser-83toPhe,Asp-87toAsn,Ser-83toTyr,Asp-87toGly)介导,引起其对环丙沙星等喹诺酮药物的敏感性降低,表1总结NAR株的关键特征[2,6]。
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04年建议将肠外沙门氏菌分离株的萘啶酸抗性试验作为氟喹诺酮药物敏感性降低的一个标志,分离株体外药物敏感性实验的敏感结果只有在对萘啶酸敏感时才是真正的敏感。
当然,该试验在欧洲并非千真万确,在对环丙沙星敏感性降低的伤寒病原菌中有11%的菌株对萘啶酸敏感[23]。
分离株的萘啶酸抗性试验和氟喹诺酮药物最小抑菌浓度测定是确定氟喹诺酮药物敏感性的最好办法。
多种药物抗性以及环丙沙星敏感性降低的特性在甲型副伤寒病原菌中也有报道,也就是说该菌存在质粒介导和染色体突变两种抗性模式[2,6]。
表1伤寒病原菌萘啶酸抗性株的关键特征[6]菌株来源NAR株的构成比NAR病人治疗失败率其它英国加拿大印度越南5实验室诊断伤寒和副伤寒病人的症状、体症无特异性,很难靠病人临床症状来做出准确诊断,需要从病人的血液、骨髓、粪便、尿液等以及和病人有联系的受污染水、食品等标本中培养分离到伤寒、副伤寒病原菌才能做出明确诊断,重复采集标本进行培养分离有时是必要的。
分离伤寒、副伤寒病原菌的目的包括两个,第一是在个体病例的层面上防止病毒性发热疾病病例使用抗菌素、确定针对性适宜疗法的抗菌素敏感性并监测日益常见多种药物抗性株的播散;第二是在社区群体的层面上监测传播链和相关感染源、确定病人群和传播途径、并提出有效预防措施。
在疫病区,除非证实为其它疾病,无明确原因持续发热大于1周或有毒血症后第5天的病人就应重点考虑患有伤寒或副伤寒。
血液和骨髓培养是主要的伤寒和副伤寒实验室诊断技术,使用标准血培养技术并采集成人>15ml血液或>1.5ml骨髓进行培养的阳性率可达90%以上,血液培养是常规诊断方法,取血量、病程、抗菌素、血与肉汤比例是影响血液培养阳性率的因素;骨髓培养更适合长病程和接受抗菌素治疗病人[24,25]。
因为血内细菌数比骨髓的少,所以血液培养的敏感性比骨髓培养的低,用10ml血液和1ml骨髓进行培养的阳性率相近[[24,25,26]。
伤寒、副伤寒病原菌粪便培养的敏感性依赖粪便培养次数与数量、病程、抗菌素使用和23%(42/179)24%(10/42)萘啶酸敏感株引起病人的氧氟沙星治疗失败率是5%(22/458)。
33%(7/21)80%(4/5)47%(82/174)27%(22/82)9%(46/504)24%(11/46)﹡病人个体因素,急性期病人粪便培养阳性率<30%,只进行粪便分离对其诊断是不够的,不过,粪便培养对带菌者的检测和管理是必须的[26]。
肥达试验用作伤寒和副伤寒辅助诊断的时间已有一百多年,该血清学试验的诊断价值存有争议而不再作为常规使用,因为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预测值在世界不同区域变化相当大而没有一致的诊断标准[27,28]。
试验的作用是通过证实感染急性期和恢复期抗体效价四倍增长而增强肠热症证据。
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抗体效价的增长并不是都能得到证实的,原因是只获得病人急性期血清样品、疫病区高水平背景抗体、或部分病人通过早期使用抗生素而引起抗体应答受阻[27,28];在临床实践中又不能等到获得双份血清样品结果才对病人进行治疗。
另外,抗体水平变化还和有交叉反应抗原的其它沙门氏菌引起感染的程度有关[27,28]。
6治疗伤寒和副伤寒治疗的重点是:
防止并发症和死亡,及时治疗临床病症,迅速清除病原菌以防止复发和粪内带菌。
支持性治疗包括体液维持、适宜营养和退热疗法。
有效抗菌素、良好护理、适宜营养、液体和电解质平衡、并发症的及时确认与处理是防止病人死亡的关键。
主要依靠临床判断以决定是否进行实验室检测并采用经典抗菌素疗法,感染菌株抗菌素药物敏感性信息对决定使用药物和有效治疗病人是至关重要的(表1,2,3)[2,6]。
根据疫病区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分离株的药物敏感谱选用抗菌素,可大概将分离株区分为一线抗菌素敏感株(FLDS)、多种药物抗性但萘啶酸敏感株(MDRNAS)以及萘啶酸抗性株(NAR)。
氟喹诺酮类药物(环丙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培氟沙星)是FLDS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最有效的治疗药物,临床治愈率>96%,平均热退时间<4d,复发率和粪便带菌率<2%[2,6,29,30]。
氯霉素(传统的一线药)在所有这几个方面的疗效没有氟喹诺酮类药物好(表2),再加上氯霉素在骨髓内的持续性原因,即便是对敏感株引起病人的治疗也不是最好药[2,30]。
有资料报道孕妇伤寒和副伤寒病人可使用-内酰胺抗菌素和氟喹诺酮类药物进行治疗[31,32]。
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儿童、成年人伤寒和副伤寒治疗中同样有效[33,34,35]。
不过,这些药物因为在生长期猎犬表现关节损害证据没有被注册为儿童常规用药[36],但是在患有伤寒、囊性纤维病、痢疾儿童中的广泛药物实验还没有显现骨或关节毒性以及生长损害的任何证据,并有文献报道该类药物对所有年龄组人群都安全、速效[29-35]。
所以,在多种药物抗性株流行和难以获得第三代头孢菌素的区域,氟喹诺酮类药物可用于儿童伤寒和副伤寒的治疗。
90%以上多种药物抗性但萘啶酸敏感伤寒病原菌引起感染病人的2、3或5d氧氟沙星短程治疗的平均热退时间是4d,<3%病人复发或治疗后粪便培养阳性,该短程治疗方案特别适用于流行控制;相比之下,萘啶酸抗性株对此方案的应答效果不好,仅有75%萘啶酸抗性株感染病人7d氧氟沙星治疗的热退时间是7d,而且19%病人治疗后粪便培养阳性[2,6,37]。
采用阿奇霉素和头孢克肟等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临床治愈率大于90%,热退时间大约是5-7d,复发率是3-6%,粪便带菌率<3%,被认为是喹诺酮类药物抗性伤寒和副伤寒的可接受治疗药物,有资料报道将头孢曲松推荐为旅游者伤寒和副伤寒治疗的首选药物(表3)[2,6,29,,30,37]。
抗菌素联用日益被认作喹诺酮类药物抗性伤寒和副伤寒治疗的较好选择。
有关环丙沙星对伤寒病原菌最小抑菌浓度1mg/L的一项体外实验证实环丙沙星与阿莫西林联用的效果比阿莫西林单独使用的好,当两种抗菌素联用时环丙沙星针对这些分离菌株的分抑菌浓度是0.004-0.256mg/L[6]。
表2在1964-2019年期间进行伤寒和副伤寒病人治疗的随机对照实验特征[2]抗菌素病人总数儿童病人数多种药物抗性菌株数萘啶酸抗性菌株数平均热退时间天(95%CI)%(95%CI)%(95%CI)临床失败微生物学失败复发粪便带菌氯霉素107829005.4(5.3-5.5)4.8(3.7-6.3)0.8(0.3-1.6)5.6(4.3-7.2)5.9(4.3-7.9)TMP-ZMZ29116006.0(5.8-6.2)9.3(6.3-13.4)0(0-1.9)1.7(0.5-4.6)3.5(0.9-10.6)氨苄或阿莫西林27947006.4(6.3-6.6)7.9(5.1-11.9)1.2(0.3-3.8)2.2(0.9-5.0)4.1(2.0-7.8)头孢曲松393604106.1(5.9-6.3)8.7(6.1-12.0)1.5(0.6-3.5)5.3(3.7-8.2)1.2(0.4-3.2)头孢克肟1601009006.9(6.7-7.2)9.4(5.5-15.3)1.9(0.5-5.8)3.1(1.2-7.5)0.8(0.04-5.3)氟喹诺酮类药物1049255643.9(3.8-3.9)2.1(1.4-3.2)0.4(0.1-1.0)1.2(0.7-2.2)1.5(0.9-2.5)阿奇霉素1562132164.4(4.2-4.5)3.2(1.2-7.7)1.3(0.2-5.0)0(0-3.0)0(0-3.0)氨曲南多种药物抗性菌株:
对氯霉素、氨苄西林和TMP-SMZ抗性。
临床失败:
在治疗结束时持续有需要进一步抗菌治疗的症状或出现并发症。
微生物学失败:
在治疗结束时血或骨髓培养阳性。
复发:
在出院后伴随血或骨髓培养阳性的症状再度出现。
粪便带菌:
在治疗结束时粪便培养阳性。
氟喹诺酮类药物:
指测试的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氟洛沙星和培氟沙星101633105.8(5.7-5.9)6.9(3.1-14.2)0(0-4.6)1.0(0.05-6.2)1.0(0.05-6.2)7重症伤寒和副伤寒出现持续呕吐、严重腹泻、腹胀、并发症的病人应当入院或按重症伤寒和副伤寒治疗。
出现肠出血的病人需要加强护理、监测,并在早期进行外科学干预,出血量较大时需要补液或输血。
早期干预是至关重要的,病人在出现肠穿孔后的病死率在10%和32%之间[6]。
尽管在重症伤寒和副伤寒病人中还没有进行过任何随机对照的抗生素治疗实验,但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喹诺酮类药物抗性株低流行区域仍然可以选用[29-33]。
在喹诺酮类药物抗性株流行区推荐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药物(头孢曲松、头孢克肟、头孢噻肟、头孢哌酮),应经过胃肠外给药途径至少使用10d抗菌素或在热退后至少使用5d(表3)[2,6,29-33]。
在巴基斯坦,用头孢曲松经静脉内治疗7d或14d病人的临床和细菌学治愈率相似,但7d疗法组的细菌学复发率是14%,而14d疗法组无一人复发[6]。
在印度尼西亚出现谵妄、木僵、昏迷、或休克的成年、儿童病人中,采用3mg/kg地塞米松的初始剂量经静脉内缓慢输液>30min,并接着以相同速度按每6小时1mg/kg的剂量输液2d的方案进行治疗,接受治疗病人的病死率由50%下降到10%[14]。
表3伤寒和副伤寒病人的抗菌素治疗[2,6]首选药物抗菌素每日量(mg/kg)天病原菌药物敏感性次选药物抗菌素每日量(mg/kg)天无并发症病人FLDS氟喹诺酮155-7氯霉素阿莫西林TMP-SMZ8(TMP)-40(SMZ)50-7514-2175-1001414MDRNAS氟喹诺酮155-7阿奇霉素头孢克肟8-107207-14NAR阿奇霉素氟喹诺酮8-10207头孢克肟207-1410-14重症病人FLDS氟喹诺酮1510-14氯霉素氨苄西林10-14头孢曲松头孢噻肟10-14氟喹诺酮10014-2110010-14MDRNAS氟喹诺酮156010-148010-14NAR头孢曲松头孢噻肟602010-14808带菌者从粪、尿等标本分离到病原菌的人员称为带菌者,分为潜伏期、恢复期、慢性、健康带菌。
带菌者应被视为伤寒和副伤寒恢复期人员而脱离涉及食品制作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
病人在起病后1年以上粪内仍然排出病原菌的人称为慢性带菌者。
大多数带菌者通过延长抗菌素疗程能获得治愈,几乎80%带菌者经过口服28d每天两次750mg环丙沙星或3个月每天两次4片TMP-SMZ,也可口服3个月氨苄西林或阿莫西林(100mg/kg.d)-棒酸(30mg/kg.d)而治愈[38]。
9预防和控制降低总人口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数的关键性预防控制策略是提供安全饮水、有效污水处理和卫生食品制作条件,其它策略还包括个人卫生和更适宜的卫生条件。
随着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抗菌素抗性的出现,预防控制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
疫苗接种是伤寒预防的另一种有效手段,对自发达国家到疫病区国家游客、实验室接触伤寒病原菌工作人员、带菌者的密切接触人员、预防控制流行、以及疫区高危人群预防是有用的。
在发达国家,带菌者的传播意义没有以前重要了,大多数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是到疫病区旅游获得的,到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孟加拉国、菲律宾和海地六个国家获得病例数占旅游相关病例数的76%,这些病例的60%在旅游地居住时间少于6周,37%少于4周,16%少于2周,5%少于1周;80%病例是拜访过亲戚和朋友的人[39,40]。
到这些国家的旅游者要特别注意饮水和食品安全,饮用煮沸水或瓶装水,吃煮熟食物,冷饮、蔬菜、水果都可能为感染源;尤其是停留时间大于2周和拜访亲戚朋友的人应为疫苗接种对象[40]。
过去的胃肠外全细胞伤寒-副伤寒甲和乙疫苗对预防伤寒和副伤寒是有效的,但因强烈的负反应(25-50%接种者出现局部不适、肿胀和全身负反应)而停止使用。
Vi多糖体疫苗(用于2岁以上人员)、全细胞活的减毒菌苗(用于6岁以上人员)和Vi复合疫苗(用于2-5岁儿童)是有效预防伤寒的三种获准生产疫苗。
目前,没有任何获准生产的副伤寒疫苗。
10结论伤寒和副伤寒是中南和东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主要累及儿童和青年。
全球多种药物抗性株和氟喹诺酮类药物低敏感性菌株的出现引起极大关注,伤寒和副伤寒的治疗变得更加困难了,有效的免疫预防和非疫苗的预防控制策略就显得实用和重要了。
疫病区有效伤寒和副伤寒病例治疗的理想目标是研究开发可靠、低费用的实验诊断技术和价廉有效的口服抗菌素。
事实上,在许多疫病区简便诊断实验或任何诊断设施的缺乏就意味着伤寒和副伤寒是在世界范围内被低估其重要性的疾病,也意味着许多非肠热症的发热病人将因疑似肠热症而接受经典伤寒和副伤寒治疗。
在过去的40-50年间已可获得价廉有效的口服抗菌素,但是这种情况是在变化着的,伤寒和副伤寒病原菌对抗菌素敏感性的总趋